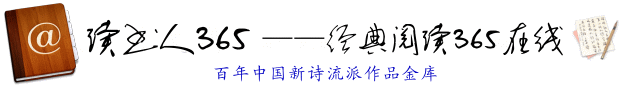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新月诗派
□石灵
一
民国十五年四月一日,借着《晨报·副刊》的地位,徐志摩所主编的《诗刊》第一期与世人见面,那就是"新月诗派"的前身。
《诗刊》一共出十一期,因要出《剧刊》,就停止了。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一文末了说:
"最后我盼望将来继续《诗刊》或是另行别种计划的时候,我们这几个朋友依旧能保持这次合作友爱的精神。"果然,后来就有了新月社的组织。可是新月派这名词,还不是由于新月社,而是由于《新月月刊》,因为在《新月》的第一期《我们的态度》那篇文章里,他们告白了《新月月刊》的出版,既非因书店叫新月,也不为他们有过新月社的组织。同时新月社没有诗,《新月月刊》才有诗。可见新月诗派的得名,系由于《新月月刊》了。新月诗派的由来,大致是如此。
新月诗既然成派,当然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了。那就是新诗规律化。
自胡适之揭橥文学革命,并自作《尝试集》以为试验以来,新诗这名词就和旧诗对峙的成立了。
根据胡适之的八不主义来考察,文学革命的惟一精神是打破因袭的束缚,用新的工具(白话)自由创造。这种精神,是所有从事新文学的人所接受,所服膺的,作新诗的人,自然也不会例来。他们服膺于打破因袭自由创造的精神,看不惯黄遵宪等人"旧瓶装新酒"的改良主义,把旧诗一脚踢开,旧诗有的东西,新诗一概不要,规律是旧诗所有的,新诗要解放,何消说,还要什么劳什子规律?所以在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甚嚣尘上的时候,不要说学衡派的胡先马肃、吴宓等人的和黄遵宪等一鼻孔出气的旧瓶装新酒的主张不为人所理会,即刘半农的"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和陆志韦的"创造新格律的实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朱自清氏说:"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这是真的。而这被忽略的原因,据我想不是他的力短,也不是他们的才低,而是时代的关系。譬如杜甫的成就,一面固因他有天才,而另外一面,他的时代也给他很大的帮助,近体诗到他的时候,已有二百多年发展,各种体裁的可能都已有个暗影伏在那里,只等一个有才能的人来把他们掘发应用,所以杜甫才有所据而发扬光大,不然,那会凭空的掉下他来?五四以后的诗人和欣赏诗的人的信念,既都受解放和自由所笼罩,谁还愿意听创造诗的规律的话?所以最初诗之形式运动倒霉,只怨时代的不巧。自由的气焰太盛。规律自然是束缚,管什么新旧!
五四以后,最活动的文学团体,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可是文学研究会据茅盾氏的《关于文学研究会》说,是非常散漫的文学团体,并没有什么集团的主张,有的只是那反对"把文艺当作消遣品"的基本的态度。在诗歌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作品虽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如果要寻文学研究会对诗歌的共同倾向,那仍然是自由创造。所以要说它的贡献,也就只在于充实自由诗的范围。自由诗大致是包括初期白话诗后来的小诗和哲理诗等,这些诗的内容,大部分是说理,和即景,抒情也很单调,总之和旧诗差不了多远,不过多一点人道主义的气氛罢了。一直到创造社,才起了大大的变革。创造社对于诗歌是有相当贡献的,可是那是在内容上并非在形式上。创造社的代表可推郭沫若,犹如新月派可推徐志摩。郭沫若的诗,充满了奔放的感情,那感情的根源,据朱自清氏说:"是泛神论"和"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这种内容的解放,使郭诗成为不羁的野马,他只顾自己的狂奔,无暇管到创造规律,也根本耐不了。
所以有意识的规律运动,一直到新月派才算正式开始。徐志摩在《诗刊弁言》里说: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的事做......"可见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抱着很大的勇气,冒着很大的险去做这件事的。这种倾向这种态度一直没有变更过,从《诗刊》起,经过《新月月刊》,各家专集,到陈梦家的《新月诗选》,都是本着这个标准去试验和创造的。
他们这规律运动的动机有二,第一是对自由诗的一种反动。前举《诗刊弁言》中的话,已足窥见端倪,但更露骨的是在《诗刊放假》里的"......在理论方面我们讨论过新诗的音节与格律。我们干脆承认我们是'旧派--假如'新'的意义不能与'安那其'的意义分离的话。想是我们天资低,想是我们'犯贱',分明有了时代解放给我们的充分自由不来享受,却甘心来自造镣铐给自己套上;放着随口曲的真新诗不做,却来试验什么画方豆腐干一类的体例!"
规律运动之第二个也是重要的一个动机乃在他们认规律为诗歌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新时代的诗需要新的规律:"......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作的工具,与美术音乐是同等性质的;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的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我们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他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
所以他们的规律运动,也并非旧的规律的复活。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二
可是一件事的形式和内容,无论就哪一方面说,总不能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总要有一点既成的坯子做为蓝本才行。新月诗派的内容和形式的蓝本是什么呢?前面说过,自文学革命以来,旧的东西,被所有热心于新文化的人一致地否定了。至于新起的坯子呢?在形式方面讲,自由诗和小诗,都无很大的成就;而在内容方面,虽然创造社的郭沫若有着不小的贡献,然而那种不羁的奔放的感情,在他们主张在感情"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的新月派看来,只是一种"精力的耗费"。因为他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在本土,(创造社的影响也是外来的)无论形式内容哪方面既然都无可借助,只好把眼光放到异地去了。新月派的领袖人物,都是受过很深的西洋诗的熏陶的,于是自然的,他们就走上了西洋诗的道路。同时,整个的中国的文学的样式,也都是接受西洋影响而产生的,新诗是其一支,大势所趋,又不仅是一二人的力量了。这可说是新月诗派形成的客观基础。
新月诗派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之后,表现出下列几种特色:
一、字句组织上的:他们没有存心倡导形式运动,即《晨报·诗刊》发刊之前,他们也不甚讲究此点。但自《晨报·诗刊》起,即孑然不同,字法,句法,章法,无往而不欧化,现在分别检查如下:
甲,字法:这是与想象之运用有很大的关系的,一方因他们用新的经验作底本,一方又因他们充分运用想象,所以就产生了许多新鲜的辞藻,和别致的使用法。这在闻一多的《死水》里最多,俯拾既是。整个《死水》那首诗,就是很好的例。现在举几个具体的在下面:
1、名词方面的如:
你看太阳像眠后的春蚕一样,
镇日吐不尽黄丝似的光芒;
和
呵,不要探望你的家乡,朋友们,
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
2、动词方面的如:
假如落叶像败阵纷逃,
暗影在我这窗前蜱睨;
和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3、形容词方面的如:
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四壁;
这贤良的桌椅,朋友似的亲密;
和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乙,句法:以行为诗的单位不以句为单位,这也是西洋化的一个特色。一句可以写成几行,韵脚在行末而不是在句末,如: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这完全是新的。
丙,篇法:一篇诗分成几章,每章几句,在中国,虽然《诗经》中有这例,但后来就渐归消灭。新月派的这种每篇若干章每章若干句,和各章相叫应的篇法,(这种例多得很,无论翻开那个新月派诗人的集子,都可找到,兹不赘举)实在并非从《诗经》来,当然也归结到欧化。
二、韵律上的:这一方面也是。在形式运动之前,他们写的是自由诗,音韵极无规则,闻一多的《红烛》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是例。至形式运动开始之后,就完全变了:
甲,音数的限定:因为西洋诗各行的音数有一定,所以他们写诗各行音数也有一定,隔行相等或每行均相半。总之规律极严,其极端所至,竟产生了"豆腐干诗"的特殊称
谓,现在我们一提起"新月派诗"首先唤起的意义,还就是"豆腐干诗",其次才是规律严整。可见他们对这原则,是如何地重视和努力过了。豆腐干诗,在徐闻等作品里倒还少,后来新月成派,才慢慢地多起来。现在随便举个例: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苍鹭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乙,韵脚的创格,在中国旧诗里,两句一换韵的诗很少,近体固绝无,既古体中也少见。但新月诗里,我们看到两行一换韵的。如:
你我千万不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记在上帝跟前起了誓。
我不仅要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旧诗中隔行换押的也没有,这当然也是西洋式的。例如:
我捡起一支肥圆的芦梗,
在这秋月下的芦田;
我试一试芦苗的新声,
在月下秋雪庵前。
还有隔几行遥押,那更是簇新的玩意。如:
我说朋友,你见了没有,那俘虏,
拼了命也不知为谁,
提着杀人的凶器,
带着杀人的恶计,
趁天没有亮堵着嘴,
望长江的浓雾里悄悄地飞渡;
他们拿西洋诗各种体裁来试验,甚至连一整篇都仿制过,比如闻一多的《收回》和孙大雨的《诀绝》、《回答》和《老话》,都是商籁体的移植。
在内容方面,虽然也与从前不同,但新月派的主要的贡献,还要算是形式方面的努力。自由诗是旧诗的反动,新月派诗和创造社诗又可说是自由诗的反动。他们,尤其是新月派,是有意识地想给那只无舵的船(新诗)找一条路,姑勿论这条路已否是坦途,但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如果我们把新诗和旧诗间的间隔比做一道河,从旧诗走上真正的新诗的领域,必须经过一架主要的桥梁,那桥梁不是自由诗,自由诗至多是桥堍上的一片泥土。建造桥梁的主要材料有两件东西,一件是创造社的内容上的扩充,另一件就是新月派的规律运动。
所以无论我们判定新月派在新诗的发展上有功或有过,有成就或一无所获,都不能把这件事丢开,都要把它放在旁边做证。
前面所举的新月派形式上的特色,第一项里是工具的刷新,第二项是技巧的刷新,即是规律的运动。这两者都是必要,尤其是第二项,理由有二:
(一)外在的原因:
文学革命后,旧诗的规律完全打破,作诗者可随意创造。然而凡是开端是好的,末流所趋,往往会产生恶果。因为没有规律可以随意创造,于是贪功急就之辈,都从新诗入手。自然哪,短短几行,无拘无束,既无翻书检卷之苦,又无搜集材料,构思布局打稿誊清的麻烦,而其结果,为文学家(诗人可不也是文学家!)则一,避难就易,人之恒情,事半功倍,何乐不为?弄到后来,不但旧诗人看了新诗要摇头挤眼,就是从事新文学甚至自己曾写过新诗的人见了它也要皱眉叹气。他们之所以没有骂,不是比旧诗人多看了几分好处,实因为不忍为旧诗张目,而暗地里他们是在怀着悲观的。所以如此,内容的欠完美和写诗的人各种修养太差,固然不能辞其咎;而为其主要原因之一的,却是一般的因新诗自由创造,遂把它误解为容易写,只要把散文分成几行就行的这荒谬的观念在那儿捣鬼。针对着这种弊端,规律运动是一剂良药。
(二)本质的原因:诗是诉之于(视听两种)感官,尤其是听官的艺术,(不同于音乐,因为它不但借助于字的声音还借助于字的意义);它不同于散文,因为它不但借助于字的意义,还借助于字的声音;意义所拥托出的影像,可以借声音之助而益显明。前面第一项中所说的章句等的组织,是有关于意义方面的;就是那方面的努力,目的在如何艺术地把通过吾人想象作用的感情形成影像。第二项的音韵的配置则是关于声音方面的,它的目的在如何通过吾人听觉而使那影像显明。所以,用文字书写出来的东西,如果失去了意义的要素就成了乐谱;如果去了声音的要素而强调意义的要素,那就成了散文。既名之曰诗,不分新旧,这声音的要素,是少不了的,正好比意义的要素少不了一样。
因此,新月派的运动,据我想是有相当的贡献。
三
前面说,新月派的努力,是属于有功绩的一面的,因为他在旧诗与新诗之间,建立了一架不可少的桥梁。但是无论一件什么事,好与坏往往伴随着。新月派在提倡规律的过程中,和自由诗招致了诗是容易写的末路一样,也招致了形式主义的恶果。第一个恶果是规律至上,写诗的人拿规律当做目的,忘掉规律只是一条路,是为着达到另外更高远的目标。当初新月派的主干徐志摩氏已经有见及此。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眼光较远,他在《诗刊放假》里说:
"但这原则(按:指音节化)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某式才是诗;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
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完全凭你体会得到音节的波动性;这种先后主从的关系在初学的最应得认清楚,否则就容易陷入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是音节(那是内在的)的担保。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剪栽整齐,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的远着;......要不然
他戴了一顶草帽在街上走,
碰见一只猫,又碰见一只狗,
一类的谐句都是诗了!我不惮烦的疏说这一点,就为我们,说也惭愧,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所以说来我们学做诗的一开步就有双层的危险,单讲'内容'容易落了恶滥的'生铁门笃儿主义'或是'假哲理的唯晦学派';反过来说,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就我们《诗刊》的榜样说,我们为要指摘前者的弊病,难免引起后者弊病的倾向,这是我们应分时刻引以为戒的。......"
他怕人误认字句整齐是音节的担保,把诗的境界搁置一边,所以他当头棒喝,提出警告。论理,在运动之初,即提出这种警告,似乎不应该再有他所怕的事情发生。无如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从好的方面解释,人们对于一件既成的事物,因怀着羡慕和钦佩,想自己也能去创造一件同样好的,但他们并不知也不愿去研究和吸取那他所钦仰的事物的精神,本质,他们只尽量去模仿,兢兢业业,惟恐模仿不像。即只模仿,着重当在形式,形式一像,大功就告成。这是不自觉的堕于形式主义。其次是投机取巧想偷据人家的努力为已有。他们并非精力不足,而是怕吃苦。这是有意的流人形式主义。
因这两种原因,新月派影响之下的后来的情势,就恰恰和徐志摩所怕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一提起新月派,人们就会想起"豆腐干诗"的原因。这也给予了新诗规律化的反对论者以很有理由的证据--因为确实的,这样会有把诗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又纳入新的桎梏的危险。第二个恶果是内容的贫乏,这与第一个有连带关系,既然把规律看成至上,就会不大注重内容,同时严整的规律,(新月派的规律)本身也会限制内容表现的饱满。丰富的感情,往往不是机械的诗式所能把捉的。郭沫苦诗之奔放,且不拿做例。因为他非新月中人,自然不足为凭。我且举出新月派里的作品看。闻一多的《荒村》和他别的诗的格式就不同。而徐志摩的《毒药》、《白旗》、《婴儿》,更几乎成了散文化。但是,徐诗也不足做证,因为他这些是作于意识的规律运动之前。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中的《我等候你》却可证明我的话。我读《翡冷翠的一夜》中的诗,往往觉得他的感情为他的形式所容不下。我仔细想,觉得这原因实在于他的《翡冷翠的一夜》中的诗,虽已完全规律化,内容方面虽也由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但究竟还有不"灰色"的成分。后来读《猛虎集》,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自然是因为"怀疑的颓废"到这时完全成熟,再没有感情多于形式的缺陷了。大概过分机械的规律,只宜于表现一点清淡的感情,反复的咏叹,以收荡气回肠之效,像《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一诗,就是最好的例。
然而规律岂不成了有害的东西了吗?不,规律是可有的,规律诗的任务,并不下于想象与情感。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规律,既收规律之效,又不妨碍诗之内容。
前述两种弊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形式主义者的偷懒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大的一个原因,还在新月派标榜的规律运动本身具有缺点。即是他们把音数限得太死。不以节拍为单位而以音数为单位。
英国诗的音数是有一定的,新月派因为要试验西洋体(新月派是受的英诗的影响)所以也就把音数限定了。可是英诗的节拍,是以一抑一扬二音(或扬扬与抑抑扬三音)组成一拍,所以他们音数相等即等于拍数相等;但中国新诗则不然,音数相等并不即等于拍数相等。比如
帝国主义者无情的炮火,
震醒了我们的沉沉酣梦。
这两句的音数虽相等,拍数实不相等,如果我们原意欲此两句属于同一模式(Patern),又以为音数相等即等于拍数相等,因而即认此两句属于同一模式,那就大错。这原因起于"新诗"的"新"字上,因为旧诗以平仄组成节拍。虽每拍不见得均含平仄或仄平两声,但全篇平仄声的数目,往往相等,其结果实仍等于二音一拍;而新诗中并无平仄限制,节拍失去凭依,并且则新诗所用的语辞无限制,而新时代的语辞,往往有以三个以上的音组成(如刚才所举的"帝国主义者")(旧瓶不能装新酒理由之一也就在此)。一个语辞(单音除外)既只代表一个意义,那无论其由几音组成,天然应该属于一拍,因为拍与拍间有相当的停顿,倘把一语辞分属于两拍,即容易破坏其所代表的意义。若不把它分开,那么拍数相等的行,音数就不见得相等;音数相等的行,拍数就不见得相等。
那么到底拍数为单位还是音数为单位呢?这就是说,那模式相同的两行,到底应该音数相等还是拍数相等?我的意见是,应该以节拍为单位,即相同的模式的两行应该拍数相等,而音数却不一定要想等,虽然有时也会相等。我的理由是,第一音数相等会以辞害意。第二所谓模式,其作用乃叫应,分而言之为期待(Expectenty)与重复(Repetieion)即在我们读诗时可以预先有种准备,而在到了那相叫应的地方的时候能得到"果然如此"的满足,在这满
足背后更藏有帮助记忆和持续感情与想象的效果。模式的作用既如此,模式即为必要。
我们再来看模式之形式。如果用音数做单位,相应模式中的音数相等,势必借独立之单音的叫应尽期待与重复的任务,而此任务实无法完成,因为独立的单音既无意义帮助,又无高下长短以为区别,如何能不引起混乱的现象呢?所以以音数为单位来做规律运动,这运动的道路将是此路不通。而新月派的规律运动的特色恰恰是这样。豆腐干诗固不必说,即别的诗也大半是以音数相等为基础的,难怪他要失败了。试无论抓住一个什么人问他新月派诗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会毫不迟疑的答复你道:"豆腐干式。""豆腐干式是好是坏?""不好。""为什么不好?""单调。""什么单调?"'因为豆腐干式。"也许普通人所能答的到这里就为止,他们再解释不出其根本的原因,但这答案还算是对的。因为单调一辞之后,就隐有我在上面所曾述及的独立的单音的机械而不自然。这也就是前面所说新月派规律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缺点。
以音数为单位的规律运动,既有这样的缺点,所以一般人就只觉得规律运动的弊而不觉其利了。象征派的诗在中国诗坛能够抬头和立脚,就由于它是对于规律诗的反动。象征派主张诗不要音乐的成分,即诗的效果可以不借助于规律。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在这里发表意见。或觉得规律运动在新诗还是必要;它的修正,依然被急迫的需要着。去年,笔者曾写过一本《新诗歌的创作方法》小册,编在《天马丛书》,那里面有一章音节论和一章韵脚论,就是竭力对新月派规律运动缺点的修正。时至今日,我的主张还没什么变。我以为形式诗歌模式的单位应是节拍,而节拍的组成的音数并无限制,纯以意义为主。时代变迁,我们用语里既添了许多新的长的语辞,诗歌里用到他们时,也就只好当做一个节拍。如果以音数来限定,势非割裂不可,意义既消失,模式也无从形成,诗的效果也就将归于乌有。
以节拍为单位还可以修正一个缺点,这缺点不是新月派所独有的,是中国诗歌传统所具有的,那就是中国诗里没有史诗没有长诗。这实在是使人气馁的事。
"......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那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那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但也无须过分懊丧,那原因并不全在我们不长进,不在我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而是另有道理。有些人说,中国无史诗系因中国无史诗的材料。自然,中国没有系统的神话,没有可歌可泣的开国元勋的伟迹,没有万物汇合的宗教,难得产生史诗这也是事实;但文字组织的限制,却也是很大的一个障碍。没有材料的话未必全对,至少最近不是这样。有什么时代和中国现代所处的能相以拟其伟大呢?固然这时代的内容,不是神话事迹,不是开国英雄,不是宗教战争,但其伟大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只要我们的工具顺手,人,好好地去努力,是可以产生像样一点的长诗的,可是我们的长诗呢?这原因(也许人也没有好好地努力)则在于以音数为诗之单位,无论从前现在,都免不了单调的病。如果把音数换上节拍,以节拍为单位,长短可以变化,那病就可以除去了,中国诗的一大缺点就可以被修正了,而我们扬眉吐气也就有日了。
新月派诗在韵脚方面的意见,我觉得没有什么例外可说的。韵脚的作用和音节的一样,是在叫应,提醒,期待,重复。新月派诗对于韵脚的需要,已经有了很好的注意了。
四
最后要叙述一下新月派的诗人。
为着叙述的方便,我把他们分做两组:一组名曰前期,一组名曰后期。前后期之间并无截然的界线;不过前期诗人,大致是见于《晨报·诗刊》中的,后期诗人则是见于以后的《新月》的。但我这里还不是每个都叙说到,而是从每一组中抽出几个比较重要的来讲讲。
在前期诗人里,我要说到的是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其实我们如果就新月派的贡献这点讲,徐志摩的功绩是远不如后两个人的。徐志摩在《猛虎集》自序里说:
"这问题,(按:指诗的艺术或技巧)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诗刊》镌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
可见他对这方面的功绩,是并不怎么大的。朱湘,虽然他是很早就和新月派分了家,可是因为他是新诗运动最早的人中的一个,以及他后来努力的方向,所给与后起诗人的,和徐、闻的影响分不出彼此,所以他依旧被算做新月派的。朱湘的第一册诗集《夏天》出版于民十四年,内所收诗系作于十一年至十三年之间,那里面的诗多半带有五四前后的气息,格式非常散漫不一致,也有具有规律的形式的,比如《回忆》、《寄思潜》、《南归》等,这正和闻一多于《死水》之前之有《红烛》,徐志摩于《翡冷翠的一夜》之前之有《志摩的诗》一样。这些书都表示着解放之初,无所适从,大胆向前摸索的痕迹,到了后来,徐氏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闻氏的《死水》,朱氏的《草莽集》和《石门集》,就大不
相同了,因为那是在意识的规律运动之后。每一篇诗的形式,都经过显然很费力气的结撰。
闻氏的诗和朱氏的诗都有刻画的痕迹,闻氏的刻画在字句,朱氏的刻画竟及于感情,说得老实点,竟至造作感情。刻画字句"使人有艺术至上之感",造作感情则不免腐儒气,《草莽集》中那篇《王娇》的长诗里,就有不少造作感情的好例。朱氏的诗还有一个缺点,即好用陈义。且属陈义陈用,《王娇》是例中的一个,其他如《昭君出塞》、《晓朝曲》等,都莫非陈义陈用。但朱氏虽造作感情,可说他到底还是注意诗之感情的成分的,所以朱诗还有好处,就是他的每一篇诗里,还包有相当多的东西,此实为后来许多新月派诗人,专在规律上用功夫,视规律为至上者所不及的。这种规律至上的先趋,不能不推闻氏的《死水》。全部《死水》里,只有《荒村》一诗是例外,题材富于挑拨性,同情到处流露,那不是假的。
闻氏既专在表现用功,朱氏的感情又不都是真的,所以徐志摩之为新月派的主干,确非偶然。他没有虚假的感情,他不专门雕琢字句。他在人的记忆中的印象,较其他新月派诗人为明显。这大概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散文方面之卓绝的成就;另一个就是诗里面真真实实地有点东西。他的诗涉及的方面很多,如情诗,哲理诗,人道主义诗,自然崇拜,宗教色彩等等。在他们初期的诗里,他的感情奔放不亚于创造社的郭沫若。他在《猛虎集》自序里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山洪爆发,不分方向地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振撼,什么半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
那是指的《志摩的诗》以前的作品,作了《志摩的诗》的也还是这样的。也是在《猛虎集》的自序里,他说:
"......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志摩的诗》的内容是比较充实的,自信与乐观的成分很多,《毒药》、《白旗》、《婴儿》,都是有力的号声。不过诗人到底是诗人,他只有抽象的希望,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同时诗人不是个社会科学家,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只凭着直观,并无研究的耐心,因而他的期望,也是性急的。而事实上社会进步之慢,即普通人亦往往为之不耐,何况诗人?所以仅仅热烈地拥有人世感情的诗人,结果没有不失望的,徐志摩又何能例外?《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之渐趋颓废,正是必然的。因为从他怀着热望之后的现实,并未好转,反而更糟。
《晨报·诗刊》建立下规律运动的根基,徐志摩在那上面竖立起柱石,盖造起墙屋,这是徐志摩对新月诗派的贡献,所以他可算是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路径--热望,碰壁,颓废--象征着整个新月派的途径。他的死也就不啻宣告了新月诗派的终结。所以新月派后期诗人所走的路,已不复是从前新月派的路,他们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新月派后期诗人,我所要说到的是孙大雨、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我们所以只说他们。把别人略过,就因为他们各人都代表分道扬镳后的一个方向。他们的总的倾向,是对字句整齐的规律诗怀疑。后面这个对照是很有趣的:前期诗人的作品,大半是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形式自由的路。便如陈梦家的《梦家诗集》多字句整齐的诗篇,而《铁马集》及最近发表的东西,就并不那样。林徽音从前写过《笑》、《深夜里听到乐声》和《情愿》,现在在实验自由诗,还用得着说?卞之琳,拿他的《望》、《黄昏》、《魔鬼的夜歌》、《寒夜》和《路过居》、《西长安街》以及《春城》等一比较也可看出。孙大雨的《诀绝》、《回答》、《老话》较之《自己的写照》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后期的新月派诗人,已经感到新月派规律本身的缺点,都在努力在找新的路,于他们的方向都各不相同:陈梦家倾向自由诗,林徽音在实验自由诗,卞之琳去象征派的路不远,孙大雨则曾努力于雄伟的长诗。
这种向自由诗的趋势,似乎有点儿回头走,可是不然:它是因对新月派的规律怀疑而起的反动,它绝非五四前后自由诗的复活,最大的一个不同之点,就是,音节的重要是普遍际被承认了,至少这又向新的合理的规律走近了一步。虽然韵脚被搁置了,而实际上那也是应该给与同等重量的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