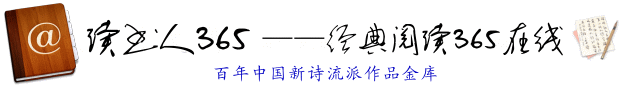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现代诗的名与实
□余光中
上
从十三年前,几个重要诗社的成立到现在,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已经有一段不算太短的历史了。就目前的情形看来,除了少数的例外,现代诗人们似乎已面临一个时渡时期:旧的局面已成过去,新的局面犹待展开。死亡,出国,丧失信心,进入中年,以及其他原因,已经使许多第一代的诗人告别了诗。另一方面,第二代的诗人之中,似乎还很少有人能够免于摹仿,而臻于成熟。1967年的创作的水位标,实在不能算高。诗社和诗刊都不能算少,诗的活动不能算不频,但是似乎缺少一股活力,不能形成一种潮流。在这种过渡时期,我想就现代诗的名与实,提出一些问题来,略加研讨,或有助于旁观者的了解,和当局者的自省。
五四初期,新诗往往称为"白话诗"或"语体诗"。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人士习用这种称呼。事实上,这种称呼是不很适当的。不错,根据文学史的经验,一种新文学创始,必然向活生生的口语去汲取生命,从但丁到华滋华斯到艾略特,都是如此。但是,原封不动的口语,只是诗的语言的原料,而非成品;必须经诗人的加工提炼,才能变成至精至纯的诗的语言。另一方面,纯口语的用字、遣词与句法,比较单调、浅显而狭窄。适度地加入文言和欧化的句或语气,可以大大增进节奏的弹性和变化。分析目前一些较为成熟的现代诗,当能获致这种结论。五四初期的新诗,在文字上每每浅显、单调而无余味,便是因为胡适、冰心等作者过分迷信白话万能。林语堂先生似乎也有这种迷信。他认为徐志摩的长处便在运用纯粹的口语,他更举例说徐志摩在诗中经常用"念头"代替"思想"。其实,"念头"与"思想"并不相等,也无法代替。例如《先秦思想史》,怎能用《先秦念头史》来代替呢?徐志摩的长处,像他在"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中所表现的,毋宁是部分的欧化。后来,有象征倾向的李金发等,更是欧化之外,融入文言的成分。这种以白话为主以欧化文言为辅的三合土,对台湾现代诗的影响颇深。目前一般"老式的新文学信徒",习于胡适式的纯白话诗,便幻想现代诗"不能卒读"了。
当然,我绝对无意鼓励青年作者,在未能驾驭文字之前,便去作"文白夹杂"的涂鸦游戏。回忆十年前诗刊上流行的"乃有"、"我遂"的句法,令人哑然失笑。因此我想到另一个不幸的名词,那便是:"自由诗"。所谓"自由诗",原是惠特曼创始的,并经意象派诗人们鼓吹的一种"没有诗体的诗体"。细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所谓"自由诗"的特质,都是消极的;不要韵,不要音律,不必讲究行与节的多寡与长短。它只是把"格律诗"全拆散了,正如毕卡索和布拉克把"印象主义"拆散成"分析的立体主义"一样。而正如"分析的立体主义"只是一个过渡一样,"自由诗"也只是"格律诗"到"现代诗"的一个过渡。没有一个成熟的诗人能够长久安于这种消极的诗体的。"艺术之中没有自由"。一个诗人必须在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之外,作一些积极的形式上的建树。也就是说,他在解除了前人的形式之后,必须自己创造出一种新形式来,让自己,至少让自己去遵循。当他写下第一行时,便已伏下了第二行第三行甚至最后一行的各种因素。一位诗人有自由不遵守前人的任何形式,但是,如果他不能自创形式并完美地遵循它,那他便失败了。以无易有,是不可能的。因此,严格地说来,所谓"自由诗",并不自由,也不容易,因为创造一种新形式来让自己遵守,此仅仅遵守前人已有的形式,是困难得多了。也因此,许多人把"自由诗"当做"形式的租界",逃到那里面去写一些既无节奏又无结构的东西,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新诗"是一个最普遍的名词了。在二分法的原则下,凡不是"旧诗"的诗创作,似乎都成了所谓的"新诗"。五四早期的诗,甚至今日报刊上常见的诗,实在只应该叫做"白话诗",因为那只是浅显化的口语化的"旧诗"。也有人(包括现代诗作者自己)把目前的"现代诗"叫做"新诗"。所以"新诗"这个名词实在内容驳杂,定义含糊,而且,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恐怕还要继续含糊一个时期。
这就牵涉到所谓"旧诗"一词了。目前,几乎所有的人,
甚至包括大学的中文教授及"旧诗人"本身,把五四以前的诗,一律谥为"旧诗"。这是非常不当的。例如李白的诗,飘然不群,距离我们虽已二十个世纪,仍像刚从树上摘下来时那么饱满、新鲜。有一次,我从美国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奥城,拜访相识已有廿年的一位中国朋友。小聚三日,我从蒙城再开车回美国去。临别的时候,他站在异国的街头,孤零零的一个人,向我遥遥挥手。自然而然,我吟起"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些诗句,虽已有一千两百岁了,仍新得令人感激涕零。以李白之万古常新,而谓之"旧诗",是一种错误,是一种罪过。
因此,我建议学者和作家们,将李白那千古不朽的杰作,改称"古典诗",而将"旧诗"一词,保留给五四以后仍然有人在写的律绝与词典之类。西洋各国文学,大半称前代杰作为"古典",从无"旧诗"一词。英国文学史上,固然也有所谓OldEnglish和OldEnglishPoetry,但那是"古文","古诗"之意。英文Old一字,可训"古","老","旧"诸义;而中文"旧"一字,似乎只有贬意。至于"古典"(Chassic)一词,则无分中外,不但在时间上,有陈年佳酿之意,抑且在评价上,有万选青钱之誉,应该是更为恰当的。
最后,便要考虑"现代诗"的正名了。"现代诗"一词,除了历史渊源之外,在台湾也已沿用了十几年了。近年有人要取消这个名词。我以为没有必要。姑不论一名既立,不可能像换街名一样,说换就换。即以"现代诗"在台湾这十几年的发展而言,作家辈出,解释互异,无论在创作上或理论上,"现代诗"的含义早已历经变迁,屡加修正,成为更丰富、更有弹性,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更中国化的一种新艺术,不完全是当初所鼓吹的,所谓自波德莱尔以降的"横的移植"了。举一个例,像郑愁予、周梦蝶、叶珊、虹、张健等诗人的作品,无论如何分析,恐怕"纵的继承"的成分还是多于"横的移植",而且,横摆竖摆,恐怕都摆不进所谓"拥抱工业文明如拥抱妓女"的现代主义里去。
当代的任何诗人,都有权利,将他自己所经验的生命,所认识的世界,用他自己认为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去表现出来。如果他看见的,不是饮苦艾酒或高粱酒的面目模糊的个人,如果他爱的,不是太妹或妓女。如果在生存的空间里他看见的不是机器横行的都市,如果他内心所感受的,是生之喜悦和活力,而不是"对于社会及其一切组织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那么任何人,即使是蓝波加上阿波里奈尔加上史班德,也没有权利要求他用别人的方式去表现别人所经验的世界。
上述郑愁予等几位诗人的作品,若不名之为"现代诗",恐怕也就无以名之了。我一向主张"现代诗"分狭、广二义。狭义的"现代诗"应该遵循所谓现代主义的原则:以存在主义为内涵,以超现实主义为手法,复以现代的各种现象,例如机器、精神病、妓女等等为意象的焦点。广义的"现代诗"则不拘于这些条件。在精神上,它不必强调个人的孤绝感和生命的毫无意义;在表现方式上,它不必采纳超现实主义的切断联想和扬弃理性,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更因为,表现上的清晰不等于浅显;在意象上,它甚至可以快乐地忘记工业社会的种种,而自己去寻找一组象征。一句话,广义的"现代诗"可以免于狭义的"现代诗"的种种姿态。
我无意在此非难所谓现代主义的信徒。笃信现代主义而且将那种经验真实并完美地表现为诗的作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并非每位诗人都有那种经验和表达那种经验的能力,于是不少作者,为求速成,为求短期之间能领到现代诗人的身份证,乃舍本逐末,做出一种孤绝而痛苦的姿态,或者语无伦次的腔调。在另一方面,广义的"现代诗"也未能免于模仿之灾。用钝了水手刀之后,便争相去采莲,而将新古典主义污染成假古典主义。曾经,我拟称从"梦土上"到"莲的联想"的一类诗为"现代词"。不过巧立名目是没有多大益处的。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这些名词都变成历史的陈迹,人们只说诗而不说"新诗",那时"旧诗"完全没人写了,而"古典诗"也不再坚持与"现代诗"脱离父子关系了。
下
说过"现代诗"之后,我想再就"现代诗"之实,提出两个重要的问题,略加论述。现代诗的实质,当然不止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也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现在我将它们提出来,同时,无论时代多么混乱、痛苦,一个人如果要活下去,仍然需要价值和意义。至于那是怎样的价值和意义,似乎倒是次要的问题,叶珊曾说,没有一个大诗人是颓废的。此点我完全同意。反过来说,凡大诗人,必抱持某种价值观念。就我所知,现代诗的大师们,如里尔克、如梵乐希,如叶慈,如艾略特,如佛洛斯特,如康明思、格雷夫斯、奥登和狄伦·汤默斯,没有一个不是肯定生之意义的。紧接在一次大战后发表《荒原》的艾略特,在二次大战之中,却思考时间与永恒的关系,并追求一种持久的价值,而写下了《四个四重奏》的后半。
混乱属于时代,但信仰属于个人。如果你相信有神,神便为你而存在。这是可以纯由个人决定的事情。"我不一定认为人是有意义的,我尤其不敢说我已经把握住人的意义,但是我坚信,寻找这种意义,正是许多作品最严肃的主题。"六年前自己说过的这句话,现在,我仍深信不疑。
1967年诗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