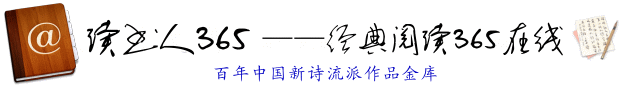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回望与超越
--评"新乡土诗派"十年
--评"新乡土诗派"十年
□沈奇
一
以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三位湖南青年诗人发起,并作为其代表人物的"新乡土诗派"自1987年春开启于当代中国诗坛,至今已整整十年历程。其间虽几经沉浮而初衷不改,最终以其独具的精神基因和艺术物质,成为这十年的中国诗歌历程中,具有相当影响的一脉走向。由这一脉走向所触及和提出的许多诗学命题,正越来越为诗界所关注,所谓"流派价值",或许正在于此。而作为"新乡土诗派"本身,其初始的使命,也似乎才渐次得以确认,并有待新的深入。
"新乡土诗派"成长的十年,正是中国大陆诗坛最为驳杂动荡的十年。以1986年秋《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为启动,继朦胧诗潮之后的第三代诗潮,进入了一个社团林立、群雄纷争、流派纷呈、变革迭起的"大摇滚"时候,成为中国新诗80年中最为壮观也最难把握的一道风景线。显然,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裂变,经由二次"能量释放"之后,泥沙俱下、混杂不清的现代诗潮,逐渐开始分流归位、朗现格局其大体脉络,以笔者个人诗学观念而言,可作如下划分:
其一、从艺术造诣分层,已可见专业性写作与非专业性写作的分野。这一分野最终使绵延十余载的"诗歌群众运动"之负面效应,亦即"运动情结"所造成的非诗因素,得以消解,使现代汉诗开始步入依从艺术规律作良性发展的稳健阶段。水静流深,沙自沙,泥自泥,专业与非专业诗性与诗形,各得其所;非专业性写作尽可向专业性写作过渡,但不再混杂一起,影响艺术层面的拓殖、收摄与整合;(有关现代诗之专业性写作与非专业性写作的理论探讨,本人有专论刊出,此处只作概念提出,不宜展述。)
第二、从诗歌立场分层,可见得生命性写作、知识性写作和社会性写作三个层面。生命写作虽一度成为第三代诗人个个挂在口头的标志,但大多数并未有真正深切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痛感作支撑,只是将"青春期诗恋症"误作了生命写作的基因。于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从诗到诗的大量"学院派诗人",便改由间接和知识性生存体验为精神底背,通过阅读与思考,专注于与"材料"而非生命/生存现实的对话,所谓"书斋写作",即知识性写作。其中不乏专业层面的高手,但其精神源流,总还是与当下有隔。至于社会性写作,乃主流诗歌亦即官方诗歌的传统写作,大都借用新诗的表面形式,作社会学层面的布道之说,或浅情、或近理、或登高一呼,皆有其诗形而无其诗性,属于非诗的另一极。但此种写作,因社会所需要,大量长期定货而历久不衰,且易为非专业性阅读者所接受,遂构成与纯正诗歌长久并存的一大景观;
其三、从所承传的诗歌源流看,大体仍在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四大路向中分流发展。尽管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大家似乎都以打出"现代"旗帜为己任,但各自所承继和认同的遗传基因不同,最终仍分属了不同的路向,只是比原先的各种"主义",其表现略有不同。或有所发展,或互为融通,但其底背所在,还是泾渭分明的。至于后现代主义,至少就眼下而言,尚只有极少数企及者,未形成流派阵营之势;
其四、从语言走势看,可见得三脉路向。一是以营造意象为能事的抒情性语势,一是以活用口语为主导的叙事性语势,再就是二者兼济的可称之为"第三向度"的语势。其中又有或过于欧化,或追求本土化,或再造古典诗质的不同倾向,取舍不一,所形成的语境也各具特色;
其五、就状态而言,又可分为激情性写作与智慧性写作两大类。前者重在诗歌精神向度的拓殖,后者重在诗歌艺术向度的拓殖,虽各有千秋,但后者的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所认同--激情的滥殇之后,"怎样写"依然是首要的命题,这也是现代诗运渐趋成熟之后的标志性认知。
"新乡土诗派"的十年步程,正是在上述动荡、袭变的格局走势中显现出来的,也只有将其置于这十年大陆现代诗运的整体认识中去作考察,才可能得以较为客观的定位,确立其不同于其他社团或流派的价值所在。
二
两个十年的现代诗潮,均以"现代性"为旗号,虽然各
自承继的遗传基因不一样,却都为这一旗号所号召所鼓促,簇拥前行。实则何为"现代性",什么是中国人现时空下自己的"现代感",在初起的潮流中,都是含糊不清的,则后来的分化也便在情理之中。中国新诗,向有"舶来"之嫌,两个十年的大陆现代诗潮,更是全面引进和渲染西方各种主义思想诗潮的空前盛会。这一"盛会",一方面及时开启并激活了当代中国的诗性思考,形成了新诗八十年中,最为宏伟壮观的诗歌造山运动,无论其拓殖的精神空间还是艺术空间,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也逐步显露出种种无法回避的后遗症,这其中,尤以本土文化根性的丧失和语言的过度欧化为烈,所谓"尘脊梁穿西服",正成为大量西方经典之本土仿写诗歌的滑稽比喻。
当然这不仅只是诗歌的问题,整个生存现实都加速度也陷入了这一"现代化"的怪圈。权力的宰制之后,是金钱的宰制,市俗化、商品化、城市化,即时消费、物欲膨胀,文化失根、精神失所,所谓"乡愁"的命题(文化乡愁与精神乡愁),便成为奔突于"现代化"旗帜下的人们,迟早要面临的喝问。
"新乡土诗"的出现,正是及时呼应这一命题,对现代诗潮所作的一次有意义的分延。这里的"分延",是指"新乡土诗"绝非背离"现代性",简单折返于所谓"田园牧歌"式的旧式套路或传统现实主义的覆辙,它依然是以"现代性"为底背的,只是其诗歌精神指向,更落视于本上,落视于现时空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感",而无意作西方精神的投影与复制。"新乡土诗"的代表人物们,在其《世纪末的田园--青年新乡土诗群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编后记"中,对这一诗歌精神指向作了初步的表述:"新乡土诗人们深入城市、农村和海洋,体验着更为广泛、更为精粹的乡土生活,诗歌的主流被重新引入到民族的生生息息苦乐哀痛之中,打通了淤塞的艺术生命之源,从内容到形式都回归到了民族的本体上。"显然,"新乡土诗"诗人们心中的"乡土",不是传统意义或普注意识中,那个与"都市"、"现代"、"洋"等词义简单对立的"乡风"、"乡情"、"土",而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一个精神代码,指在将第三代后诗歌中一再被悬置的精神根系,导引入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现实热土,以审视、批判、质疑与叩问的立场来言说中国人这段艰难过渡的精神历程。当然,这里的"现实"一词,也不是社会学层面的"现实",而系"精神现实",这也是"新乡土诗"易被人误解,而实际上与传统"现实主义"有质的区别的关键。正如诗评家燎原在其《黄昏乡土上的放逐--关于新乡土诗的精神及其走向的描述》一文中所指出的:"因之,'乡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假借物,是基于普通的精神痛失感中的诗人们,从城市退守至乡村,以乡村为背景,与物欲世界所展开的精神对峙。诗歌行为由此而导入精神行为,它在深刻的心理忧患中挺立精神匡扶的庄重的使命意识。"
由此我们理解到,"新乡土诗"诗人的对"乡土"的回归,实质上是身陷"现代化"浪潮中的清醒者,对理想中的"精神原乡"的一种回望,以此作为精神现实的凭藉或叫作价值座标,在不断的审度中实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这一"回望"与"超越"的典型意象,是"新乡土诗"之"两栖人"的诗性命名:"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陈惠芳《两栖人》)。这一命名使得"新乡土诗"诗人们有了完全不同于其他诗人们的脉搏之律动--他们"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那样尖锐、敏感、深刻而鲜活地深入到"两栖人"之两难生存困境这一命题,进而昭显对精神家园的叩寻,在第三代后的诗人群体中,确属卓然独步的超越了。
在这里,考察"两栖人""回望"的视点所在是特别重要的。作为质疑"此在"的参照,"新乡土诗"诗人们,即未陷入"精神贵族化"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世界,亦未掉头重复古典中国士大夫式的所谓纵情山水、归隐田园之矫情,而是非常自然地深入到对早年乡村生活的追忆中去,或作为城市的背弃者二度客临乡村、亲近泥土,然后,经由理想化了的淘洗与抽取,从乡土原型中提炼出为任何时代所不可磨灭的精神品质,予以诗性的创化,来导入家园的叩寻。显然,这样的落视,比起乌托邦的呼唤或呼请,无疑要亲近得多、切实得多,真实可信得多,是双脚踩实在大地上的"回望"与"超越"。非简单的两相比较,从一方逃向另一方,再由一方遁回此一方,这样的"乡土情怀",是传统现实主义诗歌的一大盲区,最终沦于简单肤浅,有其诗形而无其诗性。"新乡土诗"的"新",正是"新"在对乡土原型的二度淘洗与抽取中,这其中,有青春记忆的感性作用,更有成熟诗人们的理性思考。"两栖人"的命名是客观的,既客态于城市原型,也客态于乡土原型,由此才能确认精神的路向。不可否认,正是这一"客态",难免使诗人笔下的"乡土"常有主观美化的嫌疑,而这正是诗人的所企图建构的--这一"建构",在江堤笔下,是"辣椒长在皮肉上/是披着笋壳的风景/是骨头之神、气之神/是怀藏流水的圆柱/和蕴藏呻吟的精灵"(《生殖崇拜》),在彭国梁笔下,是"把自己的头发扯下来/搓成茶叶/水声/在我生命最深层的洞穴/呼唤我/带焦臭的乳名"(《水声》),在陈惠芳笔下,是"一座朴素的乡间教堂/在我的臂力之中渐渐升高/这些贫贱而质朴的教堂/从里到外充满着/金黄的、细长的、温柔的经书"(《堆草垛》)。"辣椒"、"水声"、"金黄的草垛",在这些最普通、最日常的"乡土"的物事中,诗人的最终所欲淘洗的抽取的,是"一种升华了的颗粒和基因"(《陈惠芳《大雨》)--这是精神的"颗粒",是民族生息之精、气、神的"基因",正是基于对这一"升华了"的"颗粒"的抽取和对这一"升华了"的"基因"的探寻,"新乡土诗"方成为横贯80年代末至90年初的独立的诗歌运动,并越来越显示出她独在的魅力和不息的生机。
三
在"回望"中调适精神路向,艺术的表现也便随之超越了浮躁的潮流,拓殖出迥然不同的诗歌语境。这一"语境",大体而言,是摒弃了翻译化语感,立足于本土的活话语,融合抒情与叙述,杂揉进具有一定地域色彩的口语,清明、硬朗、鲜活、纯净带有湘楚特色,富有东方意味,重视传统光彩而又不失强烈的现代意味-"新乡土诗"的这些艺术特质,在经由十年的磨砺之后已成为大陆现代诗之跨世纪的回顾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脉资源。
当然,因为个体生命体验和语感体验的不同,上述特质在"新乡土诗"各个代表诗人那里,其表现也均有所不同。基于取向的一致,并未影响诗人们个体的艺术风格之追求。
这一群体中最具实验精神和创造力的,当属江堤。江堤早慧而多变,涉猎广泛,恣意探求,从不满足,充沛的激情与不失时机的控制,在其身上得以较好的融合。由此气质所开启的语感,驳杂跳跃,有很宽的表现域度:浪漫的、写实的、铺叙的、意象的,或直白、或突兀、或清明、或奇幻,且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写《逆子》:"道德沉睡的地方/一个叛徒一个隐者同时流泪/一生我站过两块地方/站在故乡我是逆子/站在城里我又面目全非",直白道来,坦诚中见骨质,冷峻精警写《液态乡土》:"家在波纹上流动/每一个泳姿都是回乡的路",委婉流畅,有清亮的华丽感;写《薯干的灵魂》:"细细碎碎/卧于白的齿下/牙签伸过撬/撬不动/像石有根/并细细地放出鼾声",诡异奇崛,颇具文本外张力。这是一位深怀艺术抱负,矢志不渝的诗人,正如他的诗友非亚所说的"在江堤身上,有着一种可贵的赤子般的黄金的炽热、白玉的沉静、季节的轮转和大自然的风声......被内心的火焰和鞭子驱赶,脸上永远有着稻子一样明亮笑容的青年诗人"(《大地之子》),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气质使然,江堤在多向度艺术探求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重心不稳,风格不确定的问题,缺乏鲜明的、稳得住的艺术方向感,有待在新的步程中,得以调适,得以新的建树。
作为"新乡土诗"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彭国梁,是一位艺术修养比较深厚的诗人。语感老到,意象新奇,融古典的韵致和强烈的现代感于一体,是其突出的风格特征。在他的笔下,有颇具荒诞意味的《进城的公牛》、《坚硬的骷髅》等,对叙述性诗语把握得很有分寸,不动声色中见出诗思的特异,常有道人未所道之深刻寓意。另一类是我个人认为较具代表性的真正可称之为"新乡土诗"的作品,如《水声》、《茶青色的池塘》、《月光下的诱惑》等。这些作品中完全东方化的审美韵味和本土化的现代意识,得到了很好的创化,无论是整体的构思,意象的经营以及节奏感的把握,都十分讲究,经得起高品位的苛刻的阅读与欣赏,无论是在"新乡土诗"中还是在整个当代中国诗中,都是可圈可点的佳作。"茶青色的月亮/曾经丰满地躺在池塘/现在瘦瘦地离开了",可见古典诗质的再造;"我就是痛苦的漏斗/掉下的/一滴苍凉",可见西方诗质的溶铸。如此的诗歌品质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诗人似乎未能很好地保持这种早期的良好势头,予以拓展和深耕细做,近年反而给人以渐趋荒疏的感觉,或是蓄势而待发?我们期待着诗人新的奉献。
在"新乡土诗"群体之"三驾马车"中,陈惠芳对这一流派的风格确认,有着更深的思考。"两栖人"的命名提出,绝非偶然。正是在他的诗中,"乡土"的指向上升为"家园"。他比其他诗人更痛切地认识到:"家园无处不在/家园的窘境无外不在"(《交接仪式》)。"尽管我为民歌灌醉之后/再没有被时髦音乐感动过",但"我不可能按照故园的节奏/安排命运的起落"(《怀乡的音乐》)。这才是当代中国人对"家园意识的清醒认知--这一认知的超前之处,在于将"家园"与"故园/故土"区别开来,认领现时空下的中国人被迫以"两栖人"的尴尬身份,步入"在路上"的飘泊处境,"家园"只是一种价值参照而非可以"回归"的确在"故土",而"回望"的意义在于向前超越。无疑,当陈惠芳在《堆草垛》一诗中,将"草垛"升华为"一座朴素的乡间教堂"之后,他已将所谓"乡土"纳入现代意识而予以表现了。这一认知使陈惠芳的诗质,具有不同寻常的峭拔、坚实、给人以透明、硬朗如玻璃钢一样的质感。这些特质在其代表作《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一类作品中尤显突出,展示了诗人特具的气质和语感。同样遗憾的是,诗人亦未能在晚近的创作中,表现出更新的突进,导致一些从立意到架构的重复,滞留于初步的成就而未作更深的创建。
就"新乡土诗"群体十年步程的整体态势来看,显然都存在着一个重新定位、再度确立重心感、方向感的问题。早期的芜杂是难免的,目下的间歇也属必要的过渡,而再出发前的梳理则尤其重要。这里首先有一个"提纯"的问题:在对十年群体运动的成就中,找到真正代表"新乡土诗"的精神特质和语言特质,排除掉那些附着性的、渲练性的、非专业性的东西,同时吸取其他流派的可用之处,予以收摄和整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乡土诗"的实验,在台湾现代诗运中也曾一度盛行,但最终被导入到缺乏诗体建设与诗学建设价值的浅层面运作,反而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阻遏力量。这里的关键在于没认清"家园"命题的悖论性,误将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作为批判的武器,不解在这一"武器"的背面,同样存在着弱化生命的"阴寒",存在着另一种遮蔽、另一种孤寂、另一种异己的力量。"所谓'家园',只是一个不断推移且永不能抵达的精神所指,而非一个实存的他在;作为一种参照,它只反衬出此在的困境,却不提交他去的、返自可归的路径。而所谓'回乡之路',实则也只是一种精神自救,它只拯救一种良心,而非建立一种行为;它只给出一种诗意的开启,以引领人们踏上二度寻找自我真正的过程"。(引用拙文《时间、家园与本色写作-译陈义芝的诗》,见拙著《台湾诗人散论》(台北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296页。)诚然,相比较而言,由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为代表人物的大陆"新乡土诗",从一开始就非"浅尝",其后的成熟,可以说真正将"新乡土诗"推进到一个与现代诗运同步,并进的前到位置,影响日盛。而"回望"中提示仍是必要的,无论从诗学的发展还是从创作的建树,我们都期待着十年拓殖后的"新乡土诗",有一个更为深广丰硕的新的十年,在跨世纪的中国诗歌进程中,再显其独树一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