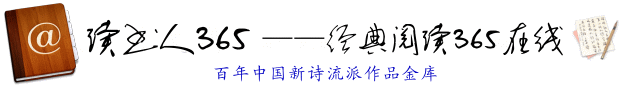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第三条道路
--兼谈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
--兼谈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
□树才
一、盘峰诗会
对于这场争论,我并非无话可说。
但争论双方像在唱对台戏,唱得正热闹处,锣鼓敲响,舞刀弄枪,我便更愿意耐心听着,当然,争论后来变成了论争。
撇开众多四散溅开旋即沦落灰尘的激烈唾沫,撇开对引发争论(总得有人先扔石头)的幕后所作的种种猜度,也撇开或多或少有些损人利己的对抗策略(这用不着细说),我相信,所有参加争论或看上去站在岸上观战的诗人心里都十分明白,这场争论把汉语诗歌一些重大问题抛到桌面上来了:什么是评判九十年代诗歌价值的尺度?诗该写什么?该怎么写?汉语诗歌的可能性何在?......
显然,争论是必要的。反抗已经形成的。这肯定没错,这是艺术发展的一条原则。不光要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进行反抗,而且要对一切形式的不公正表明反抗的态度。八九年以来,诗人星散,社会生活也急急转向,诗坛沉寂、灰暗;这十年来,诗人们暗中舍弃了什么,认定了什么,还在为什么而焦虑,他们心里是清楚的。我认为这是洪水到来的十年,一些人被冲走了,另一些人上岸换芏,只有少数人硬是站稳了脚跟,冷静地观看着周围的一切,琢磨着自己的心事。这少数人像一把沙,被撒到各自无法逃避的生活中去了。他们在沙里挣扎着,坚持着。让他们绝望的每一天,反过来又支撑了他们。在本世纪彻底背过身去之前,一个诗人心里有话,还是说出来好。一个诗人遭遇不公,他想喊,应该让他喊出来。
但争论又是可疑的。一切争论都是。一方因手握答案而可疑,另一方则因避实就虚而可疑。双方未能深入地争论问题本身。揭发性的文字偏多,嘲讽的笔法被广泛运用。不断章取义也确实找不到骂人的理由。我很遗憾争论变成了意气用事。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就不讲理。老实人受了冤屈,只好忍着,哪儿有道理可讲。但我觉得诗歌是另一回事,因为各人的写作在那里明摆着。
必须看清的倒是,在我国,一场文学问题的争论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个人的文学野心。因为不便明说,于是只好掖着。实际上,问题在争论之前就摆在每一个诗人面前。但由于从一开始,问题被设计成一个策略,因此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真讨论。双方争论着争论着,就去争另的了,就气急上火了,就骂人了。诗人在哪里都要有勇气说真话。蒙蔽羔羊,拿它们的皮毛作为投资,这就枉为诗人。
二、他们在争什么
在我看来,于坚想同王家新争什么,本来就是不用争就很明白的事情。说实话,在江湖一百零八将名册里,王家新都已成了宋江,而于坚又号称云南王,他们够功成名就的了。他们正该好好专心于写。"老子天下第一",这不是闯江湖,这种霸气要不得。
诗人的名声是怎么回事我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胡宽和灰娃的命运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他们遭遇了长期的残酷的被遗忘,但是,他们终究被"发现"了。为什么?因为有眼力的人毕竟没有死绝,因为好诗默默地忍受着并发散着力量,因为他们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诗上。瞧,最后是好诗的存在,证明了胡宽和灰娃的存在;而胡宽和灰娃则成了诗歌的见证。他们向诗歌索要什么了吗?没有。诗歌也是不能被索要的。诗歌不欠谁什么。胡宽和灰娃用全部真诚和全部才华去写。他们写出了好诗,那就谁也抹杀不了,也是谁也争不走的。一个诗人的作品,在他的有生之年,不是被高估了价值,就是有意无意地遭到了忽略,从来不会得到恰好的公允的评价。一个着眼长远的诗人必须洞悉这一点。
所以,今年以来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反对拉帮结派,把诗歌当枪使。社团狂热不仅受个人文学野心的推动,而且逐渐让人的心力从诗上偏移。一起玩儿,一起喝酒,一起夸人或骂人,一起商量事情,这当然开心;但是,它混淆了哥们友情和诗歌写作,它把个人必须独立面对的写作困难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而小集团是没真正的友谊的,它因为利益而起,必因利益而散。
三、究竟哪些是好诗
最后二十年间,究竟哪些是好诗呢?
于坚显然认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产生的一批文本:"可以说,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使由胡适等人开始的汉语新诗运动,进入了一个成熟和丰收的时代。第三代诗歌将名垂青史,它的创造精神,它的蔑视庞然大物的勇气,它的卓越天才,它的活力、自由、独立,它的深度和广度,它的中国经验,它的革命精神--"(见《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然后于坚引一段法国作家德里达的话来作佐证。这听上去像是法官在宣读判决书。
程光炜的答案当然也体现在他选定的那些诗歌文本上。他对所谓"知识分子"身份的那些诗人的文本的刻意推崇,正是引爆这场争论的导火索。
我佩服他们胆儿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国在经济上贫弱,在思想上贫乏,在艺术上贫瘠,在智慧上贫血。而新诗也就八、九十年的历史,甚至可能更短。最近二十年间,在遍地的碎砖烂瓦间,在夹缝似的贫瘠土壤上,确实长出了一些透露着未来方向的诗歌文本。但是,现代汉诗从整体上来说,正在生成之中,正在获得自己的力量和尺度的途中。所以我觉得,哪些是好诗,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我认为在下个世纪头几十年,汉语诗歌将会出现既具灵性又有深度的优秀文本。
批评家要客观些才好。批评家不要把批评设想为一种权力(腐败就跟在权力后头),而应把它视为一项严谨的工作,通过具体真切的感受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去呈现批评家的洞察力。但是,客观在哪里呢?坏就坏在,有人以客观作幌子,让偏心眼肆无忌惮。诗人莫非坚定踏实的独立态度,他在"词与物"之间通过严谨艰苦的劳作而收获的众多诗篇;诗人车前子身上的先锋精神,他在诗上求新求变的那些文本;诗人殷龙龙反抗命运的倔强个性,他的诗句越来越幽默而高超地写出自己那条苦命......在我看来,他们凸现着现代汉诗的一种独立的品格,一股个性的活力,但均遭有意无意的漠视。
至于诗倒底该写什么?该怎么写?这就跟该怎样生活一样,谁也无权教导谁。散文化,不做作,不求高昂,于平淡中见功夫,富于人情味,这样的诗挺好;但拿这类诗去削平其他的诗,也没这个必要。
诗与生活处于怎样的关系?这需要每一个诗人在生活中并通过生活去体悟。不管怎么说,你的好诗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你的生活中,包含在你的个体存在的亲身经历所能激发的灵性和觉悟中。诗歌写作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来自自己呼吸的语言。诗歌越是个人生命真实的,就越是有独创性的。一个诗人只能是一个单独者。单独者继续存在。
四、关于外国诗
说到外国诗(其实是翻译诗,外国诗的概念要大得多),我认为于坚在这个话题上说了一些胡话(像他抛出的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对立一样)。从作品来看,于坚本人深受外国诗的影响。只是他事后的态度确实与众不同。他想"绕开"。也许是打开眼界之后,返归当下现实,他更加痛切地感受到建设母语的急迫和重要。但这不是简单的"绕开"不"绕开"的问题。他有所不知的是,"五四"以来,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诗,已经成为汉语的一部分,中国诗的一部分;而他故作不知的是,因浸润了翻译家的心力和智力而格外出色的那些外国诗,不仅震醒过世纪初的中国诗人,而且会继续给中国诗人带去启发。不要忘记,你所读到的外国诗人(比如兰波)的诗,是经过翻译的媒介已经变成了汉语的那个面目;你可以对译诗不满(比如兰波的诗在汉语中缺乏活力),但你不能因此无知地骂兰波。须知兰波的诗在其母语(法语)中恰恰是极具语感和原创性才那么深远地影响了后起的诗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诗人风格上略带欧化倾向的写作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白话汉语在胚胎期就已经混入了某些欧化句式。这些欧化句式也许已融入白话汉语,如同某些艺术观念。方言体现了汉语的特殊的丰富性,但引进外来的语言资源对汉语也极为重要。各民族的语言从来都是在认知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并汲取活力。要小心那种一切中国传统和中国本色的文艺主张,首先,这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其次,这纯粹是一个乌托邦。桑戈尔提倡"黑人文化",实际上他最后只好放弃这个主张。
诗人多多当年之所以要求自己"跟上翻译的步伐",他是有难言之苦的。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那些年月,汉语诗歌整个就是权力的附庸。这就从根本上阉割了诗人的个性,也败坏了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品质。一句话,诗歌违背了真实。诗歌赖以生存的土壤的土质也就腐败了。最近二十年来的诗歌活力,来自中国诗人在观念和语言上"必须有所突破"这一信念。
突破首先来自北岛喊出的"我不相信"。他不相信什么?无莫是他脚下的现实,和他眼前的诗歌。他以他那时的方式反抗。最后,他被请到国外去了。多少诗人,一"请"就走了。甚至不请也非要走。当然他们在国外也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主要的收获是怀乡病。这说明中国的诗歌现实中有着让诗人感到可怕的东西。我敢说,这"让诗人感到可怕的东西"现在仍是中国诗歌土壤里最凶狠的杀手。北岛那代诗人能走的都走了之后。理想主义的"抽空自己"似的写作蔓延的几年,直到诗人海子自杀。海子确实结束了一个纯粹的理想的抒情的史诗的时代。海子的诗突出了语言所能抵达的抒情的亮度和理想的高度,无论是文本还是对诗歌自由精神的领悟,都堪称优秀诗人。
韩东、于坚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更加平实地处理诗歌材料的写作手法,在于他们把切身经历艺术地转化为简洁、明晰、幽默的诗句的那些文本,在于他们对中国土生土长的生存经验的美学信念。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最大的特点是多元、混乱、边缘化。你以为你是谁?你顶多是你写出的那些诗。我主张真正的多元。多元是最有利于艺术开花结果的土壤。多元就是无条件地尊重艺术个性和独立品格。
而如何对待外国诗,也确实是到了该谈谈态度的时候了。"绕开"它?实际上不可能。扑上去"搂住不放"?这也非常糟糕。从对外国诗的折服和迷醉中回来,返归当下现实,更自由也更独立地回到自己的写作中来,倒是真有这个必要。因为我相信,诗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的土壤里直接生出来,它就不会长命。毕竟,汉语是最根本的,是汉语诗歌创新的全部可能性所在。
诗歌的困难不在别处,恰恰在诗人自己身上(从心灵到观念,从语言到勇气......),恰恰在日常而具体的母语身上。求新求变,正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歌的必由之路。外国诗再伟大,毕竟不是从汉语的土壤里直接生出来,散发出的是另一些情感体悟和生活氛围。况且,不管你钦佩哪些外国诗,它们终究是翻译成汉语之后的面目,你不必百分之百地当真。文学翻译这项工作,每个国家都有人认真而深入地干着。它是必需的。诗歌翻译则是某种不可能的可能,因为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和诗歌固有的音乐、节奏、个人命运、生存体悟等特殊品质不可能被移植,然而是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神奇地得到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好诗是无国界的,在别国也能经翻译被人辨认出来。
话说回来,如果你连自己生活中的切肤之痛都不能感同身受,你又怎么可能在母语中写出活生生的真实的诗来?外国诗只能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提供二手文本和诗歌精神的观照物。
五、第三条道路
我既不赞赏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也不站在所谓的民间立场上。
我站在我的位置上(注意,不是立场)。我只能这样,否则我就不诚实。
我不相信一个诗人想成为"知识分子写作"就真能是知识分子写作,或想站在"民间立场"就在民间立场上了。在我的位置上,我积累我的单词;我写我生命中真实的诗,我写我生活中鲜活的诗。直接性和深度,仍是我的诗歌的关键所在。诗歌的最重要价值就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生命真实的内在深度。诗人必是有知识的人;没有起码的关于诗歌的知识,一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但诗歌显然是关于知识之外的东西的学问。诗歌不是可以教会的,模仿也无济于事。有人以为技巧是可学的,以为技巧能决定一切,这正是诗歌界近年来的通病。技巧其实是最经不起谈的,它内含在每一首具体的诗中。必须把一首好诗看作一个整体。尽管现代诗整体上信奉的是碎片美学,一首碎片状的诗仍是一个整体。
中国诗人不应漠视自己脚下的诗歌现实、生活现实和历史现实。回到自身中来,回到汉语的语言现实中来;要想,更要看;要争论,更要写作。
有一天,莫非跟人说:"树才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对此,我这么回答:"是啊,我一条,莫非一条,车前子一条......"。显然,"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和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在中国,真正有独立品格的诗人还是太少了!我看重第一位诗人独立探索的勇气和自由飞翔的姿态。正是在一己的生活中,你感受到时代的冲撞、压迫和剧变;正是在一己的生活中,有着你必须体悟的写作之道,它就在你无从选择、必须忍耐的生活过程中。
一只手伸向古典,另一只手伸向外国诗,双脚牢牢地站在自己的生活真实里面;从自己的边缘出发,建构起自己的世界;这是我对我未来的构想,这取决于我的写作实践。唐诗宋词,离我们远吗?形式是远了,但心灵的丰满和飞翔的灵性仍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积累单词是行动。行动的写,把诗人局限在单词的方寸之间。但方寸之间是无限。事物身上活生生的表象,对诗人来说,比人所能构想的本质重要得多。凭借你特殊的灵性和智性的混合,去写出事物的一点点本想。积累什么样的单词?这于你生活的自由度、独立性和内在深度。生活中变化着的一切,未实现的一切,是单词的藏身之所。通过并为了生活,去写诗;为了并通过诗,去生活。
一个诗人想在写作上有所突破,首先必须打碎头脑中已接受的观念硬块,也就是必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所以我说,写诗写诗,关键是写。写多了,写久了,问题就会自己跑出来烦你,难度也会凸现出来;而且,生活会提示你,你这么写,成,或不成。生活不会让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只有写你生活中鲜活、惨痛、醒目、无形的真实。你就得这么挖掘你自己的生活,否则,即使你浪得虚名,你心里还是感到失败。
1999年11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