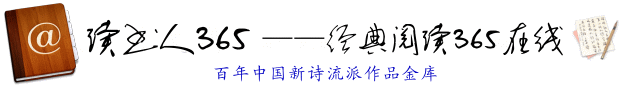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
--我与词与物
--我与词与物
□莫非
反对诗歌中的秘密行会不论是神圣的还是庸俗的。因为秘密行会只能有利于滋生形形色色的头头脑脑,相应的是无头无脑的诗歌大行其道。如果诗歌有秘密,那么行会便是赤裸裸的;如果秘密行会拥有诗歌,那么,诗歌就可以成批地安全地制造出来,并以其特有的幻术行骗。总之,行会诗歌往往以不可告人的手段为其成长寻找大小地盘,这已经无秘密可言。然而最大的秘密在于伟大的诗歌容不下秘密行会。行会的秘密因其成员苦乐不均而导致公开。因此,诗歌秘密行会不经反对亦将解体。
名堂诗歌当然是有名堂。不过,要是闹下去也就没有了名堂。
先贤祠不能指望有了十年、二十年的写作史,就可以活生生地把自己的牌坊塞到里边去。拿几家诗歌选本权当台阶,讲台,课本,宣称自家的伟大业绩,这只能让人觉得连庙门都没有摸着呢。
诗诗只有一种,那就是好诗。说诗有两种,一是好诗,二是坏的诗,也行。然而,坏诗也就不是诗,如此,诗只有好诗一种。
好诗的标准显而易见,这里的标准不见于教科书。即使在教科书上用黑体或斜体印刷出来也于事(诗)无补。好诗的标准经过伟大诗人艰难的写作实践而把握于内心深处和冥冥之中。好诗的标准只有一个字:好。好就好在从"标准"那儿离开。好诗有标准,但标准的好诗绝对没有。
坏诗坏诗即失败的诗。没有坏诗堆在那儿,一个诗人就不可能写出好诗;认不出坏诗,好诗就是他们的天敌。必须写出坏诗,这是诗人一条通往好诗的道。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好诗往往被埋葬,而坏诗生根发芽者多,而且影响深远。好诗是偏僻的,孤立的,少数的,无声的。与此相对照,坏诗是明显的,成群的,普遍的,喧嚣的。因此,坏诗容易得势,好诗往往遭殃。坏诗,看上来眼花缭乱,骨子里如出一辙。坏诗之间相同之处远远超过其不同之处,要想在为数繁杂的坏诗中选出不太坏的诗也难。
坏诗的好处可以锻炼一个诗人发现、创造好诗的能力,从而使坏诗的影响降至最低。坏诗的坏处不用说,大家都明白。因为谁都写过坏诗,这没什么丢人的。否认这一点,坏诗就真的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也一样写过坏诗,如果我的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一定是我写的坏诗起了作用,而我的好诗,要么还没有写出,要么就是有意无意地被省略了。
可耻的沉默明知是好诗而又害怕说出,对这样的沉默可以称之为可耻的沉默。因为这种沉默本身客观上为坏诗鸣锣开道,进而把好诗打入冷宫。有意忽略一个诗人的好诗,就等于帮助坏诗建立稳固持久的档案馆。
诗歌批评家混迹于学术、科研、教学机构因无法获得自身智慧而只能借助国家经费杜撰批评文章、撰写文学史诸如此类,用以谋生。他们利用职业身份巧妙地遮盖文章的业余水平;利用三流诗人的通讯录、履历表、作品名录来节约深入阅读和文本分析的时间;利用三流诗人急于强占地盘从而"诗意地栖居"的浮躁心情。尽管如此,仍旧不能让他们承担诗歌批评的混乱和诗歌创作的低俗的责任。他们也是三流诗歌泛滥的牺牲品。三流诗歌败坏了批评家的声誉,这种局面只有一流诗人和大批评家的现身才能扭转。
修辞学拿卡夫卡、博尔赫斯、德里达、福柯、拉康的名字点缀自家文章,直到出现大师的幻觉为止。
引文1、不加引号,不注出处,将他者名言名段擅自拆解,进而形成一家之言;2、加上引号,成为文章中最具可读性的部分。引文作为镜子的碎片,直接反映全部文章的平庸。
文学大事记将写诗以来所有光荣事体面事(实为陈谷子烂芝麻之事)均打上年月日重新公之于媒体的编年体私家文学史。把小事化大,把别人的大事化小或一笔勾销,是这种大事记的主要写作方法。
桌面把好诗放在桌面上。写了坏诗也不用拍桌子;好诗在握更不用跟桌子过不去。动静一大,会把好诗吓跑的。拍桌子如果不是因为写过坏诗而情不自禁,那就是由于别人的好诗而莫明其妙。文学斗争当然要文斗。桌子可以推翻、掀掉,甚至劈柴烧火。但在桌面上写出的坏诗好诗不可能因此消踪匿迹。
时间段落自以为业绩骄人之时标明章节。文学史也是人写的。如果创造文学的好办法是杜撰文学史,重写文学史,那么,这样的文学史甚至不是垃圾而是浮尘。再巧妙的分段也无法阻止时间说话。时间有它分门别类的本领。历史可能被篡改。真面目可能被当做假面具。惟有时间不容扯谎。除非有人在时间之外。果真如此,文学史就无意中成就一部魔幻小说。众所周知,小说的行文与分段是自由的。
诗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也"不成立"。原因1、持股最少的董事会成员勇于争当董事长;原因2、持股越多越没有发言权;原因3、入股即分红;原因4、公司本身只是概念股。一般结论是,"股份有限","公司无边";不破不"利","利"在其中。
朦胧诗前后有些诗人跟着朦胧诗前边跑;有些诗人跟着朦胧诗后边跑。当他们开始想着自己走路时,突然觉得应该有人跟着自己跑了。
剩下的诗所有的时间只是剩下的时间。所有的诗也就是最终被剩下的诗。
诗选本最好的选本是由时间最终选出的。因此,人之选总有不尽意之处。人家没有选你的诗(哪怕你的诗是绝唱),并不能证明人家的选本就一定是垃圾。有时,选了你的诗反倒让那个选本不伦不类了。如果你的诗是绝唱,那么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发出不可遮掩的光芒。所有落选的诗终将成为一个选本。
语言垃圾我们都制造了语言垃圾。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表明垃圾太多了,甚至让我们看不见其中的金子。
浮尘诗诗人席君秋有言,"可怕的不是垃圾,而是浮尘。因为浮尘想落下来站在地上,都是一件难事。"
伟大的诗人也一定写过坏诗,说过废话。但在最后一刻,他给最后一句画上完美的句号。这就使他从前的坏诗和废话有了不坏的意义。到最后仍旧没有写好的东西,从前的好诗也显得无出处和可疑了。
三流诗人是任何时代都大批推出的诗人。在三流诗人中可以寻找到非常有名的诗人,有名无实的诗人,自以为得道多助的诗人。
没有难度的写作写作而没有难度,结果把写作弄成了杂耍,使真正的技艺,沦为修辞。技术只能使制造更方便。而掌握技艺才可能有所创造。技艺是隐秘的,难以传授的,所以不可能是知识。有技无艺是三流诗人的通病。
黄钟对瓦釜而言,黄钟大吕也是废铜烂铁。瓦釜经不起时间的敲打,但它们的优势是遍地开花无所不在。黄钟对于有好听力的听众才是黄钟。失聪者不懂得坛坛罐罐和黄钟大吕的区别。黄钟一声不响也仍旧是黄钟。碎片横飞,终究是碎片。
斗争如果诗界的斗争不可避免,最好是让好诗同坏诗作斗争。哪怕因此坏诗名声大作,而好诗一时无言以对。从长远的眼光看,坏诗再坏也不能败坏好诗的流传。
争斗诗歌中的争斗只能对坏诗有利。热衷于争斗并采取非正大光明的手段,是让坏诗"合法化"的一条捷径。争斗不会有结果,也不会两败俱伤,因为双方都虚构了对方的形象。
民间果真有一个"民间"这当然好。不是说"真功夫在民间"吗?扛着民间大旗又总想插到对方的城头上,恐怕行不通。历史上文学起义对摧毁诗歌旧王朝的作用,不能低估。但眼下这场争斗与真正的诗歌变革无关。名份之争,往往落个名声扫地的下场。如果身在"民间"心在"汉"那就更难说是好汉了。我本人并不觉得这场争斗有趣儿。尽管它更像一场有不少备份、可以永远玩不坏的网上游戏。硬件各有不同,软件只有一份。双方都想办法利用对方的空间从而出奇制胜。正常的玩不转,就采用"黑客"偷袭的方式,或者制造病毒用以破坏对方的程序。需要找到更好的软件?不怕病毒的软件?
知识分子写作最近二十年,我以为诗歌中并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不妨碍产生别人乐意相信的"知识分子写作"。只要"写作"别糟蹋了"知识分子"这一称号就行。我的忧虑是,只剩下"写作分子"而把别的写作,包括"民间写作"当成了"分母",并以此求证,自家的写作才是惟一光荣正确的写作。不要以为自己也写了《我控诉》,就自封为左拉;也不要读了《左拉传》就自然成为左拉的"传人"。没有"小酒店"的左拉还能担当左拉之盛名吗?
第三条道路写作并非指在民间派与知识派之外另谋出路。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其代表人物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了两位。比如树才的写作,他的好诗和他从法语那里译过来的好诗,使他在当今汉语诗歌中拥有不争的地位;比如车前子的写作,他的前卫,他的连续性,他的好诗,他对诗界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是剩下的诗歌中最具光彩的篇章。没有诗人能够置身于诗歌大局之外,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诗歌最终留下她自身的判决,谁也跑不掉。
只是说只是说,说了一大堆,可惜什么也没有说出。从前至少还是要谈论"诗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现在好了,不论谁写了什么,怎么写,而是要看谁写的。知识派有人写过坏诗,"民间"那边也一样。从斗嘴斗脸到斗报纸斗版面,无非一个"名"字作怪。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再次承认我写过谁都是知道的坏诗。好诗往往是隐藏秘的,不为人知的。知识派那边的诗人代表如王家新,如西川也写过坏诗,并且影响远播。我甚至在《北京文学》上看到西川所写的一篇"反批评"文章,其中点名沈浩波,如何如何,并预言沈会因西川的"骂"而成"名"。没有诗人因骂人或挨骂成名,况且西川也还没有到骂谁谁出名的地步。否则文学史岂不成了"骂名史"。据说,西川拥有"知识分子写作"一词的优先权,就那篇"反批评"而言,实在不像他所标榜的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倒像是从"民间派"那几现学现抛,终觉不熟练,不够用。西川的妙文不妙,令人惋惜。即使如此,西川还是一个好诗人,我希望他好下去。
后知识分子写作作为先锋文学批评视野中刚诞生的工作术语,并非是指在"知识分子写作"之后另起一行。后知识分子写作,重在知识之后,激扬生命,诉求智慧;破除教条,创立规则。以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怀疑、批判和发现的精神,不仅捍卫现代汉语的神圣与鲜活,而且还要开拓汉语写作的锐气与大气。即使知识分子写作已经失效,后知识分子写作也不能挪用他处。
接受一个诗人的作品受到抵制,就要说明是哪些人在抵制;如果大受欢迎,也要追问那些人是干什么的。作品被抵制的程度与它的创新程度成正比。越是平庸的作品越是容易找到读者。
讽挖是这个贫乏的时代可能找到的隐藏深刻思想的通道。害怕讽挖的人越多讽挖就越有生命力,"挖"到痛处,"讽"才是真正疗效的药。
先锋用这个词儿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别的诗人以及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的诗人抛到一边。"他们也许写得不坏,但他们过时了"。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是,属于"过时派"的诗人都在标榜自己的队伍是先锋,而把对方贬为"跟不上趟"的诗人。
黄金时代三流诗人首先将自己的时代推举为黄金时代。那么,在三流诗人中涌现出"黄金诗人"便是自然而然的。谁反对这一点,谁就不是够分量的三流诗人。
写作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哪怕是"知识分子写作"也给人以"不够知识,不够经济"的印象。写作是为了读懂生活中最艰涩的部分。这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可能被葬送。如果写作诗人的头脑飘飘然,尔后昏昏然,那只能证明,从写作中并未获得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把写作降格为爬格子,则是另外一回事。爬格子作为劳动并不失人的尊严。要是以为还可爬到天梯上,则是危险的。写作的关键在于冰山的底部。仅仅抱住显出露水的那一小块不放,最终还是要露底。写作的通病是玩花样。玩花样不仅轻松而且容易捞名,这在三流诗人那里常见不怪。有名对三流诗人有利,无名对一流诗人无害。每个时代都会丢下一些诗人,而那些强有力的诗人也可能抛下时代,不计得失,独自远行。
说了再说该说不该说都说了又能怎样?对于可说的,照直说来;对不可说的,也要努力"说"一些。隐瞒自己的想法不是诗人的特长。
智商对于写出一流作品的诗人而言,这东西无大用。写不出好作品又要谋求好名声这就需要些智商。通俗地讲,挖空心思,算尽机关是也。
纯洁语言写作就是为我们的语言注入新鲜的活力。如果脏话说得漂亮又准确,同样可以起纯洁语言的作用。没有诗人的创造,我们的语言就会在无免疫力的条件下逐渐死去。语言无味的人大多面目可憎。作为死去的语言,再华美也"说不出"任何东西。
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这样的读法才不致误人子弟。宁负当代文学,不负诗门弟子,这样的文学史家,亦可谓"无韵又离谱,史家之绝唱。"
拉名单作为某一类诗歌批评家发明的工具,亦称"点将法"。把自家新朋故旧中从事文学者之大名源源不断地罗列在大小文章于大小杂志之中,并相信,拉出名单也就是拉出队伍。诗风日下,诗名日盛;方法简陋,效果明显。何乐不为?
会议诗人或曰"麦克风诗人"。他们以为抓到麦克风也就算把握了压倒一切的真理;相信传声筒放大音量能代替默默无闻艰苦卓绝的诗歌劳作;不在乎会上讲什么而在于会后怎么说。会议诗人因不同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群落。
诗经如果诗歌写作从此消亡,那么当代读者对诗经的理解也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诗歌的消亡正是由于诗人不懈的努力,同诗歌的消亡做斗争,才保证了诗歌的链条一环扣一环地通向未来。
占星学家在诗人的天空上,最黑暗的那一片才可能诞生最耀眼的作品。不过,占星学家不习惯这么看。
抄写员干着抄写员一样的工作但浑然不知的诗人是幸福的。
天平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而言,不论它的出现多么不合时宜,受到的待遇怎样不公平,都无关要旨。因为他本来就摆在时间的天平上。只是看起来不够公平。随着时光的推移,眼力不济的人也会认识它的分量。拙劣的作品可以不费力地得势于一时。这正是那类玩艺儿的奇妙之处。对此,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拙劣的作品根本用不着放在天平上去考量。
诗学的后花园在废墟上不会再有什么建设可言。庙堂一塌,石头、木料也就重新回到本来的地方。后花园还在,借此可以缅怀昔日的光景,但不能指望那里的小树成为栋梁。去掉棱角,圆滑透顶,是每个时代造就平庸之辈的惯用伎俩。提高警惕尚且不能幸免,更何况放下武器一逃到底。或许只有后花园里的漫步者不会迷失。一个没有什么要找回来的人正是我正要找的。在伟大的诗篇之后有诗学,在后花园之后有通往话语生命的门径。
秋这一季虽非地狱的一季,但"窄门"正在此处。坏诗人带着不坏的诗,好诗人带着不好的诗都得打这儿经过。果子长在树上,落叶落在地上。那些跑过落叶摘果子的人必须当心被脚下的烂果子滑倒。其实,不用太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抢过来是要挨罚的。别忘了,这一季还是戒律与行刑的时刻。
1999.11双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