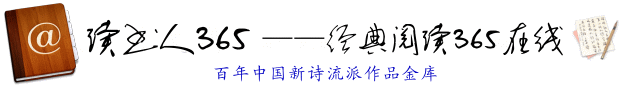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关于"丑石诗群"
□邱景华
一
在新诗史上,"诗派"或"诗群"的形成往往有二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先有社团、共同宣言,后有同仁刊物,如"新月";一种是没有社团,没有共同宣言,以刊物为中心,一些有共同爱好者,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如"九叶"。
解放后,由于政治体制和出版机制的变化,刊物都是公办的,园地公开,面向大众,不可能专门发表几个人的作品,同仁社团和同仁刊物已无法生存。进入新时期,民间的同仁社团和同仁刊物随之兴起。如《今天》、《他们》、《非非》等等。(实际上,新诗史上的那些同仁社团和同仁刊物,也可以看成是"民间社团和民间刊物"。性质一样,只是出版的形式不同:一是正式出版,一是民间交流)
民间诗刊《丑石》创办于1985年,成熟于90年代,在21世纪初产生较大的影响,被《诗选刊》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五大民刊"之一。《丑石》由青年诗人谢宜兴和刘伟雄共同创办,最初也是以丑石诗社的形式出现。后来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创办者的社团意识和同仁刊物为初衷逐渐淡化,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艺术追求的诗人加盟。由同仁社团和刊物所形成的诗群,容易形成"五指握拳"的集体力量,和"集束大爆炸"的巨大影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抱成一团",容易相互同化、泯灭个性,束缚各自的创作个性和不同诗艺的发展,也不利于长期共存。所以,这样的诗群常常是短命的。"丑石诗群"的形成,不同于上述这种模式;而是与"九叶诗派"的那种在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再慢慢地自然聚合相似。《丑石》以一种开放性的多元组合,和改成双月诗报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吸引了众多同道的聚集加盟。最后,形成了以《丑石》刊物为纽带,以不同诗歌创作和批评为多元组合的"丑石诗群"。主要成员有(按先后加盟的时间为序):谢宜兴、刘伟雄、空林子,郭友钊、陈慰、伊路、安琪、康城、邱景华、王宇、陈健、汤养宗、叶玉琳等。
"丑石诗群"的核心,自然是《丑石》的创办者谢宜兴和刘伟雄。他们是一对最佳的诗歌搭档,是最优化的互补共生。谢宜兴有"猴性",不仅个小灵活,而且脑快、嘴快和手快,有异常敏捷的思维和出口成章的快才。善于发现和捕捉新观念,新事物。点子多,善联络。在《丑石》的策划和编辑中,展示了他的才智。与谢宜兴的"快"相比,刘伟雄常常是"慢半拍"。北方人的个头,行动沉稳,其特点是"象形":慢中有方,拙中有力。思维虽慢,但细密周全,想得深。有一种大局观,善于组织和团结各方力量,在诗群中起一种稳定和平衡作用。两个人在长期的磨合中,形成一种能量很大的互补性"合力"。失去一方,《丑石》和"丑石诗群"不可能支撑和发展到现在。一个民间刊物和诗群的成败兴衰,组织者的杰出才干和远大目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在办刊和诗群活动中,谢宜兴与刘伟雄是"异中求同",追求一种互补性的"合力";而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他们却是"同中求异",似两水分流,走不同的艺术道路。这是他们成功的奥秘。后来,又演化为"丑石诗群"多元组合的基本原则。
二
谢宜兴前期是以写"乡村诗"著称。
他一方面吸收中国当代"乡土诗"的艺术营养,立足乡土,表现乡土;另一方面,又以开阔的视野,积极接纳世界诗潮的影响。他的成功在于,自觉地在世界性的诗歌大格局中,寻找自己独特的小位置。诗歌并不会因为写乡土而落后,华滋华斯、佛罗斯特、威廉斯和希尼,都是立足乡土而成为世界性的大诗人。谢宜兴后期的"乡村诗",吸收了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威廉斯诗歌的艺术营养:坚持表现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题材,反对从书本上获取象征意象的学院化倾向,特别强调现实生活的特殊性,主张在特殊性中表现普遍性,坚持把外来技巧本土化。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乡村诗",是谢宜兴最引人瞩目的艺术独创。但谢宜兴并没有在"乡村诗"上,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的创作个性是具有善变和多变的"猴性"特征,即善于化解和驾驭各种诗歌艺术矛盾,在不断变化中发展和丰富独特的诗艺。作为一个富有智性的抒情诗人,他擅于把感性与智性相融合,产生一种在更高层面上对人生的悟性。如组诗《走向黄昏》,把乡村的题材,升华为一种"乡愁",一种在哲学层面上对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寻找。佳作《听山》,以有限的意象,言说无限。通过诗人夜宿深山,静听山林的天籁之声所引发的感悟为过程,从人与自然对立,到人与自然沟通,最后是人与自然融合。在大格局中表现大意象,是谢宜兴最有厚重感的长诗。
谢宜兴的多变和善变,还表现为不断开拓富有个人特色的题材。他以新闻的敏感和政治的热情,创作国际政治题材的诗歌。如表现美国轰炸南联盟的《悲愤与同情》组诗,和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的坠毁的《最后的空中芭蕾》。虽刚起步,但已不同凡响。近作《我一眼就认出这些葡萄》,又是一种重大的诗艺变化。他把纯粹诗歌与社会诗歌相结合,关怀底层卖笑者的悲怆命运,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受到广泛好评。
谢宜兴诗歌中苦难而沉重的人生感,构成了诗歌中的"生命之重"。但作为一个抒情诗人,他不采用类似罗丹《地狱之门》那样巨型的雕塑,来表现苦难的沉重;而是擅长用精巧如琥珀般的艺术形式来传达。温润如珠玉一般的琥珀,包藏着一只小昆虫活泼生命被永远凝固的痛苦。这种"透明的苦难"和"优美的死亡",同样令读者强烈地到无法忘却的生命哀伤。也就是说,谢宜兴是采用"艺术之轻"来表现"生命之重"。
这种"艺术之轻",实际上是将现实生活中苦难和悲剧的题材,进行特殊的艺术处理:"化实为虚","舍质而趋灵"。这本是中国古典抒情诗的传统,讲究不滞于物,强调把现实生活心灵化。一般不要求对事物的外形作过于细致的刻划,而是善于表现事物内部晶莹的意境。通过艺术的提炼,对题材进行"净化"。在艺术心灵化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淘尽杂质,达到一种高纯度的结晶体。从内容上讲,就是"化现实的痛苦为心灵的悲歌"。谢宜兴的诗歌一般不直接表现苦难,他的创作基本是在生命经过痛苦的挣扎,从苦难中超脱出来之后,即在告别黑夜、迎接光明的晨曦时分才提笔的。把现实中的种种苦难,化作一种拨动心弦、惊醒灵魂的沉痛悲歌。
谢宜兴这种表现"生命之重"的"艺术之轻",体现了鲜明的抒情诗的诗体特征。抒情诗的特点,就是短小、简洁,但直抵灵魂。它不像"实验诗"那样,采用叙事化或综合性的手法,以散文化的长诗取胜。这种"艺术之轻"不但没有使苦难失重,反而使之具有拨动心灵和震撼灵魂的力量。这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的抒情诗人,在诗体审美规范上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刘伟雄把他的诗集命名为《苍茫时分》,不仅表达了他对"天地苍茫"这种特殊时空的喜爱,实际上也是在暗示他获取灵感的独特方式:独立苍茫,想象的翅膀就会飞翔起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时空感。"独立苍茫自咏诗"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刘伟雄独特的诗人形象。
他常常独自一人,在那些古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漫游:滕王阁、石钟山、六朝古都南京、陶渊明的故里、敦煌石窟......。面对积淀着历史沧桑感的古意象,他身上独特的时空感就会被激活。这是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受和体验。虽然时间的流逝是无形的,但他特别善于在有形的空间里,发现这种无形时间的飞逝:那就是凝聚在空间意象里的一种沉重的沧桑感。如《大理三塔》。沧桑感是一种侧重于古今之变的历史时间感,而"苍茫之美"则是一种在自然时间中所呈现出来的空间美。《石钟山》很好把长江月夜的旷远迷茫的境界呈现出来,体现了诗人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胸襟。对他来说,找到了旅游题材,就是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他把远游作为激发诗人内心的人生之旅--对自然对生命感悟的一种媒介。重在表现旅途中与自然相遇时,心物交融所激发出的诗意。比如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对生命短暂的喟叹,对生活意义的寻找和发现。刘伟雄之所以能在众多的旅游诗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他用自己独特的时空感,对旅游题材加以艺术的"变形"和"重塑",从而创造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旅途诗。
当刘伟雄以他独树一帜的旅途诗,与谢宜兴的"乡村诗"遥相呼应之时;他也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在更自觉的探索中,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清醒和坚定。他那"沉潜深隐"的创作个性,很容易束缚诗情。于是,为了打破过于内敛的艺术思维和定势,就向相反的方向探索:从理性的内敛,走向心灵的开放。他开始增强旅途诗的情感份量,强化抒情的手法。写出了《花园》、《闽南姑娘》、《崇武中午》,这样与他以前内敛而沉重风格迥然相异的精品。其自由的心灵抒发,浓烈而深沉的情感体验,清淡而温馨的语言,展示了诗人丰富而隐密的内心世界。他最见功力创新,是对"口语诗"的吸收。"口语诗"与他先前表现古意象为主的简短而含蓄的旅途诗,正好是处在艺术的两极。他就是要追求这样的"相反相成"。他吸收了"口语诗"用新鲜的口语,表现当代生活的优点。使他的旅途诗出现一个大的变化,重点移到表现他在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当代现实生活。如《自己的北方》和《人在旅途》组诗。
"口语诗"虽然充满着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地域色彩,让普通的读者感到亲切和贴心。但这种诗歌在手法上常常过于琐碎,大段大段照相式的摹写铺排,使诗完全散文化了,缺少应有的艺术提炼和升华。使"用最少的字,表现最多内容"的诗歌文体特质,基本丧失了。刘伟雄对"口语诗"却能扬长避短,他即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情节,又不放弃诗歌的想象力;他以独特的想象,把日常生活的细节,转换成具有新鲜艺术生命的意象。如《平原上的树》,在具象写实画面的基础上,利用抽象来深化意象的内涵。又如《在河南师范找一位熟人》,以多层次的时空错位感,把一个找友不遇的普通场景,营造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暮色苍茫的艺术时空,呈现出多义的意蕴。
刘伟雄在通过向相反方向"放"的同时,并没有走到极端;而是"放"了一段时间后,又"收"回来。即回到原来的创作个性。以各种新的现代诗手法,如隐喻、暗示、多层重叠、意识流等,来丰富自己深沉、含蓄和厚重的艺术风格。他这种不断在"放"与"收"之间的来回实验,就是在创作个性,与新诗潮之间寻找共同点。经过多次失败和反复磨合之后,才找到新的生长点,诞生新的艺术生命。于是,他创作了组诗《自己的西部》和《星光在梦里闪烁》,这样简洁、精炼和浑厚的诗篇;以及像《火狐》那种充满朦胧意味和神秘色彩的奇异之作。
刘伟雄成功的创新经验,对于当前那种因追逐先锋而脱离自己创作个性、陷入困境的诗歌写作,具有普通的指导意义。
三
伊路,是属于当代最为沉静、最为纯粹写作的女诗人之一。
她自觉地远离诗歌时尚和尘嚣,努力保持洁净的心境。像一棵树,在园中的角落静静地生长,没有喧哗,只是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长成一棵绿叶繁茂的大树。
从《青春边缘》对浪漫理想和青春诗情的吟唱,到《行程》对社会和人生的智性思考,再到近年来对自然万物和人生的感悟,伊路很好地完成了诗歌创作的"三级跳",进入了最佳的饱满状态。伊路的成熟,首先是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和胸襟的不断开阔。她在创作谈中写道:"从爱自己到爱他人到爱万物,是一个诗人成熟的过程。"近年来,她的诗歌之所以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正是来源于此。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极少。
从诗人类型来讲,伊路首先是个艺术家,其次才是诗人。她的职业是一级舞台美术设计师,在她看来,舞美设计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前期的案头设计,是天马行空的超现实想象;而后期将设想制作成可以让演员在上面走、跑、跳的平台,其尺寸的长短、材料的组合,则来不得半点差错。这种长期专业的训练和思维,正好与诗歌创作有相似之处。或者说,造就了伊路独特的艺术思维,她总是能将飞翔的想象,很好地落实在由写实意象组成的画面之中。她能在结实的意象与放纵的想象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艺术平衡。
伊路前期诗歌的意象和境界,都是美好而浪漫的。而后期的意象和画面则是世俗乃至丑陋的。从大雅到大俗的变化,不仅仅是题材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是她从爱自己、到爱他人、再到爱万物,这种精神世界成熟的自然流露,所以,她不仅能从大雅到大俗,而且能在大俗中写出大雅。她已经超脱了题材的局限,能穿透题材的表现,"看见"万物之间隐秘的联系。她一再强调诗人的"看见",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万物相克相生的独特审美发现。所以,近年来她不仅继续写她心爱的自然题材,而且一再写城市建筑工地题材。在这个尘土飞扬毫无诗意的题材中,不仅写出新意,而且写出深义。她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民工劳作艰辛同情和关怀的层面,而是在最低贱的生存状态中,写出哲理性的深刻内涵。
读她近几年的诗歌,仿佛是跟着她去更深一层地体验自然、沉思人生。她总能从一阵清风、三声鸟鸣,五只蝴蝶、甚至几个牛尾巴中,像魔术师一样,揭开被日常生活严密遮盖的帷幕,让你"看见"自然与人生中奇特而神秘的关联,以及生命中可以意会、却无法触摸的"看不见的限制"。
这个外表貌似"淑女",也常常被人称之为"淑女"的诗人,其实并不是古代大家闺秀的现代版,而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德,同时又是爱他人和爱万物的现代诗人。著名诗人蔡其矫说:"一切艺术的价值与境界决定于艺术家爱心的强弱。想象力与同情心,乃是爱心的不同表现形式。"伊路的诗歌创作,印证了蔡老的这一论断。她那日渐博大的爱心,和发现万物隐秘关联的智慧,使她的诗歌正在呈现出一种大的气象。
与伊路罕见的沉静相比,激烈的安琪则是遥遥相对的另一种极端。
古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一种迷狂,是神的附体。在我看来,安琪就是这样一种迷狂型的诗人。只要一谈诗,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她就会快速进入状态。她的语速会越来越快,眼里闪着狂热而神秘的光。诗歌于她确实有一种"招魂"的魔力。所以,人称她为"巫女"。迷狂型的诗人,很容易在创作中进入一种"中邪"似的灵感状态。激情汹涌,幻象如潮。理性常常无法控制这种来自无意识深处,像海啸一样席卷一切的激情。它很快就冲破理智的小小堤岸,奔腾冲出,倾泄而下。这样,来自无意识深处的、还处在原始状态的、混沌而骚乱的长长的词语流,也就被巨大的激情所裹挟,倾泻在纸上。这就是安琪为什么爱写那种泥沙俱下的长诗的内在原因。对于迷狂型诗人来说,能把无意识中"爆炸"产生的巨大能量,通过创作释放出来,自然是一种快乐--虽然是快感胜过美感。
也许有人会问,创作《奔跑的栅栏》的安琪,为什么与写作长诗集《任性》的安琪,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那是因为安琪的前期创作还是走传统的路子,而后期则信奉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所以,她那激烈、很难节制的个性,才会走向极端,发展为迷狂型诗人。也许,安琪仍是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真正传人,因为她具有进行"自动写作法"的心理基础。所以,赵丽华才会以女人敏锐的直觉,对安琪说:我写短诗,你写长诗。因为她看到安琪写长诗的自然与合理的一面。这就是安琪的奇特之处,也是她不同于那些"先锋诗人",其实是一群理性极强的人。他们是在意识的层面,进行虚假的无意识写作,强行扭断逻辑的脖子,营造语言的迷宫。而安琪则很容易进入迷狂状态,真正打开了无意识。西方后现代主义诗学认为:无意识是灵感之源,是语言的故乡。
西方超现实主义运动发轫于20年代的法国,随后在80年中迅速扩大影响到全世界。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其创始人所鼓吹的"绝对自由"、"梦幻万能"、"自动写作法",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但超现实主义的某些美学观念和艺术手法,已成为20世纪世界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诗人郑敏,对于用诗歌意象表现无意识,有非常周全的理解:"我觉得一个人怎样打开自己的下意识很重要,但是也不能扔掉上意识,形成文字总是有一定的逻辑性,所以这二者之间要对话。事实上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就是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最丰富的对话,那样他的创造性才会非常丰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安琪觉察到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法"的弊病,也在探索无意识与意识的对话。近年来,终于找到了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写法。引入长诗创作的实验。因为"自动写作法"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倾泻,而意识流写作则是一种意识与无意识的融合,对安琪而言,找到这一重要的联结点,就是成功了一半。
近年来,安琪倾尽全力所做的,就是实验如何在长诗的诗体中进行这种无意识与意识的对话。这自然是项大工程,但是不怕失败的安琪,这位罕见的迷狂型诗人,以她逼人的才气,和爆炸般的狂热激情,在进行最"危险"的诗歌实验,她一定要在陷入困境的"实验诗"写作中,探索出一条坦途来!
四
汤养宗是渔家子,生在渔村,又当过水兵,海洋于他,不仅是得天独厚的诗歌资源,而且是直接在他的血管中起伏涌动。所以,80年代他以海洋诗集《水上吉普赛》蜚声诗坛,得到著名诗人公刘的大力举荐。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当众人还在津津乐道于他的海洋诗时,他却表示不愿意再谈《水上吉普赛》,表现出强烈的"悔其少作"。90年代,他又重起炉灶,开始"先锋诗"的写作。诗集《黑得无比的白》的出版,反映了这种"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汤养宗这种断裂似的艺术巨变,其中的得与失,留给我们许多启人心智的思考。
汤养宗海洋诗的成功,在于他从传统的礁石、灯塔、浪花的单一象征写法中挣脱出来,从"渔人与海"的新视角,对他从小生长其中的渔村生活进行艺术的提炼与升华。"水上吉普赛",也就是汤养宗对渔民的一种诗歌新命名。他以一种写实的手法,和散文化的诗体。表现一种渔家们的日常生活。那口语化的语言,场景化的情节,都给读者以一种艺术的新鲜感。在此基础上,他又从渔村"游向"蔚蓝色的大海,写出具象与抽象相融合气势磅礴的《鱼王》。此时,我再次翻阅《水上吉普赛》,仍然为它陌生化的艺术处理而产生的新鲜感所陶醉。
当汤养宗海洋诗蜚声诗坛之时,正是"先锋诗"席卷诗界之日。他受到强大的冲击,产生了要紧紧跟上的急迫感。这位心高气傲的青年诗人,这位从不服输的渔汉,也要与这批兴风作浪的现代派比一比高低。他停止了海洋诗的写作,一头扎进对西方现代派理论、和先锋诗文本的狂热而紧张的解读。那时在文坛上正在大流行、大传染的进化论美学观,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那"悔其少作"的情结,就是在此时产生的。)这位高智商的诗人,很快就从欧阳江河的诗歌中得到启示,掌握了"先锋诗"抽象化的艺术思维。传统写实的手法,是从水中写出水意,从火中写出火意。而欧阳江河的先锋诗,却是从水中写出火意,从火中写出水意。这种逆向的思辩,就是当代"先锋诗"所孜孜以求的陌生化方法。很多人至今不明白《黑得无比的白》的题意,实际上,这就是汤养宗要告诉读者的新思维:即从黑中写出白的陌生化思辩手法。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黑得无比的白》,就能曲径通幽,豁然开朗。
当然,光有逆向思辩的先锋诗手法,还不能保证能写出好诗。换言之,它还必须与诗人独特的创作个性相结合,否则就会写出批量生产的千人一面的诗歌。在我看来,《黑得无比的白》中最大的艺术突破,就是把这种逆向思辩的先锋诗手法,与海洋题材相结合,创作了《群岛》、《伟大的蓝色》等组诗。汤养宗诗歌那种特有的开阔空间感,和越来越抽象化的艺术处理,创造了一个个宏大的艺术时空。这实际上是他早期海洋诗的又一次飞跃。大概是受逆向思维的驱使,他从海洋写到天空。《雁队》、《黄昏第一颗星》,那种通过雁队的飞翔而展示出来的无边无际的辽阔天空,以及诗人想象力的浩大,太令人神往了!
近年来,人到中年的汤养宗已日益成熟。正在对自己"先锋诗"写作进行清理和重大调整。原来激进的"先锋"观念,已经被更加周全的诗学观点所代替,在诗艺上也开始尝试多种形式的综合性写作。在我看来,他那豪放、张扬的创作个性,宏大开阔的空间感,以及那种思辩性的手法,如果能和当代现实生活,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和新传统很好地融合起来,也许,他会再一次让诗坛震惊!
叶玉琳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把自然景物意象化的抒情传统,并加以创新和发展。
中国古典诗歌那种风花雪月的传统,充满了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他们所欣赏的多数是园林和庭院里的名贵花朵。而叶玉琳所继承的主要是古典诗歌那种借自然意象来表达情感的方式,然后融入自己对自然物象那种独特的体验和情感。叶玉琳是与山野中那些充满野性和顽强生命力的景物一起长大,她自然对它们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挚爱。她的聪慧就在于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创作个性,把早已融入她生命中的自然景物,化作取之不尽的审美意象,从而获得了"大地女儿"的灵性。所以,她笔下的自然意象,就不同于古典诗歌中文人传统的意象,而是带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和乡土色彩。
叶玉琳特别擅长用意象来抒情,以奇妙华美的想象,给那些乡土物像带来色彩、芬芳和光辉。"在跌落牛羊的地方/牧归的少女一手提着草裙/一手提着夕阳"(《沙田》)。她把自己炽热的情感,都倾注于大地和自然。所以,她对大地和自然的美,才有着敏锐而独到的发现。在《杨家溪》、《木兰陂》、《雨中石竹山》诗中,那种充满爱意的意象抒情,带来了明亮欢快的诗境。对季节的敏感,可以说是古典诗人的灵感所在。因为季节的轮回,意味着岁月的流逝,引发了古代诗人们对生命苦短的悲叹,伤春和悲秋才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母题之一。后代表现自然题材的诗人,很难摆脱这种感伤文化基因的遗传。在叶玉琳诗歌中对季节性的感悟,持一种更为理性和乐观的态度。她既不伤春也不悲秋,而是在欢笑声中歌吟春天的生机和秋天的成熟,因为春去秋来也给生命带来更多的欢乐时光。她笔下的春天和秋天的自然意象,一扫古典诗歌的季节感伤,以一种健康欢乐的调子,歌唱着大地四季的风景和青春生命的绚丽。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女权主义所提倡的"躯体写作"的影响,大陆一些前卫型的女作家积极进行"身体语言"的创作实验。作为青年女诗人,叶玉琳也深受影响。但她并没有将"躯体写作"推向庸俗化,而是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依然是用传统的自然意象,来隐喻和暗示现代女性的人体美和性意识。在《红土岗之夜》、《苔藓或永不消失的足迹》、《你走不出你的月亮》《航行》、《我用语言消解你的手》等,叶玉琳也是用自然物象来隐喻和暗示性爱。这种把性爱诗化,表现得这般热烈和灿烂,令人想起此中圣手劳伦斯。她是用古老的自然物象,来表现全新的内容。她那充满泼辣野性的意象创造力,使古典诗歌用意象抒情的传统,在一个新的维度上,获得出乎意料的再生。
概言之,散发着乡村野性的饱满生命力,与现代女性的开放意识相结合,构成了叶玉琳独特的创作个性。所以她具有情爱心态的自由度,和审美激情的欢乐性。她很少表现悲剧性的题材,即使写离别和思恋,也是充满着对往日幸福和欢乐的回忆。她在诗中所展示的时空,基本上是"现时态";主要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新生活的歌唱和对生命欢乐的追求。叶玉琳这种充满欢乐激情的创作心态,对她的诗艺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她喜爱把自然景象作为自己倾诉爱情的审美对象,用充满爱意的倾诉句式,让激情裹挟着意象,跳跃和流动,从而形成疏朗和明快的抒情风格。
迄今为止,叶玉琳诗歌都是广义的爱情诗。抒发了她对自然、乡村、亲人和祖国深情的爱。也许可以这样说,叶玉琳创作的是一种欢乐的爱情诗。近年来,她不断扩大诗歌的题材,在艺术手法上,也努力吸收外国现代诗的观念和手法,表现出多向度的探索。
五
"丑石诗群"是一个跨地域的多元组合,远在北京的女诗人空林子,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她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父亲是个剧作家。所以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她已经出版了四部诗集,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在河北工作的诗人郭友钊,是个地质学博士,以他特殊的知识结构独辟蹊径,致力于科学诗的创作,把科学的理性与诗歌的激情融合起来,为"丑石诗群"增添了异彩。闽东年轻的诗人陈慰,把现代诗的手法与古典的意趣融为一炉,擅长用明亮的风景,来传达心灵的忧伤,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70后诗人康城虽是念理工出身,但内心敏感,思路独特。他的诗歌多是对生活的变形、消解,特别讲究语言的速度,令人耳目一新。
"丑石诗群"的组合,还表现为创作与批评携手同行。致力于诗评的邱景华、王宇、陈健的加盟,为诗群带来了理论的色彩,加重了研讨的风气。他们对诗群成员不断的研究和评价,促进诗群向更自觉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代诗群的一个发展变化,就是从早期有共同宣言的同仁社团,过渡到以民刊为纽带的多元自由组合。从《丑石》诗社发展到"丑石诗群",也是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丑石诗群"以《丑石》诗报为平台,没有共同的宣言,没有统一的旗号,也没有号令诗群的领袖。其成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尊重,相互碰撞,互相学习。借诗群的"合力",促多元的发展。诗群的目标,是要更有力地发展各自的创作个性,走各自不同的诗歌道路。以没有共性,作为诗群的特性。以一种开放性的心态,吸纳新生力量的加盟。这是"丑石诗群"成熟的一种标志。
不故作"先锋",不树立山头,以各自不同的歌声,加入当代新诗的大合唱,这是"丑石诗群"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