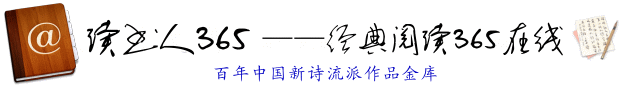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中间代"的"代"
□张桃洲
一、命名
自"中间代"作为一个命名,以大型诗歌选本《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集团形式被提出以来,一时间对之议论者甚众,除"中间代"发起人之一安琪所在的"第三说论坛"专辟"中间代"栏目(收录全部相关理论文章)外,"南京评论"网站、"诗生活"网站及《山花》、《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媒体、杂志,也开辟了专栏予以刊登作品、发表评论,其中参与论说的除部分"中间代"诗人外,尚有著名诗评家程光炜、陈仲义、燎原、敬文东等等,可谓颇具声势。
首先引起争议的,当然是连命名者自己都感到犹豫的"中间代"这一命名本身。此称呼一出,只获得了少量的赞同或默许,持反对意见者居多,"中间代"命名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均遭受质疑。不少诗人认为"命名不是必须的",因为这一命名带有太多的"暧昧"与含混。我在一次关于"中间代"的网络讨论中曾经以为,"坚持命名的意义何在呢?反对这一命名的意义又何在呢?坚持命名抑或反对命名都是一个人的自由,这其实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事"。后来我才发现,这里面实在隐含着一些难以绕开的诗学问题。
显然,相对于"第三代"的激荡与震动和"70后"的喧哗与躁动,"中间代"的命名是冷静甚至冷清的。尽管"中间代"提出后相关的文章有铺天盖地之势,但其间并没有过急的"打倒"言论或故作惊人之语和姿态。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中间代"这一命名和"第三代"、"70后"一样糟糕,虽然安琪一再宣称,"中间代"这一命名蕴藉着三重意义:"一、积淀在两代人(即第三代和70后)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三、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有待于一个可供立足的基点。可以看到,一方面,"中间代"的命名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月"、"九叶"等称呼很不一样,后者基本上是一个具有群体性质的"社团"称呼,并不指向十分严整的写作趣味、美学情致等等,尽管涵括在这些名号之下的诗人在写作趣味、美学情致等方面是很趋近的。即使像80年代的"非非"这样的名号,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其倡导的"三个还原"等主张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各自为阵有目共睹,试图以一种命名来统摄当前诗歌写作的混杂情形,简直是一个无望的奢望,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普遍焦虑。这一名称自身的含混和外延的过于宽泛,事实上起到了一种自我消解作用,当它将一些互不相干的诗人扭结在一起时,它的确什么也不是。在上述意义上,"命名"也许是不必要的?
然而,平心而论,我们也许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中间代"命名的过程和这一命名本身:与"第三代"运动情结和理论先行、作品严重滞后及圈子意识过重不同,"中间代"是先有作品实绩后试图作出的命名式概括,这起码表明了一种理论的进步,在此不应过分渲染和指责其"策划"意味;与"70后"一味依赖"年代"进行命名不同,"中间代"隐约指出了或者说自我认同了当前某类诗歌所处的仍显含混的"中间"位置,这个"中间"一词是可被阐释和填充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比照一下文学历史上任何一个命名,它们大多具有令人尴尬的"追加"性质。如果"中间代"的提出,是怀抱着"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的愿望,那么,也不妨说它严肃地提醒了我们如何看待、评价诗歌史现象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勉为其难的权宜之计。这一命名最终也许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由是观之,我宁愿将"中间代"视作一个非群体或社团、流派的称呼,视作一"代"人突破式的自我命名。燎原在谈到前述的"中间代"诗歌选本时指出,"它不是一本具有共同艺术目标的流派性的刊物,而是以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种'代'为旗帜的诗人同盟"(《为自己的历史命名》)。也就是说,"中间代"不应该将许多毫不相干的诗人拧成一团,而应该通过这一命名,标示出具有"代"的属性的诗歌面貌和精神特质。
二、依据
那么,"中间代"作为"代"的依据究竟何在呢?实际上,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代"的划分是诗歌史、文学史乃至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代"(Generation)是社会学家曼海姆所说的"社会岩层"之一,"对'代'的划分,生理学上有明确的年龄层区分,它依据的是生-死之生物性节律。但从社会学来看'代'的划分,情形有所不同。社会学依据的并不仅是生命的自然事实,必须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事实"(刘小枫《"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不过,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代"意识的全面凸面,似乎只是在"第三代"诗人那里才变得格外强烈。他们在把"朦胧诗"以前的所有(现代)中国诗人称作第一代、把"朦胧诗人"称作第二代后,将自己命名为"第三代"。"第三代"诗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诗学命,以为诗歌的历史从他们那里又重新开始。
后来的实践表明,"第三代"诗人的运动情结,冲垮了他们进行诗学建构的信心可能。他们以为通过对某种既定诗歌范式的反叛与跨越,就能够顺利地通向(抵达)一种新的诗歌范式的建构,因而在表面地"打倒"前人后,便很快产生了已完成作为诗歌一"代"的使命、置身于诗歌殿堂的幻觉。这种运动式的思维方式,和以一种诗学"想法"取代前人诗歌写作的做法,决定了"第三代"诗人所面对的,始终是一种切近的、浮浅的对象性目标,而无法回到诗歌的原初状态和高度,去提取建设性的诗学命题,因而缺乏真正从事诗学建构的根基。然而,"代"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建设性的:它首先是一种有效的给与而不是毁坏,是深入问题内部的思考而不是伸手可触的现成公式;只有具备了某种稳固的、属己的内在品质,"代"的"社会岩层"特性才得以清晰地显露。
显然,这里所谓"代",还不仅仅是人们常常理解的"年代"之"代"。以十年为一"代"的切分,其不合理性已为人所熟知。"代"也许具有"类"的性质,但毋宁说这种"类"的属性,体现了某种精神氛围和品性的聚拢、敛合。例如,"中间代"发起人之一安琪在她的开篇文论《中间代:是时代了!》里,事实上就暗含这样的期待:"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当然,实现任何意义的"天下大同"都是不是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相对于"第三代","中间代"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提出符合我们对于诗歌未来建设的憧憬;它一开始就从建构(而非抵制、对抗)的一侧,在文本(实践)和理论上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以自身的诗学问题(而不是假想的诗歌敌人)加入到汉语诗歌的进程。恰如"中间代"诗人黄梵所作的解释:"它不是在诗歌新体验的开端,就发挥预言能力,它更不是一种平衡其它诗歌势力的抗衡力,因为它有个显见的低调的人格基础:即诗歌政治的动机,在这些诗人身上烙印不深,更可能他们厌恶主义"(《为沉默的诗人作些脚注》)。可以说,"中间代"的提出,显示了从自身处境出发探寻诗歌出路的努力,它强调的不是处于历史循环中的"主义"之争,而是一种"诗歌状态"乃至"人格状态"的"无名"感。这正是"中间代"作为"代"的首要品质。
这种"代"的品质,保证了"中间代"这一名号下的诗人各自的活力,而不像"第三代"那样必须秉承某种集体的形式和面目。当然,另一方面,"中间代"作为"代"也带有祛除不掉的"年代"属性,既然它在发起之初有一个明显的意愿,将这批诗人的生理之"代"指认为60年代。陈仲义也说:"它集结起60晚生代的诗歌合力,全局上维护了先锋诗的生态平衡,促进先锋诗的良性循环"(《沉潜着上升》)。但"中间代"并不涵盖60年代诗人的全部,更具体地说,它是指60年代中没有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这一说法使得"中间代"再次与"第三代"区分开来)。这种经过明确指认的60年代,令人想到即使不与任何命名勾连起来,这一代诗人也的确背负着某种溢出生理"年代"的命运,与生俱来地感受到介于两"代"之间的逼促和紧迫。如"中间代"诗人马策所说,"这代人在50年代沉重叙事与70年代轻逸想象之间,呈现为诗学的悬空状态"(《吁请一个合适的韵脚》)。而这种"年代"的特征尚未引起足够的诗学关注。
在这里,"中间代"的"代"际属性与60年代的"年代"特征存在某种交叉关系,也许正是"年代"赋予了这些诗人特定的际遇、禀赋,以及某些历史面貌和特征的共性。最近,臧棣、桑克、敬文东、西渡在一次长篇谈话中,曾用"60年代出生诗人"的称呼来意指这一"年代"的特殊性。在他们看来,无论从"诗歌方式"、"美学趣味"、"作品情况"、"语言特点"、"先锋特征"等方面,还是从"文学史特征"、"诗歌位置"来说,"60年代出生诗人"都显示出相当的独特性。不过,他们所说的"60年代出生诗人"还包括了"第三代"诗人,并特别提到张枣、萧开愚、陈东东、孟浪、西川等诗人,因此,这一称呼仍然带有无可避免的笼统性,对此他们解释说,"'60年代出生诗人'这样一个提法,不是要抛出一个简单的诗歌史概念,它更多地意味着一个诗歌史的视角,同时也对当代诗歌的阅读作一次重要的提示"(《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四人谈》)。无疑,"中间代"一方面借助于对"60年代诗歌"面貌的澄清,参与到这种诗学的重新厘定中;另一方面,"对60年代诗人的有效推进和挖掘还有赖于中间代这一概念"(马策《吁请一个合适的韵》)。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中间代"命名具有某种合理性,它召唤历史姗姗来迟的关注。
三、个性
但在我看来,"中间代"作为"代"的真正依据和体现,仍然在于"个体"的诗人。说到底,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不是倚靠某种群团式的展示,而是维系在单个的、独立的诗人个体的创造行为上的。从目前的总体状况来看,囊括在《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中的诗人及其作品,也的确代表着近些年中国诗歌的实绩,虽说并不全面和完全准确。但是,他们决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而是众多单个的诗人。如敬文东、陈仲义所说,"诗人最终总是以个体为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以集体"(敬文东《更多的时候你需要逗号和顿号》);"集体命名的网撒得再大,永远也代替不了个人范本"(陈仲义《沉潜着上升》)。因此,只有落实到"个体"的诗人,"中间代"的"代"才能够获得成立,其所谓"中间"的内涵才是可被阐释的。
的确,对"中间代"所指涉的一批诗人的个案分析,还是当代诗歌批评有待开掘的领域。尽管已有一些零星的文字论及,如这本"中间代"选本收录的相关评论(尤以胡续冬评臧棣,苍耳评余怒,凌越评朱朱,臧棣评西渡,耿占春评沈苇,马步升、康城评安祺,沈奇评中岛,马步升评古马,马永波评哑石,车前子评树才,胡亮评史幼波,树才评莫非,蒋浩评森子,刘翔评潘维给人印象深刻),及"中间代"诗人格式对十二位"中间代"诗人所作的印象式评点,表明对"中间代"的批评和研究已初现端倪,但是,相对于一些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诸如臧棣、朱朱、黄梵、西渡、桑克、树才、岩鹰、叶辉、安琪、周瓒、代薇、穆青等而言,批评仍然是不相称和不充分的。不过,这里有个辩证的"程序"问题:对单个诗人的解析,仍然应该置放到对"中间代"的整体阐述中进行,正如"中间代"的"代"际属性的确立,有赖于这些单个诗人特点的呈示。
只有当我们以一种文学史的眼光,重新阅读和打量"中间代"诗人的写作时,他们对于汉语诗歌所作的悄无声息的变革,才变得清晰可辨。他们在诗歌的语言态度、对诗歌的功能和认知和诗歌程式的创新等方面,的确实现了一次"显著的转向"(臧棣语)。确如黄梵所说,"他们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抒情性"、"作为头脑的健美操,诗歌极度灵巧......一个随便的意象、幻觉,都企图必一个灵魂结合,任何一个自由对它来说都刻不容缓"(《为沉默的诗人作些脚注》)。在这些诗人的美学追求、文本实践中,暗含着许多革命性的鲜活因素:对诗歌的自主性的强调,对诗歌的非修辞性的关注,对诗歌的日常经验的重视(不再把诗歌的日常性看成一种'素材'性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诗人用才能加以转化、提升的东西,)等等(《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四人谈》)。这些因素都是值得详细展开论述的。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将对之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也不将对上述诗人逐一作出蜻蜒点水的评析。
就"中间代"诗人而言,60年代的"年代"既是一种生理标记,又是一种无法抹去的历史印痕;"中间"之"代"既是一种隔绝、凸显的姿态,又是一种承继、连续的动力。也许,仍然只能寄希望于时间,"时间反复淘洗的结果,最终留下的只能是那些最具才情的坚持者"(陈仲义《沉潜着上升》)。为他们祝福吧。
2002年8月,草就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