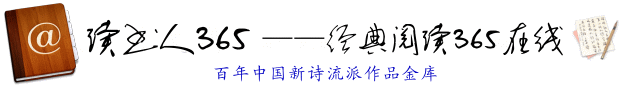
荒诞主义诗歌的几个窥视窗口
□飞沙
荒诞主义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观念提出,从而进行有意识的实验,时间还不到一年。一些感兴趣的人遇到我,最经常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才是荒诞诗歌?我回答说"荒诞诗歌就是表现存在之荒诞的诗歌",他们认为这等于没有说。真的,这等于没有说。那么,是不是可以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找到方便的窗口,窥见荒诞主义诗歌面貌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如能这样,那无疑会使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单化,说起来轻松多了。我对照阅读了几位诗人的实验作品,加上自己的写作体会,多少有所发现,认为这样的窗口是存在的,它们是:失控、反常、偏离、幻镜、发呆等,这些窗口可以是作者的关注方向,可以是文本的风格特点,也可以是修辞上的独特喜好,并不专属某个范畴的。让我姑妄言之。
窗口之一:失控
不用多说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失控的时代,对存在自身失控状态的呈现,必然的成为荒诞主义诗写的重要任务。尽管对文本有一定的定向和定位,诗人对一个诗歌材料的选择未必是理智和有意的,他的本能反映却必定是敏锐和尖锐的。在这一方面,祁国的荒诞实验最具代表性。从他的诗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无计划进行事先调控,又无能力进行事后纠正的失控之场,这种状态离世界的本质最近。他不是告诉,而是用一系列镜头展示,人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无意义和无目的可言。他在《室内》中这样写道:
他站到镜子面前
镜子中的人他不认识
他感到自己是一块肉
挂在空中
自来水龙头上的滴水声
从他身上滴下来
他渐渐被风干
成了墙上的一张相片
这时有钥匙开门
一个和他一样的人走了进来
人已经异化为一块肉和一张相片,他不认识镜中的自己,他只看到从门外进来一个人是和自己一样的,那么"他自己"又是谁呢?不知道。在《逻辑》中我们看到的是失去了个性特征后人类的产品化与共时性结局:
我同时坐在十辆车子上
其中一辆车子上的我突然怀孕了
另九辆车子上的我
瞬间生下了一个共同的儿子
电子信息业的飞速发展无疑在使失控加剧,人越来越成为"被控"物,所以,《我总是不停地打手机》∶"我总是不停地打手机/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从南京打到北京/告诉北京我在南京/从门里打到门外/说一声客人我就不远送了/有时打给天空/问一问今晚有没有飞机从我上空飞过......"
这种"被控"将会达到何等程度,谁也没法料定,而由此越走越黑的人的孤独感正把人往绝望的悬崖上逼,于是《一个人的时候》"......那就带上手套洗手/打开电筒/用电筒照自己/看电视/只看电视机的后壳/躲在衣柜里/想吓一吓自己",或者"没事干/就看看镜子中的脸/看着看着看到了我儿子的脸/看着看着看到了我儿子他女朋友的脸/......(《镜子中的脸》)有时则让一条"名字和我一样/也叫祁国"的狗"牵着我/在床上散步"(《记深夜房间里一条狗》)或者陷入深深的自恋不能自拔,"在被窝里/闻着自已的屁/觉得比桂花还香/起床时/捡起枕头上的一根落发/装进了钱包"(《我的早上》)
祁国对失控的呈现最有力的作品无疑是他的长诗《晚上》,这首诗以奇崛的想象和广阔的画面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人类及其文明的病态面孔(诗的末尾干脆就是疾病与药品的大陈列),令人绝望的语言暴力不禁使人自问: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啊,这可怎么好?乐观的人自然有乐观的说辞,可是只要想想人类制造的核武器已经足够把地球毁灭多少次,就会明白这种乐观有多么脆弱。
其他进行荒诞主义诗歌实验的诗人的作品,对失控也有各自独到的呈现,如女诗人唐果的《和"我"恋爱》,就写出了趋于分裂状态的自我的:"'我',要了我吧/我属于你/你受之无愧呀/我吃青菜,'我'吃萝卜/我唱歌,'我'击节/我害怕了,'我'一夜未曾合眼......"这种不约而同,无疑是有相同的荒诞主义诗写对世界认知的共性背景的。
窗口之二:反常
广义而言,失控的必然是反常的,我这里进行单列论述,是因为它在文本中表现得具有相当独立的生命形态。在唯美主义至今还在有力的麻醉诗歌的情况下,反常化写作特别具有破坏性意义,而这种意义是积极的。宋氏远村的荒诞主义诗歌实验,于反常之道独有心得。这种反常一方面固然是世界观,另一方面则可以看成诗人的美学风格。在《走过疯人院》中,诗人写道:
我是自由的
骑着马奔驰
踩得天空直叫
......
雨季来了
就把它装在口袋里
想抽烟的时候
当成火柴把烟缸点燃
卫生间很干净
阳光太脏了脏得有些讨厌
骑马踩得天空直叫,把雨季当成火柴,卫生间很干净而阳光很脏......这种认知是对被所谓"正面教育"所笼罩的精神生活的极端反动,在美学上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他的《墓碑》竟能把矛盾的事实平面的并列起来,其反常性令人错愕:
我即将出生
老师把我挡在校门前
说你毕业了
我无话可说
我注定是墓碑的儿子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我为什么离家出走》一诗,里面写道:"我的鞋做成船/还没命名/便运行在火中/把天空烧了/我的血/从河里流过/水没有干/河却不见了"在接下来的诗行中,抒情主人公并不在意重大意义之象征物的毁灭(新闻联播倒塌),只是"羞于看见......我的午饭/还没有熟透",这里可以诠注为对人本生活的关注,但其着眼点的反常(因其微小)却正是荒诞诗歌艺术的精髓之一。另外如《观垂钓》,写石头"穿戴很体面/微笑地/散步在水上",而鱼"已一洗如贫了/只怀揣钓杆/即将去流浪",整个是匪夷所思的反常荒诞世界。作者的《读书的感觉》和《别余怒》也因为反常手法的有效运用而大大增强了表现上的张力。
反常在祁国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运用,这里就不举例了。张小云的诗《当然》也是这样的一首荒诞诗,写的是"乌鸦和喜鹊在坟上交欢",对奇怪的社会存在进行了文本的影射,这种写法,比通常的比喻抒情具有更大的容量和多义性,提供的诠释空间也更大。还有林子的《隐藏》,也是一首从反常角度观察世界比较成功的荒诞诗:
四周都摆满了椅子
大家都跪着吃奶
天气不好,温度太高
肯定口罩畅销
门缝里看不见墙上变色的灯
哑巴手中高举着扬声器
窗口之三:偏离
作为"进行时"中的人类,它确实不断的在努力"做"着什么,它是有一个目标的,虽然一个人的目标、一群人的目标、一代人的目标彼此常常不相容甚或相斥,但当我们像观察一条河流那样观察人类时,发现它一直在向下游流淌。那么,这个"下游"是预期的吗?不,它只是一个偏离了的目标。这种偏离是不自觉的,也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有时,达成的目标与预期的目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有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偏离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写了一系列的作品,《对声音的爱好》、《拔钉子》是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
拔钉子
我提了一篮生锈的钉子去废品站
告诉路上的人我拔了这么多钉子
这些钉子是从五十根旧木料上拔出来的
我买它们是想用来装修房子
旧木料像刺猬一样黑它就是刺猬
长满了短如睫毛长过铅笔的钉子
我爱上了这些钉子有半年时间
我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拯救它们
我不能容忍拔不出的钉子
断在里面烂在里面的钉子
我动用一切工具锤钳凿锯刀
让木头没有办法藏匿一小片铁锈
把一个钉子捏在手上甜滋滋的打量
感觉比挖到一块金子还要满足
最后所有的木料都变成了柴火
而钉子全拔出来了瞧有这么多
偏离的状态如同安错了《开关》:"开厨房的灯/亮了厕所/关卧室的灯/亮了微波炉......"它是在滑动中出现的,它有广阔的能指,这是与所谓讽刺诗之类的根本区别。
偏离可以成为一首诗的构成,也作为元素在诗中的出现,如拙作《什么》中的一段:"走出纪念馆/想着那个装画像的镜框/挂得有点歪","纪念馆"是个有很多意义的大词,离开后的人没留下什么印象,却想着一个没意义的小节,对他来说,这个小节反是有意义的了。
窗口之四:幻镜
在常人看来,荒诞的是正常的。在荒诞主义者看来,正常的却是荒诞的--这是就认知而言。而作为诗作者,他的身份是常人和诗人的复合体,其眼光总在正常与荒诞两界对流,所提供的文本有时也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幻镜特征。在幻镜中,正常与荒诞不仅错位,而且交融,是与非消灭了界限,真与幻并无鸿沟,所谓"打通了墙壁",物无分别,时无先后,空无左右,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张小云的《忙碌的猫》就实现了这样一种效果:
我
被锁在空房之中
这里根本没有耗子
白白浪费了我的豪情
我嗅着
放在大厅中央的一只空碗
怕饿死
总是一舔再舔
直到把碗舔成盘子
忙碌的我
累成了一滩水
只剩两只发绿的眼睛
滴溜打转
你从门缝里偷看我
看到的是一只
将死的耗子
在诗中,猫与耗子最后融为一体。敌对的角色滑过边界,实现了在失去敌手情况下对敌手的控制,猫消失了,然而猫胜利了。李明月写有一组《荒诞词典》,其幻镜手法用得十分到位,如《镜子》:
我要在镜子上建一栋大厦
在大厦对面挂一面镜子
再养一窝黄蜂
让它们挡住想进入大厦的人
在镜子上建大厦,在大厦对面又挂镜子,然后养一窝黄蜂挡住想进入大厦的人--从字面看,每一个场景都是逼真的,但又都有是虚空的。另外如她的《苍蝇》,写一只苍蝇要赶走一只在镜子上产卵的苍蝇,最后"两只苍蝇/死在一个尸体上"。她的《猫》写"一只猫在镜子外面叫春/一只猫在镜子里面发情/两只猫找不到出来和进去的门/它们开始习惯表演高潮"都很精彩。上文所举祁国的《室内》兼有幻镜色彩。拙作《门》也是这方面的尝试:
我在纸上画一扇门
回头看看走了进去
在一所空房子里坐下
四面都是门
从十二扇门里
走出十二个人
他们在我身上
开了十二个房间
我把自己折叠起来
丢进纸篓
还有《第二眼》:"一只大肚子烧杯旁边/是一把黑铁锤/我看到烧杯突然碎了/而铁锤并没有移动"。
个人以为,幻镜诗承载更少,带有较多的游戏性,如同走一个迷宫,特别注重语言内部的探索,它从纯艺术角度能为荒诞诗歌提供的可能性应该很大,但究竟有多大,现在还没有真正凸现出来。
窗口之五:发呆
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却又不得不说点什么,这时帮得上忙的是"发呆",它以说了等于白说来表明态度或没有态度。这既是一种不合作,也是一种瓦解。它可以是装疯卖傻,也可以是瞌睡与厌倦。在这里,"意义"已经消失,然而诗歌留着,它微薄的呼吸指示着人的心跳。执着于字面是危险的,因为你将一无所获。请看唐果的《下雨》,人似乎并不在场,但人的状态却在场:
雨竖着下
斜着下
横着下
无计可施时
它还可以倒着下
雨站着下
坐着下
蹲着下
假如它累了
还可以睡着下
还有张小云《你就跟着》,把无望的爱情带进了无义的空间,呈现了单方面爱情的可笑性,最终也消解了爱情:
你要老跟着她吗
她走进厕所
你等好了
好,你等吧
好,你好好站着
她从另一个门
走了
你还跟着吗
她又走进另一个厕所
不出来了
张进步的《那个男人在楼上干什么呢》也是一首"发呆诗",写"我"想看清对面楼上一个男人在十什么,这种"好奇心"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却呈现了人的意识本身的非理性和无目的性存在:
从窗子里望出去
有个男人在楼上活动
他在干什么呢
我实在看不清
想一想就算看清了
又能怎样
我终究还是不知道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可我还是想看清
远村的新作《自叙,2002年》把新的空间引进了自己的诗写,语言更加自由;抽读其中一段就能发现,每一句都很妙,但每一句都是废话,这正是典型的"发呆"症状。是"发呆"为他带来了新的激动:
时刻表是准时的火车常晚点这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
看着那蒙面人的微笑我知道病毒已侵害记忆
我从不与任何人争辩执意牵出一条狗吓人是没必要的
还是让遗言说话从这条街延伸到夜里都没有标点
这样大家说话会更流畅一些将死未死的人总是无可申辩
除了这几个"窗口"外,其它还有一些,如越界(把诸如认真、崇高、爱、美等等理念,顺着已在的方向推进,越过合理的边界推向极端,必然出现荒诞的结局,我的《欢乐公社》、《雷锋的故事(荒诞版)》对此作了一点尝试。)、戏仿(如祁国《新流星花园》、徐乡愁《中国,我的钥匙也丢了》)、拟物等,都可以造就荒诞。当然,以上的视点与方法未必都是荒诞诗歌所独有,不过被荒诞诗写者所情钟罢了。荒诞主义者不反对什么,它只是表达--呈现--自己眼球中所映现的世界。世界是荒诞的,因此是可笑的,也是可乐的;它可恶,然而也可爱;它最大的特点是--好玩。我读祁国的诗,常常忍不住发笑;而当我把我的一大堆作品发给祁国后,我得到的反馈是:他一边读一边笑,有时是大笑。
真的,我们除了笑--大笑外,其他的都不值得做。
2002.10.28-29
31日再改
在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状态之中,听得众声喧嚣,到处都在惊呼天才,我便一骨碌从被窝里一跃而起,怀着惊喜的心情推开当代诗坛的窗口,以迅雷来不及割掉耳朵之势改革开放,然而,我把脖子望成了长颈鹿,用眼睛望断了大江大河,也没有看到什么天才,天棒倒是不少。我再换一种角度,到处都是飞火流萤。我忽然想到,洪太尉不是打开瓶盖放出了三十六座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吗,今夜怎不见星光灿烂呢?就怪高俅那斯,在这些妖魔鬼怪还没有搅得周天寒彻,就成樯橹灰飞烟灭之状了。这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我就顺便到现代诗坛去逛逛,因为沉淀多时,起码不会乱花迷人眼。虽然不是像不少人说的那么经典,但也不至于如人所云真正遍地垃圾。不过,从新诗发韧,中国诗坛的确呈现着江湖的趋向,各路人马笑傲江湖,也热热闹闹。俗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现在我们就以江湖的形式,将差不多百年以来的中国新诗流派展示,这便是《伯乐--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
在我看来,中国新诗真的缺乏天才。我所说的天才,不是指诗人本身的才华,而是指才华与作品的结合。况且,哪里来的那么多天才,即使有几个天才型的诗人,也因各式各样的原因,或自毁,或他毁。人才还是有很多,但不少变成了人精。
既然是诗歌江湖,就免不了要时常切搓诗艺。不要以为自己写的才是真正的诗,别人的就不是诗了,更不必拿所谓的"先锋"说事,先锋只是一种姿态,与能否写出好诗一点关系也沾不上边,先锋能写出好诗,同样也能写出坏诗。所以先锋不是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而且它也不可能成为一条标准,当然,自欺欺人除外,吓唬别人除外。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的玩意儿。似乎谁也没有得到什么葵花宝典或诗艺秘籍之类,借用我自己在《马或者太阳之路》一诗的开头,实际情形就是:"谁也没有找到通向太阳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管是居心叵测,还是天真幼稚,动辄惊呼天才了。中国新诗史上,胡适可算是天才地创造地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但如果放到整个中国诗歌史来看,其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这只不过是形式的变化,而形式的变化很多啊!楚辞之于诗经,宋词之于唐诗,元曲之于宋词,等等。胡适的最大意义在于,所谓的新诗不必再受形式的束缚了。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仍然有人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形式甚至于内容强加给中国诗歌的情形发生,给中国诗歌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江湖一统了,但由于缺了竞争者,自己的诗艺就不是日日新,而是日日退了。所以,这句诗,一方面表明了中国诗歌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则说明我们还有写作与探索的必要。如此说来,这篇文章就不必板着个面孔并一本正经地装酷,那样实在太累,因为我本来就够严肃的了,不如采取戏说的方式,给诗歌江湖激扬文字,浆浆糊糊。这是21世纪的《笑林广记》,供方家哂尔。
借中国申奥成功的东风,在诗坛开一次"中国新诗全运会"。这缘于我和大型综合性民刊主编夏子华的谈话,他是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但他是真正的诗歌外人士,几乎连青春痘都没有长过,由他来组织,相信要客观公正得多,因为他没有诗歌利益的顾虑。我把情况与谯达摩一说,他全力赞同。王晓生是学术界王海式的打假高手,又是首都师大的文学博士生,专事现当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研究,他的加盟可以制约我与谯达摩的私心杂念。
参加这次盛会的守则是:一、有的是文学史的命名,有的是已命名了,有的是我们的命名;二、考虑到有的介于流派与诗群之间,便都以"诗群"称之;三、为减少工作量,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一个诗人只能代表一个流派出场,这是借鉴足球世界杯的游戏规则;四、由于是全运会,无组织无纪律的闲云野鹤、人去楼空作鸟兽散而又并非真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有组织而无特点的,等等,因会场等原因,暂无资格参加第一届"中国新诗全运会",能谅解就谅解,不能谅解的可以一边骂娘去。作为选本,必有其一定的价值尺度,只有公开,不言公正,用不着遮遮掩掩,但我们相信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在一阵"锵-锵-得-得-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