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四回 咨议局绅士现恶形 盐捕营官府逞淫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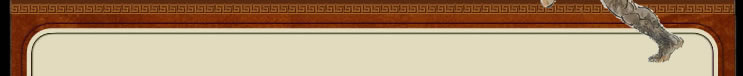 |
|
话说鲁智深见众人都笑自己,再也忍耐不住,正欲发作,经林冲、戴宗竭力劝住。看官,你道众人为甚笑他?只因智深头上戴的,是洋人夏季所用的龙须草凉帽;上身穿的,是洋人旦日驾年的大绒礼服;下身裤儿,却是秋衣。智深等三人是新从梁山下来,那里知道其中奥妙。
林冲抬头见壁上挂着章程,内有一条道:“投票所除本所职员,及投票人与巡警外,他人不得阑入。”想道:“好条严肃的章程!”只见一人皂帽直裰,打扮得公人模样,在那里往复梭巡。林冲忖道:“章程既禁止闲人,则这个人必是本所职员无疑了,但职员断无穿着皂帽直裰的。”正是疑虑,只见那皂帽直裰的人走到一绅士前弯着腰禀道:“老爷,烟烧好了,请进去用罢。”绅士道:“王老爷过足了瘾么?”皂帽直裰的人道:“过足了,老爷请用罢。”林冲道:“奇怪!照章程吃鸦片烟的不能有选举权,本所的人如何反吃鸦片?”只见两边站着五十余个地保,每到一个人,报告住址。即有个戴秀士巾的叫道:“三图地保,你瞧此人果是你图中的某人么?”只见一个三撮胡子,歪戴着帽子的应道:“小人理会得。”即把那个报告住址的人问道:“你是某相么?”那人应道:“你难道不认识我么?”林冲一想道:“糟了!我们都是异乡人,顶冒了本地人姓名,倘教地保察看起来,岂不要闹穿!”只见那人走到桌边执笔写票,那个吃鸦片烟的绅士,立在桌前低头细看,那人问道:“请问监察员,这里的规矩,选举人写票的时候,是否必要监察员监视?”绅士道:“监察员不过恐人写错,代为指点指点。”那人道:“然则请阁下不必费心,因我决决不会写错的。”绅士尚欲回言,那穿皂帽直裰的长随又道:“烟泡已经打好,请老爷快去过瘾。”绅士趁势走了进去。里边又踱出一个烟容满面的绅士来,向选举的众人道:“你们今次举那个?我劝你们最妥当莫如举某人。”一个道:“选举权是我的自由权,你如何可以干涉?”绅士道:“你这次不举某人,我定不干休!”林冲道:“选举如此,宪政扫地了。预备如此,实行可知,说什么九年实行。宣和二年的咨议局,是大宋国宪政活剧的第一出,第一出如此,以后的也不必瞧了。师兄,院长,我们回去罢。”智深道:“洒家瞧的肚子都要气破了,快出去,喝两碗酒振振精神。”戴宗道:“走罢。”于是三人一齐举步。正欲出门,只见监察员跟来问道:“你们三位不曾写票投匦,如何就走?’智深道:“洒家走自己的路,干你鸟事?”冲道:“我们有事,先走一步,请老兄不必见气。”绅士道:“有事尽管请便,只要把入所券留下就是了。”林冲道:“留下就留下,但不知有何用处?”绅士笑道:“也无非替众位代劳就是了。我把你们的入所券,换了选举票,即替你们代写代投。”林冲道:“恁地时费心了。”
走出投票所大门,戴宗道:“教头,他们当绅士的心肠,比我们强盗还要狠十倍。我们做强盗的心里头杀人放火,打家劫舍,面子上也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他们做绅士的人,满肚皮杀人放火,打家劫舍,面子上却故意做出许多谦恭礼数,文明的样子。即如方才的绅士,他明明要我们三张入所券来替朋友填写姓名,却反说是替我们出力,说得何等样冠冕堂皇!”智深道:“我们去吃酒罢。”林冲道:“前面有座水阁子,有酒幡儿挑出在门前,即去喝三碗罢。”智深道:“很好。”三人走了一会,果见一座大酒楼,三开间门面,高悬匾额,金地黑字,写着“酒家”两字。洋台檐下挂着七八块金地黑字的招牌。写着“番汉全席”“零碗小酌”“四时酒菜”等名目。三人跨进店门,见烧的烧,切的切,上灶下灶,共有一二十个人忙个不了,满屋里烧得烟雾腾腾,芬芳扑鼻。三人走进水阁,见那阁子十分阔朗,四围都是五色玻璃,洋漆的栏干,揩抹得点尘没有,一色的水磨揩漆椐木桌凳,摆列得齐齐整整,十分洁净。先有二桌酒客,在那里猜拳行令,吃得杯盘狼藉,兴致浓浓。林冲就在靠窗拣了个座头坐下。
酒保上来问:“三位吃甚么酒?甚么菜?”林冲道:“有上好黄酒,打十斤来,新鲜黄牛肉,炒十斤来、再有童子肥鸡取一对来,此外有可口的东西拣一二祥来。你也不必侍候,要什么唤你便了。”酒保答应了几声是,便喊下去了。不多一会,见酒保一手拿着三只江西瓷白地青团龙的酒杯儿,杯内放着三柄白瓷荷花瓣式的一瓢儿;一手提着一把点铜锡凿花的酒壶;肩上搭着一条半旧不新的白布儿,走将过来放下酒壶,便把肩上搭的那块布取下来,向桌上抹了几抹,然后案上酒杯,再向胸前布裙内取出三双乌木筷子来放上,便去了。一会子,又拿了两个碟子,两个碗子来放下。见一碟是腌鹅,一碟是烧鸭,两个碗子都热腾腾的:一碗是炒虾腰,一碗是青鱼片。智深道:“兀那鸟店,弄出来的东西,都是吃不饱的,敢是恐怕卖完了_不成?”林冲道:“这都是辅助品。我们点的菜,还没有来呢。”说着时,见酒保托着一大盘牛肉送上。林冲道:“与我取三只大碗来,我们不惯浅斟低酌。”酒保喏喏连声而去。一时两只肥鸡、三只大碗,一齐送到。智深道:“这方爽快。”于是三人吃喝起来,虎咽狼吞,邻桌见了尽都惊呆。三人吃喝完毕,就会钞动身,一径回招商来。刚要进去,见客店隔壁一簇人围住在那里。林冲好事,过去一问,却是夫妻两口子相骂。林冲也不在意,与智深、戴宗进客店去了。
原来相骂这一家,姓李名福全,本是个柜上商家,因赌钱输极了,盗取店中银两,被东家知道,歇掉生意,失业在家,贩卖私盐度日。近来朝廷百事维新,因经费不足,不得不取偿于盐斤一再加价,每斤盐价至七八十文,各官盐局就联名的要求盐捕营官府,请严禁私盐,于律外更增严法。官府因公款所关,不得不勉如所请,就出示严禁贩私,说不论肩挑步担,获到站桶站毙,决不宽恕。李福全这日起身,挑着盐正欲去喊卖,只见紧邻王三走来道:“如今盐是不能挑卖了,谁犯了就要捉入站桶站毙。”福全不信,亲到县前去瞧。只见一簇人围着观看,走近看时,正是那个站桶并告示,全福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心中暗暗叫苦,回到家中,对妻子王氏道:“运气真好,偏撞着这打对的瘟官,不知多早晚再有饭吃?”王氏不知底里,忙问什么。福全道:“你还在梦里呢!瘟官禁卖私盐,谁犯了就要捉入站桶内活活处死,你想日子还过得成么?”王氏道:“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碰着这小小风浪,就这般模样。难道没有别的法儿弄钱不成?”李福全道:“有别的法儿弄钱,也不去挑卖私盐了。做伙计没有人要,开店没有本钱,种田没有气力,叫我做什么呢?”王氏道:“现放着嫡亲娘舅在城外北关开设鞋铺,何不去商量商量?倘或借得些些盒了回来,也可度用一时。”李福全听说有礼,遂换上件洋布长衫,一径出城,投娘舅店中来。
跨进店门,见娘舅正在帐桌上写帐,不敢惊动,便于柜外凳子上坐了。店中伙计专心做活,也不来招呼,候了半日,方见娘舅写帐完毕,徐徐脱除眼镜。李福全连忙站起身来,抢步上前叫声:“娘舅,外甥给娘舅请安。”他娘舅只微微的略点了点头,吩咐着伙计道:“里间的存货都霉了,这样的好天,为什么不翻出来,刷刷晒晒呢?”李福全正欲说话,偏偏又有客人来了。只见娘舅弯腰曲背的迎接那客人,敬茶敬烟,一时忙个不了。一会儿客人辞着要去,娘舅再三挽留道:“此间便饭罢,吃是没什么吃的。”那客人道:“我还有事呢,改目扰造罢。”说着便去了。只见娘舅直送到店门外,至望不见那客人背影方回,李福全至此才敢说道:“娘舅,外甥一向要来瞧瞧娘舅,只因穷忙的很,总没得些空儿。如今好容易撞着官府禁卖私盐,闲了没事,得来给娘舅请安。”正欲说下去,忽见外边有人问道:“老板在么?沈老板在县前三星楼立等叙话,请即刻就来。”他娘舅应着便出去了。
李福全候至饭时,不见娘舅回店,只得归家。王氏见他空手回来,便问道:“怎么样了?难道你不去借贷不成?”李福全叹道:“自古道‘开口告人难’,我去了一趟,见是见过了娘舅,奈他总没得说话的空儿,叫我怎么处呢?”便把方才情节述了一遍。王氏道:“糊涂东西!娘舅虽然忙碌,舅母是空闲的,何不到他家里去求求舅母,岂不就完了事呢?”李福全道:“你的话不差,明日一早去就是了。”王氏道:“今天锅子内尚没有饭呢,肚子也饿得扁了,等你的钱来籴米,你还说明朝去、后日去呢!”李福全道:“没奈何,今日且借你的银簪儿典了,换些米来挨一日罢。”王氏道:“哼哼!你想我的东西么?我进了你姓李的门,还是穿过你一件衣服呢?戴过你一只簪子?都是我自己做几针针黹赚下两个钱,打一支半只簪儿戴戴,也为是张你的场面,此刻还要拿了花掉去。人家穿着丈夫、戴着丈夫的尽多呢,谁都似我这苦命人儿!”说着,便呜呜咽咽泣将起来。李福全道:“这算什么呢?罢了,把我这件洋布长衫去典了,换些米来罢。”于是勉勉强强挨了一日。
次日清晨,李福全起身,用冷水揩了揩脸,饭也不吃一径望母舅家中来。这时候他的娘舅尚在家里,见他一早赶来忙问何事。李福全道:“有一事欲与娘舅、舅母商量。只因官府禁卖私盐,外甥绝了生路,只得来恳求娘舅、舅母,意欲与娘舅暂借四五两银子,作个小本经纪,待赚了钱,本利清偿,决不拖欠一文。”他娘舅冷笑道:“银子这么容易?一开口就四五两。我自己日子也难得紧。昨天执了房单,央人去向沈老板抵借纹银二百两,许二分起息,他尚未允,如今兀自打饥荒哩,那里有钱来放债?”李福全道:“外甥急难之中,娘舅不照应,谁还肯照应。娘舅虽是艰难,然四五两银子谅也力所能为的。若为数过巨,外甥也不来开口了,望娘舅看我娘亲面上,救一救我罢。”他娘舅道:“我的儿,娘舅若有钱。还等你开口么!此刻莫说四五两银子,就是四五百铜钱也难。况且你昔日原有好好儿的生意,自己不要做,才干那挑卖私盐的营生。如今想想,究竟好不好呢?”他舅母接口道:“外甥,你那里知道你娘舅过日子的艰难。外面看着虽是轰轰烈烈,殊不知都是空场面呢。这两日生意清淡,日用开销,那一件省得?没奈何!只得典着当头度用。说也可笑,前日子你娘舅来了一个远客,欲陪他上馆去吃酒,没有钱,在我手上脱了一只银镯子去典了用的。因外甥不是外人,所以才告诉你呢。”李福全知没有望头,便起身告辞,一径回家,心下好生烦恼。
一边想一边走,忽闻有人唤道:“老李气烘烘的那里来?”抬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紧邻武三。因答道:“平白的又讨了场没趣。”武三忙问何事,李福全便把方才一段事告诉了武三。武三道:“缓急人所时有,谁能保得住一辈子没有急难日。令母舅也太觉势利了。也罢,你也不必愁苦,我恰有几两银子在这里,你要用时,只管拿去,待异日有了,还我不迟。”李福全十分感激,当下接了银子,一径回家来。那知回到家中,就生出非常风浪来。若非豹子头林冲仗义相救,几乎弄得性命都不保。正是:送雪中之炭,恶人翻似好人;藏笑里之刀,祸我偏疑福我。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再讲。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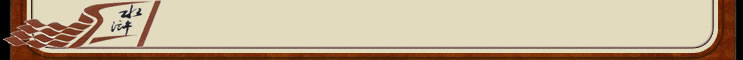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