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四回 萧圣手穷途卖字 安神医荣召入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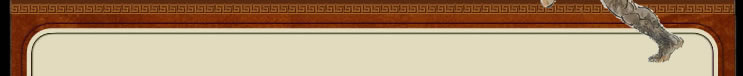 |
|
话说圣手书生萧让,对郑天寿道:“彼时张青尚在东京作翰林呢。自张青到此,与金大坚合力营业,出版的书,日多一日,生意日盛一日,不转瞬而张青附入之资本,又不足转移矣。于是百计思维,再三筹画,只得到合外国人出资合办。全国教育权已半操诸外人之手,言之痛心适有两个西夏国人愿出巨资,合营此业,从此这书铺子规模广大,生意锐盛,至目下他的生财已足值百余万银子。你想金大坚的手段,可惊不可惊?”郑天寿跌足道:“可惜了,偌大的好事业,被外国人分了利去。我要怪他当时为什么不纠合几个本国资本家,却把发财的事业,白白造化外国人?”鄙人曾发起此举,奉经理人办理不善,以致功败垂成,惜哉!萧让道:“你的话都是事后议论。你难道不晓得本国人心理么?须知本国的商人眼光,都只有黄豆一般的大小,有什么远见?果然,果然!那时金大坚尚没有发迹,不过是个穷刻字匠,开着爿小铺子,人小言微,那个肯信他?若果出来纠合人时,恁你苏、张般口舌,说得天花乱坠,人家总当他是骗子,出来诳骗人的钱财;直等到瞧见他发过大财,便都眼珠儿红红的,想来染指,思欲附几股,那知这时候他已用不着你的钱了。看官听者,资本家听者,欲兴办实业之人听者郑哥,你想能够怪他不能?”郑天寿道:“果然不能怪他。”
萧让道:“不要说别的,即如我初到此地,连扇面都没有人请教我写,后来被我想出一个法子,买了几十副金笺珊瑚洒金笺的对子,用心写好。送到多人聚集之所,如茶馆、酒楼、花园、庙宇等地方,一副副挂了起来,尽让人家赏鉴。末后撞着几个识货的绅董,买了纸来请我书写,从此生意便盛起来,镇日总有好几十件东西接下。以前观望的也都请我书写,生意一盛,连批驳我的也都会转口称赞我起来。我自己想着很是好笑:前日之我,固是一个萧让;今日之我,仍是一个萧让。手仍旧是这双手,心思仍旧是这副心思,为什么前日人人批驳,今日人人称赞?假使批驳的是,则称赞的便不是了;称赞的是,则批驳的便不是了。然而今日称赞我的不是别个,就是前日批驳我的人,并且称赞的不是别件,就是前日所写受人批驳的几个字,你想奇怪不奇怪?”其言沉痛,我欲哭矣,我知普天下锦绣才子,读至此亦必放声大哭乐和道:“你们坐一坐,我去拟一个广告稿子,拟毕就来。”萧让道:“何不即在这里拟了?”乐和道:“也好。”遂教茶房取过文房四宝。乐和侧着头想了一会子,提笔簌簌地写了,送与萧让道:“先生,我是不通文墨的,胡乱凑集的几句门面话,不通处尚祈笔削笔削。”萧让道:“大家斟酌斟酌是了。”接来一瞧,只见上写着:
江州音乐传习所广告
科目:乐典、和声学、国乐、唱歌、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
教习:乐和先生
报名处:景虞女学堂 侯仁记军服铺 本校
萧让道:“拟的很好,可以就此刊刻发贴。”郑天寿道:“听说神医安道全在江州行医,生意还过得去么?”萧让道:“安大哥么,红的了不得。他初到时,也没什么人相信他,幸亏运动的方法神妙,组织了一爿报馆,叫做<医学报>,极力的鼓吹他那学说,又办了个医学堂,禀官立案;又编辑了许多书籍,什么<新内经>、<新本草>、<新伤寒论>、<新千金方>等,不下数十种。他的命意,原不望报纸、书籍销路之广,不过欲藉此轰出个名儿。谁料这些书报出版后,倒颇有些销路,销路日广,晓得他的人就日日增添起来。一日蔡九知府患了痢疾,江州城内医生请了个遍,没有医好。”郑天寿道:“江州偌大个码头,有本领的医生,难道竟一个没有么?”乐和道:“江州的医生,吹牛皮,装身架,本领都是一等,若要他诊治病症,可糟了,因他们只会开方,不解病情。”郑天寿道:“奇极,不解病情,如何可以开方?”乐和道:“医生只写熟这几样药味,不论寒症、热症、凉症、温症,都把这几味药去应付。”郑天寿道:“这样,病人从不会好的了。”乐和道:“也有一服即愈的;有的是病症奇巧对药,愈的就快;有的是病与药齐巧反对,死的也就快速。死了后免去痛苦,那也与医好的一般,所以说也有一服即愈的。我讲给一个笑话你听:有一苏州医生在江卅行医,苏州人是著名的苏空头,吹牛皮是他拿手好戏。”郑天寿道:“老弟算了罢!休只管当着和尚骂贼秃,你难道不晓得我是苏州人么?”乐和道:“呀!对不起的很,是我一时粗忽,哥休要置怀。”萧让道:“都是自家弟兄,说差句巴话,有甚要紧?我要听你笑话呢,快说罢。”
乐和道:“这苏州医生,很会装腔做势,凡有请他出诊者,须要午后三点钟方到。午前虽没甚事,亦决不肯早行一步。向着人前夸说,上午门诊,异常忙碌,每日总要诊到一百多号,所以出诊总不能早。一日,有一老妪来请他,口说:‘老太婆只有一个女儿,现在病着,万望先生早来。先生你医好我的女儿,是大大的好事,老太婆专在门前等候。’医生见噜噜酥酥缠的不休,只得胡乱应着。这位医生家况很是艰窘,老妈子都不用一个,上市买办饭菜等事,都是亲自躬行的。这日得到老妪的请封银子二钱,遂上市去买了小鲤鱼一尾,青菜三斤,提着回来。恰恰经过老妪的门口,老妪早候在门前,一见就道:‘先生真好人,快请楼上诊脉去。’医生道:‘我尚要去看门诊呢,家下有八九十个病人等着。’老妪不由分说,把医生直拖进来。医生无奈,只得把鱼菜放在桌上,跟着上楼,与病人诊脉。刚诊得一只手,忽地想着鲤鱼在楼下,忙问道:‘下边猫有没有?’那女子听了这句话,错会了意,顿时羞怯起来,脸涨通红,一语不发。霎时一只手诊毕,又诊一只手,医生见问之不应,心中愈加着急,连问:‘下边猫究竟有没有?究竟有没有?’老妪道:‘姑娘,自古道明医暗卜,先生面前瞒不得的,有没有尽管说呀。’女子没奈何,只得低着头,轻轻说道:‘有是有的,但只微微三四根哩。’郑天寿听了,笑的捭手弯腰;萧让正含着一口茶,笑的喷了乐和一身。乐和道:“糟了糟了!这身衣服我穿着要出风头的呢。”
萧让道:“乐兄弟休讲玩话了。我被你打断了话头,恨的你切骨哩。”乐和道:“何至如此?”萧让道:“你年纪轻,阅历浅,自然不明白这道理。须知交际场中,语言识窍,谈论凑趣,可以获着无上的优利。凡一个莫不欲卖自己才学,在讲论时,正卖弄满肚皮本领时候,这时,设听讲的人淡然道:‘原来如此,此固我所已知者也。’那时讲话的人,恨不得把此人立即杀却,以消心头之恨。有人抢话亦然。记得么?昔日宋公明、戴院长和李逵、张顺在琵琶亭饮酒时,那唱的宋玉莲打断了黑旋风的话头,被他把两个指头捺的晕了过去,就是凭证。再有讲话人一句没有讲完,听话的已欲追问下句,也是很可恨之事。不过此一恨较之以上两恨,略为好些。乐兄弟,你以后要在社会上做些事业,这种诀窍不可不留意一二。”乐和道:“我不过讲一只笑话,倒惹你教训一场,如今我不说了,请你讲罢。”
萧让道:“蔡九知府的痢疾,没人医治得好,后来想着<医学报>,就专派家人到报馆请安大哥。也是安大哥的好运来了,蔡九知府别人的药都吃不好,安大哥的药刚吃下去,痢疾就变成泄泻,腹中宿食,竟是价一泻而空,病便霍然愈了。从此安大哥门庭若市,求诊者踵相接,官场中愈加相信,常常有专轮邀请的。”郑天寿道:“我想去候候他,先生与我同去如何?”萧让道:“他此刻已不在江州了。”郑天寿道:“那里去了?”萧让道:“今上道君皇帝有病,太医院各医官都治不好,因教各府州官,推荐医生进京,安大哥也被蔡九知府荐了进京。当蔡九知府保奏时,安道全是不肯答应,经不得他再四劝驾,方应允了。”郑天寿道:“这就是我们梁山人员之特色。若在他人,保荐进京,求之惟恐不得,还肯推托不去么?”萧让道:“你那里知道,安大哥生性最惜小费,诊治皇帝,非特没有银子到手,还要花费许多小费,太医院、内务府若有一条路不曾铺平,就要掉你枪花,所以他不肯去。现下他在京中,皇帝服了他的药,病势虽是减轻了些,而安大哥被太监等捉弄得弄有说不出的苦咧。第一次进宫,太监处钱没有用足,刚进宫门,蓦然间被他们兜头套上一只大柳斗,安大哥吓了一大跳。原来皇宫里头,因有许多妃嫔宫娥,所以医生入宫请脉,须套上一只柳斗遮住了眼珠儿,省得你东张西望。但用足小费的,则太监预先知照你,直等行到寝宫门口,方给你徐徐套上。安道全因惜了些小费,就吃这一场大亏。”郑天寿道:“萧先生敢是与安哥一同进京的,知得恁地仔细?”萧让道:“有人从东京来讲起,我方知道。”谈了一会,重又说到购买唱歌教科书稿子一节,乐和究属年轻脸嫩,却不过情,也就允了。
萧让问郑天寿:“你此番到此,想做什么事?”郑天寿道:“周哥处同这里,既经没甚事做,我想还是投奔李应那里去。偌大的银行,需人必定多呢。”萧让道:“老哥本业银匠,做了银行,虽只差得个把子,绝倒语。有巡检犯了事,被人至巡抚署控告,巡检忧甚,有慰之者曰:“公毋忧,巡抚与公所差只个把字,何惧之有?”一时传为妙谈。谁知<新水浒>文字被他抄袭了去究属不甚相宜。我看江州地方银匠生意,倒很做得出,不如开一爿银楼罢。”郑天寿道:“本业也好,我就此决定了。拜烦先生给我题一个店号。”萧让略一思索道:“有了,银楼的名号,很不容易题取,既要雅俗共赏,又要叫得响。这三个字似乎还可以用得。”说着,提笔写了出来。郑天寿、乐和一同瞧时,见是“九云楼”三字,不禁都叫起好来。郑天寿道:“费心一发给我写了罢。我今晚回去是来不及了,明日一早当去定房屋,置生财,赶紧办起来,这月里可以开张呢。”乐和道:“你的性真与秦明、索超一般急呢。”郑天寿道:“做商业迟慢不得的,一迟慢就要错掉机会。”于是萧让辞着要去。郑天寿道:“我也去了,明天再叙。”
郑天寿回到寓所,见蒋敬、时迁尚未回来。忽地茶房送进一张请客票,只见上写着:“飞请郑天寿老爷驾临春煦阁一叙。弟李应顿启。”下注:“蒋、时两公均在座立候。”郑天寿就问明地址,立刻坐车到春煦阁。堂倌领到第三号厢房,见李应、蒋敬、时迁均在。郑天寿与李应敷衍了一番,只见侯健、萧让、乐和、张青、金大坚也都到了。请客的回说:“客都到齐,只有景虞女学堂周老爷说谢谢。”李应道:“周通这厮,被几个老丫头迷昏了,连本山弟兄请他都不到。”乐和道:“我瞧周哥神气都没有了,他的精髓都被这一群不成材的东西吸尽了呢。”侯健道:“女学生的手段恁地了得?梁山泊上这么样一个好汉,尚被他治的……”说半句妙,若再说下去,便不雅驯了说至此,堂倌已烫了酒送来,大家让着入席。饮酒中间,萧让向郑天寿道:“你的招牌儿,我已给你写好,明日就可拿到招牌店里做去了。”众人问郑天寿:“开设什么宝号?为甚瞒着大众?我们尚拟贺贺你呢。”郑天寿遂把要开银楼的事说了一遍。蒋敬道:“只半日工夫,你我三人便都改了行,成了三样生意。”郑天寿道:“你们二位做了什么生意?”时迁道:“我做了这里警察局侦探,是李员外写书保荐的,明日就要到差。蒋哥也是李员外荐的,在商会当干事员。岂不都改了行么?”当夜席散,各自归去不提。
次日,时迁、蒋敬先把房饭资算清,上生意去了。郑天寿便忙忙的定房屋,办生财,用伙计,一月有余,方始部署妥当。于是悬灯结采,就开张起“九云楼’’银楼来,江州的梁山好汉都来庆贺。此时安道全已经请假回江,故亦前来庆贺。为遇骗伏线看官,<新水浒>写到这里,十四回了,一竟平铺直叙,毫没些儿精彩;譬之旅行,所经尽是平原、旷野,虽一草一木,皆瀑野趣。杏雨半村催牧笛,苹风两岸动渔桡,究不若奇峰插天、怪瀑泻地之能动人家心目。幸喜江州城外有几个浮滑人才,做出几桩蝇营狗苟的勾当,足以佐我笔机,资君谈助,不免待我濡毫泼墨写他出来。横竖前辈耐庵先生有过老例的,于青面兽双夺宝珠寺之后,曾把济州缉捕使臣何涛与其弟何清的家庭历史细细描写,不嫌喧宾夺主,妨害正文。就是大文豪金圣叹先生,也不曾说过半个不字,则陆士谔今日,何妨学步呢?正是:得意讵敢自娱,有奇何妨共赏。击筑和歌,荆卿安在;高山流水,钟子难逢。帐阅历于风尘,觅知音于当世。文章萃冀北之灵,群空一顾;声价哄洛阳之市,纸贵三都。虽系痴望,亦属恒情。文章至是,尽成变徵之声纵教呕尽心头血,只作巴人下里声。悲哉此语,士谔恐读者轻视此书也欲知端的,且听下回。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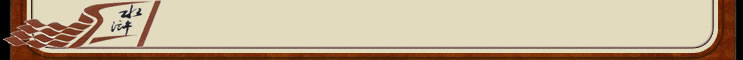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