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八回 智多星初戏益都县 魏竹臣重建孝子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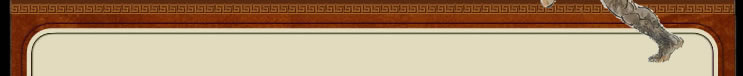 |
|
话说智多星吴用对孔家弟兄道:“此事必得我亲自一行,方可了结。但你们为甚要造这逾制的房屋?城乡绅宦那一家有这样的屋宇?”孔明道:“我们因见梁山泊上的忠义堂这样造法,十分气概,所以摹着样教匠人筑造的。”吴用道:“那是如何使得?山上是无法无天地方,由我们怎样,那个敢来干涉?这是在官吏势力范围内,如何可以胡做?”孔亮道:“先生休辞劳苦,同我们白虎山走一遭去。虽拆卸也不值什么,但特特兴工动土筑好了,重新又要拆卸,我二人脸上的光辉,岂不都被扫尽么?”吴用道:“我既允许你们,你们几时走,我也几时走,决不会翻悔的。”孔明道:“我们逛两天就要动身,先生预备着是了。”林冲道:“难得进京的,何妨就多逛几天。”孔明道:“倘找着李立、穆弘,就多耽搁几天也未可知。”林冲道:“他们两个回去多时了。因揭阳岭山矿已经争回自办,达到最初的目的,金国人开夜汗也被他一气气走了。”孔亮道:“可怜朝廷白养许多官员,到紧急时,一个也没用,倒是我们梁山泊英雄出来替他尽一把力。先生,若是我们团体放大起来,把全中国当个梁山泊,还怕什么外国人?”吴用道:“那也不能,人太多了,志愿何能齐?”一当下说了会子闲话,二孔辞着去了。过了两日,吴用收拾行李,同着二孔辞别了林冲,离了东京,投向青州白虎山来。在路无话。
不则一日,早来到白虎山地方,只见山势险峻,树木丛杂。孔明道:“好了,到我家止二里路了。”三人下冈子慢慢地走向前去。见树林中露出一所房屋,巍峨壮丽,宛如王宫内苑一般。孔亮道:“夕阳已在树梢头,我们紧行一步罢。”霎时间已经走到。只见门外蹲着两只大石狮子,水磨斗方砖子照墙,兽头大门,朱户铜环,十分气概。吴用咋舌道:“造的太觉过分。”进了门,庄客禀道:“两位官人回来了!县里差人连着来催过五七遍,小人回说官人不在。差人不信说:‘你们不拆也罢。过两天知县相公自己下乡来了,你们自去对相公说罢。’今天朝晨又来说:‘知县相公准定明后日下乡,你们预备着罢。’”一步紧一步孔明道:“如何?”孔亮道:“怎样办法?”吴用道:“休慌,保在我身上,给你办到不拆是了。”奇文吴用道:“这里离城有几许路?”孔明道:“约有三十余里。”吴用道:“快给我拿出十两银子来听用。”孔明道:“何用?”吴用道:“你不必问,我就在这十两银子上,保全这所房屋。”奇文。看官试掩卷猜之,后文果作何布置也?孔明只得拿出十两银子,交付吴用道:“唤一个庄客来。”吴用把银子付与庄客道:“连夜赶进城去,购办极精致金漆空头神牌一座,二斤重红蜡一对,檀香一炉,神龛一座。今夜不及回来,就在城中宿了客店,明晨城门一开就赶回来,不得有误。”奇文骇笔,匪夷所思庄客接着银子,如飞而去。孔明、孔亮见吴用如此作为,正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孔明耐不住,问道:“明日知县下来,如何对付?”吴用笑道:“此事只在吴某身上,你们不必过问。”本是孔明、孔亮的事,却教他不必过问,真是千古奇文一宿易过,早又东方发白,红_日照窗。孔明、孔亮忙着起身,活画出有心事人到书房来瞧吴用时,兀是酣睡未醒。二人不敢惊动,轻轻地走了出来,到大厅上四团团打转圈。约有一小时,只见昨晚差去城里置办东西的庄客,挑着一副担子进来,把神龛、神牌、檀香、绛烛一件件取出放于桌上。孔亮道:“军师莫不是和我们作耍么?置办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哥哥猜得出么?”孔明道:“军师是素来鬼神莫测的,那里猜得着?但我所信得过的是,军师必不会和我们作耍,这些东西,他一定有什么妙用,不过你我智识浅短,一时猜度不出罢了。”孔亮道:“是么?我也想他自东京跟我们到此,路程也不为少,难道赶了这许多路,只图着作一次耍不成?”
正说着,吴用已走了出来。二人连忙起立道:“先生,起身了。我们到过书房,见先生睡梦正浓,不敢惊扰而退。”吴用道:“二位所谈,小生都听的明白。小生此番实欲与益都县知县闹一会耍子,二位请瞧着是了。”随命把神牌捧上来,取过笔砚,磨得墨浓,醮得笔饱,举笔一挥,不知写了些什么。写毕,即把神牌供入龛中,放于正中桌上;又叫取出蜡台香炉,排列妥贴,插上烛,架上香。吴用道:“二位梳洗过了没有?”二人都说未曾。吴用道:“快梳洗了,预备接待知县相公。”于是三人梳洗完毕,齐穿着了吉服,叫庄客到村外官道上守候,官来速速进报。约等一个时辰,庄客飞一般进来报道:“知县相公来了,离本村只三里许路了。”吴用叫孔明速把香烛点起来,自己同着孔亮到庄门前守候。
只见那位知县坐着暖轿,鸣锣打道,呼喝而来。轿到门口,吴用抢步上前,兜头一拱道:“相公好早,敢是来拈香么?”奇文骇笔知县愕然道:“老兄说些什么?本县实在不懂。”吴用道:“这里白虎山孔家庄孔氏,乃系先圣孔子后裔,刻下庄主人孔明、孔亮为其祖先孔子建一祠堂。今日是神牌入祠之日,晚生在此帮忙。相公来此,想必也是拈香,怎么反说不懂起来?”知县暗想:“糟了,糟了!我可上了他们的大当。但既到这里,须进去察看察看。天幸或有破绽捉着,狠狠的办他一办。”随道:“既是先圣入祠,本县理宜陪祭。相烦引进则个。”吴用、孔亮即让着益都县同行入内。到正厅,只见绛烛双烧,香烟缭绕,孔明端端正正,垂着手立在那里,见了知县,忙着向前相见。知县走近神龛,仔细向内一瞧,只见雕花金漆神牌上,写着一行墨字道:“十八世祖至圣文宣王孔子神位。”奇绝怪绝,想入非非不觉目定口呆,不由他不呆半响方说出一句话来,问道:“你们建筑圣庙,为什么不来呈报?”吴用道:“此乃家祠,似可以不必呈报么。”知县无言可答。迁延了一会子,拜也不拜,讪讪的去了。吴用拍手道:“如何?我说只在吴某身上,叫你们不必忧虑。你看这堂堂百里诸侯,被我略施小计,就弄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由他说嘴孔明、孔亮齐道:“先生妙算,今古无双。我们若非先生,此番定遭羞辱;但我们虽是姓孔,并非是尼山圣裔,这一来岂不渎圣了么?”吴用笑道:“这叫做兵不厌诈。权宜之道,那里当得真?你们休要刻舟求剑才是。”二孔听了,方无甚说话。自此孔明孔亮便被众人公举,做了白虎山乡董。至于他做了董事老爷后,如何武断乡曲,如何侵吞公款,因调查得不曾仔细,不敢平空捏造,枉弄笔端。以文为戏却说智多星吴用,自办理此事以后,能名大著,白虎山一带数十村庄,苟有艰难事务,无不与之斟酌。吴用则视其事之轻重,以定酬谢费之多少,虽不足以发财,藉此亦不无小补。好笔,以收柬作开引一日,与孔明、孔亮闲坐讲话,忽见庄客入报道:“有后山杏花村几个乡下人求见吴先生,说有要事面商。”孔明道:“生意上门了,先生。”吴用便命引他们进来。庄客应着出去,不多会子,同着三个乡人进来,施礼毕,问道:“那位是吴先生?”吴用道:“小生便是。众位有甚见教?”乡人道:“我们的事重大非常,弄的十分尴尬,没奈何,只得来恳求先生,倘能为我们解去这困厄,情愿奉送银子五两,给先生买杯酒吃。”吴用道:“请把这事的始末情由先说一遍,苟有可以效劳之处,我是没有不肯的。银子数目呢,此刻且不必讲。”乡人道:“我们村前有一座石牌坊,听说是从前村上出了个孝子建造的,到今已数十年了。前几天发大风,把牌坊顶上的大石块吹了下来,我们不合贪便宜,把有字的石块儿,取来修了猪圈墙。谁料被前村的举人魏竹臣会诈人查知了,立即要把我们送县,说石块上所刻之字乃‘奉旨’两字,我们把‘奉旨’隔了猪圈,奇句就是个违制之罪,轻则充军,重则斩首。先生你想:我们又不识字,可怜误犯了这种重罪,倘吃起官司来,一家人怕不都休了?所以特地来恳求先生,可有什么法子救救我们?”吴用听罢,把头摇了一摇道:“此事很难。你们犯了这样重罪,即使诸葛复生,也不能替你画策,叫我那里想得出什么法子?故作一跌承你们情,应许我五两银子;但是你们的性命,难道只值得五两银子么?”孔明道:“你们果欲吴先生搭救时,快把银子数目增加起来。”乡人道:“我们家里穷的很多,恐怕拿不出。”吴用道:“你们去请教他人罢。”说着立了起来。乡人道:“再加五两如何?”吴用依旧不肯答应。孔明道:“先生,他们实在穷苦,就替他办一办罢。银子再教他们拿出五两来。”吴用道:“我本是不办的,既是孔大官人如此说,我看孔大官人面上,就替你们办一办。快去拿十五两银子来,保在我身上,使你们不吃官司是了。”乡人大喜,就在身边摸出十五两银子,交付吴用道:“先生,银子是十五两,只恳求早些请过来,我们先回去了。”吴用向孔明道:“瞧不出这个乡人,倒会这等放刁,带着十五两银子,开口只说得五两。”孔明道:“这个人本是著名的赤脚讼师,不难到极地,不出来求人家了。”吴用笑道:“如此尚算是行交行了。”孔明道:“此事易办么?”吴用道:“在我手里的事,不曾有过艰难的。怕难也不敢答应了。你们倘高兴,何妨跟我去瞧瞧。”孔明、孔亮齐声:“愿去。”
当下三人同着起行。越过冈子,就是杏花村,霎时间便早行到。几个乡人已在村口等候,一见了吴用等三人,便如拾着活宝贝一般,喜的眉开眼笑道:“先生来了!魏举人正在我们家里呢。”吴用道:“很好。你们先去对他说,隔猪圈的石块,并不是牌坊上跌下来的,也并没有什么‘奉旨’的字,都是你老人家欺我们不识字,诬枉我们。不信时,只要叫识字的人来一瞧就知道了。他如同你们争执时,我便来帮你们硬赖。”孔明道:“若实有其事,则证据确凿,如何硬赖得过?”吴用道:“你不要管,瞧着就是了。”这时候,乡人已依计而行去了。只听得一片喧嚷之声,自篱落间渡越而出。孔亮道:“哥哥不听得么,里边争论的,想是打架了?学究先生快走一步罢。”孔亮一语,而四边都已关到,其文一何妙哉!
吴用等紧行几步,穿过短篱,只见草堂中那魏举人怒气勃勃,颈间青筋一根根绽了起来,满口“放屁,放屁,真真狗屁”说个不住。可笑吴用走进道:“老先生,屁放完了没有?”妙人妙语_乡人道:“好了,吴先生来了。吴先生是读书人,也识字的,请评评这个理看,究竟谁是谁不是?”魏竹臣一见吴用也说:“好了,恐不好呢识字的人来了,真真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吴用道:“你们二位为着何事争论?”魏竹臣道:“这里一座孝子坊,是仁宗皇帝圣旨敕建的,前日大风,顶上的石块吹了下来。石块上刻有‘奉旨’二字,被此位赤脚讼师取去,隔作猪圈墙,你想荒谬不荒谬?谁料今日尤其荒谬,竟敢和兄弟白赖,说兄弟诬枉他,石块上并没有‘奉旨’二字,也并不是牌坊上跌下来的。似此证据确凿的事,竟欲以一赖了之,岂有此理不岂有此理?”乡人道:“猪圈墙的石块,我们自己家里的,并且隔好已一年多了;牌坊是前日才吹下的,明明是诬枉我们。吴先生,你是识字的,替我们瞧一瞧就知道了。”吴用道:“是非曲真,总要明白的。待我瞧了再说。”于是同着进内。魏竹臣、吴用、赤脚讼师、孔明、孔亮一共六人,走到猪圈间,一阵秽恶之气,向十二个鼻管子里直钻入来,五个人作恶不迭,只有赤脚讼师薰惯了的,倒也并不觉着。魏竹臣一手掩着鼻子,一手指着猪圈墙道:“你们瞧左边的那块石子,不明明刻有‘奉旨’二字么?”吴用随着所指的地方瞧去,果见一块嫩黄小石板,上刻着“奉旨”二字,四围都刻有龙纹,惟硃书为风雨所剥蚀,已是瞧不大清楚。吴用道:“兄台误了。这块石上那里有什么字?字都不有,何来‘奉旨’也?”魏竹臣道:“怎么老兄也说起此话来?石上明明有二字,不过硃书剥蚀,瞧不清楚罢了。”吴用道:“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孔家二兄也都识字的,一问他们就知道了。”孔明、孔亮齐道:“我们也瞧不清楚,恐怕不见得有字么。”弄得魏竹臣焦躁起来,大声道:“你们串合着指鹿为马,不给你们个真凭据,你们如何肯心服?我去雇匠人来,安放上去,那时再与你们理论。”吴用道:“一定安放不上的。若果丝毫不差,我就帮助兄台办这赤脚讼师。”魏竹臣道:“很好,很好。”说着去了。
一会子同了三个匠人来,把猪圈墙所嵌的那方石块挖了出来,用水洗净,然后再把红硃将字填明,布好梯子,把石块安放妥贴,四围用油灰布满牢固。抽去梯子,仰面一瞧,见伏伏贴贴,丝毫不误,魏竹臣喜极,回头向吴用道:“老兄瞧见么?”吴用道:“瞧的很清楚。”魏竹臣道:“丝毫不误么?”吴用道:“果然丝毫不误。”魏竹臣道:“然则如何?”吴用道:“有甚如何?兄长说他把牌坊‘奉旨’石块隔作猪圈墙,如今有何凭据?妙妙!难道兄台好把牌坊上石块重又移到猪圈上去么?这私拆牌坊的罪,料兄台必不肯犯的。”魏竹臣跌足道:“罢罢,我上了老兄的大当!请教贵姓台甫?”吴用道:“不敢。敝姓吴,草字加亮。”魏竹臣道:“原来就是智多星吴加亮先生!可知我撞着对手了。”吴用道:“此事本是兄台自己失检。若我做兄台时,当我硬说不是时,便可说你我争不明白,禀报了知县相公,待他自己来瞧罢,我就可没法了。”魏竹臣道:“领教,领教。”吴用又对乡人道:“你枉叫了赤脚讼师,却白花掉了十五两银子。若我做你时,便半夜里悄悄地把石块上去安放好,或者依旧丢在外边地上,岂不省事?”乡人懊悔不迭。
忽见孔家庄庄客急汗淋漓的跑来道:“吴先生,县里差人在庄上立等,接笔迅疾说知县相公有要事,请你马上进衙门去。”吴用道:“有函信没有?”庄客道:“不见有。”吴用道:“有帖儿没有?”庄客道:“也不见有。”吴用道:“奇怪!我与知县素没有交情,怎么会请起我来?并且又不听说有函件、帖儿,其中定有缘故。我们回去瞧光景,再筹对付之策。”于是吴用、孔明、孔亮辞了赤脚讼师,回向本庄来。无多路程,霎时便到。那差人已等的不耐烦,一见吴用,便道:“这位可就是吴先生?知县相公立候着,有要事面商。请即同行罢。”
吴用道:“既蒙相公恩唤,必有信函或帖儿,敢请借观则个。”差人道:“来的匆遽,都没有带。”吴用寻思:“此必骗我到署害我也,倒不可不防。”差人催道:“请先生即同行罢。”吴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差人道:“上下,知县相公呼唤吴用,有甚事务,望略告知一二。小生有银子十两,送与上下买碗酒吃。”差人听说有银子,顷刻笑逐颜开道:“既蒙赏赐,小人自当报效。先生你那里知道,大祸临头了。”吴用愕然道:“怎佯的大祸?”正是:底事张仪鼓舌,惹起万丈波涛;遂教李白逞才,撰出一天星斗。欲知益都县公差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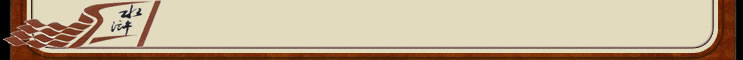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