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二十一回 盘报馆吴用论行情 吃番菜李逵闹笑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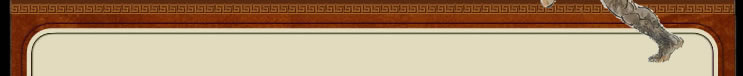 |
|
话说智多星吴用在江州组织了一爿<呼天日报>馆,议定日子出版,当下到主笔房与萧让商议道:“我们这报,总要有几样特色,方能惹起人家的兴致。我想编辑的清楚,是最要紧的事。现在所行各报,不是杂乱无章,便是猥鄙可厌,我们须要别开生面,独出心裁。扫尽芜秽的积习,发出万丈之光焰,推倒智勇,开拓心胸方好。”萧让道:“要编辑清楚,也很是容易。放出我们做强盗的手段,怎样是智取,怎样是力攻,画清门类,自然一目了然了。”吴用道:“好极!费神拟一个样子来。”萧让略一思索,提笔一挥,把报纸格式,送与吴用。吴用接来一瞧,见上写道:“言论之部,内分社说、代论、时事商榷、天声人语四类;纪事之部,内分宫门抄、电报、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埠新闻五类,而每类内又画分官事、民事、讼事、杂事各细目;丛录之部,内分小说、佚史、诗话、谐文、小言五类。”吴用道:“好果很好,本埠新闻内,须另外分列几部,以醒阅报人的眼目。综本埠每日之事,都不过淫拐、诈骗、杀伤、倒欠、火灾、开会、词讼之类,我们何不就把他作为标目?淫拐的事务,标目就叫‘淫拐类’;诈骗的事务,标目就叫‘诈骗类’,推之于杀伤、倒欠、火灾、开会、词讼,无不皆然。萧兄,你道使得么?”萧让连口称妙。于是就照此样式编辑起来。
萧让把各地来函,一一披阅。有用得着的,随手笔削了付与手民排印,用不着的随即弃去。阅到清河来信,见上写道:“行者武松回乡后,设立了个武学会,招致四方青年,较量拳棒,习练武艺,会员陆续增添,刻下已有三万余人,发达已臻极点。兹闻于下月将有武术比赛大会之举行,果尔,必有一番也。”萧让忙拿着信到事务室给吴用瞧。吴用瞧毕道:“武二天人,其举动毕竟与他人不同,磊落光明,毫无暗昧情事。萧兄,我此话确么?”我知其不确。如果确了,如何会跑到<新水浒>中来?萧让道:“怎么不确?”吴用道:“兄真忠厚。他不有利益,干这事做什么?武学会有到三万多个会员,入会费以每人二两银子计算,已有六万多银子了。再有月费,以每人二钱银子计算,一月也有六千余金的进益,你想他会弄钱不会弄钱?不过他这一举,是公私俱利的,比了我们只从一方面着想的,略为高了些。”萧让道:“此话如何解说?我不甚明白。”吴用道:“目下我国弱极了,外人在我国的势力,日盛一日,凡有交涉,外人无不是,吾人无不非;裁判官断事,不必问事理情由,只消一望外人控吾人,可立刻把吾人判罪收禁。为什么呢?做了吾人,没有不犯罪的。吾人控外人也立刻把吾人判罪收禁,为什么呢?吾人本无罪,探告外人即犯了重罪。语语是血,句句是泪,是和血和泪之文,呜呼,吾不忍读矣!这样压抑下去,郁极思泄,必有溃决之一日。你想那时的人,倘个个身无缚鸡之力,如何可以御外侮呢?此刻他举办武学会,提倡起尚武精神来,人人练就了本领。那时节,岂不是有恃无恐么?目下虽丢掉几个钱,也很值得。照此做去,武二于自己一面,虽有利益,于社会一面,也未始无功。这就教公私俱利,如何会解说不出呢?”萧让道:“原来如此。”
看官,智多星吴用,真不愧为智多星,凡事算得到,做得到。忽然一提,文笔奇幻莫测他那<呼天日报>发行后,果然万众欢迎,销路大畅。官场中传观色变,因其掊击无私,语语触着痒处。于是聚众会议道:“吴用这厮兴妖作怪,放他在江州,终非了局。大家斟酌个法子,把他除掉方好。”于是有主张用强硬手段的,派遣委员密行拿办;有主张用柔软手段的,贿以白镪,暗示牢笼。那知<呼天日报>馆的消息比鬼还灵,拿办他的委员尚没有出省,他的报上已登载了出来,道:“某官欲拿办本馆之办事人,然本报之发起,为吊民伐罪也,故对病民之官吏,口诛笔伐,毫不假借。而此辈病民之徒,生平恶劣行为,无人揭破,忽受意外之打击,遂现出种种鬼哭神号之状态。欲更正则系实事,无可更正,欲不更正,又恐为朝廷所闻,饭碗不保。一种暴戾之气,无地发泄,不得已出一拿捉办事人之下策。噫!误矣,误矣!若辈亦知各处之有报馆为国律所许者乎?倘敢私拿,本馆当提起五式交涉,控尔违犯报律之罪,不假借也。”那些用强硬手段的官吏,一见这个告白,早一吓吓软了,销声静气,拿也不敢拿,办也不敢办。至于几个用柔软手段的呢?银子送去,果然照单全收,然而送者自送,骂者自骂,银子收了,依旧不肯假借一些儿。
官场中到了这个时光,真弄的计穷力竭,和战均难。后来蔡九知府究竟想出了一条妙计:创议收归官办。知小李广花荣与吴用很有交情,遂派他到<呼天日报>馆来,与吴用商议。吴用接进花荣,分宾主坐定,先谈了一番别后情形,然后说到本题。吴用开口要二十万银子。花荣咋舌道:“军师心好狠,欲好奢!只费了一二千金本钱,索利竟达百倍之巨,比我卖路所得,竟多一倍还不止!”吴用道:“你卖掉过那处的路?共得着多少银子?”花荣道:“卖掉过那处呢?就只一条江浙铁路罢了。从江州通到浙江杭州的路,延长只有一千多里,是我讲成的。卖给与金国人的,只得着个九五扣回用,五六个人分派,我只派着八九万银子。幸亏外间不曾知道,所以骂不着我;那受骂的人,所得银子较我也多得有限,却弄的通国皆知,人人不以人类相待。你想这个人呆不呆呢?”吴用道:“花兄,你乖果然乖了。但我看起来。终不及汤隆、李立、穆弘他们三个人,两个争矿;一个争路,声名鹊起,全国人民仰望之如泰山北斗。”花荣不等说完,笑道:“先生,奈何也说起这样话来?花荣不是奉过先生将令么?的是花荣语‘文明面目,盗强心肠’,花荣只不过照着这八个字做罢了。做强盗的只要有银子到手,管甚么声名不声名?况花荣的声名并不曾坏掉呢。汤隆见争路可以获利,就何妨出来争路;李立、穆弘见争矿以获利,就何妨出来争矿,我花荣见卖路可以获利,也就何妨出来卖路。说我花荣卖路是私,他们争路、争矿,也未必不是私,不过各人的手段不同,做法各异罢了。即如先生办着这<呼天日报>,面子上说是吊民伐罪,难道真个为吊民伐罪么?这也瞒不过花荣的。”确是花荣语,文甚利甚吴用笑而不言。花荣又道:“本山弟兄如阮氏三雄及二张、二童、李俊等,素在水中生活惯了的,即以海权为莫大之重要,练着渔团,一勺水都不肯失掉;王英、周通专靠着吊膀子度日,一个女子都不肯放过,也都不过为一个‘利’字。蒋敬、时迁以倒闭银行为得计,李应却以不倒闭为得计。岂不是各人的手段不同,做法各异么?”吴用道:“够了,够了,不用说了。是吴某一时失言,我们谈正事罢。蔡九知府意思肯拿出多少银子来?花兄必定是知道的。”花荣道:“倒也不曾仔细,大约十来万银子是拿得出的,再多呢,恐怕吃力,想他不过叫我来探探先生口气。”吴用道:“此事全仗鼎力。费神,费神!”又向花荣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花荣道:“笑话!自己弟兄,可以帮忙,没有不尽力的。”笔墨生动,真如生龙活虎,一奸一滑,宛然纸上,吴道子画有此神妙乎!吴用道:“花兄大裁,斟酌着是了。”花荣道:“我去讨了知府示下,再来奉候。”说着,便起立告辞,吴用执手相送。
送到大门,忽见一人急烘烘走来,与花荣撞个满怀,连吴用也撞倒了。三个人搅做一团,在地下打了个转身,绝倒把花荣穿的一件簇新西湖色熟罗长衫,滚的都是灰尘,胸前挂的一个茉莉花球儿也跌散了。绝倒花荣大怒,正欲发作,立起身来一瞧,猛吃一惊。只见那人雄纠纠,黑凛凛,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不是别个,正是那杀人不翻眼的黑旋风李铁牛李逵。吴用一见,喜不自胜,我亦喜不自胜执着李逵的手,忙问:“几时到此的?听说你在沂水县里吃官司,如何会出来?敢是宋大哥保你出来的么?”
李逵道:“我回到本乡时,在路上遇着一伙客人,与我十分要好。见我说回到沂水县去,他们也说要到沂水县去经商,同借在客店里,一切照料,很是周到。当夜一个黑矮客人说:‘客店里沉闷的很,打几方牌九消消闲。’我听得赌钱,高兴的了不得。他们就拿出牌来,教我做庄。起初几场都是吃进的,倒赢下许多银子,那知后来记记配,记记配,把赢进的钱,尽数输掉还不够,连身边所带四百多两银子,一齐输了个光,还欠下他们一百多两银子呢。当时不曾觉着,出去小解,店主人与那黑矮客人讲拆分头,被我躲在门背后听了个明白:什么对筋牌,什么滚铅骰子,方晓得这厮们诈骗我的钱,并不是公道赌法。我一时性起,推进门,起手一拳,把黑矮汉子打死了。叵耐他们把鸟门闭上,一时逃走不脱,吃这厮们拿住了,解到县里受苦。盼望个人来救,足足望了三个月,方遇着朱仝、裴宣到县里,与知县一阵争论,把我救了出来。”吴用道:“朱全与你有杀死小衙内之仇,如何倒肯来救你。”李逵道:“他知我奉着将令行事,并不是有心作对,早已不恨了。我出了牢监,即到济州赈捐局见宋大哥,宋大哥给了我一百两银子,教我到江州来投奔军师,寻个事业做做,因此特特赶来的。”
吴用向花荣道:“花兄,像李大哥这样一个人,一块天真,不识些儿诈伪,世路崎岖,人情叵测,他都不晓,只道天下人都似自己一般的直,一般的真,这种人到新世界上来,怎么会不吃亏?李大哥,我劝你不必寻什么事做,因现在世界,配你做的事,尚不曾有呢。此言也,誉铁牛欤?贬铁牛欤?哀铁牛欤?人必曰:哀铁牛。然而吾知作者实以自哀,而无暇为铁牛哀也。吾与士谔友十年矣,见其踔厉风发,才气过人,然潦倒天涯,漂零蓬断,北海乏孔融之赏鉴,汉庭无狗监之游扬,是诚何故?曰:惟戆直故。士谔有<自题小影>云:“连年奔走敝精神,琴剑漂零剩此身。阅尽炎凉深自悔,问君何苦入红尘?”吾是以知其自哀也你既到这里,玩上几天罢,不必寻事业做了。花兄,你也且慢进城去,李大哥难得到此的,陪着玩一天罢。”花荣应允,重行入内。又引李逵、花荣到主笔房与萧让相见了,再到排字房、印刷房逛了一会子。花荣摸出金表一瞧,道:“五点半了,我们出外晚饭去罢。这里开辟商埠后,李大哥不曾到过,今日到万家春去尝尝番菜风味好么?”李逵道:“饭莱有甚滋味!酒肉是铁牛喜欢吃的。”花荣道:“番菜就是外国酒菜的别名,肉也有,酒也有。”李逵道:“那么便好。”于是三人立起身来,花荣到主笔房邀同萧让一起去。萧让道:“各埠新闻,尚没有编齐,你们先请罢。”花荣只得同着吴用、李逵径投“万家春”来。
一时行到,步上楼,就有西崽引着到靠东小小一间洋房内。但见“但见”者,李逵但见也。读下“李逵暗想”句自明。此倒句法<左传><史记>多有之四壁粉白,微尘不染,中间摆列着一只不长不方的桌子,四围都是穿藤单靠背圆梗椅子。可煞作怪,那桌上兜着一块儿大白布,李逵暗想:“敢是死了什么人?方才上楼,见一排六七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大块白布,那领我们进来的人也是这样打扮。这些人很是清洁,一定是店里的亲戚前来吊丧的。倘说不是,为甚都成了服呢?桌儿为什么也成起服来?呸!误了!这乃是白布台围,他们扎差了地位,扎在上边的。”花荣道:“李大哥请坐罢。”李逵一想:“他们请我,我自然要上坐的。”见长桌的两头都只摆着一只椅子,就向朝外的那只椅上坐下。花荣道:“李大哥,这是主位,你请此间来坐。”李逵道:“偏我坐不得,花兄休恁地欺人!论年岁也是我长些呢。”吴用道:“横竖没有外人,胡乱坐坐就是了。”李逵道:“怎么不见拿酒和肉来?”花荣尚未回答,只见那个胸前挂白布的人,端进一只盘来,盘里放着三只玻璃杯子,杯内白雪雪、硬簇簇、高爽爽堆着不知什么东西,只见他把来按在各人面前。李逵想道:“这必是外国点心,我若不吃,必被他们笑我外行,休等他们开口。”说时迟,那时快,早一手抢了向口里只一送,绝倒狠命的咬嚼,休想动他半毫。吴用笑道:“此乃揩手的帕子,预备着围在胸前,防汤水滴到身上所用的。你现在吃下肚去,敢是肚子中污秽积得多了,欲把他去揩拭揩拭么?”花荣道:“李大哥不曾晓得规矩,军师休要打趣。”李逵把帕子吐出,已咬得不成个样子了。西崽收去,重换了块洁净的,放在杯中。李逵道:“怎么盅筷尚没有拿来?”花荣道:“番菜是不用筷子的。”
此时西崽见李逵闹了笑话,不敢前来询问,又见他坐在主位上,不敢不来询问。只得拿了笔砚,送到李逵前请点菜。李速被吴用打趣了,心下正在不快,遂把西崽出气道:“你这厮拿这鸟东西来做甚么?”西崽道:“请先生点菜。”李逵道:“没有你娘的鸟!你这鸟店里有甚东西?酒肉只顾卖来,少顷一发算钱给你,偏欺老爷不识字,拿这鸟笔来。”西崽听了不解。吴用道:“你不懂,我给你代点了罢。”吴用晓得他喜欢吃肉的,给他连点了四五样都是肉、牛排、羊排、猪排、牛尾汤等。吴用、花荣各拣自己喜食的东西点了几样。吴用点的是薰鱼、酱鸽、虾仁汤、介辣鸡;花荣点的是鲍鱼、蛤蜊汤、禾花雀、羊排。西崽接了点菜单,去一会儿,拿了刀叉来按下。李逵道:“这鸟东西什么用的?”吴用道:“此乃代作筷子用的。”李逵道:“不怕割碎嘴么?”花荣道:“休要怪李大哥,蔡九知府总算乖的了,第一次吃番菜,见了刀又,尚吓的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吴用道:“为什么吓?”花荣道:“当时暗杀风潮正在盛旺之时,梁中书遇刺,幸中的不是要害处,不致有性命之忧。而各处大吏,都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蔡九知府一见刀叉,只道是刺他的,就吓得个半死。”
正说着,西崽上来问:“吃什么酒?”花荣道:“开两瓶皮酒来。”于是开了酒,送上一道菜。李逵见是盆儿内只薄薄一片肉儿,发话道:“你这厮!敢是欺侮老爷没钱,不肯多卖给我?”花荣道:“还有多着呢,你尽吃是了。”吴用道:“这牛排儿味儿很是可口,较你我往日所吃之牛肉高起多倍呢。”李逵听说好吃,便也不用刀儿又儿,用手拿起全块儿向嘴里只一送,叫声:“阿呀!”身子直跳起来,吐出不迭。奇文奇事原来这牛排儿刚从百沸的滚油里拿出,夏季天气,热性儿轻易不肯减去,李逵又不用刀叉划散,全块儿一齐送进,舌儿上的皮肉,又是便于全体中最嫩的地方,这一烫,烫得个黑如焦炭猛如水牛八字是李大哥极妙的徽号的李逵,在坐椅上直跳起来,口中大骂:“这厮欺侮老爷,不拿冷肉给老爷吃,却烫老爷!”吴用道:“拿刀子划开了,叉着慢慢地吃,就不会烫了。”李逵道:“谁耐烦?我撕着吃好么?”花荣道:“很好。”吴用嫌菜儿太热,与花荣重讲起盘卖报馆一事。吴用道:“此事全仗吾兄。”花荣道:“不消军师吩咐,花荣自当竭力。”李逵自吃完了,见吴用、花荣盆里都不曾动,吴用盆里是五香酱鸽,花荣盆里是禾花雀,便伸手过去捞过来道:“我替你们吃了。”妙人妙事,妙笔妙文吴用、花荣谈的正入港,不曾听见。李逵把一只鸽子、两只雀儿和骨头都嚼吃了,等到吴用、花荣想着吃时,早都剩了个空盆儿。花荣道:“李大哥一味的率真。”吴用道:“世界上人若都似他一般,你我做事还要容易呢。”说着,西崽已收了家伙去,揩抹刀叉,重又送上一道菜来。此时李逵道地了许多,虽不用刀叉,撕着慢慢地吃,不再闹笑话了。一时酒菜吃毕,喝过茄菲茶,西崽送上帐单。花荣抢着签了字道:“明日营里来收。”西崽应着,又敬上三支雪茄。李逵道:“此物作何用场?好似我身上一件东西,不过小了些。”花荣道:“老哥算了罢,休再闹笑话了。”
李逵道:“今日很不利市,被你们引到这丧事人家来。”花荣道:“那个引你到丧事人家来?”李逵道:“这里不是丧事人家么?你瞧白台围兜在桌上,白布幔挂在窗上,这几个搬送食物的人,胸前都挂着白布儿。”花荣早笑弯了腰。吴用道:“窗上的乃是软帘,桌上的乃是台单,胸前的乃是围身布。软帘是遮隔日光用的,台单与围身布是防备汗秽用的,因爱清洁,所以都用白色。”李逵道:“你为甚么不早说?”花荣道:“李大哥既嫌这里不利市时,我就引你到喜事人家去如何?”李逵点头。于是跟着花荣、吴用出了番菜馆,朝东转弯,走不多路,果到一家喜事人家。只见门外扎着彩牌楼,挂着灯,灯火点的彻亮,那彩牌楼下还有一块块红纸牌儿,上面不知写些什么字,里边鼓乐喧天,乐声一阵阵传入耳管里来,大约正在坐席喝酒。李逵本不曾吃饱,一听应了顷刻馋涎直流。有分教:以假为真,不妨老拳痛赠;因得虑失,可怜小子无知。要晓得李逵到了这家喜事人家,再闹出什么笑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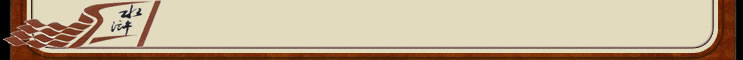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