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宋江考证(转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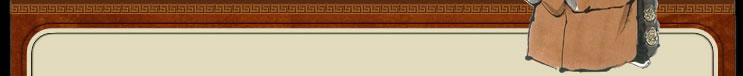 |
|
历史上宋江实有其人。近人余嘉锡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载《余嘉锡论学杂著》),收集考辨甚力,可以参看。<![endif]>
《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谓:“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张叔夜传》所叙最详:“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史书尽管没有明言宋江一伙就是在梁山聚啸,但“梁山泊在宋为盗薮”也是名著史册的。例如“梁山泊素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脚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不可胜计”。(《宋史·蒲宗孟传》)“梁山泊多盗,皆渔者窟穴。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同上《江几传》)“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刻名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同上《任谅传》)。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大浸的,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据《邵氏闻见后录》卷三0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五亦载同事。苏辙《栾城集》卷六有《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咏梁山泊》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氵于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注谓:“时议者欲干此泊,以种菽麦。”可知这个问题的确在“新”“旧”党之间引起过争议。从苏诗头两句描绘的情况看,梁山泊作为连接南北的水路枢纽,在当时经济上显然还有多重作用。所以成为“盗薮”,原因正在于此。一直到宋徽宗时,“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杨)戬……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号为‘西城所’。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可见仍然是利之所在,故成为“官”与“盗”争夺的焦点。
宋江的性格是在说话人的描述中逐渐丰富起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其“童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水浒传》成书过程中,又结合杂剧戏曲的刻划,对其人其事进行了全面“包装”,首先是对“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和“呼保义”作了解释,又用“宋十回”展开了他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清人王望如评论“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时有“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这令人想到作者所以为宋江取字“公明”,实在是给赵匡胤钦定的《官箴》“公生明,廉生威”一个讽刺。但也因此决定了他与晁盖、吴用、公孙胜等梁山泊上层人物的紧密关系,为他日后取代晁盖成为首领奠定了基础。
“招安”可谓宋代特色。语云:“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要想富,跟着行在卖酒醋。”历史上的宋江确曾招安,并且参与了征讨方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征方腊攻帮源洞)王涣统领马公直并稗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上述史书文集相左的记载,是1939年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其中叙及折在征方腊以后才擒拿宋江的,算是相反孤证。但是自美籍学者马泰来发现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忠愍集·捕盗偶成》诗,其中提到:“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谔。”反对“招安说”者也收回了看法。可知宋江一伙接受招安是当时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而后世说话人所据亦有本。考虑到《水浒传》的形成过程,几乎与主张“尊王攘夷”的理学传播同步进行,就不难理解为何百回本、百十七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都描写了宋江征讨方腊之前,先写他参与征辽战事。电视剧删除了这一节,则宋江之全力经营,就惟有“招安征腊”一事了。
金圣叹评点天下“才子书”,以《水浒》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并列,尤其赞赏《史记》之胆识:“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序一》)被金圣叹“腰斩”(或鲁迅所言“断尾巴蜻蜓”)之由。
应该说,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讨好。《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
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播映,宋江又成了议论的中心,一时使人想起了七五年的那场“评《水浒》,批宋江”———最近一家南方报纸用将近一版的篇幅批评小说《水浒》,犹有过之。李雪健没有参加剧组的播出宣传活动,不知是否因为受不了身边听得的种种议论和批评。显然在表现宋江英雄聚义与朝廷招安的两难处境中,他对角色的把握也陷入了两难。这就牵涉到宋江是否是“农民起义领袖”的问题。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宋江身份的历史材料。余嘉锡据南宋末年龚开的赞词“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而《宋史》记载“保义郎”为五十二阶武职中的第四十九阶,揣测“宋江以此为号,盖言其武勇可为使臣。”“江起于平民,以流俗所习知之卑秩自名。”他考证当初随宋江“横行河朔”的三十六人中,也没有可以称为农民者。这涉及到对宋代社会的认识问题。日本史学界占上风的看法,是把“宋代社会看作已克服了封建性的社会”(中华书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册425页),黄仁宇的看法,则以为“王安石变法”已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三联书店《中国大历史》)。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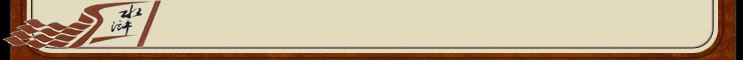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