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序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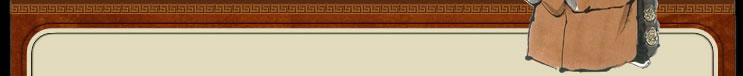 |
|
我從不寫書。究其原因,是怕寫不好,落個貽笑大方,不是耍兒。如今要寫,大半爲消磨時光,不敢更有他想。
2003年,我由一介小豪紳,淪落到露宿街頭,內心是惶恐的。2004年,相士說,這個凶年,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聽了,真乃不寒而慄。老實說,我是個迷信的人,事無巨細,都必問吉凶而後行。相士這一說,真把我嚇壞了。於是我閉門不出,躲在屋裏看地板,看樓頂。略有些瘋言瘋語,都吐在紙上了。
再說,我除卻迷信,還有狂人本性。如今獨處斗室,身邊又無人叨擾,樂得異想天開了。我想,既然要吐真言,索性吐個痛快,將往日束之高閣的想法,付諸實踐。從前想到的,但沒有做的,統統付諸實踐。管他呢,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字,天馬行空,爲所欲爲。
我這樣做了。
多年來,我在人世沈浮,見識了國民劣根性。親眼目睹的,都是急功近利的人,物欲膨脹的人,貪得無厭的人。確切地說,那不是人,是狼,是一群不知羞恥的傢夥!我日夜在想,知書達理,守望相助,莫非只是個美麗傳說?我不太敢肯定。但我有些不安了,我要將我所見到的人和事,付諸筆端,寫進《濁世圖》裏。用我僅存的良知,講述我的惶恐不安。
我平常愛讀書,尤愛讀小說。但我的眼福實在不好,看到的不是流水帳,就是人云亦云的庸俗之作。看那一篇篇口頭文——請允許我這麽說,不是白話文——我驚呆了。你看,那一部部小說,裏面的用語與口頭語毫無二致,一成不變的照搬過來了,實在平淡無味,通篇混帳!我在想,口頭文先生的筆墨,必然是佳妙的。然而寫出這等粗劣之作,莫不是藐視我等讀者諸君,視我等只有小學生水平?若然如此,這實在令人汗顔。
曾幾何時,主張新文學運動的先輩們,何曾料到文學已退化成一句說話?就象喝白開水一般,人人都能喝下去,一個咕嚕嚕,便入了喉。然而論及滋味,實在是不敢恭維的。這究竟是誰的錯?是先生們的錯?還是時代的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急功近利了,我們退化成黃鼠狼了,我們瞎了雙眼,聾了耳朵,分辯不出好壞了。悲哀啊!我們還追求文學嗎?或者,僅僅是說話就足夠了?把口頭語照搬過來,就足夠了?我不得其解。我只知道,小說不是政客演說,不是附在機箱裏的說明文,不必追求一目了然。如果能意味深長些,則儘量意味深長。能精練些,明快些,文縐縐些,總是好的。
現在,有人提起古文學、明清小說,便蹙眉不已。論其心思,只怕是將‘舊’等同於‘朽’了。我只想說,所謂‘舊’,不過區別於‘新’而言。而所謂的‘新’,不過是那些留洋歸來的青頭小子,翻臉不認人,造祖宗的反罷了。論其手段,不見得比前人高明。而其所用的言語,多半不洋不土,現在讀起來,還感覺酸溜溜的。罷了,這都罷了,新文學運動,不過是剪了文學辮子,換了文學長袍,原本無傷大體。而傷筋動骨者,卻是那個整風運動。自此文學色變,面目全非了。其實,整風運動是一項頂好的運動,貼近生活,切中時弊。在當時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文學作爲救國工具,淺顯易懂,是大有必要的。然而時過境遷,今日該變化變化了。不必唯淺白是好。只要有閒情逸致,寫寫八股文何妨?寫寫駢體文何妨?不必視作洪水猛獸,也不必視爲老古董。平心而論,著書也罷,讀書也罷,統統如品飲料,如果純喝白開水,不沾些香茗美酒,終歸是不健康的。
初時,我爲寫作題材搜腸刮肚。我想,如果用傳統語系,來寫現代題材,多半會招人非議,說我食古不化了。我有些惶恐。後來,我想到了一條快捷方式,大喜。何喜之有?我欲借《水滸傳》之軀殼,承載我的創作主張。這一點,讓我沾沾自喜了幾下。畢竟,能和小說鼻祖拉上關係,那是我莫大的榮幸。爲此我通宵達旦地寫。直至寫了幾章,才發覺大事不妙,事情不似原想的簡單。於是開始犯愁。犯甚麽愁?一是鼻祖過於高大,我怕高攀不上,反掉下來,落個粉身碎骨;二是意識到自己的拙笨,怕狗續貂尾,挨人笑柄了。這樣惴惴不安,過了好幾天。直至許久以後,我才豁然開竅:狂妄終須付出代價。於是心下釋然。
《水滸傳》的成功與否,自不消筆者多言的。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壯。千百年來,關乎《水滸傳》之紛爭,有人褒,有人貶,意見不一。小弟一介鹵人,胸無半點墨水,原不夠格趁此熱鬧。叵耐生性好動,誤打誤撞趕上這趟混水。到醒悟時,已然悔不可及了。我原想,《水滸傳》之僞說太多了,於是忿忿不平,一心要爲古人翻案,以正史之姿態,爲人物打假伸冤。直至寫到最後,我才發現,打假的那個人,竟變成造假的人。這實在令人沮喪。而我也只好認命了。畢竟能力所限,學識與文采,都遠不及他人,於是認命罷了。或許文學本身,多少都帶有虛構性。而我所做的,已將原來的五十步,走出了一百步。雖然尚未抵達終點,但我已經知足了。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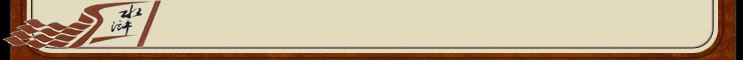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