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水浒传》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倾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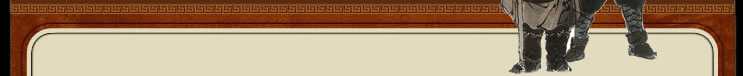 |
|
周腊生
一 内在美与外在美呈对立状态
总的看来,《水浒传》与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不同。它不热衷于塑造既具外在美又具内在美的女性形象。在多数女性人物身上,作者似乎在有意造成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对立与分离。这种对立与分离有两种形式。
其一、外貌美的大都因其内在之丑而成了反面角色。
她们有的失于“淫”。例如阎婆惜和潘巧云。前者“花容袅娜,玉质娉婷”,犹如“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仙子下尘寰”(21回,指通行版百回本《水浒传》,下同);后者是 “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的“二八佳人”(44回);貌都够美的。可作者不是要通过外貌之俏来激起读者的美感,而是把美貌当作淫荡的物质基础,并带着理学家“万恶淫为首”的观念,极力渲染她们“偷汉子”的丑行,以及她们为了达到长期“偷”下去的目的,因淫致恶:一个借端敲诈,一个倒打一耙。于是,引起了一般读者的厌恶乃至愤恨,似乎不杀不足以究其辜。
有的罪不在“淫”而在“泼”。第32回写清风寨刘高之妻“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鬓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闭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好词用了一堆,是要读者喜欢这角色么?不!作者先通过花荣的嘴对她进行了否定:“打紧的这婆娘不贤,只要调拨她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33回)。然后又以她仗势欺人、忘恩负义、差点陷宋江于死地,并挑起一场大战等品行之恶来彻底地否定了她。不仅书中的好汉们要剥她皮,读者也恨得牙痒痒的,终于被燕顺一刀砍成两段。
“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色艺双绝”的白秀英(5l回)则是既“淫”且 “刁”。“淫”用虚写——“他和知县来往得好”;“刁”是明叙:她仗着县令的势,一再羞辱血性汉子雷横,甚至打骂他的老母。结果惹得雷都头火起,一枷“劈开了脑盖”(同上)。按作者之意,这是罪有应得。 至于“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的潘金莲(24回),那更是淫荡与歹毒兼而有之的典型。作者一笔带过她当使女时敢于拒绝大户主人的纠缠这一内在的积极面,也毫不同情她在婚姻问题上的苦恼,却重笔强调她“为头的爱偷汉子”(同上),连那段具体描写她美貌的韵文中,也处处含有贬语。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每句都暗示着“淫”,美貌还怎给人美感?似乎不仅人物的外貌可以一目了然,连她日后的行为也可以从脸上看出,足见作对美貌妇女警惕之深。
因美貌而好淫(或刁、泼)最后遭报应被杀,是其女性反面形象的铸造模式。
其二,正面形象则多半外貌丑陋。
梁山泊只有3个女英雄,着墨多一点的孙二姐和顾大娘便都是丑陋的。
孙二娘给人的印象最深,她有怎样的尊容呢?第27回写道:“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外貌实在丑得可怕,但这不要紧。作者马上以赞赏的笔调尽量赋予她以内在美:有气力,有主见,有血气,讲义气,身手不凡,敢作敢为,为朋友两肋插刀……于是她那粗蠢的身躯里便凸现出一种粗犷雄壮、豪爽慷慨的风韵神采。外貌不美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整个形象是可爱的,甚至连她开黑店、杀人吃肉的罪恶行径也似乎不值得计较了。
再看对顾大嫂的描写:“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49回),而且杀耕牛,开赌场,包藏泼皮闲汉。这一切又被她仗义救人、两次深入虎穴,还具有成功地指挥一大群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与大伯子)以营救解氏弟兄的大将风度所掩盖。
形象较模糊的扈三娘,生得漂亮一些,这一则因她是降将,二则好衬托王英的好色,又另当别论。可见作者在塑造女英雄时,不大愿意赋予她们以美貌,好象一沾上美色便有损英雄气慨似的。
《水浒传》中这种将内在美与外在美对立起来的倾向,表明作者有“女色祸水”的思想。第24回回前诗云:“酒色端能误国邦,由来美色陷忠良。纣因妲己宗祧绝,吴为西施社稷亡。”又说明作者的“女色祸水”思想受历史上“女色祸水”思想的影响。从作品一再以大致相同的情节写已婚妇女热衷于“偷汉子”这种现象看,似乎作者通过社会上大量的桃色事件,已强烈地感受到市民妇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冲击,以及她们对爱情,对以相爱悦为基础的夫妻生活的向往。所谓“水性从来似女流,背夫常与外人偷”(24回),大概正是这种感受的反映,可惜作者并不能正确理解这一点。作者虽然敢于肯定造封建政治、封建秩序的反,大胆地歌颂反叛,却未曾意识到还应进一步造封建伦理道德与婚姻制度的反。作者不承认妇女追求美满婚姻的合理性,并将其一概贬之为肉欲,如第25回云:“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甚至认为女性外貌美与“淫”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二 褒阳刚而贬明柔
从另一角度通观《水浒传》中的女性,除了被鲁达救过的金翠莲、被武松救了的蜈蚣岭下张太公之女以及荆门镇下被假宋江所抢的刘太公之女等三四个极次要的角色,是以弱者面貌出现外,其余都程度不同、方式各异地体现了某种强者气质。这里有义军女头目孙二娘、 顾大嫂、扈三娘,有深得最高统治者眷顾的李师师及其鸨母,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理想配偶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卢俊义之妻贾氏,四柳庄狄太公之女,有“开言欺陆贾 、出口胜隋何”的女帮闲王婆,更有强蛮无理、仗势欺人的刘高之妻与唱妓白秀英,还有为虎作伥的李鬼之妻与蒋门神之妾。尽管她们的身份、性格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可鄙可憎,但有一点却相同,即都不是那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胆小怕事、毫无主见、无所追求的“软货”。至少她们都外向,都伶牙利齿。连遵奉公守法的林冲之妻及其使女银儿也曾竭力在高衙内的魔爪下挣扎,林妻终于不屈而死;潘巧云的丫环迎儿也不是省油的灯,曾大胆帮女主人勾引第三者穿针引线;何九叔的女人其精明世故竟令颇为机警的丈夫叹服……
作者这样写这些女性,字里行间透着不屈不挠的阳则之气,恰恰有力地证明了作者审美意识的基调——对阳刚之美的偏好。如果说,在女性反面形象上流露了阳刚之气是无意的,那么在女性正面人物身上体现的阳刚之美则正是作者要努力展示给读者的。
前面已经说过,作者对女性反面形都曾慷慨地赐予了美貌,最后又有意地用她们的丑行一一掩盖掉了。这被掩盖的正是与阳刚美相对的阴柔之美。似乎在作者看来,那些体现阴柔之美的漂亮外表、风花雪月、男欢女爱不应放在视野之内。其实,作者这种近乎禁欲主义的思想正是塑造全书人物形象的指导思想之一。这和有意无意给大多数女性着上一层阳刚色彩是一致的。
在男性形象中,宋江、李逵、武松、鲁达等均“不以女色为念”,因而被当作顶天立地的刚烈好汉。而王矮虎王英也是义军头领,造反甚早,也曾出手不凡,只因他两次当着众人要寻配偶,作者便以好色之徒目之,在男性身上如此,在女性身上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貌美的扈三娘之所以不失为英雄,主要不是因武勇过人,而是她作为待嫁闺女不仅未曾在男女之情上有任何表示,还在阵上暗骂过有不轨之心的王英:“这厮无礼!”(48回)再说孙二娘,她开黑店,杀无辜并残忍地做人肉馒头,比之潘金莲同别人合谋杀死一个武大,其罪不知大多少倍。只因这种杀人与色情无关,加之她好打抱不平,敢与官府为敌,所以作者把她当作英雄歌颂,还为她立下3条根本就有名无实的“戒律”来加以开脱。对潘金莲则不然,一涉男女之事便得否定,并在“淫”字上大作文章,将她做使女时的某些可贵之处也轻轻带过。真可谓但求阳刚不及其余。
由于作者褒阳刚而贬阴柔的审美倾向跟作品的造反主题正好合拍,所以作者在有意显示一这种倾向时,便着重于表现政治上的反抗,并将其置于贫富对立的尖锐矛盾之中。凡是触犯了封建王法的人,作者都予以同情,让他们得到救助,而从这些仗义救人的斗争中肯定抗争,肯定敢作敢为、疾恶如仇,肯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这是一种更为强烈的阳刚之美。
正因为作者偏于政治上的反抗,所以就无视某些妇女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亦带阳刚之气的追求与抗争,甚至对此加以否定,这就是矛盾。作者无法摆脱这个矛盾,于是,他(他们)所着意肯定的女性身上的阳刚之气都严重地男性化了,而女性身上那些真正属于女性的成份,作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掏出封建道德的尺子来加以规范。
《水浒传》偏爱阳刚之美的倾向,还重重地打有时代的烙印。《水浒》故事发生的年代与成书的年代,都是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的时代,大动荡、大变化是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在到处都是火与血的社会氛围中,最打动人心的自然不是和风细雨,不是风平浪静,不是良辰美景,不是卿卿我我,而是争取生存的斗争,是拯民于水火的勇力、胆量与智谋。这就无怪乎作者有意无意地在女性人物身上都平添了阳刚之气。
三 重“理”而轻“情”
《水浒传》在刻画女性形象时,特别是涉及男女关系时,还明显地表现了重“理”轻 “情”的倾向。 纵阅全书,就人物的年龄而言,女性远没有男性那么复杂。有名有姓的男性人物中,自十五六岁(如郓哥)至六七十岁(如王进)的几乎都有。而女性则不然,有名有姓的基本上都是少妇。其中有的明确交代了年龄,如金翠莲十八九岁(3回);阎婆惜18岁(21回);潘金莲22岁(24回);卢俊义之妻贾氏25岁(61回)等。多数则是暗示。如扈三娘刚出场就介绍已许配祝彪,“早晚要娶”——大概十七八岁;潘巧云曾自言比裴如海小两岁,而裴在石秀眼中是“一个年纪小的和尚”,参之其夫杨雄才29岁,那么她可能二十四五;白秀英虽早就跟知县有来往,毕竟尚未正式嫁人,显然只在二十上下;刘知寨的恭人象“嫦娥”,如“织女”,年纪一定很轻;孙二娘、顾大嫂都是上着绿衫下穿红裙,亦在少艾之期……
约而言之,《水浒传》中绝大部分女性的年龄均在十七八至三十左右之间,或已婚或当婚,亦即恰值少壮盛年。这正是感情奔放之期,不可避免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追求幸福的爱情与美满的婚姻,而且大多数已婚,不必象少女那样羞涩与矜持,可以较为大胆地有所表示。但是,作者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作过肯定性的描写,不给她们以丝毫表露内心情感的权利。
在女性正面人物身上,不仅带有严重的男性化倾向,而且作者还把她们一个个写得少年老成,从不涉及对爱情、婚姻的态度,也不提及她们婚前婚后的心理活动。这方面最突出是扈三娘。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待嫁的闺女,突然祸起,由于祝家庄跟梁山泊的冲突,全家老小被李逵砍光了,未婚夫也被杀,自己还当了俘虏。这是多么大的人生灾难啊!可是作者笔下的这个少女不仅对此无动于衷,而且糊里糊涂地当了宋太公的义女。对她来说,这其实是投靠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更有甚者,事平之后,当宋江要她嫁给她并无好感的王矮虎时,“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5l回)这哪里还有个人感情的位置?且不说家破人亡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这婚姻大事决于片言,一丈青竟象服从战斗命令似的,毫无异议地听从了宋江出于政治目的的安排,正是“情”对“理”的屈从。这“理”有激于义气的成份,更多的却是封建伦理——“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宋太公是义父,宋江是义兄,有父兄之命,又有众头领作媒,作者以为这太名正言顺了。其实作者只注意了婚姻上必须从“理”,却忘记了一丈青成婚时,她所有的亲人都尸骨未寒。
在女性反面人物身上,作对她们的否定恰恰主要是从“情”字着手。这“情”是“风情月意”(24回)、“雨意云情”(45回)的“情”,简直可以跟“淫”字划等号。潘金莲走向堕落之前,企图摆脱大户作为复手段而强加的配偶,另找一个般配的丈夫,这不能不说是正当的感情要求。而作者把这也视作非“理”进行贬斥。潘巧云守过1年多寡,心灵上带有伤痕,而由其父作主再嫁的又是一个心粗气豪不善温存的汉子,感情生活上显然存在着缺憾。作者并不体察这个少妇的苦衷,只牢牢地把握着对女性的种种道德要求,于是对她们的感情转移一味大加挞伐,甚至十分欣赏地细写杨雄对她的残忍杀戳:“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这妇人的七件事分开了。”(46回),后来,金圣叹在论及这件惨案的导演者石秀时,曾公允地指出他是个“残刻狠毒的恶物”(金评本《水浒传》第45回总批)。
在阎婆惜身上更是如此。宋江只把她当作外宅,而且对她并无感情,连得知她另有新欢也不以为意,显见只是偶或需要的玩物。那么,她希望跟对她有些感情的张文远过正常夫 妻生活,便完全是合理的追求。然而作者显然不这样看。当她跟宋江发生正面冲突时,作者口口声声骂她“婆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仍然是封建社会片面要求妇女贞洁的 “理”在作怪。
最典的莫过于第73回所写的四柳庄狄太公之女。她并未出嫁,而以装神弄鬼的方式跟情人王小二背地里做夫妻。这其中必有缘故。应该说这正是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行为,跟《西厢记》所讴歌的崔张之恋颇为相似,乃是以“情”反“理”。作者却跟王实甫相反,把这当作大逆不道,借李逵的口,骂狄小姐是“肮脏婆娘”,又借李逵的板斧,将小两口剁得稀烂。狄太公痛哭自己的女儿,作者不仅让李逵大骂:“打脊老牛!女儿偷了汉子,兀目要留他!”还站出来直接议论道:“痴翁犹自伤情切,独立西风哭未休”。这恰恰是以“理”灭 “情”。 《水传》写到女性时的重“理”轻“情”,还表现在这些少妇都无子嗣上。作者似乎在有意避免通过子女构成的或强化了的夫妻之爱,以及另一种重要的“情”——母爱,以便不陷入“儿女情长”之中。
考察《水浒传》描写女性时对“情”、“理”的依违,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它对女性形象的审美要求的落后性、封建性。
《水浒传》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指出某些方面的局限与不足,并不致损害它的伟大。虽然它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倾向显得比较落后,但它塑造的某些女性形象至今仍能给广大读以强烈的印象。
(此文曾带到在绍兴召开的全国《水浒》研讨会上交流,后发表于内刊《十堰党校通讯》1988年第4期。)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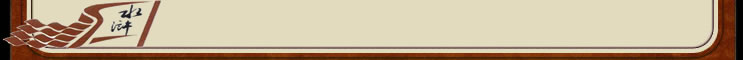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