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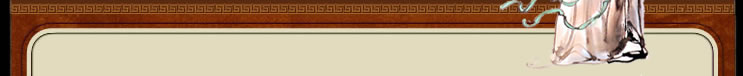 |
|
此是柴进失陷本传也。然篇首朱仝欲杀李逵一段,读者悉误认为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与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热铛,趁作煎饼,顺风吹花,用力至便者也。
吾尝言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如此一段文字,瞒过世人不为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处道破,当于处处思过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写作继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亲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既已无儿无女,乃其妻又是继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决裂可胜道哉!继室则年尚少,年尚少而智略不足以御强侮,一也。继室则来未久,来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压众心,二也。继室则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继嗣未立,内有帷箔可忧,三也,四也。然则柴大官人即使早知祸患,而欲敛足不往,亦不可得也。
嗟乎!吾观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殷直阁又倚仗姐夫高廉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岂不甚哉!夫高俅势要,则岂独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仅其一也。若高俅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当莫不各有殷直阁其人;而每一高廉,岂仅仅于一殷直阁而已乎?如殷直阁者,又其一也。
若高廉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又将百殷直阁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呜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当知之。夫知之而能痛与戢之,亦可以不至于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纵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为高俅也。
此书极写宋江权诈,可谓处处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绝者,如此篇铁牛不肯为髯陪话处,写宋江登时捏撮一片好话,逐句断续,逐句转变,风云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庵,即何难为江拟作一段联贯通畅之语,而必故为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乃至敢于欺纯是赤子之李逵,为稗史之《梼杌》也。
写宋江入伙后,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劝晁盖:“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如祝家庄、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恶,能以权术软禁晁盖,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何也?盖晁盖去,则功归晁盖;晁盖不去,则功归宋江,一也。晁盖去,则宋江为副,众人悉听晁盖之令;晁盖不去,则宋江为帅,众人悉听宋江之令,二也。夫则出其位至尊,入则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余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软禁晁盖,而作者深著其穷凶极恶,为稗史之《梼杌》也。
劫寨乃兵家一试之事也。用兵而至于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儿女投掷之戏耳;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者,盖为欲破高廉,斯不得不远取公孙;远取公孙,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杨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学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进失陷,然至柴进既陷而又必盛张高廉之神师者,非为难于搭救柴进,正以便于收转公孙。所谓墨酣笔疾,其文便连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亏公孙救柴进,亏柴进归公孙也。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前曰:“终日看习天书。”
此又曰:“用心记了咒语。”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明乎前之看习是诈,而今之记咒又诈也。前曰:“可与天机星同观。”此忽曰:“军师放心,我自有法。”岂有终日两人看习,而今吴用尽忘者?明乎前之未尝同观,而今之并非独记也。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