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二十五 荒岗古庙义士歼仇 小镇秘宅书生探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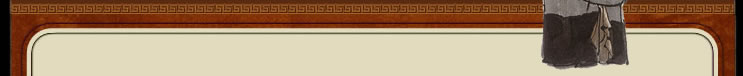 |
|
施耐庵离了宿迁井头街,径直北上够奔梁山故垒。一路上免不了逢店寄宿,遇庙躲雨,晓行夜住,餐风宿露。在路不则一日,早走入山东境内。
这一日,他正在埋头趱行,蓦地,一派屋角撞入眼帘,左近一座荆棘丛生的乱岗之上,孤零零兀立着一间屋宇,瞧那之势,仿佛是一座神庙。
走近一看,只见那神庙早已椽朽墙塌,廊庑毁败;山门前蔓草丛生,石碑倾倒,只剩那油漆斑驳的匾额还端端正正悬在檐下,上面依稀可以辨认出七个泥金大字:“敕建泗洲大圣庙”。
施耐庵也顾不得细看,一把推开早已腐朽的庙门,在神殿前放下伞囊,顺手挪过那吱呀作响的香案,掩上大门,抵好插栓,回身坐了下来。
此时,尽管神殿上四壁透风,比起在旷野之上,端的暖和了许多。施耐庵舒了口气,摊开行囊,从里面找出栽绒范阳笠和青布夹斗篷,穿戴妥贴,然后寻着了昨夜在新安县瓦窑镇那家客店里存下的半壶酒,倚在墙壁上,一边倾听着庙门外那呼啸的风声,一边细斟慢饮起来。
这些日子里,他只顾赶路,许多情由来不及细想,此刻忙里偷闲,稍事喘息,又有那半壶冷酒聊作助兴之物,心头便立时蓦起许多事来。回想起数年前,那铁尔帖木儿为了一阕曲子,竟自惨杀了一门老幼,令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依赖着堂叔供养方才勉强成人,后来堂叔又在悲愤中含恨死去,一介书生家徒四壁,顿时犹如飘蓬断梗,无依无傍。眼见得元室江山日坏、酷吏横行,哪里还有心仕进?正自彷徨踌躇之际,亏得在钱塘、祝塘教馆之机,得以与隐居草莽的大侠刘伯温、鲁渊、游谦等人相识,促膝把酒,讲论国是,方始悟出一番“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挟愤而起除苛政不为盗贼”的道理。后来在杭州行刺铁尔帖木儿不遂,运河侧畔巧遇红巾军飞凤旗首宋碧云,乌桥镇白莲教总坛得识那叱咤风云的绿林魁首刘福通,亲眼目睹了义军将士的声威豪气。然后又于极奇巧的机遇中领受了那一桩绝世大秘,辗转东台、淮安、牛栏岗、临河集、洋河集,北上去寻找那幅记着一百零八位梁山后代的白绢,先后又结识了许多绿林枭雄、江湖豪俊,诸如张士诚、徐寿辉等人,无一不是当今陈涉、吴广、张角、黄巢。开初从那宋碧云手中接过大秘,还只道寻找梁山英雄血裔只不过一场虚话,谁知数月之间,连逢奇境异遇,居然找着了十余个当年梁山英雄的后代,一个个豪气干云、生龙活虎,王擎云、索元亨的勇猛刚直,欧普祥、邹普胜的质朴英勇,童氏兄弟的深沉豪爽,徐文俊、时不济的诙谐机智,还有那金克木、潘一雄、阮氏三杰等人无不是耿耿刚肠、凛凛正气,令人倾倒。尤其是两个女子,一善一恶、一侠一奸,同是英雄后代,行事却是迥然不同!一想起秦梅娘临死之时的那番凄楚情景,想起那四首藏着苦衷的小令,施耐庵胸中便隐隐作痛。此刻,他脑际又浮现出宋碧云临离开汪家营时,将那“流萤箭囊”上的奥秘向自己一人倾诉的情景,他心底不由得涌起一阵悸动。唉,自己一介寒儒,这位奇女子寄望如此之深,期待如此之切,实在叫人铭感五内。
这些时他之所以拚命趱赶,也正是为了不辜负宋碧云一片苦心。“梁山之阴,蓼儿洼之北”,藏着她祖辈的遗愿,也藏着抗元大业的将来,既然已经知道了秘密所在,理当早日将它找到!
想着想着,忽地一股狂风从倾圮的墙隙中卷进,施耐庵不觉心中焦躁:种种迹象表明,不仅绿林群豪在觊觎这桩“秘宝”,便是铁尔帖木儿、董太鹏之流也在处心积虑企图攫取这绝世的“大秘”。世间无有不透风的墙,如耽搁得太久,保不定已有大盗奸臣获悉风声,一旦被他们捷足先登,窃走了那幅记着一百单八名梁山后代的白绢,后果岂堪设想?这股怪风早不起晚不起,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刮了个无休无歇,实在招人心烦!
施耐庵正想得入神,忽地,庙门外竟响起了说话的声音,仿佛有五六个人来到这泗洲大圣庙前,正在低声争执。施耐庵不觉心中一凛:这荒郊旷野天寒地冷何来人声?五六个人来到庙前,自己竟然丝毫也未察觉,看来这批人不是风高杀人的强徒,便是身负绝技的绿林义士。此刻,相隔只是两扇腐朽的庙门,倘若这伙人一头撞入,值此孤身独处、人地生疏之际,万一有个闪失,那将如何是好?
庙门外人声愈响愈嘈杂,只听一个中气充沛的人声言道:“不要争了!便是拿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也休想从俺手上换走这两颗奸贼的头颅!各位,动手罢!”
这时,只听得“唔唔”之声叠起,仿佛有人被堵了嘴,兀自挣扎着想说话。
一个沙哑嗓门的人说道:“大哥,这两个贼夫妇的性命值得几何?可俺们饮马川大寨的军需粮秣出落在他们身上,万一杀了他们,几百名弟兄喝西北风去?”
又一个细声细气的人道:“着啊!再说,这两个肥羊乃是济南城鲁王驾下的宠幸,杀了他们,银子飞了事小,引来元人铁骑兵,俺饮马川可难以抵挡!”
那声音浓重的人又道:“怕他个鸟!那鲁王知道了,叫他来找俺赛玄坛晁景龙便是。连个鸟王爷都怕成这般模样,亏你们还天天叫喊什么灭元扶宋!”
话音中“铮”地一响,仿佛是兵刃掣出。
只听那“大哥”又道:“俺六人在饮马川八拜订交,有劳众位尊俺为大哥。今日若还念兄弟义气,就与俺一起宰了这两个狗男女,祭奠先祖先父在天英灵!”
余下四五人齐声道:“谨听大哥吩咐!”
话音未落,只听得庙门外兵刃出鞘之声“铮铮”连响。接着便是“嗨”、“嗖嗖嗖”、“卟哧卟哧”、“唔唉”、“卟通卟通”一连串奇怪声音响起,显然是群刃交下,那几个人所说的“狗男女”已被杀倒在地。
躲在殿堂上的施耐庵屏息凝神,浑身毛发直竖。他倾耳聆听庙门外的动静,不觉一怔,眨眼功夫,庙门外早已声息全无,那几个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去,正如来时一样,迅如飙风。
施耐庵兀自不放心,蹑手蹑脚地踅到庙门后,眯着眼从破缝中往外一看:门口哪有一个人影?!
他壮了胆子,拽开顶着门栓的香案,打开那吱嘎作响的庙门,一只脚恰才跨出门槛,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差一点叫出声来。
只见山门前的草地上,躺着两具无头尸首。瞧那服饰形容,分明是常在官府衙门里行走的男女清客,胸腹四肢被兵刃戳得大洞大眼,仿佛入秋的黄蜂窝,身上的锦缎衣裳也剁得筋筋片片,地上汪着两滩血水,染得草棵石砌都红了。
施耐庵不忍看这惨象,他一步跨回神殿,忙忙地收拾酒壶伞囊,举足便走出了破庙。
忽然,山门前草丛中一阵“簌簌”骤响,旋即青锋闪烁,衰草败垣之间陡地涌出一伙人来,一色地扎着黑色包头。身着黑色箭衣,执着明晃晃的刀剑,怒目立眉地围了拢来。
施耐庵望着这伙气势汹汹的人众,不觉心下一愣:怪道适才杀了人后无声无息,原来他们是隐在暗处,乘自己不备,偷袭了上来。
想到此处,他一只手悄悄握住湛卢剑的剑柄,口中却客客气气地吟道:“萍踪浪迹,书剑飘零,人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不期齐鲁逢诸位豪俊,古庙歼仇,血殷衰草;书生无缘,就此远行。诸位,晚生别过了!”说着,拔步便要奔下荒岗。
人丛中一个大汉笑道:“兀那穷酸,倒好兴致,到这杀人场掉书袋来了!”说毕,朝其余的人叫道:“列位,你们说把这小白脸如何发落才解气!”
人丛中纷纷嚷道:“拖来吊在树上,一顿藤条,将他那肚里的酸气抖落出来,让咱们瞧瞧是个啥模样?”
一众豪客嘻嘻哈哈、龇牙咧嘴地逼了上来。施耐庵一见,向一旁退避两步,大声说道:“晚生路过宝地,因避风沙偶入破庙,与众位好汉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苦苦相逼?”
那领头的壮汉呵呵一笑,说道:“大胆穷酸,俺主人如今杀死在当地,还敢胡说什么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施耐庵听毕一愣:什么,被杀死在庙前的竟然是这伙人的主人?他掉头一看:只见这群人中已有两个壮汉正毕恭毕敬地脱下衣裳,包殓被杀在地上的两具尸体。看来这被杀之人果然是这伙豪客一条路道上的人物。那么,适才在庙内亲闻的杀人惨剧到底是何情节?难道,杀人的另是一伙人么?
想到此,他抱拳唱了个肥喏,说道:“众位好汉,贵府主人不幸遭难,晚生这厢致哀了!不过,小生一介书生,决不轻易杀人。冤有头,债有主,众位休要寻错了对头。”
那领头的壮汉笑道:“哈哈,你说的不假,谅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模样,休讲杀死俺主人、主母,便是毫毛也动不得他们一根。杀人者,俺们早已瞧见,那是另有其人。”
施耐庵记起在庙门后听到那豪气横溢的好汉声音,不觉忘了眼前险境,忙忙地问道:“哦,那是何人?”
那壮汉说道:“俺们躲在破墙后看得清清楚楚,杀人者便是钦马川山上落草的那伙强寇,领头的便是那恶名昭著的‘赛玄坛’晁景龙!”
施耐庵听了,心中不觉暗暗好笑。这伙豪客也实在古怪,亲眼见主人被杀,躲在暗处不出来救助;既然知道了仇人姓名去处,却又不去报仇雪耻,直至好戏唱完了才出台,偏偏来寻自己的晦气,煞是叫人纳罕。此刻,他也顾不得再去抒发感慨,急急地插剑入鞘,结扎好衣襟鞋带,望了望躺在庙门前的两具包着黑衣的尸首,长叹一声,认明方向,大步奔上了道路。不多时,早已走出了新安县境,进了郯城地界,眼前这一大市镇,便是苏鲁皖三省交界的通衢市廛——有名的张秋古镇。
施耐庵信步走进街市,只见铺面繁华、人物齐楚,街面的青条石铺得十分整齐,到底又是一省风物,亚赛苏北那些城镇。
施耐庵也顾不得观赏人情风俗,一边走一边沿街张望,打算寻一爿僻静整洁的店堂打尖用饭。
走着走着,眼见来到一家酒楼门前,只见门面倒也鲜明,店堂里也还清静,正欲跨步入内,猛听得身后一个声音叫道:
“年兄,这酒店乃是虎狼渊薮,住不得,住不得!”
这一声呼唤尽管声音低微,但却来得突兀,把施耐庵吓了一跳。
他回身一看,身后哪里有人?施耐庵心下正自纳罕,忽然耳衅又响起那个低沉而震人耳鼓的声音:“年兄,请朝这边看来!俺说的是真话!”
施耐庵寻声望去,只见街前人来人往,但一个个躬腰曲背,匆匆奔走,显然都在为生计奔忙,没有人驻步讲话。
他眼角一扫,蓦地瞧见离酒店五尺开外摆着一爿卜卦摊子,一块布招上写着“吴铁口天下神相”七个大字,卦桌上摆着龟蓍签筒,一个年约四十余岁的相面先生仰面靠在椅子背上,只见他手捺长须,双目向天,面前并无问卦相面的客人,他那嘴唇却嚅嚅而动,实在是古怪之极。
施耐庵心中一动:“瞧这相面先生的模样,敢莫是他在暗中招呼?他那嘴唇微微嚅动,五尺开外,声音竟是如此清晰有力,敢情又是一位大有来历的角色!
想到此处,施耐庵连忙奔下酒楼门前的阶砌,走到那卦摊之前,朝那相面先生深深打了一躬,喜眉笑眼地说道:“仁兄在上,晚生这厢有礼了。”
那相面先生听了,兀自仰头看天,不发一言。
施耐庵又道:“仁兄生意兴隆,晚生谨此致贺了!”
那先生坐起身子,冷冷地说道:“年兄少礼,俺与你素不相识,若要相面,先拿卦银来!”
施耐庵心想:既然来了,索性将礼性尽到堂,倘若此人并非与自己招呼,说完便走。想毕,他又说道:“晚生由南省来此,人地两生,前途未卜,先生若肯眷顾,一切都盼多多给予帮衬!”
那先生忽地站起,一脸怒容,不耐烦地说道:“俺相面素来是有缘随缘,无缘走开。谁耐烦你这浪荡书生胡搅蛮缠,扰了俺半日生意。”说毕,他七手八脚收了算卦摊子,双脚在地下蹭了几蹭,气咻咻地拂袖而去。
施耐庵讨了个没趣,半晌做不得声。忽然,他双目瞧见地下的灰沙上留下了几圈脚印,细看竟是“随我来”三个大字。施耐庵心中一动:哦,既然他划地留言,其中必然大有深意!
想到此,他也顾不得腹中饥饿,一双脚不由自主地跟着那算卦先生走了过去。
那相面先生却也蹊跷,在前边大袖甩甩地走着。施耐庵走得快,他便走得快,施耐庵走得慢,他便踱起了方步,两人之间始终离着十步之遥。穿街走巷,不觉便走了几条街面。
转过一道高大的青瓦府第,再过了一道石拱桥面,那相面先生大步踅进了一条树木葱郁的冷巷。
施耐庵疾走几步,也跟进了巷子,一进巷口,他不觉惊得呆了。
这条巷子却原来是条死胡同,那先生早已失了踪影。施耐庵心中诧怪:难道他能飞上天去?正自四处搜寻,猛听得左侧“吱扭”一响,一座门楼的两扇红漆大门忽然开了一条缝,从里边探出一颗梳着丫髻的小僮儿的头来。轻声唤道:
“相公莫非是寻一位卜卦先生?”
施耐庵点点头。
那僮儿也点了点头,伸出手招了招,倏地消失在门缝里。
施耐庵见状,连忙掸了掸袍襟,推开那扇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座极深邃的住宅,房屋虽不宏丽,但却廊庑雅致、曲径通幽,一抹古藤沿墙屈曲,看来屋主人是一位情趣高雅的林下隐士。
施耐庵略略走得几步,忽听得耳畔响起一阵娇滴滴的叫唤之声:“客到,沏茶!”那声音听来煞是悦耳。
施耐庵满院睃巡,哪里见一个人影?
正在惊讶,只听得娇声又起:“有请主人出堂!”
施耐庵循声望去,不觉失笑:只见正厅檐下一个金丝鸟笼迎风摆动,里面一只翠羽红头的鹦鹉正在喋喋学语。
那鸟儿叫声未歇,一阵窸窸窣窣的衣裙声响过,只见花厅上迎出两个少年女子来。
走在前边的一个约摸十八九岁年纪,穿一袭素白纻罗短袄,婷婷立在这阶砌上,仿佛一株傲雪的白梅花。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子,身着红装,看起来年纪略小两岁。两上女子,一红一白,一高一矮,神态各异,期期然立在花厅前的阶砌上,把个施耐庵看得呆了。只听两个女子齐声问道:“何方游子,竟来此处充不速之客?”
施耐庵唱了个喏,说道:“晚生岂敢?是你家主人引我来的。”
那白衣女子浅浅一笑,说道:“俺家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施耐庵道:“是一位年约四十余岁,沿街相面的先生。”
那红衣女子哈哈大笑,说道:“好个耍贫嘴的书呆子!此处是俺姐妹俩的家。俺姐妹俩便是此处的主人,哪里来的什么相面先生?敢莫是你这书呆子闯错了门径?”
施耐庵听毕一怔,心想:前此分明看见那相面先生踅进这巷子,事后又是这家门内一个僮儿招手请自己进来,为何无端搅出这两个女子?
他看了那两个少女一眼,心想:适才那应门僮儿只怕是碰巧认错了人,自己糊里糊涂便误闯了门径,平白无故遭了一番奚落,也是晦气照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既然找不见那相面先生,还是一走了事。
想毕,他陪个笑脸,说道:“两位大姐休怪,只怨晚生地头不熟,误打误撞了闺阁人家,晚生告罪了!”说毕,打了一拱,转身便欲走出。
忽听那白衣女子“嗤”地一笑道:“相公既然登门造访,如此匆匆而去,只怕有些失礼罢!”
施耐庵听毕驻步,回身说道:“大姐逐客又留客,为了何故?”
那红衣女子笑道:“哈哈,你家姑娘天生的古怪脾气,想进门的俺偏赶他走,想走的俺偏偏要留他!谅你这书呆子也不晓得:一进俺这院子,便是皇帝老儿,胆敢违拗姑娘们的意思,一样儿地挨顿打叫着娘出走!”
施耐庵听了,心中叫道:好一个风风火火的野妮子!管他子午卯酉,既留之,则安之,看这两个女子有何花样耍出来。他索性垂手立在当院,说道:“既有此话,晚生听凭处置。”
那红衣女子斜眸瞟了一眼施耐庵,抿嘴一笑,蹬蹬几步走下阶砌,上下打量了施耐庵一阵,忽然问道:“相公,你也会武艺么?”
施耐庵没想到她竟问了这样一句,茫然答道:“大姐问这个作甚?”
红衣女子答非所问,指着施耐庵腰间的湛卢剑又问:“那么,你带着这柄剑是作什么的?”
施耐庵答道:“哦,大姐原来问的是这把剑。想晚生一介寒儒,四方游学,哪里会什么武艺,这把剑不过是挂在腰间做个摆设,沿途吓吓偷儿,壮壮胆子罢了。”
那红衣女子怒目横眉,喝道:“休要罗唣,快拔出剑来,与你家姑娘比试比试!”
施耐庵曼声吟道:“大姐儿乍变红线侠娘,小姑娘忽成怒目金刚,弱书生无拳无勇,怎敢来比武走场?大姐休要取笑了!”
红衣女子不再答话,双手掣开绣鸾刀,抖两圈刀花,直朝施耐庵裹将上来。
施耐庵急忙退开两步,右手掣出湛卢宝剑,朝着那红衣女子抱拳说道:“大姐慢来!既然要晚生献丑,那便要立个章程,否则如何判别输赢?”
红衣女子收刀问道:“又来罗唣,你说说,还要订个什么章程?”
施耐庵道:“既然大姐如此看重晚生,晚生只好奉陪。比武之时,晚生先让你三招,倘若三个回合之内不败,大姐便可接晚生剑式,若是一合之内大姐失风,晚生便要告辞了!”
这“大姐”“晚生”的一串罗嗦,加之三合对一合分明是露骨地小觑于人,早把那红衣女子气得满脸涨红,只听她怒喝一声:“好一个欺人太甚的书呆子,俺姑娘依你,出剑罢!”
喝声未歇,那两把绣鸾刀虎虎生风,着地卷了上来。
施耐庵哪敢怠慢,曲臂擎剑,护住要害。
好一个红衣少女,那一对绣鸾刀使得精妙无比,施耐庵一面凝神架格闪避,一面暗暗叫好。只听得三声铿锵激耳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过,眼前的三团翻卷腾挪的红光倏地消失,那红衣女子早已收刀跳出战圈,擎刀兀立。
她凝视着施耐庵的身形,眼底隐隐露出诧异钦佩的神色,拱手说道:“饶你躲得快!三合已过,你出剑罢!”
施耐庵接过这三合,心中早已吓得“怦怦”直跳,暗暗叫声惭愧,心道:好险,若不是当年叔父教了这“快活剑法”,今日只怕脱不了一刀之难!若是再斗上两三个回合,一定要露底出丑!想到此,他擎剑当胸,朝红衣女子客气地说道:“大姐承让,晚生适才不过说笑,那一剑不必接了。”
红衣女子闻言大怒,俏脸气得通红,仿佛被人迎面唾了一口唾沫,不觉叫道:“兀那书呆子,休要卖乖逞能,再不出剑,俺便要乱刀剁过来了!”
施耐庵见这女子如此要强,只好说一声:“如此,晚生得罪了!”说毕,手腕一松,竖在当胸的湛卢剑倏地平伸,他略抖一抖剑圈,大步直进,剑尖如奔雷闪电直点红衣女子的眉心。
红衣女子一见,不觉嗤嗤一笑:“这书呆子出剑竟然如此拙劣!只道他这一剑是什么精妙绝技,哪知竟是如此平易普通!这时,一直站任阶砌上冷眼旁观的那位白衣白裙女子早已看出胜败,不觉脱口叫道:“相公下手休要忒毒!”就在那红衣女子左手刀贴上剑刃,右手刀堪堪便要劈到施耐庵身躯之际,她猛地觉着左手那股“嗖嗖”寒风堪堪袭到颈脖,森森霜刃已触及肌肤之际,那柄剑忽地收势上挑,削下了她发际那枝赤金打就的红梅花。红衣女子只吓得心房“怦怦”乱跳,一踊身跃出了圈子。
此刻,金铁交鸣之声甫歇,雅洁的庭院一时显得十分幽静。红衣女子惊魂甫定,脸色羞惭,手执双刀呆呆兀立。
施耐庵收势拂袍,还剑入鞘,意态闲适地站在当院。稍顷,只见那白衣女子裙衫飘飘,从容不迫地从大厅前的阶砌上缓步走下,来到适才二人激斗之处,俯身拾起被湛卢剑削下的那朵赤金红梅,端详一阵,对红衣女子说道:“妹妹,还不快去谢过这位大哥不杀之恩。”
红衣女子又羞又气,忸怩不语。
施耐庵说道:“大姐既然交过手,晚生侥幸,此时若无他故,晚生便要告辞了!”
红衣女子悻悻说道,“恕不远送!”
施耐庵闻言,撩袍举步,便要离去。
忽听一声呼唤又在身后响起:“大哥且慢,还有小女子一关未过哩!”
施耐庵心下一惊,回身望去,只见那白衣女子早已走到跟前,手里不知何时捧着两个髹漆檀木小盒,裙带飘飘,神态优雅,一双晶莹的眸子里显出不容置辩的神情。
施耐庵呐呐问道:“怎么,大姐也要与晚生交手么?”
白衣女子微微笑道:“非也!小女子这里有围棋一副,愿与相公纹枰切磋一局,倘若胜了小女子,相公悉听尊便!”
施耐庵心想:这两个女子煞是古怪,说好了比武赢了悉听尊便,此刻又翻出花样,要手战斗棋,看来今日麻烦不少。
他略略沉思片刻,觉着这白衣女子口气谦和,仪态娴雅,却之未免不恭;加之这纹枰斗棋,乃是往日在黉门中操习已久的技艺,多日不下,此刻竟然觉着技痒难耐。此时有闲庭幽院,不妨下它一局,也可驱除多日的劳碌。想到此处,他欣然答道:“大姐既然有此雅兴,晚生理应奉陪。”白衣女子赞声“好爽快”,引着施耐庵走到右侧回廊之下。日见凭栏放着一张红木小桌。两侧摆着红绒包裹的锦墩,小桌上早铺好了一副赭色贡缎的棋盘,那横横竖竖的三百六十一个棋目竟是用金色丝线绣成。缎子棋盘四角压着缕刻着狮头的田黄石镇纸。望着这雕栏静院,面对这别具风格的棋桌,施耐庵益发兴致勃然,对白衣女子道声“请”,正襟坐上了锦墩。
一时间,那径尺见方的棋盘上金戈铁马、合纵连横,隐隐有风雷之声。约摸两个时辰,棋枰上的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处处燃起战火,无一区不陷入“金鼓”杀伐之境。
白衣女子正自凝思默想,忽听得身后有人叫道:“哎呀不好,这局棋输得冤枉!”
白衣女子回头一看,只见红衣女子满脸沮丧之中,指着棋枰又道:“姐姐,你输了!”
白衣女子俯身一看,只见东角上那一线黑棋早已陷入重围,只要再补上一目,这局棋果然胜负已判。
此刻,只见施耐庵捂着肚腹,一手拈着棋子,正瞅着那白棋链上的唯一缺口,作势欲下。
白衣女子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觉长叹一声,褰裙而起,双手一推棋枰,轻轻地说了声:“相公好棋艺,小女子输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