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三十四 莽县令乔设鳌山会 奇书生姑射春灯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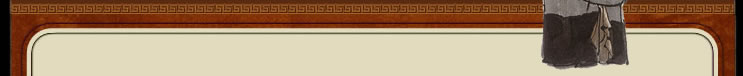 |
|
融和初报,乍瑞霭霁云,故都春早。翠华竞飞,玉辔争驰,齐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也,九门剔透,千衢玲珑,袞冕与红袖轻摇。缥缈广寒传韶乐,依稀瑶池饮蟠桃。一轮冰盘大,数点星辰小,游人归来处,洞天未晓。
亘古以来,也不知始于何日何时,哪朝哪代,兴起了一桩元宵夜赏月观灯的习俗。每年到了这一日,无论是帝子皇孙,抑或是草野编氓,都要放下手中的生计,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涌上街头巷尾,仰瞻天上娟娟寒月,聆听人间处处笙歌,把那一段去旧迎新的未了之情尽兴付与彻夜之游。这一首《绛都春·元宵》,便是咏的那元宵夜天上人间、金吾不禁的情境。不过,月有阴晴圆缺,世有清明混沌。这首《绛都春》把元夜之乐写得淋漓酣畅,透露出那一番海晏河清、娱乐升平的世态。至于兵连祸接、乱世浇漓,却又是大大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谓予不信,有一首著名词人王磐的《古调蟾宫·元宵》为证:
听元宵,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家。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哪里有闹红尘香车宝马?只不过送黄昏古木寒鸦。诗也消乏,酒也消乏,冷落了春风,憔悴了梅花。
话说元朝至正十六年(公元一三五六年)正月十五,又正值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青州府属下的长清县城里,午后响过一阵噼噼啪啪的炮仗,早有几户官宦殷实人家稀稀落落挂出几盏灯来,把个寥落冷清的街市巷陌照耀得斑驳陆离,影影绰绰。这些年,水旱饥馑、兵戈不息,休道那些逃兵荒、躲徭役的下户灾民,便是寻常工商士农人家,每日朝朝都愁着那开门七件事,天色向晚,一声狗吠便心儿颤颤地关门不迭,却哪里有心思作彻夜冶游?早把那庆赏元宵之事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此刻,冷冷清清的长清县城里,倒还有个热闹去处。只见县衙前青蔑搭着灯篷,篷檐下扎着一溜彩绸,笸箩儿般大小的花团下垂着流苏;灯篷居中那座金晃晃的鳌山周围,悬着三十六盏玲珑剔透的走马灯儿,薄薄的轻纱上一式画着花鸟、山水、人物,题着诗词歌赋。笙箫檀板声中,几名扮着杂剧脸谱的伶人在灯影下做张做致地扭捏得一回,立时便走出一个吏员模样的人来。只见他紧一紧腰间丝绦,对围在灯篷下面的众人敞声叫道:
“各位听者:本县太爷为与阖城军民人等共庆元夕,特地耗银百两,堆了这座鳌山,制下这一组灯谜,在场各位父老,有幸猜得下的,每一道谜语赏黍米一升、制钱十文!”
说着,这吏员一只手揭开身边满盛着黄灿灿黍米的笸箩,另一只手在怀内掏得一掏,立时将沉甸甸的两贯制钱“啪”地掼到案头上。
这一掼不打紧,倒恰似半空中倾下盆冰雪水,把一众围观百姓的兴致浇得彻骨冷,本来就稀稀拉拉的几个人,立时大眼瞪小眼,有几个胆儿小的,猫腰耸脊已自悄悄地溜出了人群。内中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厮走的飞快,嘴里头兀自嘟囔道:“快走快走,瘟疫神撒出花狐盅,没的却惹得满身腥!”
他正自一头走一头叽咕,猛古丁墙根影里踅出个人来,那小厮收脚不迭,立时撞了个满怀,不由地脱口骂道:“瞎眼撞尸,也不拣个日子,偏偏今日碰了俺一个趔趄!算俺晦气!”
那人却不见气,笑嘻嘻唱个喏道:“得罪得罪!晚生有一事动问。”
小厮见此人和颜悦色,心中气先自消了一半,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立着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学士子,青巾芒鞋,书剑伞囊,扎缚得十分齐整。一张清癯的脸庞早已晒得如铁,眉目间却处处透着谦和儒雅;青衿袍襟上沾满泥迹黄尘,顾盼间依然一派倜傥风流。这小厮久处小邑,哪曾见过这等齐楚的人物,不由心中一喜,忙道:“该死该死,小的口拙冲撞了尊客,没的打嘴现世。不知尊客动问何事?”
那游学士子道:“晚生偶经此地,适才见那县衙之前,灯篷之下,悬灯猜谜、射覆投彩,正是元夕盛事,不知众位为何一见那吏员拿出奖物,竟尔哄然走散?”
小厮一听,脸上扮了个齮虎,连连摆手道:“休提,休提!俺县的这位太爷乃是普天下一等一的铁爪篱,皮筲箕,这些年把个长清县境的地皮也刮走了一层!素常日只要抛出一文钱,满县百姓便须千倍万倍地与他纳贡,今日在那鳌山之下搬出黍米制钱,八成又是聚敛盘剥的花招,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那士子听毕,微微一笑,整一整头上青巾,勒一勒腰间丝绦,便要走向灯篷。小厮一见,连忙一把攥住衣袖,问道:
“尊客敢莫想去猜谜投彩?”
士子点点头道:“正是。”
小厮连忙劝道:“使不得,使不得!尊客休要去赶这一趟浑水!弄不好,轻则白送了你这衣服行囊,重则丢了性命!还是快些赶你的路要紧!”
那士子也不答话,拱一拱手,说了声“大哥放心”,撩衣直奔那闪烁着灯火的篾篷。
此时,灯篷前早只剩得五七个浮浪子弟,兀自口里嗑着瓜子,指点着灯谜儿叽叽呱呱地乱笑,却哪里有一个人敢上前猜谜射覆?那吏员心中焦躁,正待发话,猛然间人丛里起了一阵骚动,一团青影疾奔灯篷而来,霎时,荧荧的灯影之下早站出个儒雅秀士,只见他叉手兀立,从容问道:“请问尊驾,这些灯谜许得过路人射覆么?”
那吏员皱眉打量着面前这位不速之客,说道:“看你这位年兄,敢莫也想来博些彩头么?”
士子点点头,呵呵笑道:“正是,正是,晚生四海求师,八方游学,这两日盘缠告罄,行囊羞涩,可巧今日碰上尊驾在此设篷射覆,晚生不才,愿以胸中锦绣,换得几升黍粮、数串银钱,以解绝粮之厄!”
吏员瞠目扫了士子一眼,笑道:“年兄有此雅兴,委实令小邑今日灯会添了光彩!只要年兄猜中谜底,自然按规矩奉送黍米、制钱——”
那士子不待他说完,对在场众人说一声“众位乡邻,恕晚生僭越了”,拔步便要跨进灯篷。那吏员呵呵一笑,忽地一把拦住,又道:“年兄也忒性急,适才俺只将这猜谜射覆的规矩讲了一半,还有一半,你且听得明白:三十六道灯谜倘若一并猜中,这一箩黍米、满贯制钱自然归你所有。不过,若是有一道谜面猜得错了,须按所有彩头赔偿,那便是足足百两纹银!”
这番话尚未落音,早将在场的众人吓得伸出舌头半晌缩不回去。那士人却只当没听见,微微笑道:“有赏有罚,这也不足为奇!”说毕,从容闲适地解下肩头伞囊,交到那吏员手上,说一声:“这些物事,便是晚生今日猜谜的押头”!
此时,一见有人出头猜谜,那些走散的人又踅了回来,此外又添了些看热闹的百姓,灯篷下渐渐聚拢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众人屏息敛气、凝神注目,一面想见识这位游学士子的才气学识,一面又担心这外乡孤客堕入官府的彀中,一个个手心里都攥出冷汗来。只有那吏员依旧不动声色,拱一拱手,将这士子让进灯篷,然后吊着眉梢眯着两眼,嘴角挂着冷笑,注视着这冒冒失失、大大咧咧的秀才如何猜出谜语来。
只见那士子背翦双手,仿佛踏宫商踱律吕般地在灯篷里转悠起来,他忽而拨一拨这盏灯,又忽而戳一戳那盏灯,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喃喃自语:“好手艺好手艺!”半晌也不曾猜出一只谜底来。
围观的众人见他这模样,不由得悄悄议论起来:“瞧这秀才一身书卷气,兀的却是银样枪镴头!”“俺只道是个会念经的和尚,怎的变成没嘴的葫芦!”吏员已自按捺不住,正待发作,蓦地,那士子却转过身来,双眉高挑,两颚轻抖,大袖呼呼拂风扬起,嘴里迸出一阵大笑:“嘻嘻——呵哈哈哈!”
这一阵大笑委实起得突兀,仿佛平地卷来一股狂飙,直震得宿鸟惊飞,砌草抖索,把那吏员与一众围观的人们一齐惊呆了。
没待众人回过神来,只见那士子早已撩起青衿袍襟,几步奔到案头,袍袖晃处,早把那两贯制钱抓到了手里。
吏员厉声喝道:“兀那秀才,未曾猜出灯谜,取了俺太爷这赏饯,敢莫要放抢么?”
那士子兀自呵呵乱笑,一面将那两贯制钱抖得叮当响,一面指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灯谜说道:“嘻嘻,你家太爷忒也惫赖,大好一个元宵佳节,怎的胡诌出这些下三滥的馊词拙句充作灯谜?兀的不污了读书人口舌?”
吏员劈手夺过那两贯制钱,冷笑道:“哼哼,胸无点墨,休在此处充圣人!既然口出狂言,便将这些灯谜一并猜出,倘若漏了一个,立时将你拿到县衙之内打折了你那双腿!”
士子叹口气道:“既如此,那就休怪晚生出你家太爷的丑了!”说着,戟指朝那些灯谜划了一圈,说道:“这前面三十五道谜语,甚么‘一点一横长,一撇到汉阳’,‘有嘴不言声,有足不登程’,甚么‘四面不透风,十字在当中,若把田字猜,不通又不通’,便是三岁小儿都能猜到,晚生就不讲了。晚生只把这第三十六道谜语,也就是最难解之谜道出,也教你见识见识!”说毕,他疾步跨到最后一盏灯前,一把扯下那灯纱上的字条,只见那上面写道:
“目字加两点,不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猜。
射二字。”
士子将字条在众人面前晃了两晃,伸手在案头提笔蘸墨,飞龙走凤,立时在谜面下头写出两个字来。
众人聚拢一看,只见他写的是“贺”、“资”二字,满场上立时暴雷般喝起彩来!
吏员捧着那张字条,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猛听得灯篷深处暴雷般响起一阵怒喝:“哪里来的野秀才,搅扰了太爷的灯会,拿下了!”吼声未落,只见县衙的金钉朱漆大门“豁喇喇”开了,几个皂衣衙役虎狼般涌了出来,只见荧荧的灯烛之下,立着个锦衣貂帽的虬髯官儿,正自瞪着铜铃般两只怪眼,嘿嘿冷笑。守灯篷的吏员走上前来,先将那张字条递给虬髯大汉,又在他耳畔窃窃絮语一阵。那官儿忽地收住冷笑,拍案喝道:“兀那秀才,吃了熊心豹胆,竟敢来撩俺的虎须!本待打折你这双腿,念你肚内尚有几滴文墨,俺这里还有几道谜语,只要你再能猜得出,俺便放你一条生路!”说毕,嗽了嗽喉咙,敞声念出一道谜来:
“行人弓箭各在腰。——唐诗一句,射一字。”
那士子不假思索,脱口答道:“夷也。”
虬髯官儿点点头,又道:“蔺相如完璧归赵。——射二人名。”
士子应答如响:“保住。连城。”
那官儿续道:“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射一字。”
士子才思如泉,赓即答道:“佯哉!”
这一番驳诘较量,只在瞬息之间便判了胜负。那虬髯官儿直惊得眼都直了。
谁知那士子却不放过,跨上两步,对虬髯官儿说道:“君子之交:投桃报李。大人若有兴致,晚生也有一道谜语请教。”
虬髯官儿怒道:“俺不与你计较倒也罢了,你穷秀才也充起鸿儒来!有什么谜语便做出来听听,没的俺便输与你!”
士子道声“痛快”,轻挽丝绦,款踱方步,立时吟出一道谜来:
“客从东来,歌讴且行。不从门入,窬我墙垣,游戏中庭,嬉娱殿庭。击之啪啪,死者攘攘。碎彼皮囊,何惧我伤。——
射一物。”
这一番抑扬顿挫的轻吟曼语,竟把满场人等听得呆了,这伙人几曾听到过如此古怪的谜语,一时面面相觑,啧啧连声。那虬髯官儿更是皱眉蹙额、抓耳挠腮,把张脸都齐颈儿挣红了,却哪里答得出半个字来?
那游学士子望着这尴尬模样,叉手伫立,径自嘿嘿冷笑。笑了两声,只见他袍袖一卷,早又将那两贯制钱卷到手里,朝着那虬髯官儿吟道:“大人慷慨设谜,晚生侥幸发市,区区黍米制钱,舍与百姓度饥!”吟毕,转身对围观的众百姓叫道:“众位父老乡亲,这一箩黍米、两贯制钱,请拿回去度一个元宵佳节罢!”说毕,手臂一扬,将那两贯钱“唰啷啷”抛进人丛。有几个胆大的百姓奔了过来,“嗨”一声抬起那满满的一笸箩黍米,叫一声:“这都是俺们的血汗,索性分了罢!”
霎时间,灯篷里鸦飞鹊乱,众百姓饥馑之年也委实饿得慌了,立时蜂拥而上,拾钱的拾钱,装黍的装黍,不多时,笑呵呵地一哄儿走了个净尽。
那虬髯官儿设谜儿输了道行,一时吃瘪,大庭广众之下哪能食言,心里暗暗叫苦。一边眼睁睁看着众百姓分了制钱黍米,一边钦佩地注视着面前这游学士子,半晌不发一言。
稍顷,那吏员在耳畔轻声说道:“大人,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官府钱粮,你便罢休不成?”
一句话提醒了这官儿,他眨了眨双眼,喝道:“都是这野秀才弄鬼,还不与俺拿下了!”说毕,“铮”地一声拔出腰间长剑,便要寻那士子。
只见灯篷之下,空空如也,那游学士子适才分明站在众衙役圈中,眨眼间却失了踪影。虬髯官儿正自惊诧,只见那吏员双手从案头上捧起张纸头呈了上来。
虬髯官儿摊开一看,只见纸头上写着数行蝇头小楷,却是一首打油诗:
“大腹长喙,昼伏夜行,嗜血无厌,嘴脸狰狞。幺么小丑,名之曰‘蚊’,谨告谜底,休再横行!”
虬髯官儿一时忘形,连声赞道:“好谜底,好谜底!怪道俺猜它不出!”
那吏员却附耳说道:“大人,这穷秀才忒也可恶,他这道谜语,骂你是吸血虫哩!”
虬髯官儿不羞不恼,脸上抹起一阵赞许的神态,摆摆手道:“撤灯罢会,退堂,退堂!”
话犹未了,只听灯篷外陡地响起一声大叫:“慢来,慢来!”随着叫声,只见一道黑影凌空掠过,“豁喇喇”一声大响,县衙墙头倏地跃下一个人来。
只见他头挽太极冠,身着明黄道袍,袍带上斜插着一把尘帚,两撇浓眉斜挂,一双豹眼环睁,说什么超凡脱俗方外士,分明森罗殿内黑煞神。这游方道士满脸漾着怪笑,踅进灯篷,忽然跨上两步,一把攥住虬髯县令的手腕,瞠目喝道:
“阿腾铁木儿大人,你做的好事!”
虬髯县令闹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挣脱道士的手掌,一边说道:“道长究竟有何见教?”
游方道士嘿嘿冷笑道:“俺把你这不知死活的赃官!如今举国大乱,盗贼蜂起,江淮乱党已然遍及齐鲁,半月前刘福通、吴铁口余党逃窜济南,破了省城大狱,青、滕、济、兖等数十州县已然草木皆兵!这长清县与济南近在咫尺,你身为朝廷命官,不去修缮城池、缉拿乱党,却在此张灯结彩,寻欢作乐,你、你、你、你敢莫不想要这颗驴头了么?”
虬髯县令听了这番话,脸上漾起一丝难以觉察的冷笑,他望了望眼前这游方道士,暗暗忖道:区区一个云游道士,如何晓得这些军机大事?再说这些时县境内太平安宁、鸡犬不惊,哪里见什么盗贼踪迹?敢莫是这道士饿慌了,口出大言,想在此讹诈些钱财不成?想到此处,他问道:“多承见教,下官敢不闻命?不过,能否请仙翁昭示来历?”
道士听毕呵呵笑道:“区区七品县令,也想知道俺的来历?说出来怕不吓你一跳!俺,华山紫云洞坛下银镜先生,大元朝济宁路总管帐下记名副将公孙玄是也!只因半月前群寇大闹济南城,内中走了一名朝廷软犯,俺奉‘山东王’护廓大人与济宁路总管董大鹏之命,沿线缉拿归案!”
虬髯县令忙问:“不知这软犯又是何等样人!”
公孙玄道:“此人姓施名彦端,又号耐庵先生,乃是浙江钱塘县的一名潦倒书生!”
虬髯县令听了,不觉失笑:“俺听了半日,只道是走了一条铜头铁臂的混世魔王,没想却只是个书生!堂堂天朝,竟为了此等人物兴师动众,未免小题大作了罢!”
公孙玄听毕,不觉怒声斥道:“你这赃官知道个屁!休看这施耐庵只是一个秀才,这些年却出没于草野之中,奔走于江湖之上,妖言激众,四处煽惑,所到之处,便似播火的祝融,立时就撩拨出几只潜藏的猛虎,燃起反叛朝廷的烽烟!眼下此人又胸藏一宗绿林中的绝世大秘密,要去寻找当年梁山泊叛党余孽,倘若叫他唤出那一百零八名魔头的后代,齐集到叛贼麾下,不要说你这个小小县令的驴头保不住,便是大元朝的锦绣江山也危如累卵了!”
虬髯县令一听,心中猛地一动,蓦地又记起适才大闹灯会的那个游学士子,敢莫他便是施耐庵?想到此处,他嗫嗫嚅嚅便要将此事说出。赓即一想:天下如此大,秀才多如牛毛,偏偏这施耐庵便闯到了长清县?世上决无如此巧事!
虬髯县令正自疑疑惑惑,只见那公孙玄双眼骨碌碌在灯篷里扫视了一圈,忽然奔到案头,一把抓起那张写着谜底的纸头,仔细审视一阵,蓦地双眉陡竖,怪眼圆睁,立目喝道:
“县尊大人,这纸头从何而来?”
虬髯县令心下一凛,连忙支吾道:“这个,这个,乃是卑职门下一个清客写的谜底。”
公孙玄听毕,双手团成一团,将那字条揉在掌心,骂一声“咬文嚼字,一派胡言”,扬手便要掷到脚下。他一条手臂恰才抬起,猛觉得腕骨上一紧,紧接着一声嗄哑村人的喝叫在耳畔响起:“等一等!!”
这一声大叫仿佛暗夜中陡起一声霹雳,饶是这公孙玄胆儿大,亦自吓了一跳,他一扭腰脊挣脱束缚,跃开两步,说话间早掣出腰间尘帚,瞪目看去,不觉惊呆了:
只见灯篷内立着一条大汉,身躯奇长,形销骨立,一张长脸上抹两撇虾须吊眉,嵌一双泛青鱼眼;两颊深陷,双颧凸出,头戴一顶镶珠镔铁毡盔,身着一领海天青团花战袍。就在一抓一纵之间,公孙玄手里那张纸头不知如何早已到了他的手里。此时,只见他一边展读,一边眉目耸动,神情似嗔似喜,似惊似怒。
公孙玄认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元朝新任济宁路总管、声威赫赫的“三界无常”董大鹏!不觉收起尘帚,挥一挥袍袖,迎面唱了个大喏,说道:“俺只道遇了江湖魔头,不料却是董将爷。贫道这厢有礼了!”
董大鹏摆了摆手,径直走到那虬髯县令面前,嘿嘿冷笑两声,蓦地肩膊一耸,早抓住了虬髯县令的脊梁骨,厉声喝道:“好个瞎眼奴才,分明放走了朝廷钦犯,却在此拆白掉谎!”说着,一抖手中纸头,瞠目斥道:“这究竟是何人所写?”
虬髯县令见他那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先自吓了一跳,此时被他抓住脊梁骨,仿佛楔入了一只钢爪。他也不呻唤,想了想,慢慢说道:“卑职该死!这乃是一位过路的秀才所写,卑职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董大鹏怒道:“什么过路秀才!这施耐庵的字迹,点、横、撇、捺,哪一笔瞒得过俺这双眼去?煮熟的鸭子教你这赃官放了生!可惜了你爷娘给的你这双眼!”说毕,他那只瘦骨伶仃的长臂也不知哪来这般骇人的力道,将虬髯县令滴溜溜拎得转了几圈,只一送,便将他掷倒在阶砌旁。
在场众人听董大鹏这一说,一齐惊呆了,痴痴地立着,半晌回不过神来。在一旁早恼了的公孙玄,须眉倒立、怒声如雷,大踏步奔了过来,手腕一抖,早从一个衙役腰间拔过一把朴刀,喝一声:“赃官,放走了钦犯,俺拿你这颗驴头回去交差!”说毕,将那虬髯县令劈胸提起,兜头便剁。那官儿既不闪避,也不惊惧,只是嘻嘻乱笑。
董大鹏身躯一闪,早插到公孙玄面前,哑哑笑道:“银镜兄刀下留人!”
公孙玄收回刀势,不觉诧道:“董大人,朝廷早有明令:施耐庵乃名教罪人、衣冠败类,知情不举,杀无赦!这赃官私纵钦犯,罪不可逭,大人如何便要回护他?”
董大鹏也不答话,忽然仰头发出一阵哑哑怪笑,那身骷髅般的骨架也仿佛“轧轧”作响,那笑声犹如空山枭鸣,令人浑身起栗。笑毕,他以手加额,扬颔说道:“银镜兄差矣!这位县尊大人不仅无罪,而且是一个大大的功臣!试想,那施耐庵自离了济南,潜踪晦迹、昼伏夜行,既有江湖强贼庇护,又有丛山峻岭藏身,俺千里追踪,遍地搜索,把这青、滕、济、兖十余州县几乎篦子般篦了一遍,兀自不见他的行踪。亏得这位县太爷想出这设奖猜谜的玩艺,撩拨得这穷酸技痒,可可儿露了行藏!你道他这功劳大是不大?”
一番话说得那县令暗暗打了个冷战。那公孙玄却是茅塞顿开,不觉拊掌大笑道:“不错,不错!果然,果然!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赃官歪打正着,俺们正好拿人受赏!董大人,此时不捉那施耐庵,更待何时!”
董大鹏哑哑笑道:“银镜兄稍安勿躁,长清县以西,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区区一个施耐庵,已成瓮中之鳖,不怕他走上天去!”说毕,伸手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扬手掷到那虬髯县令面前,说一声:“足下功不可没,待俺拿了施耐庵,再与你请赏!”说毕,只见暗夜中呼喇喇涌出数十名蒙古长刀侍卫,拥着董大鹏、公孙玄溜缰上马,霎时便隐入了夜幕。
此刻,灯篷里只剩下那虬髯县令兀自怔怔地瘫在地上,半晌回不过神来。约摸一盏茶功夫,他缓缓站起,一番奇变委实出人意料,听了董大鹏那番话,兀自不敢相信,懵懵懂懂只道是在梦中。此刻,他望了望眼前,分明躺着那一张银钩铁划的谜底,而面前仿佛还留着那游学士子的气息,他默然良久,脸上神色变幻,不知是惊是悔、是忧是喜?
适才见了董大鹏那凶神模样,吏员衙役们怕惹了狐骚,一个个忙不迭躲了。此时一见无灾无难,大伙儿便又从树影墙角里走了出来,揉腰的揉腰、捶背的捶背,七嘴八舌地趋奉起来:“老爷金钩钓鱼,不想钓出件大功劳,可喜可贺!”“老爷神机妙算,哪里是斗灯谜,分明是引蛇出洞,可可儿便叫那施耐庵上了钩!”
虬髯县令捺着虬髯,仰着头颅,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摇头叹气,也不答理。
良久,忽然沉脸竖眉,挥挥手道:“休要啰唣,本老爷要安歇了!”说毕,揣上董大鹏留下的银子,拂袖走入了县衙。
众人讨了个没趣,只好怏怏散去。虬髯县令捂着怀中那锭纹银,心里仿佛揣着个鬼胎,施施然走入了县衙后庭,推开厢房槅子门,剔亮了昏昏蜡烛,正待唤醒县令夫人,好将这一腔心事诉与内人知道,谁知他一撩罗帐,不禁吓了一跳:
只见“县令夫人”并未娇卧锦衾,却似蜗牛般蜷缩在墙角,定睛一看,她双臂倒缚,嘴里堵着一团破布,只穿一身薄薄的寝衣,兀自冻得索索发抖。
虬髯县令正欲失声大叫,猛觉着肩头按上了一只手,接着响起一声舒徐从容的问话:“县尊大人,别来无恙?”
虬髯县令浑身一凛,掉头一看:面前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斗灯谜的游学士子,只见他长衫窄窄,大袖飘飘,依然一副闲适潇洒气度。
虬髯县令只道此人早已远走高飞,或是堕入董大鹏的罗网,哪里料道他又在眼前现身?事出仓卒,他只说了一句:“你、你、你真是那朝廷钦犯施、施耐庵?”只听那士子从容笑道:“正是晚生,今日幸会,真是天缘凑合哩!”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