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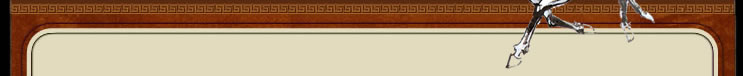 |
|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穿一领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著禅杖,轮起来打两个公人。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认得是鲁智深。林冲连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
话说!”智深听得,收住禅杖。两个公人呆了半晌,动弹不得。林冲道:“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分付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
鲁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断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得你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寻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他倒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两个!”林冲劝道:“既然师兄救了我,你休害他两个性命。”
鲁智深喝道:“你这两个撮鸟!洒家不看兄弟面时,把你这两个都剁做肉酱!且看兄弟面皮,饶你两个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喝道:“你们这两个撮鸟,快搀兄弟,都跟洒家来!”提了禅杖先走。两个公人那里敢回话,只叫“林教头救俺两个!”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著林冲,又替他驼注:手字旁它。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来。
行得三四里路程,见一座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来坐下,唤酒保买五七斤肉,打两角酒来吃,回些面来打饼。酒保一面整治,把酒来筛。两个公人道:
“不敢拜师父在那个寺里住持?”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著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
两个公人那里敢再开口。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还了酒钱,出离了村口。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两个公人听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坏了我们的勾当!转去时,怎回话!”且只得随顺他一处行路。
自此,途中被鲁智深要行便行,要歇更歇,那里敢扭他;好便骂,不好便打。两个公人不敢高声,只怕和尚发作。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著车子行著。两个公人怀著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随顺著行。鲁智深一路买酒买肉将息林冲。那两个公人也吃。遇著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两个公人打火做饭。谁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们被这和尚监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廨宇里新来了个僧人,唤做鲁智深,想来必是他。回去实说,俺要在野猪林结果他,被这和尚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下手不得。舍著还了他十两金子,著陆谦自去寻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干净。”董超道:“说得也是。”两个暗暗商量了不题。
话休絮繁。被智深监押不离,行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七十里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无僻静处了。鲁智深打听得实了,就松林里少歇。智深对林冲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了,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洒家已打听实了。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林冲道:“师兄回去,泰山处可说知。防护之恩,不死当以厚报!”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却待分手。鲁智深看著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二人答道:“小人头是父母皮肉包著些骨头。”智深轮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得树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与这树一般!”摆著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们自去罢。”两个公人道:“好个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树!”林冲道:“这个直得甚么;相国寺一株柳树,连根也拔将出来。”二人只把头来摇,方才得知是实。
三人当下离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三个人到里面来,林冲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才得自在。只见那店里有几处座头,二五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林冲与两个公人坐了半个时辰,酒保并不来问。林冲等得不耐烦,把桌子敲著,说道:“你这店主人好欺客,见我是个犯人,便不来睬著!我须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说道:“你这人原来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卖酒肉与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听了,对两个公人道:“我在东京教军时常常听得军中人传说柴大官人名字,却原来在这里。我们何不同去投奔他?”薛霸,董超,寻思道:“既然如此,有甚亏了我们处?”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问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庄在何处?我等正要寻他。”
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约过三二里路,大石桥边,转湾抹角,那个大庄院便是。”
林冲等谢了店主人出门,走了三二里,过得桥来,一条平坦大路,早望见绿柳阴中显出那座庄院。四下一周遭一条阔河,两岸边都是垂杨大树,树阴中一遭粉墙。转湾来到庄,前那条阔板桥上坐著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乘凉。三个人来到桥边,与庄客施礼罢,林冲说道:“相烦大哥报与大官人知道,京师有个犯人--迭配牢城,姓林的--求见。”庄客齐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时,有酒食钱财与你,今早出猎去了。”林冲道:“如此是我没福,不得相遇,我们去罢。”别了众庄客,和两个公人再回旧路,肚里好生愁闷。
行了半里多路,只见远远的从林子深处,一簇人马奔庄上来;中间捧著一位官人,骑一匹雪白卷毛马。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齿皓朱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胸绣花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环条注:
糸字旁条。;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带一张弓,插一壶箭;引领从人,都到庄上来。林冲看了寻思道:“敢是柴大官人么?...”又不敢问他,只肚里踌躇。只见那马上年少的官人纵马前来问道:“这位带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为因恶了高太尉,寻事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刺配此沧州。闻得前面酒店里说,这里有个招贤纳士好汉柴大官人;因此特来相投。不期缘浅,不得相遇。”那官人滚鞍下马,飞奔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连忙答礼。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庄上来,那庄客们看见,大开了庄门。柴进直请到厅前,两个叙礼罢。柴进说道:“小可久闻教头大名,不期今日来踏贱地,足称平生渴仰之愿!”林冲答道:“微贱林冲,闻大人名传播海宇,谁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来此,得识尊颜,宿生万幸!”柴进再三谦让,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薜霸,也一带坐下。跟柴进的伴当各自牵了马去院后歇息,不在话下。
柴进便唤庄客叫将酒来。不移时,只见数个庄客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著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柴进见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恁地轻意!唗,快将进去!先把果盒酒来,随即杀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谢道:“大官人,不必多赐,只此十分彀了。”柴进道:“休如此说,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庄客便如飞先棒出果盒酒来。柴进起身,一面手执三杯。林冲谢了柴进,饮酒罢。两个公人一同饮了。柴进道:“教头请里面少坐。”自家随即解了弓袋箭壶,就请两个公人一同饮酒。柴进当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两个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说些闲话,江湖上的勾当。不觉红日西沈,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进亲自举杯,把子三巡,坐下,叫道:“且将汤来吃!”
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报道:“教师来也。”柴进道:“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好。快抬一张桌来。”林冲起身看时,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著一顶头巾,挺著脯子,来到后堂。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那人全不睬著,也不还礼。林冲不敢抬头。柴进指著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林冲听了,看著洪教头便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亦不相让,走去上首便坐。柴进看了,又不喜欢。林冲只得肩下坐了。两个公人亦就坐了。
洪教头便问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礼管待配军?”柴进道:“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洪教头道:“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头’,来投庄上诱得些酒食钱米。大官人如何忒认真!”林冲听了,并不做声。柴进便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伴教头怪这柴进说“休小觑他”,便跳起身来,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柴进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师,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头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会,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来惹林冲使棒。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柴进道:“且把酒来吃著,待月上来也罢。”当下又吃过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来了,见厅堂里面如同白日。柴进起身道:“二位教头,较量一棒。”林冲自肚里寻思道:“这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师父;我若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须不好看。”柴进见林冲踌躇,便道:“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林武师休得要推辞。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柴进说这话,原来只怕林冲碍柴进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林冲见柴进说开就里,方才放心。
只见洪教头先起身道:“来,来,来!和你使一棒看!”一齐都哄出堂后空地上。
庄客拿一束杆棒来放在地下。洪教头先脱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条棒,使个旗鼓,喝道:“来,来,来!”柴进道:“林武师,请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话。
”就地也拿了一条棒起来,道:“师父,请教。”洪教头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
林冲拿著棒使出山东大擂打将入来。洪教头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来抢林冲。两个教头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见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叫一声“少歇。”柴进道:“教头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输了。”柴进道:“未见二位较量,怎便是输了?”林冲道:“小人只多这具枷,因此权当输了。”柴进道:“是小可一时失了计较。”大笑道:“这个容易。”便叫庄客取十两银来。当时将至。柴进对押解两个公人道:“小可大胆,相烦二位下顾,权把林教头枷开了。明日牢城营内,但有事务,都在小可身上。白银十两相送。”董超,薛霸,见了柴进人物轩昂,不敢违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两银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随即把林冲护身枷开了。柴进大喜道:“今番两位教师再试一棒。”
洪教头见他却才棒法怯了,肚里平欺他,便提起棒,却待要使。柴进叫道:“且住。”叫庄客取出一锭银来,重二十五两。无一时,至面前。柴进乃言:“二位教头比试,非比其他。这锭银子权为利物。若还赢的,便将此银子去。”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著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
“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己乱了,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著洪教头镰注:月字旁廉。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著扶了。洪教头羞惭满面,自投庄外去了。柴进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后堂饮酒,叫将利物来送还教师。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过,只得收了。
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数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两个公人催促要行,柴进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写两封书,分付林冲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即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又将银五两赍发两个公人,吃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吃了早饭,叫庄客挑了三个的行李。林冲依旧带上枷,辞了柴进便行。柴进送出庄门作别,分付道:“待几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来与教头。”林冲谢道:“如何报谢大官人!”两个公人相谢了。三人取路投沧州来。将及午牌时候,己到沧州城里。打发那挑行李的回去,迳到州衙里下了公文,当厅引林冲参见了州官。大尹当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营内来。两个公人自领了回文,相辞了回东京去,不在话下。
只说林冲送到牢城营内来。牢城营内收管林冲,发在单身房里听候点视。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来看觑他,对林冲说道:“此间管营,差拨,都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林冲道:“众兄长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钱,把多少与他?”众人道:“若要使得好时,管营把五两银子与他,差拨也得五两银子送他,十分好了。”林冲与众人正说之间,只见差拨过来问道:“那个是新来的配军?”林冲见问,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著林冲便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刺刺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那里敢抬头应答。众人见骂,各自散了。
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著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言轻微。”差拨看了,道:“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林冲道:“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差拨见了,看著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林冲笑道:“总赖照顾。”差拨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书礼,说道:“相烦老哥将这两封书下一下。”差拨道:“即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直一锭金子。我一面与你下书。少间管营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时,你便只说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来与你支吾,要瞒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谢指教。”差拨拿了银子并书,离了单身房,自去了。林冲叹口气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的苦处!”
原来差拨落了五两银子,只将五两银子并书来见管营,备说:“林冲是个好汉,柴大官人有书相荐在此呈上,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无十分大事。”管营道,“况是柴大官人有书,必须要看顾他。”便教唤林冲来见。
且说林冲正在单身房里闷坐,只见牌头叫道:“管营在厅上叫唤新到罪人林冲来点名。”林冲听得唤,来到厅前。管营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驮起来!”林冲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头道:“这人见今有病,乞赐怜恕。”管营道:“果是这人症候在身,权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拨道:“见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时满了,可教林冲去替换他。”就厅上押了帖文,差拨领了林冲,单身房里取了行李,来天王堂交替。
差拨道:“林教头,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时,这是营中第一样省气力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从早直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拨他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谢得照顾。”又取三二两银子与差拨,道:“烦望哥哥一发周全,开了项上枷更好。”差拨接了银子,便道:“都在我身上。”连忙去禀了管营,就将枷也开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内安排宿食处,每日只是烧香扫地。不觉光阴早过了四五十日。那管营,差拨,得了贿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来拘管他。柴大官人来送冬衣并人事与他,那满营内囚徒亦得林冲救济。
话不絮烦;时遇隆冬将近,忽一日,林冲--己牌时分--偶出营前闲走。正行之间,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林教头,如何却在这里?”林冲回头过来看时,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
火烟堆里,争些断送余生;风雪途中,几被伤残性命。
毕竟林冲见了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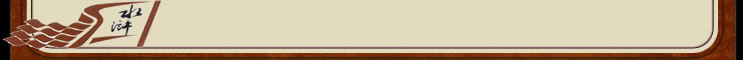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