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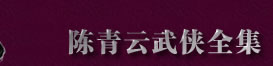 |
|
 |
|
 |
| |
|
第二章
|
|
另一间卧室里。
同样的时间和场面,只是人不同,是刚接掌家主的石大公子家庆和他的妻子月女。
灯下,月女充分显了她的冷艳,她是个美艳得令任何男人看一眼便心跳,看两眼便发抖的女人,隐藏的锋芒会让你切实地感到,像一把末出鞘的利剑,杀人的利剑,这种女人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也有令人承受不了的压力。
石大公子红脸带笑,他的脸色不知是酒染的还是由于接掌家主尊位的兴奋所促成。
“家庆!”月女开口:“从今以后你必须多用头脑,凡事不可任性随便,‘天下第一堡’的家主在武林中也是第一等的人物,举足轻重----”
“这我知道!”伸手把爱妻揽到怀里,端起酒杯,凑近樱唇:“来!喂我!”
“刚刚才教你正经----”
“这是卧房,我们夫妻俩的天地怕什么?来,快!”
月女斜了他一眼,把酒含在嘴里,然后口对口把酒倒吐回去,然后,两夫妻抱成了一团,合成了一体----
“唉!”窗外传来一声叹息。
“什么人?”石大公子喝问。
没有反应,但那声叹息似乎仍在空气里回荡。
月女一阵风般旋了出去,很快又折回来。
“什么也没见!”
“会是爹么?”石大公子有些惊慌。
“没听说过当公公的偷窃儿媳房间,不过----”
“不过什么,快说!”
“石家堡从来没发生过太岁头上动土的事----”
“你的意思是外人?”
“对!这里是内宅,家规森严,堡里人绝不敢犯禁胡来,所以我认为是外人,敢于轻褛虎须的绝非泛泛之辈,而正好在你接任家主之日发生此事,显然是对你的一项挑战。”眸光一闪,又道:“我想到了你说的?
抢绰凡幻鞯男〗谢俗尤伞 ?
“一个豆渣大的小子也敢胡来?”
“大郎,你错了,越是不起眼的人越可怕,他敢在那种场面之下搅局必然有所倚恃,爹在开创局面时结下了仇家无数,上门报复是迟早的事,我判断那小叫化子身后必有极可怕的主使人,而小叫化子本身也不可轻视,他来去自如,你们布的网竟然连他的影子都没网到,这一点便可证明,同时据管事的说,那小叫化在堡门对警卫露过一手,功力不是等闲,看来----本堡从此多事了。”
“我非逮到那小子不可。”大公子咬牙切齿说。
“你怎么个逮法?”
“发动所有各结盟门户的人力,一根针也能搜出来。”
“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
“这----该怎么办?”
“加强戒备,以静观变,现在只不过是猜测,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猜测,如果是一桩意想不到的巧合误会,岂不是丢人现眼?”
“唔!对!月女,你真了不起,如果你是男----”
“我如果是男人怎么样?”
“最恰当的家主人选。”
“哈!大郎,你这一说我好像真的当了家主,可惜,女人永远是女人,绝不会变成男人,就算有神仙把我变成男人,也必须是石家堡的男人,否则哪有当家主的份,要是我真的变成了男人,那你呢?”
月女偏起头,风情十足。
“我----变女人,作你的替身。”
“格格格格----”
“哈哈哈哈----”
两人搂抱在一起!
内宅上房。
老家主石中龙在房里徘徊,样子像个梦游者,跺跺脚可以使风云变色的“武林千岁”现在似乎又变成一个衰弱的普通老人,他停下脚步,半闭着眼,喃喃的自语道:“我真的老了么?不,我没老。”
腰一挺,虎目圆睁,仿佛豪气重生,但随即目光又黯淡下来,颓废依旧:“老了,不中用了,石中龙的时代已经过去,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是每一个人命中注定的悲哀么?
人为什么要老,可是,能不老么?
募地此刻,一声叹息倏然传来。
“什么人?”石中龙双目再睁,抢出房外走廊。
空庭寂寂,月色凄凄。
当年杀一个人如同按死一只蚂蚁的人物,竟然被人作弄,的确是不可思议。
“来人啦!”石中龙一声虎吼,像平地一声雷,差不多连外院都可以听见了。
内院没派人巡逻,因为没人敢闯。
大公子石家庆夫妇首先奔到,二公子石家辉夫妇也跟着来到,然后是内宅的下人仆妇,最后才是二夫人。
“爹!发生什么事?”石家庆问。
“老爷子,怎么了?”二夫人睡眼惺忪。
“爹!到底什么事?”石家辉挨近。
“刚才谁在我房外叹气?”
家人面面相觑。
“真有这事?”石家庆望了月女一眼。
“这可不是偶然!”石家辉也斜扫了他妻子如萍一眼。
“怎么说?”石中龙瞪着两个儿子。
两兄弟分别把听到叹息声和发现人影的经过说了一遍。
石中龙双目又大瞪,电炬似的目芒熠熠生威。
“真的有人敢闯入本堡?”
“老爷子!”二夫人也眸光大盛:“也许有内奸?”
“搜!查!”石中龙暴叫。
两兄弟四口子即转身奔去。
“你们通通下去!”二夫人摆摆手。
下人们纷纷下去。
“我石中龙还站得稳、挺得直,居然有人敢----”
“老爷子,让他们年轻的去处理吧!”
“怎么?玉凤,你也任为我衰老无用了?”
“老爷子,别望了,现在已经有新的家主。”
“我不能作主指挥?”
“难说!”
“家庆是我的儿子,他敢不听我的?”
“天下第一堡的家规与别的门派不同,是你自己订的,怎么,你想毁弃?”二夫人声音很冷,不知是何居心。
石中龙怒瞪二夫人,眼里的光焰简直可以灼人,但没多久光焰暗了下去、消失,又变回原来的颓丧,神情充满了哀伤与无奈,颓然道:“玉凤,我心上这根钉子钉得太牢、太深,永远拔不掉,莫非----是上天惩罚我?”
二夫人道:“老爷子,你一生不信鬼神之说,怎么才只短短的时间便变了另一个人?”
石中龙呻吟似地道:“你不会明白的!”
二夫人道:“我明白,你是为了----”
石中龙暴声道:“不要说下去!”
抬头望月,月已西斜,但仍照出老劾锏睦峁狻?
应家祠堂----
位置在太原府城西门外大街的尾梢,是一座古老的大建筑,虽然已经被时光洗刷得退了色,但从结构势派看来,仍可依稀想见其昔日的风貌。
应家在太原是望族,虽然已经没落,不过人换而物不移,名望仍在。
除了春秋二祭或是族中有什么特殊事故之外,祠堂大门是不开的,从大门边另开的小门出入,守祠的是一对老夫妻,当然也是应家的族人。
午时不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毛头小子拖拉着脚步进入祠堂,他,正是在“天下第一堡”胡搅的“浪子三郎”。
紧跟在他身后面的两名劲装汉子,在十丈之外停立,互相交谈了一阵之后,其中一个朝原路飞奔而去,另一个隐入了一片修竹之中。
不用说,这两个是石家堡的武士,家主已经下令全力捉拿“浪子三郎”。
一盏茶功夫之后,尘土飞扬,蹄声杂乱踏,二十余名武士飞风般卷到,原先踩线的武士从竹丛中现身。
众骑刹住。
带头的与踩线武士匆匆数语之后,在一个手势之下,众骑散开,包围了应家祠堂,武士头目带四名武士徒步进入。
祠堂大门是一个石板铺砌的宽敞院地,正面是供奉祖先神位的大殿,特别屯高而建,门前有长长的石级,这是配合祭祖大典的排场而设记的。
院地侧中隔短墙,由月洞门通向三合的东西跨院,大殿两侧有穿道通后进,祠堂外围则是整圈的围墙连结大门。
四名武士与头目站在石板地中央,神气十足。
武士头目约莫三石岁左右,彪悍得像头野豹。
“搜!”头目挥了下手。
“是!”
四名武士齐应一声,左右各二分别转身朝月洞门奔入跨院。
“为一个毛头小子劳师动众,真不懂竟然把他当一个人物看待,逮到了先好好把他修理一顿再拖回去交令发落。”
武士头目自言自语。
没多久,一阵鸡猫子喊叫,四名武士拖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妪出来,两个老的满头飞霜,年纪在花甲以上。
武士头目瞪眼。
“怎么回事?”
“毛头小子没影子,分明是被窝藏了,两个老家伙又死不承认,所以带出来由头儿问个明白。”武士之一回答。
武士头目上前一把揪住老头的胡子。
“啊!啊!”老头痛得怪叫。
“别鬼叫,你是守祠堂的应老头?”武士头目喝问。
“是!大爷。”
“那小要饭的呢?”
“小要饭的?”应老头瞪眼:“什么小要饭----”
“少跟老子装蒜,快说,是不是藏起来了?”
“我们祠堂从不许化子进门。”老太婆代答。
“这么说----是你们儿子?”
“我两老天生孤寡命,哪来儿子?”
“老太婆进门四十年,屁都没放一个,哪来儿子?”老应头接回了话。
“嘿!人刚进祠堂就化了不成?老应头,老子是看你年纪大了所以才这么客气,你不说实话先拔光你胡子。”
揪住胡子的手一扭。
应老头又痛得“哇!哇!”怪叫。
“杀人啦!”老太婆尖声大叫。
两老的胳臂被武士扣住,丝毫不能动弹。
“放开他们!”
一个冷森的声音像从地狱传来,令人汗毛战。
一个俊逸高挑的贵介公子出现在大殿石级顶端,人如玉树临风,手持一支乌光发亮的洞萧,那一身华贵的衣着便已代表了他的身份,这么一个足以令任何女人发昏的佳公子会有那种阴森透骨的声调,简直是难以想象。
四武士和头目全为之错愕莫名。
“我说放开他们!”
声音冷森,但神情并不可怕,也许是他长得太俊的缘故。
武士头目不期然地松手后退一步,仰起脸。
“你----”一想不妥,立即改了称呼:“朋友是谁?”
“你还不配问!”冷傲得令人受不了。
堂堂“天下第一堡”的武士头目,从来没被人如此轻视过,就是堡里一只狗出来,人见了也畏惧三分;光凭胸襟上绣的黄龙标志,就足以使道上人不敢正视,贵介公子这句话使他几乎疑心是听错了。
“朋友刚才说什么?”武士头目脸色已变。
“说你不配问本人名号。”贵介公子冷漠回答。
“嘿!好大的口气,你算那棵葱?”
“当心你的狗嘴。”
武士头目的脸变成了猪肝。
“把他揪下来,准是‘浪子三郎’的身后人。”
“是!”
四明武士“轰!”应一声,放开了姓应的二老夫妇,扑上殿阶,动作倒是相当地俐落矫健,窜如跃飞。
贵介公子单手随便一挥,罡风卷出,空气起了波裂之声,四名武士同时口发闷哼,像狂风中的四片落叶旋起,然后摔落青石板地面,“砰!砰!”声中,变成了四只死狗,趴在地上挣不起身来,凄哼不止。
武士头目一窒之后,虎吼一声,野豹般扑上。
故事重演,在贵介公子挥手之间,倒涌飞坠,他蹦得高,摔得也重。“啊!”了一声之后,昏死过去。
“朋友好身手!”
一个虎背熊腰的半百老者出现在小门边,手里提了根又粗又长的旱烟杆,襟绣银龙,脸红得像婴儿,双目炯炯有神,煌歉瞿诩腋呤帧?
他身后是四名襟绣红龙的武士,比刚倒地的黄袍武士头目高了一级。
贵介公子不言不动。
老者走到石阶前三步处停住。
原先昏厥的武士头目业已醒转,四名红龙武士上前扶起四名黄龙武士和头目,然后要他们退出祠外。
“阁下是石家堡武士总教习‘满天星’蔡云?”
“不错!朋友是----”
“‘浪子十三’!”
“‘浪子十三’?”蔡云满面惊疑,还皱起了眉头。
这么一个俊品人物竟有这么个外号,令人不解?
“对!很容易听清楚的四个字。”
“那----‘浪子三郎’?”
“没听说过!”回答的非常干脆。
蔡云的眉头没有舒开,他在想“浪子三郎”与“浪子十三”。
据踩线的手下报告,“浪子三郎”是进了应家祠堂,而这里却冒出了个江湖上不见传名的“浪子十三”,都是以“浪子”为号,二者之间有关联么?问题在于一个是贵介公子,一个是叫化子,说什么也扯不到一块,可是“浪子三郎”进了祠堂,“浪子十三”又出现在祠堂,这绝非巧合,因为祠堂不是茶楼酒肆,更不是客店,如果说是在玩易容的把戏,双方的高矮差了几乎一个头,是截然不同的两人,这到底怎么回事?什么蹊跷?
姓应的老夫妻这时已退得远远。
“朋友是新出道的?”蔡云试探着问。
“对!故而名不见经传。”
“什么门户?”
“天理人道流!”
蔡云和四个手下齐齐色变。
“天理人道流?”蔡云重复一遍,声音已寒。
“一点不错,本人首创。”说法与“浪子三郎”一样。
“朋友是流派之主?”
“当然!”
“‘浪子三郎’的说词与朋友一样,怎么说?”
“哦!有这种事?唔!八成是冒充的,不过本人叫十三,他叫三郎,差了两个字,还不错,他不敢十成十地冒充,总算有了顾忌。”
“同流又同称创始者怎么说?”
“本人会查清楚。”
蔡云沉思了片刻,然后脸上浮起一抹冷笑。
“朋友怎会到这祠堂里来?”
“清静,不受任何干扰,是暂时歇脚的好地方。”
“哈!”蔡云挑眉瞪眼,目光如闪闪电光:“‘浪子十三’,不管你这名号是胡诌还是混说,真佛面前不烧假香,光棍眼里不揉沙子,看你的确是人模人样,闲话少说,你差遣‘浪子三郎’到本堡搅局,意图何在?
”
“本人说过不认识‘浪子三郎’。”
“很好,你到本堡亲自向家主解释。”
“本人没空,也没解释的必要。”
“敬酒不喝么?”
“蔡总教头,照子放亮些,别看错了对象。”
“老夫的照子亮得很,如果你喝敬酒,就随老夫上路,如果要喝罚酒----”
“怎么样?”“浪子十三”的神色一点不变,冷漠如常。
“押你回去!”
“哈哈哈!蔡总教头,本人是看在你还正派,所以才跟你说了这么多话,要押本人到石家堡,凭你还没这份能耐,还是省省吧!”
淡淡几句话但语意相当狂傲。
武士之一向蔡云施礼道:“禀总教头,我们的目标是‘浪子三郎’,人就在祠堂中,外围已经封锁,他漏不出去,是否做一次严密搜索,连正点子一并带回。”
蔡云略作考虑道:“好,你去传令。”
那名武士立即奔了出去。
“浪子十三”淡淡地道:“蔡总教头,你们要搜索,本人不反对,但注意一点,绝不可伤及无辜,看祠的与此无关。”
蔡云不假思索地道:“可以!”
不久,出祠传令的红龙武士带了数十武士蜂涌入祠,其中部分是黄龙武士。
蔡云低声交代了几句,数十武士散开,分成四组开始搜索,他身边的武士在指令下负责搜查正面的大殿。
“浪子十三”照诺言不予拦阻。
约莫两刻光景,奉令搜查的武士陆续回到院地。
回报是一无所获。
蔡云瞪眼道:“人上了天不成?”
想想又道:“这祠堂有地窖或是密室之类的设置么?”
以名似是头目的红龙武士道:“没有,已经盘问过守祠堂的老头了,他赌咒说没有,卑属等也没发现可疑之处。”
蔡云挥手道:“你们退到外面去。”
后进的武士悉数退了出去,现场剩下蔡云和四武士。
蔡云仰面向殿阶道:“‘浪子十三’,你下来!”
“浪子十三”道:“你不敢上来么?”
蔡云冷哼了一声,嘱咐四名手下道:“你们守在下面!”
然后像一只灰鹤般冲天而起,凌空一折,姿态妙曼地落在殿廊之上点尘不惊,这一手不说惊世骇俗,至少是令人叹为观止,江湖中实不多见。
“好身法!”“浪子十三”赞美了一句。
“‘浪子十三’,言归正传。”蔡云似乎并不领受这句赞美之词:“你既然不愿自动上路,划出道来吧!”
“真要见真章?”
“你改变主意了?”
“笑话,出尔反尔就不配当浪子了,听着,洞萧对烟杆非常公平,三照为现,本人输了随你到石家堡,若是你失手那就请退堂,如何?”
“可以!”
“好!你准备好就可以出手。”
旱烟杆和洞萧同时扬起。
双方都没有特意作势,高手,无势之势。
目光已空,气势已凝。
这不是普通的交手,“浪子十三”输了便成阶下之囚,名号也就毁了。
蔡云是奉命带队执行任务的,要是失手的话,任务无发达成,总教头这位子可能就保不住了,甚至连在江湖上混的资格都将被否定,因为“浪子十三”是初出道的,可以说是个无名小卒,名不见经传。
应老头夫妇这时已失去影子,可能是不敢看这种场免。
一声沉哼,旱烟杆划出,点、戳、劈、挑、拐、挂,像是好几根旱烟杆同时以不同招式出手,诡异玄厉臻于极致。
“呜----”洞萧像一条乌光灵蛇窜起,发出使人心神皆颤的尖锐啸声。
紧接着“叮叮”连响,金铁互振交鸣,显示出洞萧与烟杆都是特殊金属打造的。
杆影消失,乌光和厉啸不止,这一个回合很短暂,双方又回复原来的姿势。
“第一招!”“浪子十三”平静地说。
蔡云这时发觉自己低估了“浪子十三”,但只是心意一动,他不能分心去想,分心便是犯错,高手对敌之大忌。
“呀!”旱烟杆再度出手,这一招跟头招大异其趣,旱烟杆仿佛一条出洞灵蛇,窜出,但无法判断攻击的部位,似乎所有要害大穴都在攻击范围之内,看似缓慢,其实极快,使人有防御闪避无从之感。
“呜----”洞萧又发厉啸,极奇古怪的一萧,竟然轻易地化解了这一玄奥无匹的攻招,旱烟杆的路全被封死。
“这是第二招!”“浪子十三”气定神闲。
蔡云的心神浮动了一下,但随即按耐下来,现在剩下最后一招,胜败的关键,他自成名以来,还没碰到过这?
裙αξ薹ú舛鹊亩允郑馐夭还ィ梢苑椿鞫环椿鳎擞眉偈某擅肌叭盒情媛洹币酝急乘?
战之外别无良策。
殿阶下院地里的四名红龙武士眼鼓鼓地向上望着,由于廊檐平切的死角,他们只能看到一半,紧张当然是免不了的,总教头亲自出击不奏功的情况简直每有。
蔡云的老脸泛出了酡红,这是功力运到极限的表示。
“浪子十三”的神色也趋于凝重,毕竟他还是初历大风大浪,对自己的功力还不能确切地肯定,信心并未十足。
沉寂了好一阵。
“呀!”蔡云的栗叫。
旱烟杆不是线,也不是圆,而是幻成了无数的点,像漫天花雨缤纷摇落,变成立网,变成了罩,而每一点只消沾上便足以致命,罕闻罕见的绝招,“满天星”的外号便时从这一招得来;的确是满天飞星,激射暴泻。
“呜----”尖厉的啸声像利刃戳刺人的耳膜、心脏,功力稍差的,光这啸声便禁受不起,别提洞啸的攻击力了。
洞萧划线交织成网,网罗漫天殒星。
惊世骇俗的对仗,像是神话中的斗法。
连珠密响有如万颗铁弹般破空击地。
时间不长,像骤雨暴临乍止。
“第三招,承让了!”“浪子十三”的洞萧抵在蔡云的“志堂穴”上,他要是下杀手,蔡云早已经躺下。
堂堂“天下第一堡”的武士总教头竟然输了。
蔡云的老脸已经扭曲变形,不只是输招,同时输去了名声地位,以及大半辈子辛苦追求得来的一切,输得很惨。
“‘浪子十三’,你赢了!”七个字,很困难地吐出来。
“蔡总教头,你心服么?”“浪子十三”的声音很低。
“----”蔡云答不出口,但神色已经默认。
“本人只是侥幸。”
“‘浪子十三’,你吐劲吧,算是对老夫的成全!”
“这并非寻仇对敌,本人不想流血!”
“老夫会走,走出江湖,永远!”英雄末路的悲哀。
“蔡总教头,你是个血性的人,在石家堡是唯一有正义感的长者----”
“本人早有耳闻,事情没这么严重,武学深如瀚海,没有绝对的高下,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各有专精,不必如此气馁,在江湖上你的武功仍然是被肯定的。”
顿了顿又道:“本人很愿交你这个朋友,现在再出招,我逃你追!”
两人声音很低,石阶尽头的殿廊是场面死角,在院地上望,只能看到上半身,所以这情况四名武士并不清楚。
蔡云颓丧地望着这神秘的年轻高手,他无法揣测对方的心意。
“蔡总教头,本人别无他意,快行动,莫让你的手下起疑。”
“浪子十三”的态度很诚恳,不像有什么居心。
“‘浪子十三’,你没有理由这么做?”
“算是惺惺相惜吧!”
“你准备籍此作为将来对老夫要挟的口实?”
“蔡总教头,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说完收萧、划弧、击出,锐利的萧声再度震破空间。
蔡云的旱烟杆像灵蛇般夭矫而起,他反击没经过思考,是武者的本能,以他的身手,一动便显示出威力。
金铁交鸣中,“浪子十三”收手电退,大声道:“本人一向不打无意义的架,后会有期!”
声落,人已凌空掠起,如天马行空,冲向跨院屋顶而没。
四名红龙武士也急起直追。
外围的武士当然阻止不了“浪子十三”,眼看他突围而去。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