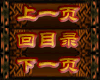|
|
|
第二十章 星月船
|
|
天刚亮,曙色已在窗前。
积满雪的小院,枯零的白杨木,二三只独脚伫立树梢发颤的寒鸦,灰朦朦的天空降着白朦朦细雪,天与地一片肃杀。
潘小君打了个大哈欠,高挺懒腰,伸直双腿,他已经整整睡了二天。
打从他白花四娘那里逃出来后,他就似已决定好好的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管他天高地远的好好睡一觉。
因炝他一想到就连花姑妈也来了,他就开始头痛。
幸好对一个躺了二天没有吃东西的人来说,最疼的应该是肚里的五脏庙。
潘小君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听见五脏庙抗议的声音。
但是望着窗外飘雪,他也只有叹气。
这样的斜风急雪,哪还会有小贩出来叫卖生意,也许连个卖绵花球,糖葫芦的老婆婆也没有。
看样子只有等雪霁了,潘小君摇头叹气。
风吹的很冷,冻得竹简子编成的竹床,已发出“吱吱”声音。
潘小君到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饥寒交迫。
那种又冷又饿的滋味,实在和上断头台差不了多少。
他那张和风一样冷的眼神,痴痴看着窗外。
雪花斜斜飞舞,要等雪霁,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雪霁了,天却未晴。
没有处处的腊梅香,就连骑驴过霸桥的小孩也没有看见。
潘小君对着已冻得发白的小窗,看向院前小霸桥,小霸桥上有人。
人不是孩童,是一个腰已经弯的不能再弯的老太婆。
老太婆手里提着竹篮,走过霸桥,小霸桥上有人。
人不是孩童,是一个腰已经弯的不能再弯的老太婆。
老太婆手里提着竹篮,走过霸桥,地也的样子就像一个少妇提着竹篮过市场买菜一样,兹铢必计的模样。
老太婆居然不是往市场而去,居然往他住的院落走来。
潘小君感到好奇了,他眨了眨眼睛,只希望老太婆的篮里千万莫要是她的袜子。
他忽然想起十四岁,挽着竹篮过鱼市时候,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若再提竹篮过鱼市,我就是小狗。”
“为什么?”
“因为无论你再怎么的买很多鲜肉、青果,别人还是都会觉得你的篮里装着的是你那又臭,又长的老袜子。”
潘小君想起了这段话,忽然觉得有趣极了。
他再抬头看那老太婆的样子,就真的觉得这说的并不是抬杠话。
潘小君很想笑,但他刚张开嘴,却又忽然闭回去。
花姑妈?
要命的花姑妈!
那个老太婆会不会是花姑妈?
难道花姑妈已扮成老太婆模样,要来取青魔手,要来和他拼命?
潘小君就像见鬼般的,忽然从床上跳起来。
他靠在床角,双眼透过小窗一角,紧紧盯着老太婆的一举一动。
院前白杨一株,白杨后小筑一栋,小筑里有白窗一只,窗下皆栽种腊梅三株,梅上有花,花上残雪犹新。
老太婆绕过雪梅,走到窗下,转进小筑,就再也没有出来。
潘小君已经盯了半盏茶时间,还是不见动静。
他已经开始感到好奇,潘小君的好奇心一向比他爱管闲事的毛病还要重。
他忽然纵身一提,跃过窗沿,取出他那一袭海水湛蓝色披风,披风一卷已穿在身上,然后他的人也同时间跃出窗外。
窗外,雪虽霁,寒意却正浓。
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躲在梅梢上偷看别人,那个人一定就是潘小君。
只是他这次偷看的并不是个绝世美人,更不是倾城佳丽,而是个腰已弯的不能再弯的老太婆。
腊梅正盛,花开艳红,残雪苍白,而他身上的披风却是湛蓝色的。
只要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他这样的地物掩护实在不怎么高明。
除非老太婆是个大色盲。
只可惜现在有色盲的人,居然不是老太婆,而是潘小君。
潘小君双眼透过纸窗,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房内。
房里有人,二个人,二个女人。
二个应该都还算青春年轻的女人。
那个老太婆呢?
潘小君亲眼目者她驼着背走进小筑的,但是里头的居然不是她,而是二个年轻的女孩子。
潘小君看得差点从树梢上掉下来。
* * *
女人只要是年轻,就不会太难看,最起码在男人的心里,愈是年轻的女孩子才算愈有女人特有的原始媚力。
至少她们的皮肤摸起来不会像风干的皱橘子皮。
潘小君站在树梢上,已经开始在叹气。
他忽然一个飞兔穿墙,翻身入屋。
二个年轻的女孩子,居然一点吃惊的样子也没有,居然还满脸对潘小君“吃吃”的笑着。
潘小君实在站不住脚了。
一个眼睛比较大的女孩子笑得最大声:“我叫小星。”
头发比较短的指头潘小君道:“我叫小月。”
潘小君本来脸上已推满男人一惯的“自我陶醉”表情,只可惜他一听到她们的名字,他的眉毛就已先皱了起来。
“小星,小月。”寒风吹在他脸上,他忽然摇头:“星月?星月公主,你们二个和星月公主有什么关系?”
大眼睛的小星,抢着道:“公主是主,我和小月是仆。”
小月的短发娇俏,一如她的笑脸:“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江南那个拿剪刀的男人。”
二个年轻的女孩子忽然笑了,而且笑的很好看,很动人。
潘小君却只能摇头。
年轻女孩,总是好奇,小星又抢着说:“听说江南最美的并不是西子湖,也不是钱塘听雨,而是女人,江南美人。”
小月道:“难道我们会输给江南的女人。”
小星道:“北国虽然终年气寒,冰封万里,但起码我们的皮肤比她们江南人还好,还要白嫩。”
小月道:“除了皮肤好之外,我们北国女人的脾气也好,至少没有江南人的母老虎过街。”
小星道:“也许公主应该到江南走一趟的,才不会让天底下的男人,只知道去江南迷金醉纸,寻欢作乐。”
小月双眼睡着道:“君自江南来,应知江南事,公子你说,我们哪点输给你们江南人了了”
潘小君只有苦笑。
他忽然道:“我可以说话了?”
小星道:“是的。”
潘小君道:“好,我来告诉你们。”
小月道:“请说。”
潘小君道:“我只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我已经很饿了。”
小星又笑了:“看来公主说的没错,原来他不但是酒鬼,还是个饿鬼。”
* * *
竹篮里装的并不是老太婆的臭袜子。
肉,状元奎的红烧牛肉,肉上青葱伴蒜泥。
寒带的大白菜,白如雪,清蒸白菜和菇蘑。
潘小君抹着嘴,坐在一张很高的椅子上,一口一口的往嘴里送。
小星、小月站在一旁看他,就像看着一个饿了十几天的饿鬼在狼吞虎咽。
小星抿起嘴笑道:“我敢打赌,你前世一定是鬼,饿鬼。”
小月摇着头道:“要是知道你那么会吃,我们一定帮你准备个特大的大碗,喂狗的那种。”
碗已空,碟已尽。
潘小君抹了抹嘴角道:“好,好菜。”
他忽然又道:“哪一样?”
小月抢道:“酒,若有酒那就更好了。”
小星忽然板起脸道:“对,酒,好菜若不下酒,岂不是对不起祖上十八代。”
她们二个说话的口气,完全就像潘小君的口气。
潘小君看着她们二个叹道:“看来你们二个是我肚子里的虫。”
小星一如夜星,闪动双眼:“是公主要我们这样说的。”
小月宛若新月明亮:“她说,对你这样的人,就必须说这样的话。”
“星月公主。”潘小君真的板起脸了:“她说我是怎样的人?”
小星道:“你非但不是个君子,而且是个坏蛋,大坏蛋。”
小月道:“还是个大混蛋。”
潘小君居然没有生气的样子,他只是觉得这些话很熟悉,他仿佛在哪里听过。
他真的板起脸:“你们早就知道我在这里。”
小星道:“不错,自你从后窗溜进这间院落后,我们就一直在盯着你。”
潘小君道:“你们已算准我哪时候会睡醒,所以扮成老太婆模样,引我上当。”
小月道:“公主说你的好奇心,一向比你爱管闲事的毛病还要重。”
潘小君道:“星月公主并不是白请顿早餐。”
小星星眼闪烁:“看来你并不笨。”
“大将军威震七海,一手掌天。”潘小君眼里已闪起亮光:“星月公主艳冠群昨,绝代月华,能得大将军、星月公主之赐,实在是我的荣幸。”
小月道:“老实说,这顿早餐还是公主亲自下厨的,能让公主亲身洗手做羹汤,你还是第一个。”
潘小君脸色似已发白,他忽然抱拳一揖道:“谢谢。”
他说完话,掉过头,居然就要走。
小星却已忽然站在他眼前,如银铃般的笑着:“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白吃的早餐也是没有的。”
小月也已挡在他眼前:“星月公主躬身下厨,为得公子胃肠一欢,难道公子你吃完了,拍拍屁股就想走?”
潘小君脸色更难看了:“难道你们还要我跟你们走?”
小星星眼闪烁:“你非但不笨,简直聪明极了。”
小月眼亮胜月:“请。”
* * *
正午,日影过竿。
没有下雪的时候比下雪更冷。
白班肌雕成的细雪,已结成冰珠,冰珠就结在红梅上,红梅却当红。
杨开走在碎石路,一块块碎石发出“剥剥”声响,就像紧石已碎成冰块。
“白石镇”并非石头都是白色的,而是都已结成白色冰石。
杨开转出羊肠弯道,踏上小径,抖落一身风雪,走进一家小栈。
这家小栈就在小径旁,小径远在层山间,层山已在风雪外。
杨开人已在小栈里。
当杨开跨进栈里,抬头第一眼看见的并不是店小二,居然是东篱居士。
方形菜桌,干净的一尘不染,就像东篱居士一身的黄菊长衫,他无论对任何事,任何东西,都讲究一尘不染。
就连桌上菜肴,也是一碗清汤煮蛋,清淡的如方外修者。
杨开脸上露出笑容嘲椅子坐了下来:“先生难道只吃蛋花汤?不吃肉?”
东篱居士白须微飘,自若的神色,看不出任何表情:“肉质太杂,浊而腥烈,易燥鼓火,多食无益。”
杨开看着桌上一壶陈年花雕,微笑着道:“自古酒肉难分,先生既忌肉食,为何还喝酒?”
东篱居士双眼仿佛在远方:“酒质最纯,酒纯于水,酒内二者岂能相提。”
杨开大笑:“高见,先生果然高见,听先生一言,我杨开又长一智。”
东篱居士忽然道:“请。”
他话刚说完,手上五指忽然一转,桌上的酒杯竟已滑到酒壶口沿,五指一扣,成个爪形,竟已隔空将酒过提起。
提起的壶口,恰巧对着杯沿,酒已流入杯中。
杨开脸上看不出一点吃惊的样子,但是他的眼中,已闪出刀锋般锐利锋芒。
杨开忽然伸出右手,朝桌上一按,溢满的酒杯已跳在半空中,风声带过,他手腕再一转,已将酒杯接在手里。
杯上陈年花雕,一点也没有溅出。
杨开持杯对口:“请。”
东篱居士看着杨开将酒一口倒进胃中,眼神也似锐利如刀,他道:“庄主以枪成名,想不到有此指力。”
“指力?”杨开又笑了:“孔促尼前卖文章,关云长前舞大刀,我这点江湖杂耍功夫,怎敢献曝于先生名动天下的折菊手下。”
东篱居士看着杨开忽然冷笑。
杨开皮笑肉不笑,他岔开话:“先生动作并不慢,已早一步到这里,有没有那个人的下落?”
东篱居士冷道:“哪个人?”
杨开道:“潘小君。”
东篱居士道:“没有。”
杨开并不意外:“他迟早要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他。”
东篱居士已看穿杨开,就如同杨开也已看穿他:“是的。”
* * *
杨开叫了一碟七分熟的火烤小牛肉,却没有牛肉。
店小二站在他面前,居然连一点害怕抱歉的样子也没有。
杨开似乎感到好奇,他看着这位店小二一脸的胡渣乱须道:“酒蒜乌鱼子。”
店小二吹胡子瞪大眼:“没有。”
杨开没有生气:“闷烘风鸡。”
店小二眼睛瞪得更大:“也没有。”
杨开笑了:“那么贵小店里有什么?”
店小二拉开嗓门:“肉。”
杨开道:“什么肉?”
店小二道:“人肉。”
杨开豁然从椅上站起,一手打在桌上,“砰”一声,已将桌子打了个大洞。
但他脸上还是保持着君子笑容:“请贵掌柜的来,好吗?”
店小二居然连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他居然还说道:“可以。”
* * *
掌柜的脖子并没有挂算盘,也没有一双贼碌碌的眼睛,就连商人特有的市侩粗俗气也没有。
杨开的眼睛已先亮起来。
因为她是女的,而且还不难看。
杨开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年轻漂亮的女掌柜。
杨开双眼比雪更亮:“听说贵店里卖人肉?”
女掌柜面无表情:“是的?”
杨开道:“为什么要卖人肉?”
女掌柜道:“奸臣贼子,卑鄙无耻小人,人人得而诛之。”
杨开忽然大笑:“贵店卖的都是这些人的肉?”
女掌柜道:“是的。”
杨开道:“这种人的肉有人要吃?”
女掌柜道:“有。”
杨开道:“谁?”
女掌柜道:“狗。”
杨开道:“这里有没有狗。”
女掌柜道:“有二个。”
杨开道:“谁?”
女掌柜道:“你们二个岂不是。”
杨开没有等她把话说完,当她说到第四个字时候,他已瞬间抽出腰畔上的梨花枪,手势一扬,已笔直刺向她的眉睫。
杨开、东篱居士成名江湖至少也有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中,很少有人能够用这种语气跟他们说话,不但少,可以说几乎没有。
梨花枪雨,枪若花雨。
杨开的梨花枪一如半空梨花,让暴雨飘舞的又急又斜。
花雨中的枪势,几乎看不出夺命的枪头是在哪里。
高手相争,你死我活,不得有所闪失,一点点的小地方疏忽,就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错误,更何况连夺命的枪头在哪里都看不出。
杨开双眼露出的杀机,就如同一头猛虎已盯上濒临死亡的羚羊。
女掌柜的双眼也正在盯着半空的梨花枪。
她已感到一股死亡杀机,就在她头上。
就在这时,她忽然缓缓伸出一只手,一只修长洁白的手。
她举手的动作很劝,很柔,却有种难以形容的奇幻妖异。
当她举出起手势,退坐一旁的东篱居士,忽然离地站起。
东篱居士眼瞳孔瞬间收缩。
只见他手一扬,名动武林的“东篱折菊手”已瞬间争先出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没有菊花,何来折菊。
东篱居士折的并不是菊,是骨头,人的骨头,应声而断的骨头。
只是这次东篱居士居然没有折人的骨头。
他那一双优雅的折菊花,折上的是杨开的梨花枪。
雷霆般的梨花杀人枪势,已在他手中瞬间停住。
* * *
杨开收回梨花枪,冷冷看着东篱居士。
东篱居士已退到一旁,他的双眼竟也是冷的,冷的可怕,他看着女掌柜:“敢问姑娘贵姓大名?”
“欢欢。”
欢欢的眼中布满血丝,充满怨毒,仇恨血丝。
东篱居士转眼看着店小二:“你呢?”
“月下老人。”
东篱居士眼里似乎更冷了:“你就是那个专刻死人骨头的月下老人。”
月下老人道:“是的。”
东篱居士忽然一个转身,黄衫飘舞,居然已慢慢的走出门外。
杨开似乎也已感觉到东篱居士脸上的变化,但他还是对着月下老人道:“听说你用的是刀?”
月下老人道:“刻骨不用刀,刻不干净。”
杨开道:“我书读的不多,大字倒识几个。”
杨开脸上青筋忽然突暴:“寂寞夜雨梧桐时。”
月下老人道:“窗外没有下雨,我也并不寂寞。”
杨开已看不出有任何表情:“杨鹏尸体上这几个字是你刻的?”
月下老人道:“我一生刻骨无数,杨鹏是谁,何人的骨头是杨鹏,我并不知道,也不需要去知道。”
杨开没有再说话,他眼中的杀机,几乎已再次拔枪,但他还是转身走出去。
当他走出第五步,他忽然开口:“后会有期。”
月下老人看着他:“不远。”
杨开已走出门外:“那时候,你最好亮出你的刀。”
月下老人双眼也像刀,一字一字很清楚的说:“是的。”
* * *
小径的尽头是风雪,风雪犹在小径中。
潘小君身上湛蓝色披风,已沾满雪花,甚至连他的头发也被染成雪一样的白色。
小星、小月站在一堆高高的雪堆顶端,似乎在眺望远方。
远方没有青山,没有白云,更没有悠游水中的小白鹅。
却有黑星一点。
千里的冰封,无边无际,跟本不知道现在是在哪里,身处何地,眼睛的尽头除了银白的冰雪,还是冰雪。
潘小君双眼也似已结了一层冰,连眼前的景物都模糊了,但他还是能很清楚的看见远方渐渐靠近的黑点。
他的眼睫刚一眨,却已发现眼前出现的居然不是小小的黑点。
船,巨船,二十丈高的船。
船板漆成黑色,油漆仍新,船就迎着他们破冰驶来。
潘小君张开的嘴巴,已几乎可以吞进一只鸡,他现在才明白原来眼前是一条河,只是河畔早已结冰,看起来就和陆地没有两样。
随着巨船破冰而来,潘小君的嘴张的更大了。
船板上伸出的船浆至少有五个人并排,握浆的显然都是很有经验的水手。
潘小君眼睛盯着那些握浆人的手,他的嘴巴开的已足吞进一只大象。
水手的手居然都很白晰,很细。
居然是女人的手。
潘小君已开始摇头。
小星忽然笑了:“公主果然算的很准,果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
“星月旗。”小月指着船桅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道:“大将军最喜欢的星月旗,看来大将军就在船上。”
潘小君抬头望着飞扬的星月旗:“威震七海,一手掌天的大将军在船上?”
“是的。”小星笑的很可爱:“星月起,刀光落,将军一手掌天机。”
小月眼亮如月:“大将军不但在船上,公主也在。”
潘小君道:“哦?”
小星道:“你运气不错,能同时见到大将军和星月公主。”
小月道:“看来你的动气一向不坏。”
潘小君眼神里似乎已瞬间黯淡,他一个字,一个字说的很慢:“是的。”
* * *
船虽下锚,风雪却不止。
一条长长的甲板自船舱滑了下来,就恰巧延伸到他们面前。
船舱上忽然奔出了二十四个水手,她们奔跑在长板上,发出“蹦蹦”的声音,就像是沙场的战鼓声。
潘小君并没有去听这些响震云霄的声音。
他连年都似已来不及看。
他的双眼落在奔下来的水手身上,二十四个女人身上。
她们穿的都很少,就像在大海中挥汗操浆的水手。
发上束红巾,身披露肩短战袍,黑色的战裙更短,短的几乎伸展出整双浑圆结实的大腿。
二十四双腿,充满弹性,是最能激起男人原始欲望的那一种。
潘小君看得眼睛都花了。
小星勾起眼角,瞪着他:“你难道病了?”
小月揪着眼:“看来病得不轻。”
潘小君摇头着,忽然叹道:“心跳加速,热血翻腾,的确是一种病。”
* * *
风雪降在远山,远山在千里冰封外。
潘小君伸出手拨去发上银花,却拨不掉眼前一幕幕的急雪。
他跟在小星、小月身后,走上甲板,长长的甲板上已下满雪,漫天风雪中,就像在走一条无处是尽头的不归路。
不归路,人断魂,一阵冷风吹来,道:“忽然觉得很冷。”
大将军一手掌天,星月公主艳冠群星。
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传奇人物,像他们这种人是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他的。
潘小君似乎到现在才想到他的处境有多么的危险。
* * *
雪在窗外。
这艘大船里,居然不比一间豪华的酒楼差。
潘小君盘膝坐在一顶舒适的软榻上,一块小小的低儿,几上不但有酒,还有一瓶白色的小瓶子。
瓶中斜插着一株水仙花。
潘小君并没有看水仙,他的双眼盯在酒瓶上的“善酿”二字。
善酿是江南西湖名酒,不但每个江南人都爱喝,就连远自西域的西北大汉听到了都会流口水。
酒在桌上,却没有酒杯。
酒当然并不是用来看的,潘小君的嘴巴已开始痒了。
就在潘小君痴痴望着酒瓶时,软鹅黄色的门扉忽然打开,一个弯着腰的老头子,已咳嗽的走进来。
潘小君并没有看他。
老头双手捧着二只杯子,杯是金樽,绘有唐时仕女饮酒作乐的瓷杯。
他走到潘小君身后,停下脚步,轻轻咳一声。
就在这时,潘小君双眼忽然射如利刃锋芒,因为他已瞬间感到一股杀气,自他背后传来,迫人的寒气透过背脊,穿进脖间。
老头子并没有再动,他一动不动在潘小君身后,双脚似已钉入地板。
他所站的方位,居然已完全是一个高手瞬间出手就能使人毙命的距离。
也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瞬间抓到这种致命的出手距离。
这不但要敏锐的观察力,更是多少经验的累积。
他无疑是一个真正会杀人的高手。
潘小君已估算出,他在精神上,只要有所松懈,背后的老人就能瞬间出手。
他并没有把握能躲得开。
潘小君额前已开始冒出冷汗。
门是虚掩的,风在吹。
一阵阵赛风卷来,卷上潘小君一身湛蓝色披风。
氢风猎猎,随风飞起,潘小君整个人忽然就像随风飘起的披风,已卷向半空中。
弯老头子也就在这瞬间出手,他的身体是猎豹一样,同时间扑向半空中的猎物。
老头以手反切,以掌为刀,居然连续砍出了九刀。
刀刀精准,刀刀夺命。
一刀九斩!
* * *
风还是在吹,人却已不动。
潘小君已坐回原来的位置,一动也不动的就像连动都没有动过。
他身上的披风,飘舞在空中,也同时间落下。
他顺手一抓,一个回手,湛蓝的披风已穿回身上。
“一刀九斩。”潘小君盘膝坐在榻上,他忽然笑了:“阁下莫非就是仇一刀?”
原来他并不是个老头子,他已挺直腰身,也落回原地,就在潘小君背后。
仇—刀双眼发出亮光,双手拿着金杯一只,走出脚步,大步间已走到潘小君的眼前。
他拱起手:“潘小君不愧是潘小君,看来你的确配为大将军的上宾。”
仇一刀话说完,已坐了下来推出一只金樽,倒满酒,一口干了。
潘小君看着他:“仇一刀不但刀快,看来喝酒也不慢。”
仇一刀脸上一道刀疤,自额前天庭直直划下,穿过眉心,划过鼻心,一直到两片薄薄的嘴唇,他的人仿佛就是一刀二半,分为二个部分。
仇一刀笑了:“小君一剪,名动天下,我的刀再快,也快不过你手上的剪刀。”
潘小君倒满酒,仰起脖子,一口倒进胃里:“要不是我发现的早,只怕我已是你‘一刀九斩’刀下游魂了。”
仇一刀道:“我并没有带刀。”
潘小君道:“刀已在。”
仇一刀道:“刀在哪里?”潘小君道:“四面八方,九天十地,无处不在。”
仇一刀道:“我看不出。”
潘小君道:“你的心有刀,刀在你心里,心有刀,手上就有刀。”
仇一刀道:“心刀?”
潘小君道:“相由心生,意随念转,心即是刀,刀即是心。”
仇一刀道:“这就是你看见的刀?”
潘小君道:“是的。”
风在动,人却不动。
仇一刀双眼鹰隼般盯住潘小君。
他的眼睛锐利如他的刀。
但潘小君的话却比他的刀锐利,已砍进他心里。
虚掩的门窗,这时忽然一开,一俱走了进来。
“佩服,佩服。”一个脸上有十字刀疤的人笑着道:“能够亲眼目睹当世二大刀手对决,看来我万杀并没有白活。”
“一刀九斩,仇一刀。”潘小君看着仇一刀,又看万杀:“一剑十字,万杀。”
“看来今天的日子并不是什么好日子,江湖上二个要价最高的杀手都到齐了,早知道是你们二个,我情愿躺在破床上睡大头觉,也不愿醒来。”
万杀已解下背上的金边长剑,盘膝坐下,倒满酒,拱起手向潘小君、仇一刀道:“请。”
仇一刀举杯对口,一千而尽。
潘小君仰头长饮。
万杀忽然将解下的长剑抛在桌上:“刀剑无眼,饮酒不适带剑。”
潘小君握着空杯道:“昔有公孙大娘舞剑器,一舞剑器动四方,剑乃舞姿之祖,为饮酒观舞之器,何来饮酒不适带剑之说?”
万杀看着潘小君,“唰”一声,忽然抽出长剑。
剑刃青光兴亮,剑作龙吟。
仇一刀瞳孔收缩。
潘小君并没有动。
万杀手举长剑,剑尖朝天,左指在空中划了个圆弧:“今日不见唐玄宗,更不闻杜甫诗名,潘兄、仇兄可为观者,闻在下一舞。”
万杀话说完,手势一扬,长剑脱手飞出,他的人也紧跟着跃向半空中。
他长剑流转,宛若流金,瞬间已变化了二十个方位。
万杀一袭长布青衫,流转空中,就像一条在东方翻腾云海的己木青龙。
潘小君看得眼睛都花了。
仇一刀眼里闪亮的锋芒却更亮。
万杀突然一声叱喝,剑锋一指,瞬息间一剑飞出,刺向潘小君。
这一剑挟龙腾之姿,虎啸之威,万杀的剑法确已名列武林名剑榜。
血形十字,一剑十字。
万杀的血形十字剑已刺出。
潘小君并没有躲开,他只是突然伸出手,轻轻的摘下桌上花的一角。
花是白色水仙。
白色的水仙花已经潘小君手指轻轻弹出,迎向万杀势如劈竹破空刺来的一剑。
剑光一闪!
* * *
剑,金边长剑。
剑很长,三尺七寸长,剑锷黄铜打造,剑柄镶碎石细纹滚金边。
万杀手上有剑,金边长剑,剑上有花,花是白色水仙。
万杀动也不动的站在原地,他手上金边长剑,穿刺着潘小君背景出的水仙花,花很冷似有水雾,但万杀表情更冷。
潘小君居然以一朵水仙花,化解了万杀势如龙虎的一招杀着。
仇一刀双眼瞬间黯淡,已看不出任何神采。
万杀苍白的脸色,就像大病难愈的病者。
万杀忽然举起长剑,剑锋一弹,剑上水仙射出,“铿”一声,长剑入鞘。
潘小君忽然笑了:“公孙大娘舞剑之姿虽已成绝响,却还有其弟子李十二娘为部一舞,虽然我不是唐玄宗,你也不是公孙大娘,但阁下之剑舞,已可名列当世一二了。”
他话未说完,已提起酒盏,为万杀、仇一刀倒酒。
“刀剑无情,总要见血,还是不如喝酒。”潘小君笑着又说:“来,喝酒不伤情,不见血,我们的确应该多喝酒的。”
仇一刀豁然站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下次记得亮出你的刀。”
仇一刀话未说完,风一吹,他的人竟已如风般的飘出窗外。
万杀也同时站起,提剑回身,斜插背上。
他捧杯,拱手:“我也该走了。”
潘小君看着他:“万兄何不留下,多喝几杯。”
万杀道:“别忘了我是来杀你的。”
潘小君道:“我知道。”
万杀眼神中仿佛露出敬意:“不谈交易买卖,我倒希望能交你这样的朋友。”
潘小君道:“你我立场不同,各为其事,将来假如我潘小君活得够久的话,我一定找你喝几杯,大醉几日,不醉不欢。”
万杀脸上十字剑痕,已似隐隐颤动:“那一天并不会太远。”
潘小君再进酒一杯:“是的。”
万杀走出门外,忽然回头:“那你最好闲事少管一点。”
潘小君握着空杯,他大笑:“我倒真的希望能改掉这个要命的毛病,闲事少管一点岂非活得较久,也较愉快。”
风在吹,门在动。
万杀已消失在门下。
潘小君对着寒窗独饮,他并不愉快,他的心仿佛也像寒窗一样冷。
夜,夜却将临。(潇湘子提供图档,xie_hong111OCR)
|
;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