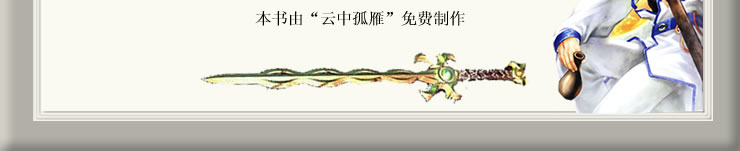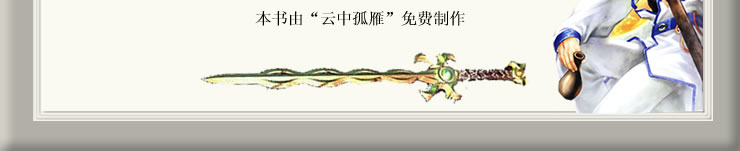|
第二回 往事峥嵘
|
|
古润松坐在摊前卖字画。
他画得一手好画,也写得一手好字。
他喜爱山水画,笔下景物既有唐寅的洒脱超拔,又兼仇英的秀润清雅。
自然,唐仇二位乃扬名天下的大画家,他不过是边陲重镇怀才不遇的穷秀才,以字画糊口,只怕难以扬名。
在书法上,他较喜爱宋代米芾,刻意摹仿,写出的字洒脱不拘、雄健明快。
所以,本城虽也有不少书法家画家,他古润松倒也赫赫有名。只是他一个穷儒。官府士绅中的风雅之士,不屑接纳他为座上客,自然就对他熟视无睹了。
然而古润松这人性格豪放、倔强清高,对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向来嗤之以鼻,即使过着清贫的日子,也决不卑躬屈膝。
他卖字画并无定价,视购买者财力而定,有钱的多收,囊中羞涩者,则少收或不收。
这天,他带着七岁的独生子古山紫照例摆摊,一些字画放在席子上,供人选购。他则坐在一条矮几前,教儿子写字。
古山紫年虽幼,却已写得一手清秀的小楷,他五岁启蒙念书识字,两年来已读了不少文章诗词,平日伶牙俐齿,很受古润松喜爱。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字画,当为滇中一绝矣!”
父子俩正专心书字,忽闻一喑哑之声,抬头一看,却是一位面相清癯、脸色微紫的老僧正站在字画摊前。
老僧给予字画如此高的赞语,无疑又遇到了知音。
上下一打量,一身洁静袈裟却缀着补钉,加之相貌古奇,认定是有道高僧,当不是戏语。连忙从小凳上起立道:“大师谬赞,晚生随意涂鸦,怎敢当一个‘绝’字,惭愧惭愧,身无技能谋生,徒以此糊口耳,倒叫大师见笑了!”
紫面僧微微一笑:“出家人不打诳语,先生字画,不亚于当代名儒。”
古润松道:“不敢不敢,大师既如此抬举晚生,摊上字画只要不污大师清目,就请随意挑选,由晚生礼赠……”
“不可不可,老衲岂能随意取拿先生字画,出家人身无财物,只能以薄金相购,倒是委屈先生了!”
古山紫这时并未停下笔来,嘴里却道:“老菩萨不必谦让,爹爹平日大方得很,奉赠字画是常有之事,我娘常说:‘你爹只要遇到知音,锅里没米也不在乎,空着手回来可以大笔一挥,画饼充饥,让一家人吃饱的!’所以老菩萨尽管取吧!”
这番出自童稚之口的言语,活脱脱道出了古润松的为人和家中清贫而又不失谐趣的生活,使紫面僧和古润松先是一愣,继而大笑起来。
紫面僧见小儿边说边写,字迹仍然清秀端正,一丝不苟,人也长得隽秀聪慧,心中不由一动,好一个练武学文的良秀坯子。
古润松道:“大师可看中了哪一幅山水?或是……这样吧,让晚生猜一猜如何?”
紫面僧微笑道:“老衲欲挑一画,先生就请猜吧。”
古润松刚要说出自己所猜,哪知古山紫这小家伙又抢了先。
“老菩萨想必是相中了那幅普光殿山顶宝塔图,不知小子猜得对也不对?”
古润松奇道:“咦,山儿猜得与为父一样,不知大师以为然否?”
紫面僧也十分惊奇,道:“不错,老衲正是相中了这幅山水,只是令郎何以猜到呢?”
古润松道:“山儿,你如何猜的?”
古山紫放下了笔,仰起脸来,两只黑如墨晶的眼珠一转,答道:“摊上山水画中,只有一幅画寺庙,此画绝顶有塔,山形前出三支,后伸一支,就如鸡爪四趾,西北处又有龙雪山,鸡足山乃祖释迦大弟子迦叶大师修道之地,佛门中人,自会看中这幅画的,不知山儿说得对也不对?”
紫面僧不由暗赞,此儿当真绝顶聪明,于是笑道:“不错不错,正是老衲心意。”
古润松当即将此画取上案几,提笔问道:“大师法号如何称呼?”
古润松提笔写上敬赠字样,下面落下款。
紫面僧取出二两银子,还未开言便被古润松制住了:“大师且勿使晚生心意沾上铜臭。”
古润松道:“大师从何来,欲何往?”
“老衲一生遍游名山,只未到过滇黔,此次专程往鸡足山一游。”
“大师潇洒,令润松羡极!”
“山野之人,有如雨云,四处朝佛,以慰平生。先生笔下纵横,挥洒自如,尽收天下美景于一页之上,未始不如老衲潇洒耶?”
言毕,两人大笑。
古润松道:“今日得遇大师,也是有缘,且请舍下一酌如何?”
当即收拾小摊,将字画卷成一堆,用席子包了,引大师前往宅第。
古山紫跳跳蹦蹦跟在一旁,不时向紫面僧问长问短,活泼开朗。
紫面僧对他甚是喜爱,有问必答。
从大街拐进了一条小巷,巷中又套巷,来到一幢矮小的土宅前。
古山紫跳上去拍了拍门,嚷道:“娘,快开门,有贵客佳宾自远方来呢!”
遂听屋中有一清脆嗓音道:“来了来了!”两扇大门“呀”一声打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美貌妇人俏生生立在哪儿。
润松道:“夫人,治一席素斋,款待淳心大师。”
夫人向紫面僧行了礼,极为恭谨地请老僧人内。
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虽是土屋,倒也被主人扫洒得十分干净。
上房三间,侧房为厨,紫面僧被请到中间堂屋坐下。只见正面有条几。案上供奉着观音菩萨白瓷像。
谈谈说说,彼此十分投缘。
吃了上顿,又留吃下顿,当晚留宿。
一连三天,紫面僧被苦苦留住。
第四天,紫面僧坚持要走,说游鸡足山回来后再来盘桓。
临别,大师道:“老衲一生闲情逸致,不曾收徒,令郎与老衲也算有缘,欲收到门下,传其衣钵,不知施主可愿?”
夫人一惊,插言道:“大师美意,本是小儿之福。无奈古氏门中只此一脉,又系单传,若小儿出家为僧,岂不断了古家香火?”
紫面僧笑道:“夫人误会了,老衲并不让令郎出家,只是将老衲的一点武技,传给令郎罢了。
古润松大喜:“多谢大师,如此甚好,晚生手无缚鸡之力,常见不平之事而束手无策,若让小儿习得一身绝技,长大能文能武,就比晚生强多了!”
夫人笑道:“原来是习武练技,小妇人唐突大师了。不知大师要将小儿带往何处?一年间能见面否?”
“施主放心,老衲不将紫儿带往远处,就在附近觅个清静处便可。”
夫人最怕爱儿远去,闻言大喜,道:“县中五华山林木茂盛,平日游人不多,是个好去处。”
润松道:“不错,除五华山,还可到太华山,太华山离城较远,那才是个真正的好去处呢,等大师从鸡足山返回再作定论。”
紫面僧见两夫妇都愿让儿子学艺,心里十分高兴,当下辞别而去。
他哪里料到,等从鸡足山游罢归来。早已物是人非,古家已经败亡了。
就在紫面僧走后十多天,这天一清早,古润松卷好字画,正叫了山紫,准备出门摆摊。
此时突听有人敲门,古润松把门打开,却是衙门里的小官儿。
官儿道:“敢问先生可是古润松?”
润松道:“正是在下,爷台光临小舍,不知有何公干?”
官儿道:“布政使大人有请。”
润松一愣,布政使乃滇省最高行政官,怎么找到他这个平民百姓的家来了?便道:“在下一介草民,布政使大人招在下何事?”
官儿道:“下官只是奉命来请先生,内情并不知晓,还请先生快快上路。”
古润松惊奇已极,便匆匆换了件青衫,随差官出门。
门外早已备了小轿,差官则骑马,还有四个兵丁相随。
古润松钻进小轿,心里一直纳闷,想不出布政使大人招他的理由。他所能想出的,大概是凑巧看了他的字画,命他去画几幅山水什么的,以示风雅,其他还能有什么理由?
布政使司衙门在九龙池一带,小轿经过宏伟的衙门前并不停下,而是绕至后院,从一道大门进去。
只见园中花木扶疏,中间有一凉亭,小轿直到亭前停下。
古润松从轿中出来,早见一四十来岁的儒生从亭中走出。
差官道:“这位就是布政使大人!”说着抢上前躬身道:“启禀大人,古润松带到。”
布政使张志忠道:“先生不必多礼,请。”
润松祖上也是做官人家,到父亲一辈厌倦了官场,不再入仕,由于祖父两袖清风,所以也没有传下家业。
但穷虽穷矣,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家,因而润松见了布政使大人,也未惊慌失措。
当下答声:“有僭。”便往亭中去。
这亭子中间摆有一张小方桌,有四把檀木太师椅,主客二人遂坐下,自有家人送上香茗,然后随同其余仆役退开,远远站着侍候。
张志忠道:“久仰先生才名,只因冗事缠身,公务繁忙,未能前往拜谒,望先生鉴谅为幸!”
好个谦和的布政使大人,古润松忙道:“大人日理万机,岂有闲情,况古润松一介草民,才疏学浅,岂敢当得大人溢美之词?”
这时,一个年约五十来岁的老者,身着褐裳,倒背两手,从小径而来。
未到亭前便笑道:“古先生不必过谦,张大人一向求才如渴,只是上任不满两年,对贵省不熟悉,否则,早就便衣出访,拜望古先生的了。”
张志忠道:“这位是敝宅管事宗振武,先生住宅,还是宗管事打听到的呢。”
古润松又与宗管事见了礼。
坐下后,宗振武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对着古润松一扬:“七十二家士绅联名上告黔国公沐大人的上书,是出自古先生笔下么?”
古润松大惊,知道今日布政使大人招他来的用意了。
上告滇省最有权势的黔国公,这自然是提着脑袋才敢干的事。
一个月前,他毅然答应了士绅们捉笔代刀的请求,便有了大祸临门的准备。
他抑制住一时的慌乱,定下心神,道:“不错,此状正是晚生所写,晚生虽是一介书生,但平生最恨贪官污吏。黔国公沐总兵,身为国家重臣,不思报效朝廷,安抚黎民百姓,竟然依仗权势,在滇省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西郊石鼻里一带,何止良田万顷,黔国公非法掠夺田庄不说,还纵其爪牙阻截水源,独霸水利二十多年而无人敢予干涉。除此而外,还滥杀无辜……”
宗管事接口道:“藏匿罪犯,纵容江洋大盗,鱼肉良民,霸占民田,无论官民,遭其残害者无数……古先生,总兵大人的劣迹,在下与张大人早有耳闻,不劳先生详说。”
古润松冷笑道:“既如此,那倒是晚生饶舌了。不过,晚生斗胆请教布政使大人和管事先生,身为滇省大员,对沐氏的种种作为,难道只是听听说说就算完了么?”
张志忠道:“先生的意思下官明白,先生是指责下官官官相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不然,只是下官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宗管事道:“古先生,在下随张大人由浙至滇赴任,一到滇省,张大人便微服出访,由在下陪同,出人间巷大街、茶肆酒楼,对总兵大人的劣迹种种,听得不知多少。但张大人在国公之下,况沐氏在京宫中颇有称兄道弟的佳朋贵友,岂是一省之布政使治得了的?”
润松道:“不然,张大人官衔虽无国公高,但身为一省之行政长官,足可上奏皇上,弹劾沐氏。”
宗振武笑道:“先生,恕在下无礼,先生之说如同儿戏,当不了真的。因为,张大人等的奏章只怕还未递到朝廷,张大人就被革职查办、刀斧加身了!”
润松一愣:“竟敢如此嚣张?”
宗振武叹道:“沐氏朝中有人,一手遮天,个中情形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们还是先谈眼前的事吧。先生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正义凛然,直言不讳,秉笔直书,将沐府霸占水利、侵占民田的种种恶行,兼及滥杀无辜、残害百姓的罪孽,遍数不漏……”
张志忠接嘴道:“先生之忧国忘家、急公好义的一片丹心,跃然纸上,下官十分敬佩,故请管事暗里察访,欲与先生一会。”
古润松道:“大人过奖,还望大人秉公执法、除暴安良。”
“下官惭愧,以己之力,岂能撼山?但身为朝臣,食国家俸禄,又岂能坐视不管?但时机还未到来,不可妄动,否则白丢了身家性命。”
宗管事道:“今日请先生来,除了结识先生,还有一事相告,请先生今后不再提此事,也不再代人捉笔,一旦被沐府爪牙察觉,先生性命只怕不保。届时即使张大人出面相救,也难保先生脱出虎口。”
润松道:“石鼻里七十二家士绅,莫非也会遭灾!”
张大人道:“此书留在布政使司,只要不外传,七十二家士绅当可无虞。”
润松道:“此书一式两份,还有一份递交提刑按察使司衙门。”
张志忠大惊:“糟!先生危矣!”
宗管事也道:“不妙不妙,这状子若递到了提刑按察使赵大人那里,无疑是给沐府报信,得赶快想个办法才好!”
润松怒道:“怎么?难道专管地方刑法、监察的按察使,竟是个贪赃枉法、蝇营狗苟之辈么?”
张志忠叹道:“赵弭一来慑于黔国公的权势,二来只想官运亨通,凡有敢到按察使司控告黔国公的,无不被他以‘诬告朝廷命官’下狱治罪的。”
宗管事道:“先生在何处有亲眷?不妨举家暂避一时。”
张志忠道:“这走不是办法,下官有一两全其美之法,不知先生可愿答应。”
“请大人明示。”
“下官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小儿已九岁,但府中亲眷及下人子女甚多,请先生移驾府中,设一教席,岂不两便?”
古润松明白,张大人一片好心,欲将他置于府中以保性命。但他对官府中人有些顾忌,加之住在别人家里也不是长法,所以一时委决不下,没有回答。
古润松道:“住在大人官府,只恐不便。”
张大人道:“先生不必多虑,下官命人在花园腾出几间房屋,既可充学堂,又可让先生一家居住,平日不准府中人来打扰。至于任教期限,由先生自定,决不敢相强。”
古润松听大人如此说,心里有些活动,但道:“晚生回家后与拙荆商定,再答复大人。”
张志忠道:“可以可以,不过先生最好不要耽搁时间长了,以防不测。”
进府任教一事,就议到此。
接下来谈些字画之类的雅话,张大人的书法也颇有根底,二人谈得极为投契,倒是那宗管事对此所知甚少,只在一旁凑趣。
谈到高兴处,张大人命人取来笔墨纸张,请古润松当场挥毫作画题字。
古润松画了一幅滇池海景,太华山西岸壁立,只见月日朗霁,水光映澈,远看太华,犹似一美人侧卧池畔,典雅清丽,令人遐思。
一气画完,书上张大人官衔,下落字款以题赠。
张志忠赞叹不已,命人找画匠裱糊,以作珍品留之传代。随即又命摆席,三人对饮,直谈了一天,傍晚才归。
第二日,张大人又命差官去请古润松。不一会,差官匆匆忙忙赶回禀报道:“古润松不知犯了什么法,昨夜被按察使司的人给抓去了,连家也封了呢。”
张志忠又惊又怒,忙命差官持布政使名帖,到离府不远的按察使司索人。差官刚走,他又将他叫回,命备大轿,亲往按察使府。
宗振武闻讯赶来,陪同张大人前往。
按察使司在九龙池北侧,与布政使司隔池相望。半个时辰不到,就到了彼处。
张志忠下轿,按察使赵弭早已闻讯出来迎接,两人相互见礼寒喧,请至内堂议事。
赵弭四十来岁,人倒生得端正,只是一腔存着坏水。
他首先开言道:“张大人光临,不知有何吩咐?”
张志忠道:“赵大人,本官直说了吧,昨夜闻听按察使司捉了一位名儒,不知可有此事?望明告。”
赵弭故作惊讶:“张大人哪里来的消息?本城名儒彼此都是相识之人,下官岂能将他入绳之下狱?只怕大人误听传言了吧。”
“误听还不至于,昨夜捉的人不是叫古润松么?他若不配称名儒,还有谁配称?”
“啊,原来是古润松,那个摆摊卖字画的。不错,昨夜确曾捉了此人。”
“古先生所犯何罪!”
“此人胆大妄为,自恃颇有文才,竟敢捉笔代刀,诬告……”
“慢,此人捉笔代刀,那就是替别人写状子了?”
“是,张大人,此人诬告沐大人……”
“慢,不是替人写状子么?”
“虽是替人写状,但沐大人……”
“摆字摊糊口,替人写状也就不足为奇,怎么就有了罪呢?”
“大人,沐大人非比普通人物,身为平民百姓,怎敢替人写这样的状子……”
“赵大人,古润松不过一个穷儒,卖字画为生,代人书状,谋生而已。”
“张大人,此人所写,恶毒异常……”
“赵大人,此人昨日已被本官聘为西席,赵大人就高抬贵手,不必过份了吧!”
“张大人,请恕下官不知之罪,若下官知道古润松已被聘为大人西席,自不会将他逮捕下狱。”
张志忠心一松,道:“那就请赵大人看本官薄面,将古先生放了吧。”
赵弭却将头一摇,眉头一皱,面有难色:“张大人,此事下官实难从命!”
张志忠面色一沉:“如此说来,赵大人是有意给本官难堪了?”
赵弭道:“哪儿的话,这古润松激怒了沐大人,已被总兵府派人提去,下官已无能为力,张大人只好到总兵府要人了。”
这话的讥讽之意,谁都听得出来。
张志忠又惊又怒,人已被提到总兵府,他留此何益,便匆匆打道回府。
他与宗振武商议了一阵,决定由宗振武夜中潜入察按府第,查明古润松一家下落。
宗振武乃山东名师,江湖人称神炮锤,张志忠在山东任府台时与之相识,遂敦请宗振武来府管事,以御盗贼强人的报复。宗振武念其为官清廉,公正不阿,遂结为莫逆之交,在私下里以兄弟相称。
当夜宗振武背插单刀,穿一套黑色紧身夜行衣,直奔提刑按察使司衙门。
按察使赵弭在衙门后花园内,宗振武从园墙跃入,此时不过二更,园中小楼灯火通明,园内有兵丁巡逻。
他跃上紧挨小楼的一株树上,从窗口望得见楼室中情景。
只见赵弭正拥着四个妻妾小酌,说说笑笑,得意已极。
“知道么,大爷今日又立一功!”
“哟,什么功啊?”
“石鼻里七十二家乡坤,居然联名上告沐总兵大人,而且竟然把状子递到按察使司来了,大爷我把写状纸的人找到,送交总兵大人处置去了,总兵大人对我大加褒奖呢!”
“啊哟,大爷,不把那七十二家乡绅捉起来,干么要捉个写状子的人呢?莫非是他牵头?”
“错了,此人只是写写状子而已。”
“咦,那又为何……”
“你们妇道人家哪里知道,这状子自来由人写成,因人而异,有的写得条理分明,有的写得含混不清,有的罗列事实,干干巴巴,唯独这份状纸,嘿嘿,却是笔锋犀利、慷慨激昂、说理入骨三分,气势恢宏,叫人看了怦然心动,要是呈到朝中,对总兵大人可是有些不便呢。所以,总兵大人见到状纸之后,定要大爷将书写之人捉来处死!”
“这人是谁啊,莫非吃了豹了胆?”
“这是个卖画为生的穷儒,手下差役足足查了月余,才知他是捉笔之人。一家三口,嘿嘿,只怕活不过明天了呢!”
“咳,这人也真是的,空有一肚子的书,却不知道总兵大人是得罪不起的么?”
“好啦好啦,别替旁人担忧,这叫自作自受,岂能怪他人哉!”
“大爷,总兵老爷会给什么奖赏呀!”
“奖赏么不曾给,不过嘛,总兵大人保举大爷以后任布政使,主管一省之政务……”
古润松一家既已送到总兵府,宗振武不再继续听下去,急匆匆直奔西门。
他丝毫没有发觉,后面尾随着一条黑影。
来到总兵府后院小巷,他不免有些犹豫。
闻听总兵府内除了官兵之外,还有不少江湖黑白两道人物,其中不乏顶尖高手。
这沐朝弼在滇称霸,一来仗着祖上的荫庇,世袭黔国公兼领总兵之职,在滇省无人再出其右,就是朝廷他也有许多掌握极大权势的朋友,二来便是广招武林黑白两道高手,不便由官府处置的人和事,就由这些武林暗中进行,来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无头案,叫你无法查核。
由于他为人暴虐残忍,也怕仇家暗算,所以对江湖人物十分礼遇。若干年来,总兵府进进出出,招有不少好手。特别是在中原内地作了大案的巨盗,或是杀孽太重被武林正道共同追杀的魔头,他们要是无路可走遁入云南投到总兵府,他都一概结纳包庇,藏于府中,为他所用。
宗振武势单力孤,定了定心神,从小巷中一跃而入。
墙下芳草萋萋,他伏于地上,等着巡逻过来,打算点倒一个士兵,查问古氏关在何处。
不久,四盏灯笼从墙对面的树荫下,闪着一团团昏黄的光亮,渐渐走近了他藏身之地。
他等到五名兵丁刚走到离他十步远时,一下从草中蹿出,不等兵丁叫喊,早点倒了他们,然后将灯灭了。
拖一个到墙角,拍开哑穴,问他古氏一家关在何处。
兵丁战战兢兢回答,听说就关在靠马厩一角的地牢里。
“是街上卖字画的儒生么?”
“是,是的,小人听说,两口被捉来后……”
“不对,是三口。”
“小、小人只听说,是两、两口,据说、还有、有一个小孩,却逃、逃走了,没有、捉到,现还在、在沿街查找呢!”
宗振武点了他睡穴,沿墙根向对面的马厩掠去。
这园子十分宽大,两边相距不下五十丈。
掠到马厩,才发觉马厩后面又有一道围墙,围墙筑有望楼,只不过楼并不高,只伸出围墙三尺许,了望的士兵器出上半身,多半不是对着墙外而是对着墙内。
宗振武明白,是监视墙内关押的犯人的。
望楼悬着几盏风灯,把墙外二三丈的地方照得通明。
这便是总兵私设的监狱。其中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
宗振武顺着墙角来到距哨楼四丈外停下,猛提了口真气,如一只苍鹰,向岗楼上的卫兵扑去,一下就把他点倒瘫在地上。
可惜,岗楼对面五丈的另一座岗楼,上面也立着个卫兵,清楚地望见了宗振武飞身而至的情景,惊得他立即顺手抄起放在石台上的锣,“咣咣咣咣”狠命地敲打起来。
宗振武临危不乱,审问点倒的士兵:“快说!古润松夫妇关在里面么?”
士兵吓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道:“昨、昨夜、就、处、处、处死了……”
“真的?小心大爷要了你的命!”宗振武一手捏住他喉头威胁道。
“真、真的,小,小、小的要是、有有半半句谎言,定叫五五五雷轰、轰……”
不等他说完,宗振武点了他死穴,怕他第二日泄露出有夜行人来找古家的事,以免祸及张大人。
锣声慌乱地响着,顿时狱墙内人声鼎沸,宗振武赶忙一长身,从岗楼上往外跃出。
可是,早已有高手尾追而至。
脑后一阵风声,他知有兵刃袭到,急忙一个侧跃,躲开一击。就这么一耽搁,前头就被堵了路。
宗振武面上蒙着黑巾,不怕被人认出,他“嗖”地从肩后扯出朴刀,大吼一声向挡住去路的三个江湖汉子攻击。
那三人各持一柄鬼头刀,毫不示弱地迎了上来,而他身后又有几人向他出招。
他来不及再攻对方,一把朴刀舞起,遮挡架格,抵住了七件兵刃的攻击。
七件兵刃有刀有剑,有软有硬,而且全是好手,宗振武武艺虽高,但双拳难敌四手,七个人的轮番进攻,迫得他手忙脚乱。
站在斗场不远的,还有一个相貌凶恶的五旬壮汉,正是他在发号施令,指挥从园内和从狱墙内赶出来的看家护院、卫士兵丁。
“抓活的!别让他走了!”那壮汉喝道。
若不是这道命令,进攻的七人不敢伤他,他早就饮刃倒下。
眼看情势危急,他已无法冲出重围,便想杀到离狱墙十来丈的花园围墙处越墙逃走,但沿墙根已站了不下三十个持硬弩的箭手。他纵然能冲到那儿,也逃不出三十支机匣弩的攻击。眼看已无出路,他把心一横,决心拼一个够本,拼两个就赚了他一个。于是,提起八成功力,用的全是拼命招数,要与敌来个同归于尽。围攻他的七人,既不能把他一刀杀了,又要保住自家的一条命,只好放松了进攻,以防守游斗去消耗他的真力。
这样一来,宗振武就惨了。
他想毙敌一两个,可人家一攻就退,你要是想进一步追击,后面的人又向你攻来,等你回身去拼杀,他们又立即离开。
他明白了对手的战术,可又无可奈何。
正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了一阵像蚊蚋似的语声:“壮士不必恋战,速向弓弩手处退却!”
与此同时,挡在他正面的三人,忽然一个个兵刃脱手,如木雕菩萨般站立不动了。
哪里还顾得上思索,他当即一冲而过,只见墙根脚的持弩兵丁并未施放弩箭,任由他从他们头上越过,出了院墙。他明白,今夜幸遇高手相救,弓弩手已被制住。
越出院墙,便拼命向街巷飞蹿,也不听见有人追来,这自然又是高人替他挡了追兵。
回到布政使司署,张志忠还未睡觉,正焦急地等着他归来。
见面后一说情况,张志忠不禁喟然长叹,惭愧身为一省布政使,居然连个穷儒都保护不了。又听说古家独子未被抓获,便让宗振武天亮后派人到巷中寻找,务必将此子带回布政使司署抚养。
第二日,除了派出大量人员,宗管事也亲自到街肆中查访,结果无望归来。
哪知张志忠却得了消息,这是查访人员亲自目睹的场面。
这三人奉命一早出府,沿南城查找,在城门附近,却听到一阵小儿哭喊声。
三人听听像是从一条小巷传出,便向巷里奔去。走不到三丈,就见五个如狼似虎的沐家校尉,揪住一个七岁小孩,连拖带拽,正往巷口走去。
三人中一人上前道:“大爷,这小儿……”
为首的校尉以为他是平民百姓,牛眼一瞪:“他妈的!想管总兵府的闲事么?这小子是要犯古润松的小儿,你们想怎的?”古山紫趁他说话当儿,猛在他手上咬了一口,痛得这厮怪叫了起来,一只大手不由放开了小儿衣领。
古山紫立即奔逃,但不出三步又被校尉抓住了:“妈的,你敢咬大爷,大爷要了你的命!”
他提起斗大拳头,朝古山紫的小脑袋瓜砸去。这一拳若是打个正着,小小的古山紫哪里还会有命?
说来让人不相信,这大汉一拳只砸了一半,离小儿头上还有尺余,便停住不动了。
原来,这校尉是吓唬他呢!
可是,不对了,小儿拔脚飞奔,他却不闻不问,依然举着个拳头,这又是吓唬谁呢?
岂但这校尉怪样令人不解,就是其余四个校尉也都呆站着旁观,也不追赶。
三人不禁大奇,还没明白过来,只见一个瘦干的老和尚,也不知从何而来,突然间就到了小儿面前,一把将他抱起,眼一眨便不见了。吓得三人目瞪口呆,赶紧作揖念佛。
这不是菩萨显灵又是什么?
听完张大人的叙述,宗振武叹道:“在下昨夜就遇到高人暗助,古家小子有福,被高人救走,异日学得一身上乘功夫回来报仇,当慰古先生夫妇之灵!”
至于古山紫怎么会逃出沐府爪牙之手,他们却是弄不明白。
原来,那夜古氏一家正在酣睡,忽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听门外气势汹汹的阵势,古润松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还是白天在布政使家由张大人点醒的,只是没料到会来得如此之快。傍晚他回来后,与夫人商议半天,夫人竭力主张到布政使家去任教,以避祸端。这本是决定好的事。哪知天不由人,半夜就来了灾星。古润松当机立断,命古山紫从后窗逃走,不准回头。
古山紫在门外气势汹汹的嚷叫声中,又在父母的催逼之下,惶惶然不知何事,便流着泪跳出后窗,沿巷道直往外奔。
黑夜里行走,他心胆俱寒,不知不觉就奔到了南城一条小巷中,由于疲乏过度,便靠在一家门坊上睡着了。
天亮后,他不知该往何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自然又想起回家。
还未走到家门,就遇见了邻居黄老伯,黄老伯一见大惊,忙将他带到巷内,告诉他家中遭了灾祸,沐府兵丁、按察使署的兵丁正在查找他,叫他快快离城,找个乡下人家暂躲几天,还给了他一些铜钱。
他并不明白到底家中出了何事,只知道不能回家,便哭着又朝南门走。
可是,出城又到何处去呢?
他不敢去。
除了买点零食充饥,他便在小巷里呆着,心里既恐惧又悲苦。
他正想走出巷道,不料却遇到了五个校尉。校尉们细问他的来历,他回答支吾,又经几番恐吓欺诈,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分,于是被拖起就走。
至于救他的老和尚,除了紫面僧又能是谁?他从鸡足山返回,一到古润松家,就见门上的封条,大惊之下,向街坊邻里打听到了情况,夜间便往按擦使司府第去探查,正好发现了宗振武潜在树上,后又尾随他去了总兵府,并助了他一臂之力。
次日,他找到了古山紫并把他带到了西北沙州沙南山,在那里授业传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