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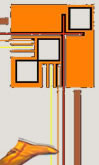 |
 |
|
 |
 |
|
第 六 章 父债子偿
|
|
杨柳随风飘汤,荷花绽放清香,一抹绿意笼罩着位于交通要道上的邺城,时值春暖花开的烂漫季节。
位于邺城东胡同底的宅子,建构宏伟,门前雄狮张牙舞爪,神态飞扬。大门朱漆新□,色泽亮丽动人。门上茶杯口大小的铜钉闪闪发亮,门顶匾额上写着荆府二字,比划雄劲有力,气势磅礴。大宅门前两个仆役手持着竹拨扫帚,用力的将门前枯黄落叶扫除。
突然间一匹骏马疾奔而至,马匹全身乌黑,马勒脚蹬都是烂银打造,鞍上之人年约三十多岁,身穿蓝黑长袍,头带白翎羽帽,腰间系着一柄长剑,腰□笔直挺立,脸上显现出英悍之气。
门前仆人见马匹站定,急忙上前牵住马□,哈腰躬身道:“李总捕头。”
李飞是邺城府衙总捕头,接位已逾五载,是荆铁山卸任后第二任的总捕头。荆铁山担任总捕头有八年之久,其间邺城夜不闭户,一片安乐升平之相。其中朱亦谋太守勤政爱民,为官廉洁,居功蹶伟。但是荆铁山铁捕无敌,宵小盗匪闻风而逃,功劳也是不小。韩云娘深懂经营之道,数年间荆家行商致富,本来不用荆铁山继续任职,但是朱亦谋倚为重任,所以荆铁山一直等到朱亦谋告老后才辞去公职,由于其威名远播,后两任总捕头受其庇荫,这段时间邺城还算平静。
荆府大堂之上,荆铁山坐在太师椅中,正在闭目沈思。荆铁山虽然人到中年,但是身体强健,精力充沛,不输给年轻小伙子。但是韩云娘两年之前身染重疾,久病不愈,荆铁山虽然遍寻名医,韩云娘依旧没有起色。夫妻两人结□越久,情意越深。荆铁山忧心爱妻病情,眉头紧皱,面有愁容,不复昔日英姿飒飒,豪迈爽朗的神情。
门外仆人领着李飞进来,荆铁山见李飞来到,纵使心情沈重,也不能给小老弟脸色看。
于是荆铁山强颜欢笑,站起身来拱手笑道:“李老弟,这么久才来看看老哥哥,是不是嫌弃老哥哥啊!”
李飞当然知道荆府状况,本来不应该再来麻烦荆铁山的,只是此事关系重大,不得不硬着头皮前来。
李飞回礼笑道:“小弟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专程前来麻烦荆大哥,我这总捕头干的真是汗颜。”
荆铁山右手一请道:“李老弟请坐。”荆铁山说完扬首道:“阿福,奉茶!”
李飞忙道:“荆大哥不必客气,我这儿坐着行了。”
两人寒暄一番,这才就坐。
荆铁山心中有底,面色凝重的开口道:“李老弟,你今日是否为了荥阳之事而来?”
李飞点头道:“荆大哥消息灵通,邺城有您真是万幸。”
荆铁山微微一笑道:“不用客套,京里派了按察使到各州郡视察,身边带着名震京城的四大名补,消息早已传开。你不用多说,我知道怎么做。”
李飞得到荆铁山允诺,面露喜色,急忙起身一揖道:“多谢荆大哥相助,否则小弟难逃此劫。”李飞心中狂喜,语音竟然微微颤抖。
荆铁山右手往前一阻,道:“邺城平安无事,是百姓之福,小事一桩,不用多礼。”
李飞面色甚愉的和荆铁山谈了一会儿,起身告辞。
荆铁山目送李飞离去,脸上笑容骤失,心情又沈重起来。
李飞走到大门前,一名锦衣少年,年约十八九岁,面貌英挺俊秀,剑眉入格,眼眸精光四射,只是眉宇之间,隐含着淡淡忧虑。
那少年看到李飞走来,展颜一笑,道:“李叔叔,您来找我爹啊?怎么不多坐一会儿?”
李飞微笑道:“我有事麻烦你爹,怎好多叨扰片刻,天云,你代你爹去收租啊?”
荆天云颔首道:“对啊!李叔叔有空常来坐坐嘛!”
李飞客气的道:“一定一定,我先走了。”
荆天云微笑着挥手目送李飞离去。
李飞离去时摇头叹息道:“这孩子早几年转性就好了,可惜现在迟了点。”
荆天云是荆铁山和韩云娘唯一的儿子。荆天云从小受到夫妻两人宠爱,顽劣不堪。兼之朱亦谋夫妻又是荆铁山夫妻的义父母,所以朱亦谋夫妻当荆天云是孙子,这荆朱两人在邺城权倾一方,荆天云更是目中无人。所以荆天云不到十岁,就已经是邺城恶名昭彰的小霸王了。但是荆韩两人长年布施行善,邺城人都看在两人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一直到韩云娘病重,街头巷尾盛传是荆天云克死自己母亲。荆天云本来嗤之以鼻但是母亲一病不起却是事实。荆天云心中忽然大彻,一改往日杰傲不训的脾气,开始学着父亲为人处事的方式,每日循规蹈矩,安守本分。
荆铁山见儿子走了进来,道:“你又把租金发还回去了,是吗?”
荆天云面有愧色,垂首道:“是的。爹。”
荆铁山叹口气道:“施有所求,这叫市恩。”
荆天云嚅喏道:“对不起,孩儿错了。”
荆铁山微笑道:“算了,我又没怪你,你的孝心,你娘和我都很清楚。”
荆天云想起刚才李飞曾到来,问道:“爹,李叔叔来做什么?”
荆铁山起身踱步道:“上个月荥阳县一夕死了三百多人,传说是吃了毒盐而死。荥阳离京城近,消息传到皇上那儿,皇上大为震怒,派了专使严加查办。这各州郡莫不兢兢战战摒息以待,丝毫不敢马虎。”
荆天云想了一下,道:“李叔叔要爹爹抓些盐枭交差是吗?”
荆铁山哈哈一笑,右手一拍荆天云肩膀道:“错。”
荆天云眉头一皱,问道:“不是这样,嗯……喔,我知道了。”
荆天云豁然明白,道:“李叔叔请爹爹警告那些盐枭暂时销声匿迹,等风声过了,再出来活动,是不是这样?”
荆铁山满意的点点头,道:“你学的很快。”
荆铁山解释道:“如果故意抓盐枭交差,则朝廷必定会责怪以前执法不力,而且这样做又得罪那些人。假设按察使真的抓到盐枭,李捕头可以硬说那是从其它城镇逃来的。其实盐枭这行,利润高,干的是杀头的生意,常人牵扯不得。”
汉朝实施多项产品公卖,盐是其中一种。当初公孙弘以目之所及,皆为王土,深山大泽,皆为国库为由,实施专卖被指为与民争利。因为盐是民生必需品,所以争议最大。盐大概分为海盐,岩盐,湖盐三种。海盐因为取得容易又生产量大,所以市面上买卖的大多是海盐。但是内陆因不靠海,所以衍生出偷运海盐到内地贩售情事,因为产地和当地价格相差数十倍,所以利润可观。但是盐因为是公卖,私下贩售罪同盗窃国库,律法上是唯一死刑。所以盐枭大多是强悍的盗贼,或是视死如归的贫户。
就因为如此,一般衙门捕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理就不理。但是盐枭毕竟是匪徒,有些盐枭为了增加质量,在盐中掺了杂质,有些杂质是有毒的,所以荥阳的惨事,有可能是百姓贪图便宜,吃了有毒的盐而死。
荆天云摇头道:“这些人真是人不浅,爹,我先进去看娘。”
荆铁山面色一沉,道:“你娘好些天没见着你,嘴里直念着,你快去吧。”
荆天云暂别父亲后,举步往西厢房而去。
韩云娘病□久卧,脸颊深陷,骨瘦如材,尤其长时间未出房门,脸色苍白的吓人。
荆天云来到母亲床前,握着韩云娘的手,轻声道:“娘,我是云儿,我回来了。韩云娘听到声音,勉强的睁开眼睛,嘴早微微一扬,气若游丝的道:“平安回来就好。”
荆天云见母亲日渐憔悴,眼眶不由的红了起来。
此时从门外走进来一名少女,手上捧着脸盆,年约十五六岁,雪白的脸庞,眉弯嘴小,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头挽双鬟,生的秀丽绝伦。
荆天云见那少女进来,问道:“巧儿,你服侍我娘吃药了没?”
巧儿见到荆天云,□首低垂,道:“启禀少爷,夫人已经服过药了。”
荆天云低头在母亲额头上一吻,道:“娘,您多休息,孩儿不吵您了。”
荆天云转身走了出去,经过巧儿身边时,停下脚步,道:“巧儿,我娘就麻烦你了。”
巧儿头垂的更低,小声道:“奴婢知道。”
过了一会儿,荆铁山走了进来。巧儿屈身一福,道:“老爷。”
荆铁山右手一挥,要巧儿出去。
等到巧儿出去后,荆铁山将韩云娘扶起靠在胸前,道:“时间好像不多了,我想是该交代事情的时候了。”
韩云娘睁开眼睛,双眼因为久病的缘故,眼白显现暗黄色。
韩云娘无力的靠在丈夫胸前,道:“云儿还小,他需要你。”
荆铁山微笑道:“天云不小了,我当年这个年纪,已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挫敌无数了。”
韩云娘摇头道:“云儿怎能跟你比,他从来没吃过苦,需要人帮他的。”
荆铁山轻抚着韩云娘乾涩的头发道:“这一年来他表现得很好,很有男人的气魄,我们该放心让他自由飞翔了。”
韩云娘哽咽的道:“这个家还需要你。”
荆铁山红了眼眶道:“我说过不论在何时何地,我都不会离开你的,不是吗?”
韩云娘待要再说,荆铁山语气坚决的道:“这事儿没的商量。何况”荆铁山语气一转,柔声道:“多活这些年我们都该满意了,等我们走后,义父会照顾天云的。”
韩云娘知道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丈夫的心意,心中既是情意缠绵,又是伤悲不已,眼泪不由的潸潸流下。
荆天云到帐房将帐册入库后,步履蹒跚的回到自己的房间。房中一支大红蜡烛,照的满室生春。床上白色珠罗纱帐,轻缚在床边。床前桌上摆着一张雕花石砚,笔筒中插满了大大小小六七枝笔。壁上挂了一幅飞龙猛虎博的泼墨画。荆天云从墙柜中取出乾净衣衫,将身上的脏衣服换下。
忽然门上叩叩两声,仆人小石子在门外说道:“老爷请少爷即刻到夫人房中。”
荆天云心中略感讶异,父亲有什么事这么急着找自己,于是匆匆回答道:“等我换好衣服,马上就去。”
荆铁山看着儿子急急忙忙到来,身上衣衫尚未整齐,他心里暗道:“这样的孩子,我走的安心。”
荆铁山脸色严肃,道:“坐下吧,我有事要告诉你。”
荆天云看着父母亲的眼神,感觉到气氛不对,虽然坐下,但是如坐针毡的不安使的他打破沈默道:“爹,娘,您找孩儿有事吗?”
荆铁山慈祥的看着荆天云道:“有一件事埋藏在我和你娘亲心里近二十年了,今天若非逼不得已,我也不会告诉你。”
韩云娘知道荆铁山正在交代后事,心头一酸,将头偏了过去,眼泪又流了下来。
荆天云看见母亲伤痛的模样,心中蓦然明白现在情势,道:“爹,有什么事等娘病好了再说吧。”
荆铁山微笑道:“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云娘,我们孩子多聪明。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韩云娘难掩哀痛,紧闭双唇,避不答话。
荆天云霍然起身道:“爹,娘没事的,我们再去请高明的大夫,一定。一定可以治好娘的病。”
荆铁山左手轻挥着要荆天云坐下,道:“我师父说今年是我的劫数,原本我以为是我自己,没想到是你母亲。天意如此,人力岂能抗衡。孩子,父亲无用,有件事要你替我去办。”
荆天云按耐住心中的恐惧,只感到自己四肢不听使唤的颤抖,嘶声道:“爹,您千万不要放弃。”
荆铁山长吁一口气,缓缓道:“你静静的听我说,我和你娘本来住在曲阜,当年我……”
窗外日沉月起,月光轻轻的□在地面上。家家户户亮起烛光,正是辛勤一天后难得的休憩时光。
荆铁山一口气将事情说个分明,虽然这担子压在不经人事的儿子身上显的沈重,但是他是荆家唯一的传人,无论如何这责任都要他来扛。
荆天云听完父亲的话后,心情异常平静,道:“父亲要孩儿照顾外祖父,想法子补偿小沛梁家,孩儿一定遵从。”
荆铁山颔首道:“你能明白就好。虽然我时时注意着你外祖父和梁家的情况,但是我始终提不起勇气去见他们。本来在你及冠后,我和你母亲想回去一趟,可是,唉……”
荆天云抬头望着父亲,烛光柔和的照在荆铁山脸上,原本刚□分明的轮廓显的松弛无力,一时之间父亲似乎老了十多岁。荆天云从小对父亲的映象就是永远豪气干云,意气风发。在众多认识的人中,只有父亲重情重意,内外兼顾,好似完人一般。自己永远比不上父亲,他有了这个想法,索性自暴自弃,惹的家中无一日安宁。只是现在眼前的父亲,却如此心灰意冷,甘于天命。
荆天云胸中忽然感觉到热血汹涌,豪气顿生,他起身坚毅果决的道:“父亲母亲养我育我十九年,我却只当了两年荆家子弟,若不能报答亲恩,孩儿枉生为人。”
荆铁山闻言面露喜色,大笑道:“一朝闻道百花齐放,云娘,你闻到满室馨香没有?”
韩云娘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心想:“我这一生有生死不渝的丈夫,孝顺懂事的孩子,还有什么好遗憾呢?”
韩云娘衔着泪水,道:“云儿,你外祖父还要你多担点心儿。”
荆天云双脚跪地,磕头泣道:“爹娘请放心,孩儿一定竭尽所能。孩儿下辈子,一定还要作爹娘的孩子。”
荆铁山深情内敛,仅仅点头称许。韩云娘听到儿子心中真情意,忍不住泪水滚滚而下。
荆铁山感觉贴在身上的韩云娘心情激动,生怕韩云娘因此病情加重,因此忙着对荆天云道:“天云,你先出去吧,我和你母亲还有些体己话儿说。”
荆天云离开韩云娘房间,双眼含着泪水到了大厅。忽然小石子从门外急急跑来,道:
“少爷,有个老道士要找老爷。”
荆天云心中一凛,忙道:“你快去请我爹爹。我去门口看看。”
两人分头而行,荆天云来到大门前,一个三髻道人背对着大门,身穿青色道服满头银丝,一柄拂尘斜挂身后,尘尾迎风飘起,显得出尘不染。
荆天云见那道人气势脱尘绝俗,不敢怠慢,上前拱手道:“请问道长法号,找我爹爹有何要事?”
那道人闻言转身,嘴角一扬,道:“生死攸关之事。”
荆天云看清那道人长相,眉发雪白,须长三尺,面容和蔼,虽然年纪已有七八十岁,但是步伐轻盈,双眸隐含柔和晶莹之意,显然内力相当深厚。
荆天云心中立刻想到一人,他毕恭毕敬的道:“请问道长是……”
荆天云话未说完,身后一阵劲风袭到,荆天云一惊,往旁边一闪,回头却见父亲跪在地上,他心中有数,接着跪倒道:“徒孙拜见师组爷爷。”
来人正是三绝真人。三绝真人通晓天机,他早知荆铁山今年劫数,此刻时机已到,三绝真人这才现身相见。
荆铁山见师父风采依旧,身轻体健,激动的跪地伏拜道:“弟子好久不见师父,心里想的紧。今日见师父金体康安,不胜欣喜。”
了尘右手捻须,面容慈祥的笑了笑,道:“进去再说吧。”
荆铁山父子欣喜若狂,恭迎三绝真人入内。了尘往太师椅一坐,见荆铁山站立下首,双手轻拂,道:“你们两人也坐下吧。”
荆天云见荆铁山点点头,回身对着惊讶不已的小石子道:“你快要厨房里准备素斋,还有,准备上茶。”
荆铁山右手一拉要荆天云坐在下首,接着说道:“师父这些年云游四海,弟子未能尽伺奉之职,深感不安。徒儿请起师父一定要在这儿稍歇,让徒儿尽尽孝道。了尘微笑道:“打扰是一定要的,不过…”了尘话未说完,右手从怀中拿出一颗橘黄色的珠子道:“这颗避神珠,当初就要给你的,谁知你硬是不要,今日总算物归原主了。”
荆铁山一见此珠,泪水直滚而下。他上前跪下双手高举,将避神珠接在手中。荆铁山的双手因为兴奋过度而颤抖着。
了尘叹息道:“生死命也,万劫轮回无止无尽。关山易度,情关难破。若非你这些年行善积德,这因缘也落不到你的头上。”
荆铁山泪水滴在地上,前来奉茶的小石子看的一愣一愣的,因为坚毅刚强的荆铁山,从来没在众人面前示弱。可是了尘就像他的父亲一般,什么心思都被了尘一眼看透,既然遮掩无用,荆铁山强忍的情绪如山洪爆发,狂奔不止。
荆天云见状亦是骇然,此时了尘两眼看着荆天云,荆天云感觉两到寒光直射入心田,全身起了一阵寒战。
了尘道:“你是铁山的儿子,叫天云是吗?”
荆天云听了尘问起,急忙起身跪倒。了尘颐首一笑,荆天云身前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将荆天云撑住,荆天云双膝一弯竟然跪不下去。
荆天云心中惊异师祖惊人的内力,可是身形未动,劲力远及二丈之外,这功夫令荆天云感到不可思议,心想师祖人称三绝真人,果然名不虚传。
了尘点点头道:“资质不错,不过命带桃花,灾噩难解。”
荆铁山闻言一惊,抬头问道:“师父,您老人家说我孩子多灾多难吗?”
了尘见荆铁山惊慌的模样,起身右手一拍荆铁山肩膀,道:“运命有如马入夹道,不得不行。先别说这个,你将避神珠混着温水给你夫人下吧。”
荆铁山心中大喜,叩谢师恩后急忙大步跑回夫人房中。
荆天云本来要随着父亲而去,了尘却示意要他留下。
荆天云战战兢兢的垂手而立,了尘语气淡淡的道:“你坐下吧。”
荆天云顺意的坐下,可是他心中担忧母亲的情况,又惶惶不知了尘为何要留下自己,脸上表情自然有些尴尬无礼,坐立难安。
了尘解释道道:“这避神珠服了以后全身淌汗,必须全身褪去衣衫,再以内力在周身按摩,疏血活脉。旁人不宜观之。”
荆天云闻言大悟,只是他被看穿心事,脸上惭愧的表情显露无遗。
了尘微笑的无言看着荆天云,大厅中几乎可闻落尘之声。荆天云感觉了尘目光如炬,直要将自己燃烧透底,不由的浑身都热了起来。
正好此时巧儿从偏门中进来,荆天云见有人到来,松了一口气。
荆天云趁机转头问巧儿道:“巧儿,我爹娘还好吗?”
巧儿低头回答道:“奴婢不知。”事实上荆铁山一进夫人房间便要巧儿离开,所以巧儿根本不知发生何事,她到大厅之中看到了尘时也是楞了一下。
了尘看了荆天云的面相,忽然喟然叹道:“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
神虽王,不善也。”
荆天云闻言一愣,心想师祖是在说我吗?他思索一下后回答道:“德厚信□,未达人气,民闻不争,未达人心。夫天地之化,立天地而不足矣。”
了尘哈哈一笑,反手抽出拂尘起身,轻轻挥□道:“萧然尘俗思民意,飘飘仙家虚若谷。”
荆天云回答道:“碧落黄泉下,飘渺人间里。”
了尘潇□的走到荆天云面前,仔细端详了一下,道:“凡事切莫强求,该放则放。”
荆天云心中明白,恭敬的回答道:“行所当行,止于当止。”
了尘听了荆天云的话,脸上一股凄凉萧索之意。了尘抬头瞑思了一会儿,道:“万事皆有缘法,你自己要小心谨慎啊!”
荆天云听了尘语出惊人,心中惶恐不已,急忙跪下道:“师祖训示,徒孙必奉行不渝。”
了尘摇了摇头,笑着将荆天云扶起道:“灾恶之数,天定人为。”
巧儿虽然听不太懂两人的对话,但隐约知道了尘在说荆天云大劫难逃,巧儿脸现忧虑之色,玉齿轻咬下唇,偷偷的用眼角瞧着荆天云。
过了一会儿,荆铁山从偏门中进来,他的右手正在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了尘面容一变,严肃道:“铁山,师父老实告诉你。这避神珠能挡这一次,三年后还有一次啊!不过,若能渡过此劫,百年不是难事。”
荆铁山心中一片茫然,心想连连的厄运如何能解,他无助的跪下道:“请师父明示。”
荆天云见父亲下跪,他亦急忙跪下叫道:“求师祖救救我爹娘。”
了尘缓缓坐下,语气徐缓的道:“办法不是没有,只是缘而已。”
荆铁山父子听了以后不明白了尘的话,互相对看一眼,四目交投都呈现难以理解的眼神。
了尘颔首一笑,道:“老道生平最会炼制丹药。不过药材难求啊!但是,铁山你若能找到我指定的几种药材,或许可事情还有转寰余地。”
荆铁山抱着噗通乱跳的心,求问道:“请师父说明。”
了尘不疾不徐,嘴角一扬,淡淡的道:“五毒回魂草,千年雪里红,赤焰火睛蝉,冰心玉莲花,白江黑龙胆。这五味药材,分属不同区域,这是一难。其中冰心玉莲花和白江黑龙胆要在取得后十二个时辰内服下,其它的用来炼制成丹药。所以铁山你必须与你夫人同行,这是二难。这些事要在三年内达成,这是三难。”
荆铁山知道师父说的轻松,其实困难重重。但是韩云娘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荆铁山双手紧握,语气铿锵有力的道:“尽人事,听天命。”
了尘神清气定的颔首道:“你能明白就好。等你夫人将养十日后,我们就出发吧!”
荆天云听荆铁山并没有将自己纳入之意,急忙道:“爹爹,请让孩儿同行吧!”
荆铁山见了荆天云的神情,毫不动容的付之一笑道:“我交代你的事情,你这么快就忘了吗?何况这三年之中,家里还要你照顾呢。”
荆天云心头一急,双眉不住耸动,结结巴巴道:“爹爹,多一个人总是好的。”
荆铁山摇头道:“师父都说这是缘,人多又有何用。三年之期转眼即过,若是我和你娘没有回来,你也不用找我们了。”荆铁山坦然一笑,荆天云心中明白父亲金石般的决心,虽然心中黯然,却也不再多言了。
荆铁山察觉师父脸上似乎有些忧虑,他关心的问道:“师父心中可有难解的疑虑。”
了尘宛如大梦初醒般,回过神来道:“荥阳之事,透着古怪。”
荆铁山忿忿不平的道:“盐枭害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只是抓不胜抓,似乎没有办法可以抑制。”
了尘缓缓摇头道:“荥阳之事并非盐枭所为。他们只是被利用而已。”
荆铁山阿的一声,奇道:“非盐枭所为?弟子不明白。”
了尘轻抚拂尘,眉头紧皱道:“荥阳之人,中的是安乐一笑散。”
荆铁山吃了一惊道:“安乐一笑散?那是皇宫禁药,民间怎会有这药,而且份量如此巨大,简直匪夷所思。”
安乐一笑散是皇帝赐给臣子的毒药,据说吃了后全身舒畅,但是一入眠后就此长睡不醒,死者脸上大多怀着笑意,所以被称做安乐一笑散。
了尘沈思一会儿,问道:“那按察使徐广元,你可认识?”
荆铁山摇头道:“徒儿不认识,但是此人出身草莽,徒儿确实听过些许传闻。据说此人心狠手辣,栈恋权谋,是个厉害角色。”
了尘点头道:“皇上大概是因为禁药外流才如此震怒。这以夷制夷的策略,给了徐广元一个机会,若是让他统一了盐枭众帮派,那么他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民间皇帝了。”
其时运盐皆藉水道而行,于是乎盐枭帮派三雄鼎立。
北有黄河流域的三江帮,帮主翻江神龙段武,两个副帮主为袖中剑阮御风,破山刀司徒难。统管黄河口起的平原,甘陵,阳平,白马,官渡,河内,荥阳,成皋,洛阳,渑池,弘农,华阴,新丰,长安,武功以至陈仓附近。可谓掌管中原精华之地。
中有淮水帮,帮主碧眼金雕尚崇龙,其下五位把兄弟,分别为鬼爪常天,玉面神箫单中立,无常剑萧平,夺命银勾巴东喜,笑面佛朱乐。淮水帮所统辖区虽然不如三江帮,但是淮水连接泗水,雎水,涡水,颖水,汝水等水道,其中城镇如淮阴,□贻,寿春,汝南,豫州,许都,谯郡,陈留,小沛,徐州,琅琊等等市镇,其密集程度在管理上又较三江帮优异。
南方的长江流域有鄱龙帮,帮主落龙鞭诸葛无双,帮内十堂七十二分舵,统管建业,丹阳,芜湖,濡须口,皖城,柴桑,江夏,夏口,江陵,长沙,豫章,白帝城,甚至汉中,巴郡,成都,梓潼等等,都在鄱龙帮的范围内,掌管区域最大。
荆铁山对此感到无力可施,无奈的道:“朝廷尚且无力,独臂如何支天?而且弟子忧心内室,力有不逮。”
了尘右手一阻道:“为师并不是要怪你,这事儿还得静观其变。这十多年,为师技拙,耍了几套功夫,趁这时候传给你们两人吧!”
三绝真人在十天之中,将自创的三绝剑法,擎天指法,拂花散手传给荆家父子。
虽然十日太短,两人难以融会贯通,但是三绝真人却道凭着口诀和苦练,有朝一日必可克尽全功。
短短十日已至,韩云娘面容已经恢复八九分颜色,荆家父子喜形于色,虽然前面路途艰难,父子两人却心意相通,不再为此挂怀。
韩云娘正默默的收拾简便行囊,巧儿从门外进来,轻声道:“夫人找奴婢有何吩咐?”
韩云娘坐在床边,左手拍拍床沿道:“巧儿,你过来坐这儿吧!”
巧儿感到纳闷,走过去轻轻坐在床边,不解的看着韩云娘。
韩云娘和蔼的看着巧儿,微笑道:“巧儿,荆家待你如何?”
巧儿心头微感讶异,小嘴儿一张,道:“荆家待奴婢恩重如山,夫人视巧儿有如己出,巧儿无以回报,请夫人让奴婢随伺在侧。”
韩云娘双手将巧儿的小手握在手中,道:“巧儿,你喜欢云儿是不是?”
巧儿心事被当面点破,心中小鹿乱撞,霎时间满脸通红,害羞的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久久以后,巧儿红着脸轻声道:“奴婢只是下人而已。”巧儿不否认就表示她喜欢荆天云,韩云娘温柔的看着这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当年自己也是这般年纪时和爱人分离的啊!
韩云娘好像对着女儿说话般,轻笑道:“我从没当你是下人啊!如果你能当荆家的媳妇儿,那是荆家的福气。”
巧儿□腆道:“奴婢无才无德,配不上公子爷。”
韩云娘□首轻摇道:“你很好,我是怕云儿生性顽劣,配不上你。”
巧儿心中犹豫了一下,道:“公子现在很好,又孝顺又懂事,对人也不会像以前一样趾高气昂的霸道无理,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公子爷的。”
韩云娘叹口气道:“若是云儿早几年变的如此懂事,我和老爷早就抱了你们两人的孩子颐养天年去了。可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福气。”
巧儿听韩云娘语气深长的叹息,忙道:“夫人一定看的到的,夫人吉人天相,一定没事的。”
巧儿话未说完,双眸瞥见韩云娘四笑非笑的神情,不由的大窘,急忙辩解道:“夫人,奴婢没有这个意思,奴婢……”
韩云娘看巧儿急的涨红了脸,不忍心再戏弄她,韩云娘笑着道:“瞧你急的,我和老爷离开后,云儿就交拜托你了。”
巧儿泪水在俏目中打转儿,她伤心如亲娘般的夫人一去生死未谱,又不知以后该怎么办,不知不觉中两手紧紧握着韩云娘的手。
两人细语不停的谈论荆天云,巧儿脸上晕红未褪。忽而娇羞含怯,忽而抿嘴轻笑。两人一副婆媳薪传之象。
荆天云奉了父亲之命,前来接母亲到大厅。他一进房间,见巧儿哭的泪眼婆娑,心想这小姑娘对母亲真是依恋,以后得多照顾她些。
韩云娘见儿子走来,拉着巧儿迎上前去道:“云儿,巧儿就交给你了。”说完右手拉着荆天云的右手,左手将巧儿的柔荑放在荆天云的手中。
荆天云握着柔软滑腻的小手,心中一荡。但是他惦着父亲的交代,没有注意到巧儿粉脸通红,一双柔媚的眼睛正偷偷的瞧着他。
荆天云放开巧儿的手,道:“娘的吩咐,儿子自当遵从。爹和师祖在大厅等候着娘。”
韩云娘点点头,荆天云拿起行囊,和巧儿一起随着韩云娘来到大厅。
大厅之中,荆家奴仆三十多人齐聚一堂,准备恭送主人远行。
荆铁山拍了拍荆天云的右肩,神情严肃的道:“你要保重。”
韩云娘红了眼眶,将儿子紧紧搂在怀中,心情激动的无法言语,但是母爱之情溢于言表。
了尘见时间不早了,轻轻咳了一声,道:“走吧!”
荆铁山轻柔的安抚韩云娘,韩云娘回头看着丈夫,依依不舍的放开儿子。三人缓缓走了出去,门外一辆篷车正等着。
荆天云跪伏在地,大叫道:“孩儿等着祖师爷爷和爹娘平安回来。”
荆家家丁亦全部跪下道:“小人等祝老爷夫人一帆风顺。”
荆铁山右手一挥,马儿铁蹄翻滚,春风吹起黄尘渐渐遮掩住车身。
荆天云抬头见篷车远去,泪水不由自主的滑下脸颊。巧儿如小鸟依人般靠着荆天云,玉颊上也是泪珠点点。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