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第十五章 路见不平
|
|
这两个汉人,看了看他,那个肿面小眼的少年,冷笑了一声道:“不叫你叫谁?你是干什么的?”
蒲天河不由有气道:“我是走路的。怎么,不行是不是?”
肿面少年短眉一挑,口中骂道:“他妈的!”伸手就想打过来,却为那个驼背的道人拦住道:“少东家何必与他一般见识!”
说到此,冷冷一笑,望着蒲天河道:“你大概不知道,我们是哈里族屠家堡来的,只问你几句话,你可曾看见一位姑娘在这附近吗?”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可是转念一想,却摇了摇头,道:“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肿面少年气得瞪着那双小眼道:“妈的,你是瞎子呀!她明明往这边来,你怎么会没有看见?”
蒲天河面色一沉道:“你说话嘴里干净一点!”
肿面少年再次扬手,却又为那道人拉住道:“少东家,算了,还是先找着那丫头要紧!快走吧!”
肿面少年冷笑了一声道:“小子,你记住,只要你不离开蒙古,早晚都要碰在我手上,那时我叫你知道我屠一夫的厉害!”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我也不会忘记的!”
二人恨恨地离开,一路向前找去,蒲天河忽然心中一动,暗道:“糟了,看此情形,这两个家伙别是要去找方才那个姑娘吧!他二人形似恶狼,说不定会不利于那个姑娘也未可知!”
这件闲事,本来他是不想管,可是自己身为侠义道中人,总。不能见危不问,再者受害者是一个少女,岂能容人加以欺凌?!
想到此,蒲天河不由一时雄心陡起,他悄悄转过身来,循着方才之路,向二人寻去。
不想才走了几步,就听见先前那个肿面小眼少年狂笑之声道:“三妞,别藏了,我已经看见你了。哈!真是亏你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地方,竟会藏在船上面,你乖乖地出来,我保证不伤你一根头发如何?”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惊,赶忙纵身过去,果见那小眼睛的少年,同着那个驼背道人站在池水旁边,池内画舫仍然在水中飘着。
那个叫屠一夫的少年话声方落,就见船头上人影一闪,现出了一个姑娘。月光之下,蒲天河已认出了这姑娘正是先前自己所见的那个姑娘。
这时就见她立在船头上怒冲冲地道:“什么藏不藏的,我爱上哪里就去哪里,谁也管不着!你们找我干什么?”
肿面小眼的屠一夫赫赫笑道:“三妞,你是明白人,屠少爷看上了你,是你的造化,干嘛躲躲藏藏爱答不理的,你莫非还能逃脱我的手掌心不成?”
船上的姑娘冷笑道:“屠一夫,你不要作梦了,你以为你们家有几个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可是看错人了,别说我看不上你,就是我真有嫁你之心,我师父你惹得起么?”
屠一夫冷笑道:“令师若是没有此意,又何必派你来向家父拜寿?再说我屠家财产武功,均不在你师父之下,你嫁给我还会委屈你么?”
船上姑娘一声清叱道:“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没有工夫跟你乱说!”
说罢,转身就向船舱内走去,那肿面小眼少年冷冷一笑道:“三妞,我屠一夫垂涎你的美色已不是一天半天了,今天难得你送上门来。哈哈,如此美景良宵,姑娘你一个人水上戏舟,未免太寂寞了!”
说罢身形一纵,竟向船上落去,他身子方纵上船,那名叫三妞的姑娘,却由船上窜身而下。
可是这时岸边那个驼背道人,却怪笑道:“算了吧,姑娘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
你不要跑呀!”
说时,身子一晃,已到了那姑娘身后,伸出双手直向少女肩上抓去,少女肩头一沉,已躲开了道人双手,猛然一声怒叱,一掌直向道人驼背上击去。
道人怪笑了一声道:“算了吧,讲打你是不行了!”
道人说时身子滴溜溜一个转身,已到了这姑娘身侧,同时他身子向下一矮,双手同出,直向少女后腰上撑去。
这时船上那个小眼睛肿面少年,已自船上纵身下来,他眯着一双小眼,在一边嘻嘻笑道:“匡师父,小心别伤了她,还不施出你的‘迷魂掌’尚待何时?”
道人闻言,嘻嘻一笑道:“少东家不必关照,我怎么会如此煞风景呢!哈哈!”
说时,就见他身子一转,已到了一旁,忽见他由身上取出了一个白色的小口袋,道人右手探入袋中,猛地向外一掌打出。
当空白雾一起,那叫三妞的姑娘,想是身躯过于接近,再者也不识厉害,白烟一起,她由不住口中“啊呀”一声,顿时倒地人事不省。
道人哈哈一笑,向着那肿面小眼少年道:“贫道这一手怎么样?别说是他,就是她师父春如水只怕也是逃不过了。少东家,今天晚上……嘻嘻……野渡无人……哈!往下就看你的了!”
肿面少年屠一夫,这时已扑了上去,把倒在地上的姑娘抱了起来,闻言笑道:“匡师父,你果然有一手,等我对父亲说过,乌鲁可士那个道院,要你来接管。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你可以去了!”
驼背道人喜得哈哈大笑道:“谢谢少东家了。少东家,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好好享受吧,贫道去了!”
说罢,倏地转身飞驰而去!
暗中窥视的蒲天河看到此,真是血脉怒张,由方才对话中,他得知那叫“三妞”的姑娘,原来竟是春如水的弟子,自己师徒此来,正是要找春如水其人,此刻既遇见了她的弟子,自是不便放过!
再者,这个叫屠一夫的少年看此情形,必定是想在今夜玷辱了这姑娘,以达到逼婚的目的,其心之淫毒,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蒲天河想到此,不由蓦地腾身而出,却见岸上已无人迹,他想了想,料定那屠一夫这时必已抱女跃上了池中画肪:行那不可告人之事了,此时此刻,如果自己再不下手营救,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如此想着,蒲天河已跃身上了大船。
他轻功极佳,身形纵上大船,船身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定了定神,细细向船内一望,果然后舱内灯光闪烁,似有人影移动。
蒲天河这时真是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他足下一点步,已窜到了那间船舱窗前,由窗缝间向内一望,果见那屠一夫这时自身已脱下了外衣,正在急切地脱着那姑娘的衣裾!
那个叫“三妞”的姑娘,这时牙关紧咬,面色红晕,还没有苏醒过来。
屠一夫方自脱下了姑娘一件衣服,蒲天河已忍不住一声厉叱道:“大胆的淫贼,快滚出来!”
口中叱着,双掌一现“喀嚓”一声,已把一扇花格窗子砸了个粉碎!
那屠一夫鞋袜已脱,裤带半解,将脱未脱之间,闻此喝叱,真个是吓得魂飞魄散,惊吓之间更生出了无比怒火。
他好事将成,平白无故有人横出作梗,以他素日在地方上之威焰,简直是不可忍受。
当下暴叫了一声道:“是哪一个?坏了屠少爷好事,老子剥了你的皮!”
说罢,随便拉了一个床单子,先把那姑娘裸露部份盖上,自己连鞋也顾不得穿,双手搬起了一张坐椅,哗啦一声,抖手打出,紧跟着他身子自窗内窜了出来!
屠一夫身子一落,尚未站稳,只觉背后一股冷风,劈背而下,不由吃了一惊。这家伙也并非是个脓包,身手倒也不凡。在冷风一袭下,他身子一个旋转,已飘出了丈许以外,落在了前舱板上,身子已转了过来。
当他看清了来人,原来就是方才自己问话的那个汉人,不由怔了一下,随之暴笑了一声道:“好个小杂种,你有多大的本事,竟敢多管你家屠少爷的闲事,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说话之间,这屠一夫顺手撩起了船上长篙,身子向前一挺,这支长篙,当作扎枪的施法,猛的一枪,照着蒲天河面门上点来。
蒲天河哪里会把他放在心上,今夜他已决心要把这个家伙溅血剑下,当时一抬手,抽出了那口天下知名的“五岭神剑”,剑上光华映着明月,顿时映出一股冷冷的流光,有如是一泓寒泉也似。
屠一夫长篙点到,蒲天河剑身一滑,已贴在了他篙身之上,向外微微一挣,叱道:
“去!”
他右腕上已贯足了内力,这一抖之力也不可轻视,屠一夫立时双手一酸,长篙差一点脱手而出,足下更吃不住向前一个踉跄。
这一来,这家伙才知道对方的厉害,吓得“啊”了一声,他手中长篙就在这时使了一招“倒打金龙”,随着他身躯一转之间,这条长篙,夹起了一股劲风,“呼”的一声,直向着蒲天河兜头抽打下来。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无耻之徒,看一看我们谁的死期到了!”
兵刃经上有渭:“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长兵刃固可封敌十面,可是敌人一旦进身,就非短兵刃莫能为力了。
屠一夫显然是明白这一点道理,所以他要在敌人未进身之前,至对方于死命。
这一支长篙之上劲力十足,如为他打上,必死无异,可是蒲天河在他挥杆将下之间,身子已腾空而起,反向屠一夫身前落来。
屠一夫吐气开声,长杆一收一吐,完全是用“大杆子”的打法,长篙的铁头尖子,闪出了一点银星,就空向着蒲天河前心上点去。
蒲天河冷笑了一声,左掌霍地向外一撩,已拧在了长篙的顶尖之上,随着他身子向下一落,两个人就算在竹篙上较开了内力:
长篙一进一缩。那屠一夫忽然“哦”了一声,右手虎口鲜血像洒豆子似地淌了下来,长篙已到了蒲天河手中、
屠…夫也真算猾,就见他身子一滚之间,已在地上又撩起了一条铁链子,身子跟着一个反撩,再次到了蒲天河身前,手上的链子施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蒲天河肩头上砸去。
蒲天河抛下了手上的长篙,掌中剑向外一贴,已和对方铁链子纠缠在了一块,他右腕向外一挣,叱了声:“撒手!”
只听见“哗啦!噗通”两声,水花四溅,铁链子已由屠一夫手中飞出落人池水之中。
屠一夫这时早已吓昏了头,哪里还敢恋战,身子猛地腾起,向岸上落去。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姓屠的,你纳命来吧!”
说时,他身子跟踪而起,却较那屠一夫先一步落在了岸上,屠一夫身子向下一落,正迎上了蒲天河前进的剑锋,顿时血光一现!
那屠一夫口中惨叫了一声“啊呀”,一只右腕随着蒲天河的剑光翻处,已齐腕断为两段。
屠一夫拼命用力地腾身纵出,落地后,只痛得他在地上打了个滚,鬼哭狼啤叫了一阵,才又跳起来一路落荒而去!
蒲天河反手摸出一支暗器,正要抖手打出,转念一想,彼此终无深仇大怨,不如饶他一命算了。
想到此,就临时住手,忽然想到了船上少女,不知是否已遭了贼子毒手,当下忙纵身上船,踢开了舱门,见那个叫三妞的姑娘,盖着一个床单子,身子正在颤动着。蒲天河忙过去揭开床单子,只见对方上衣已脱下来,露出细白的一抹酥胸。
蒲天河赶忙为她盖好,见几上瓦罐中,盛有半罐冷水,就取过来兜头浇下,自己退身一边。
床上的三妞,长长地漫吟了一声,又过了一会儿,才睁开了眸子,忽地坐起身来道:
“好个强盗……”
忽然一眼看见了蒲天河背影,不由尖叫了一声道:“你是这时候她显然是发现了自己赤露着的上身,赶忙又躺了下来。蒲天河冷冷一笑道:
“姑娘不必惊怕,那姓屠的贼子,已为我打跑了。姑娘衣服,就在旁侧,快快穿上才好说话。”
少女闻言忆及前情,当时一张玉脸,羞了个绯红,口中颤抖道:“可是你……你是谁呢?”
蒲天河冷然道:“姑娘穿好衣服,一对面也就知道了,何必急于一时?”
少女闻言这才赶忙把衣服穿好,走下地来道:“好了,你可以转过身子来了!”
蒲天河转过了身子,那姑娘乍见对方面貌,不由吃了一惊,面上讪讪地道:“原来是你……”
蒲天河鼻中哼了一声,道:“如非是在下及时赶回,只怕姑娘已经……”
少女闻言不由眼圈一红,垂下头道:“我真该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也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给你磕头!”
说着真地跪了下来,蒲天河忙把她扶了起来,叹道:“姑娘不必多礼,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我们身为侠义中人,理当管这些不平之事,只是姑娘何以会与那姓屠的有所来往,那姓屠的又是一个什么人?姑娘是否可以见告一二?”
少女闻言冷冷一笑道:“我怎会与这种人交往!”
说罢低头又叹了一口气道:“还不知恩兄大名如何称呼?”
蒲天河想了想,含笑道:“我姓娄,单名一个骥,姑娘呢?”
少女闻言面色立时大变,惊喜道:“啊呀!原来你就是河漠里那个奇侠娄骥,真是人仰大名了!”
蒲天河不由面色微微一红,不自然地哼了一声。他之所以不愿意吐露姓名,实在是怕对方走露了风声,以致令春如水有了准备,却未曾想到这姑娘,竟然对娄骥如此敬仰崇拜!
只见她面上带出了极度的兴奋之色,欣喜地道:“这些年来,娄兄的大名,哪一个不知,哪一个不晓,想不到娄兄会来到蒙古!我好像听说,娄大侠你兄妹曾有不出河漠之说是不是?”
蒲天河含糊地道:“不错,这里也是河漠呀!”
少女一双杏目,微微瞟了他一眼,似笑又羞地道:“方才我记得也曾问过你的名字,怎么好像不是姓娄,是姓……”
蒲天河暗吃了一惊,这才记得先前自己原本报过了名字,只是那时自己并不知道她的底细,才会真名相告,这时少女一问,他不由呆了一呆,窘笑道:“方才因不明白姑娘底细,所以才以假名相告,尚请不要见怪才好!”
少女笑了笑道:“这么说娄大侠现在是明白我的一切了?”
蒲天河点头道:“明白一二。第一,我知道你是春如水春夫人的高足;第二,你来此是拜寿来的。”
少女面上立时一惊,遂点头笑道:“娄大侠果然神机妙算,猜得一点不错,小妹复姓上官单名一个琴字,和舍妹上官羽,乃春夫人新收弟子,此次因‘哈里族’的屠庄主六十大寿,特派我携礼来此代师贺寿,却想不到……”
说到此,一双秀眉蓦地一挑,气得粉脸通红。
蒲天河忽然记起,当初春如水对己之戏言,不由向着这上官琴面上转了转,微微笑道:“如果我没有猜错,那上官羽必定与姑娘是一对孪生姐妹了,可是?”
上官琴眼皮撩了他一下,微笑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蒲天河笑而下答。上官琴又想起前事,恨恨地道:“屠庄主与家师,乃是蒙古地方西北二王,平素感情并不甚好,屠庄主因妒家师之财富,是以多年来,常常惹事生非,存心想把家师驱出蒙古,他好独霸蒙古,他还想鲸吞家师的财产呢!”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令师如此精明厉害之人,岂是容易欺侮?我想那屠庄主未免太天真了!”
蒲天河此语分明是带有讽刺的意思在内,可是上官琴哪里听得出来,当即便道:
“娄兄说得不错,他在哪一方面,也是不能与家师相提并论的!”
蒲天河微微一笑道:“既如此,春夫人又何必容他存在呢?”
上官琴看了他一眼,笑道:“你对此事,.我看是很感兴趣。娄兄,你哪里知道,虽说这屠庄主在财势武功上,都不如家师甚远,只是他这地盘内,却控制着整个蒙古的水源,他如切断供水,那么家师的半壁河漠,无疑是寸草不生,虽富也是非死不可,所以家师为此不得不略事容忍罢了!”
蒲天河不由暗笑了笑,心想这可真是应上了“恶人自有恶人磨”的那句话了。
当时,他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令师就该下手除了他才是!”
上官琴摇了摇头道:“这些地方你不会明白的,家师手下所控制的只是内地流窜来的千余汉人和一部分极少数的蒙古人,可是这屠庄主手下全是本地的蒙古人,以少数的汉人,是无法与这么多的蒙古人对抗的!”
蒲天河点了点头,笑道:“这么说来,令师的雄心始终是不得逞了!”
上官琴以一双秋波眸子瞟着他,过了一会儿,才道:“方才那个坏东西,就是屠庄主的长子,人称‘燕尾镖’名叫屠一夫,他在暗器上有很厉害的功夫,不知方才有没有向你发出?”
蒲天河一笑道:“今后他这一手暗器,只怕再也施展不出了。”
上官琴一惊道:“娄兄莫非已杀死了他?”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杀倒没有杀,只是斩断了他一只右手,只怕他要落成一个终身残废!”
上官琴忽然一惊道:“那只断手呢?娄兄可曾捡到!”
蒲天河微异道:“断手就在岸边,姑娘以为如何?”
上官琴立时推开舱门道:“快捡回来埋了。你不知道,方才那个道人,最擅接骨续脉,如为他捡了回去,不出一月,又能回复原状,岂不是又要为恶了!”
蒲天河一想有理,当时同上官琴,双双纵身上岸,蒲天河记得那只断手落处,可是此刻却是遍寻不着,不由吃了一惊,跺足道:“姑娘说得不错,果然不见了!”
上官琴冷笑道:“那道人本是中原武当的一个恶道,武技虽是平平,但生平最精诡术及医道,人称‘鬼道人’,他在走头无路之下,才投奔了屠庄主,不想那屠庄主竞是百般看重他,金银财宝只要他开口,无不奉送,道人也就乐得在此不去,助纣为虐,真是可恨之极!”
蒲天河叹道:“只怪我一时大意,想不到这厮还有这么一手!”
上官琴叹了一声道:“我倒无所谓,一走了之,只是娄兄只怕日后要提防他们一二了!”
蒲天河冷笑道:“他如再碰在我手中,只怕他是自寻死路!”
上官琴一双媚目望着他,甚是关怀地道:“话虽如此,可是他们哈里族人多势众,屠氏父子是无恶不作,娄兄还是要小心一二才是!”
蒲天河闻言,不由剑眉微微皱了一皱,忽然抱拳道:“今逢姑娘,总是有缘,后会有期!告辞了!”
说罢转身就走,上官琴忙道:“娄兄请稍待!”
蒲天河回过身来,上官琴娇笑了笑道:“娄兄是一个人来此的么?”
蒲天河道:“不错,我一个人!”
上官琴低头想了想道:“恕我多话,我只是想,娄兄虽是技高胆大,但是到底初来蒙古,人生地陌,诸多不便,我可以问一问娄兄此行欲去何方?”
蒲天河想了想,总觉不便直言,当时信口道:“我因向往蒙族‘八旗马会’,所以不远千里而来,实在是想去看一看这场盛会!”
上官琴不由秀眉一启,笑道:“这就太好了,我明日正要转回,那赛马会,其实就是家师举办的,到时我带你去就是了!”
蒲天河不由甚喜,当下点头道:“姑娘如此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不过……”
上官琴一笑道:“我一点也不麻烦,娄兄住在哪里,明早我去找你、我们一同上路岂不是好?”
蒲天河心中暗想,这倒是一条最好接近那春如水身边之路,也许由上官琴口中正可知道一些那“寒碧宫”中的奥秘!
想到此,便点头道:“也好!”
上官琴见他一口答应,不由大喜,由不住在地上跳了一下道:“你真好,有你一路,我胆子也可以大多了,再不怕那屠一夫动什么坏主意了!”
蒲天河想了想,又问道:“令师所居的寒碧宫,离赛马的地方有多远?”
上官琴点头道:“很远,不过碧寒宫戒备森严,非经家师的信物令珠,任何人不得妄入一步!”
蒲天河想到甘肃时,春夫人曾授予自己一串珠子,想必就是她的信物或是令珠!
当时他没有说话,上官琴又问明了他居住之处,才举手作别而去!
蒲天河独自回归,却见那乌克兰术夫正在向这边张望着,见蒲天河来到,笑道:
“唉呀!你可回来了,我正要去找你!”
蒲天河笑道:“那边风景甚美,一时竟忘了回来了!你找我有事么?”
乌克兰术夫摇头道:“事情倒是没有,只是前边是哈里族的境界,那边的人都很厉害,我怕你会上当吃亏!”
蒲天河笑着转回帐篷,是时天已将亮,木尺子正在坐着调息运功,见他回来,眯眼笑道:“小子,交了桃花运了!”
蒲天河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什么事还能够瞒得过我老人家这双眼睛?小于,告诉我那个小妞是谁?深更半夜在水池旁边,你们谈些什么来着!嗯?”
蒲天河不由有些啼笑皆非,当时红着脸道:“你老人家别开玩笑了!”
于是他把方才所经过之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木尺子听后,半天才点了点头道:
“原来是这样,你说的那个屠庄主,我也知道,此人姓屠名三江,人称‘风火魔王’,对于各种火器暗器很有研究,相当厉害,你伤了他的儿子,这件事只怕不会善了,你倒是要注意才好!”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这一点我倒不怕他!”
木尺子哼道:“这老头儿如找你麻烦,由我来对付他就是。倒是春如水那边,徒儿,你可要费点心了!”
蒲天河点头道:“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与那上官琴约好同行的!”
木尺子一手摸着下巴,想了想,点头道:“好吧,这件事完全由你去办吧,我去了诸多不便,那春如水如知道我去了,定必会躲着我,反倒是不容易找了。你如暗中探寻,倒是再好不过的事。只是有一点,千万不可让春如水看见了你,她如知道你来,定必也就推知我也来了!”
蒲天河皱了皱眉叹道:“这事好是好,就是欺骗了那上官姑娘于心不安,再者娄大哥如得知,亦必定不乐!”
木尺子嘻嘻一笑,拍了拍他肩膀道:“这一点你大可放心,那姑娘我也看过了,娄骥年岁也不小了,到后来将错就错,给他说上一房媳妇,岂不是好?”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莫非你老人家不知道天山白雪山庄的蒋瑞琪姑娘,对娄大哥一往情深么?”
木尺子怔了一下道:“咦!对了,我竟然忘记了那个主儿了。”
想了想,又笑道:“你放心,这事也是不得已的,他们双方必定能谅解你,你收拾收拾,准备着上路吧!为师的宝贝,全靠你大力追回了!”
蒲天河想了想也只有如此了,当下就静坐一边,运功调息,不再言语。不久天亮,二人相继起身。
乌克兰家人都有早起的习惯,天一亮大家全都起来了。早点吃的是青棵粉做成的饼,就以新鲜的马奶,蒲天河虽是不习惯,但是“入乡随俗”,也只好吃一些。
饭后,他把随行的衣物,装进皮褡裢里,放在马上。乌克兰一家这时已纷纷干活去了,这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有工作。
蒲天河步出帐外,正自心想那上官琴不一定会来,一念未完,就见远远一匹红马风驰而至。
马上的上官琴,红衣红帽,再衬着她座下的红马,人马一色的红,看来真是风姿飒爽,英秀脱俗,端的是个大美人儿!
上官琴远远看见蒲天河,不由玉手频挥道:“喂!快来呀!”
蒲天河打马而上,木尺子却笑立在一旁,打量着二人,连连点头不已。
上官琴偏头看着木尺子,惊异地问着蒲天河道:“咦!这老头于是谁呀?”
蒲天河随口应道:“是马克兰门下一个寄食的汉人,我们走吧!”
上官琴低头一笑,一双小红靴在马鞍子上磕了一下,道:“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早上我去屠庄主处辞行,可又看见了他那个宝贝儿子屠一夫了!”
蒲天河冷笑道:“他那只断手可曾接上了?”
上官琴点了点头,道:“接是接上了,却包扎着柳枝,反正半月之内,他是不能再干坏事了!”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这只怪我当时一念之仁,否则岂能还会有这畜生的命在!”
上官琴鼻中哼了一声道:“总有一天,我也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说罢抖了一下缰索道:“那厮既知我此刻上道,只怕还有歹意,我们还是快一点走吧!”
说完带马先行,蒲天河紧紧策马,二马一路飞驰,扬起了滚滚黄沙,直向前道驰进。
不一刻已来到了滚滚的沙漠,前望漠地,一片黄烟,任何人也会望之却步,心生出一种莫名的畏俱感觉。
上官琴用手上的小马鞭,向沙漠里指了指道:“我们要横过这片沙漠,最少要走三天的路程;你可带了夜宿的东西没有?”
蒲天河怔了一下道:“这个我倒忘了!”
上官琴撇嘴一笑道:“我一猜你就会忘记,我已经为你带了,吃的喝的你都不用愁了!”
蒲天河见她坐在马上,那种轻颦巧笑的样子,倒有几分与娄小兰相似,内心一时不禁兴出一些伤感,他暗暗思忖道:“那娄小兰此刻不知如何了?她是否已经把我忘记了呢!要是真的如此,我内心倒还安些,否则双方痛苦,未免太残忍了!”
想到此,那双炯炯的眸子,只是望着上官琴身上发呆,内心却又思念着,看来这上官琴,分明也是一个纯情善良的美貌姑娘,也是一个良好的终生伴侣,只是自己此刻心情,竟然不容许对她生出一丝情意,别说是自己对她生不出一些情意,即便是有此心情,也要赶快打消,否则就太对不起娄小兰了。
他思念及此,由不住兴出一些伤感,遂自把头低了下来。
偏偏上官琴纯洁天真,她哪里能了解蒲天河内心所想,当时被蒲天河看得垂下头来,羞涩地笑了笑道:“娄大哥……你的眼睛不好!”
蒲天河一惊道:“此话怎么解释?”
上官琴“噗哧”一笑,眼皮一瞟,微微地哼道:“老爱看人……”
蒲天河忙自镇定心情,笑了笑道:“姑娘一身大红,倒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上官琴道:“我早知道,是想起了令妹娄小兰了可是?”
蒲天河哈哈一笑道:“姑娘太聪明了,我们快走吧!”
说罢催动坐骑,双双骈马直向大漠黄沙深处驰去。
这是一片广瀚的沙漠,沿途上渺无人迹,非但是没有人畜,就是连草地也看不到一片。
二人催马疾驰,中午时方,来到了沙漠丘地,只见数百个黄土沙丘,耸于黄沙之间,看过去就像是一座座的坟头!
这时烈日低照,仿佛就在头顶。炙热的阳光,真像要把人晒化了。几只大秃鹫“哧哧”地叫着,低空盘旋着,似乎想寻人而噬!
上官琴勒住了马缰,玉手挥汗道:“我的老天爷,我可是要下来歇歇了,再走别说是人,就是马也受不了啦!”说罢翻身下马。蒲天河也觉得热渴难耐,当时也飘身下马。
两匹马不待主人牵行,就自己走到了沙丘旁边,借着沙丘的阴影凉快凉快。
上官琴自马身后面,取下了大皮袋,喂二马喝了些水,然后又取出食物,二人找了一处沙丘背影坐下来,饮了些水,吃了个饱。
蒲天河见上官琴这时摘下了帽子,以粉色汗中拭了拭脸上的汗水,她现出几分懒散地望着蒲天河道:“我睡一会好不好?”
蒲天河点了点头,他把草帽拉下来,遮住双目,也闭目养神。整整一个上午的奔驰,人马都有些倦了。
正当他二人似睡非睡之际,就闻得一阵马嘶之声传了过来,当他二人急忙望时,就见两匹快马,风驰电掣地由眼前疾奔而过!
坐在马上的显然是两个女人,二女之一是一个灰衣芒履的老尼姑,另一人,却是一个头戴马连波编花草帽,身着杏黄绸衣的少女。
蒲天河猛觉出那个少女,似在哪里见过,正想出声招呼,二马已带起了大片尘土,风驰电掣而去。
这时上官琴也发现了,她望着二马的背影,皱了皱眉道:“奇怪,为什么这几天,很多外来的汉人,都往蒙古跑?怪事!”
蒲天河问道:“姑娘可猜得出是为了什么事?”
上官琴微微一笑道:“要是这些人,想来打我师父的算盘,那可是妄费了心机了!”
蒲天河假装不明白笑了笑道:“令师又有什么好算计之处?”
上官琴向他一瞟,低笑道:“你是想套我的话是不是?”
她又把眼睛在他身上转了转,接笑道:“其实告诉你也无所谓,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师父最近发了一笔横财!”
“哦?”蒲天河佯作惊异。
上官琴点了点头道:“一笔大财,听说是由青海得了两大箱珠宝,另外还有四颗价值连城的珠子!”
“四海珠?”蒲天河脱口而出,上官琴倒怔了一下,接道:“不错,是四海珠。你怎么知道?”
蒲天河点了点头,冷笑道:“这四颗珠子,闹得满城风雨,我焉有不知之理,不过我倒是不知道,这四海珠,竟然落在了令师的手中!”
上官琴一笑道:“你当然不知道,这是一件大隐秘,我妹妹已负师命,特别东去天竺,专程请天竺王来蒙古看宝,如果可能,这四颗珠子,要卖很多钱呢!”
蒲天河心中倒是一惊,表面并不现出来,微微一笑:“令师真不愧是理财专家!”
上官琴又道:“你来得真巧,也许你还可以看见那位天竺的王爷,我师父请他来蒙古看赛马,顺便观赏那四颗珠子!”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我很想拜识这位王爷。他也参加赛马么?”
上官琴点头道:“也许参加,每年马会,来此参加的人极多,你会发现很多骑术精良的人!”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皱眉道:“不好,有人来了!”
站起身来,一拉蒲天河道:“我们快走吧!”
蒲天河向着沙漠里一看,果见黄沙滚滚之中,间杂着十数骑快马,马上各人,都披着一领黑色的披风,被风吹起来,与肩一般的平。
上官琴见状,冷冷笑道:“这些人是哈里族屠庄主手下的人,我们还是少惹他们为妙!”
蒲天河虽是心中气愤,可是外出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避之为佳,当下就要过去拉马。
风沙之间,有人陡地射来一支弩箭,到了蒲天河身边,已成了强弓之弩,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蒲天河伸手捏在了手中,就听得上官琴尖叫道:“当心!”
这“当心”两个字方一出口,就听那支箭,“波”的一声炸了开来,箭身之上冒出了大股的红烟。
蒲天河哪里知道那屠氏一门,专门擅施各种毒药迷药暗器,这支弩一炸开来,蒲天河鼻中忽然闻到了一阵奇腥之味,听到了上官琴话后,他赶忙闭住了呼吸。
尽管如此也由不住一阵头昏目眩,足下一个跄踉,一交坐倒在地。
上官琴大吃了一惊,忙过去扶他起来,蒲天河只觉得阵阵翻心,“哇”地吐了一口,上官琴拉过马来,道:“娄大哥,快上马!”
黄沙弥漫里,那十数匹快马,已来到了近前,坐在最前的一匹马上,正是那个驼背弯腰的道人,他冷冷笑道:“小杂种,你上了道长我的当了,还想跑么?”
说话之时,这些马已迅速地包围了上来,上官琴一眼已认出了来人之中,竟有那屠一夫在内。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屠一夫,这时一一只右手吊在颈项之上,双目赤红,他在马上嘿嘿笑道:“匡师父,务必要生擒这个小狗,我要亲自挖出他的心来!”
蒲天河这时虽已跳上马鞍,可是只觉得头昏眼花,摇摇欲坠,那个驼背道人赶上来,当胸一掌打来,口中厉声叱道:“下来吧,小子!”
蒲天河还没有为他掌风沾上,已咕噜一声自马上摔了下来,那道人怪笑了一声,自马背上飘身而下,向着沙地里的蒲天河就扑!口中大笑道:“小子,你还往哪里跑!”
上官琴急得尖叫了一声,霍地由马上一窜而下,一剑向着道人劈去,却为另一人持刀当的一声磕开!
眼看着那姓匡的道人,双手一探,已抓在蒲天河双肩之上,怪声笑道:“抓着了,你还往哪里跑!”
蒲天河右手方自举起,已禁不住一阵头昏眼花,顿时人事不省,昏死了过去。
上官琴跳过来,又是一剑,道人大袖一拂,磕开了她的剑,哈哈笑道:“三妞,你原来心里有了人啦,怪不得对咱少爷不问不理!”
坐在马上的屠一夫,这时气得面色发青道:“把她也绑上!”
立时过去了好几个人,刀剑齐下,屠一夫大骂道:“混账,我要活的!”
这些人吓得俱不敢再下手,只是拿着刀剑,虚作式样。上官琴一口主剑,翩若游龙,立时就为她砍倒了两个,那个道人这时已把蒲天河绑上,放在沙上,回过身来,向着上官琴道:“三妞,我们看在令师的面子上,对你已是十分留情了,今日你还想跑开是不能够的,还不丢下宝剑,我们少庄主是舍不得伤害你的!”
上官琴厉叱了一声,陡然纵身过来,掌中剑劈面而下,可是那个道人,右手向外一抖,却由袖筒内,飞出了一条软兵刃——蛇骨鞭。
道人“蛇骨鞭”到手,向外施了一招“拨风盘打”,只听得“呛啷”一声,上官琴的宝剑,差一点为他震脱了手!
上官琴向外一跳,口中叱道:“你们快放了他,要不然的话……”
屠一夫这时已命人把蒲天河捆绑在马鞍子上,闻言冷笑道:“放了他?哈哈……三妞,我要你活活地看着,这小子一刀一刀死在我手下!”
上官琴跺脚道:“不要脸的东西,不敢一刀一剑跟人家比划,却用迷魂药去暗算人家,你知他是谁吗?”
姓匡的道人,正要挺剑而上,闻言一怔,道:“他是谁?”
上官琴鼻中哼了一声道:“告诉你们,他就是南疆里的沙漠大侠客娄骥,你们惹得起吗?”
此言一出,那个道人及屠一夫,均不禁吃了一惊,道人目光在蒲天河身上一转,嘿嘿一笑道:“原来他就是娄骥,怪不得如此棘手!”
屠一夫愤愤地道:“他就是天皇老子,今天屠大爷也要动他!你这丫头一意地护着他,是安了什么心思?”
上官琴冷笑道:“我护不护他,关你屁事!”
屠一夫短眉频扬,嘿嘿笑道:“三妞,我一再对你青眼相待,你不要不识抬举!”
上官琴冷笑一声,道:“你如敢对我妄图非礼,我师父焉会平白地饶你?”
屠一夫冷冷一笑道:“傻丫头,你哪里知道,你师父早已有心把你嫁给我,否则又何必单单派你来这里拜寿呢?”
上官琴怒嗔道:“你胡说!”
足下一顿,一剑向着屠一夫身上撩去,却为一旁道人持剑格开了一边。那道人怒道:
“上官姑娘,我们已对你特别开恩了,你还不丢下宝剑,快快随我们回去?否则贫道就对你不客气了!”
上官琴这时望着马上反绑的蒲天河,不由眼泪滚滚地流了下来,道:“好!你们听我说,要我跟你们回去也可以,可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屠一夫双眉一展,喜道:“可以,你说吧!”
上官琴用手一指蒲天河道:“你们得先放了他,要不然我宁可一死!”
屠一夫面色一沉,哼了一声道:“这一点办不到!”
上官琴紧了一下手中剑,冷笑道:“那休想让我随你们回去!”
屠一夫向道人使了一个眼色,那道人一只手探入怀内,正要施出迷药,忽听得身旁一人道:“道爷快看,是谁来了?”
众人立时转身望去,就见一骑快马,如同是沙漠飞龙一般,风驰电掣而至。
尤其显目的是,人马是一色的白,马上挺坐的乃是一个头戴草帽的长身少女。
这匹白马行走在沙漠里,真可谓翩若游龙。刹那之间,已驰到了近前,众人都由不住吃了一惊。
白马本是路过,可是中途发现了如此异状,却猛地停住了。
马上那个长身少女,像似经过了长途的奔驰,一张清水脸,已为汗水湿润,只是看起来,越觉其红晕晕的,艳丽已极!
白衣少女突然的出现,顿时使在场众人都不由眼前一亮,平心而论,这些家伙自出娘胎以来,还真没有看见过如此漂亮的人物!
但见她柳眉高扬,杏目微睁,疏朗的上额,飘着几根秀发,衬以她挺秀的身材,那么昂然的坐在马上,真有如玉枝临风,好一副娇姿飒爽!
马上的屠一夫,本是一腔疾怒,这时见状,那张胖肿的肥脸,挤满了轻浮的笑容,道:“这位姑娘……嘻嘻……有何见教?”
白衣少女一双杏目在各人面上转了一转,很惊异地看了看上官琴,点了一下头。
然后她目光,又落在了马上的蒲天河身上。
蒲天河仍在昏迷之中,他是被脸朝下,绑在一匹马背上,因此白衣少女看不见他的面貌,不过,她脸上却也现出了一些惊怒!
驼背的道人哈哈笑道:“大姑娘,走你的路吧,这件事你也管不了!”
屠一夫却向道人使了个眼色,嘻嘻一笑道:“这位姑娘芳名如何称呼?”
白衣少女也不理他,冷笑了一声,望着上官琴道:“你一个人,和他们这么多人打吗?”
上官琴点了点头,叹了一声道:“姐姐,这件事你管不了,何必白饶上一条命呢?
你去吧,让我跟他们拼了!”
白衣少女冷冷地道:“你怎么知道我管不了?上马去,跟着我走!”
上官琴呆了一呆,她真想不到,对方一个孤伶伶的少女,竟然会有如此口气。
白衣少女见她不动,不由怒道:“怎么,你不想走?”
上官琴用手中的剑,向着马背上的蒲天河,一指道:“可是他……他呢?”
白衣少女哼道:“你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许多!上马咱们走,看他们谁敢拦我们!”
上官琴犹豫了一下,摇摇头道:“可是……我……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白衣少女眸子在蒲天河身上一转道:“他们男人的事,叫他们男人自己解决,何必管他们!我们走!”
一旁的道人呵呵一笑道:“姑娘,你说得好轻松!你来得正好,我们二庄主缺少一房媳妇,就把你算上吧!”
话声方说出口,就见马上的白衣少女,娥眉一挑,玉手虚晃了一下,就听得“叭”
的一声,那个道人被打得身子一个踉跄,一时顺着口角向下直流血。
这一手“凌空劈掌”的功夫,顿时把在场各人都吓得一呆,马上的屠一夫更不禁神色一变道:“啊呀……你是谁?”
白衣少女掌打道人之后,玉手一压帽沿,腰间露出了系着金穗的剑把子来。
姓匡的道人身子向一旁一跳,怪叫了声:“好丫头……你下来!”
白衣少女一声浅笑道:“我下来了!”
话落身飘,不过是一闪,已站在了道人身前。漠地里吹来的风,把姑娘那顶大草帽,吹得荷叶似地卷了起来,红色的帽穗子,飘起来,就像是一双彩蝶,看起来真是美极了。
驼背道人呆了一呆,猛地身子向后一退,掌中蛇骨鞭向外一抖,直向白衣少女胸前点去。
白衣少女一声冷笑道:“凭你也配!”
就见她玉手向左面一分,一领剑诀,右手同时宝剑出鞘,发出了“呛”的一声,反向着道人面上劈去。
道人身子一拧,灰衣飘动,闪向了一旁,蛇骨鞭舞起了一片光华,反向着白衣少女足下缠去。
这时四周的人,纷纷叫嚷着助威,可是白衣少女临场镇定泰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旁边有人一样,道人鞭到,她单剑轻轻一拨,“叮”一声,冒出了一点火星,整个身子已飘出了一边。
白衣少女口中娇叱了声:“道人无耻!看我剑下伤你!”
道人点足退身,可是白衣少女宝剑不知怎么一分,就见那道人怪叫了一声,身子一阵蹒跚,差一点坐了下来。
遂见由道人左胯部位,涌出了一股鲜血,一件道袍立时被鲜血染红了。
驼背道人一只手按在伤口处,咬牙道:“好贱人,你敢伤了我!”
说时身子忍痛纵开一边,陡地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黑布口袋,霍地向着白衣少女面前一抖。
随着道人这一抖之势,就是红烟一起,有如是大片云霓自道人口袋内倾出一般!
那立在一旁观战的上官琴看到此,知道这道人黔驴技穷,竟然又施出了他看家的本领了。
上官琴怕白衣少女不知道,吃了大亏,赶快叫道:“姐姐小心!”
红烟随风飘过去,每个人眼睛都睁得极大,尤其是那个道人与马上的屠一夫,都巴不得白衣少女倒下去。
可是红雾渐渐消失之后,白衣少女依然固我,站在当地动也不动。她冷冷一笑道:
“这些玩艺儿,只能欺侮那些不知底细之人,拿来对付我,未免太幼稚了!”
道人一怔,大吼了一声,猛扑上前,掌中蛇骨鞭,搂头就打!
这时另外两侧,在屠一夫目光暗示之下,另有二人倏地扑了过来。
两个人全是用一口鬼头刀,分左右,齐向白衣少女身上剁了下来!
三方夹攻之下,依然是占不到一点便宜。
白衣少女一声清叱,就见她长剑左右一舞,那两个暗袭的汉子,已左右翻跌而出,仰卧在血泊之中。
驼背道人大吃一惊,口中怪叫道:“风紧,扯呼!”
足下一顿,就向马背上扑去,可是左胯上因为负伤不便,起势自是不快。
白衣少女足下踏进一步,宝剑一闪,道人身子一歪,一只左脚断落而下,可是道人拼死在地上一滚,却把那只断脚抱在了手上。
就见他面上一青,身子一阵战抖,已痛得昏死了过去。屠一夫见状,在马上吓得面色大变,拨马就跑。
白衣少女一声叱道:“回来!”
屠一夫徐徐转回马来,苦笑道:“姑娘莫非还要赶尽杀绝不成?”
白衣少女哼了一声,道:“你这厮一看就知不是好东西,可是你既未对我出手,我也就网开一面,饶你一命!”
屠一夫闻言,在马上点头卑笑道:“多谢姑娘开恩!”
说罢,他转脸对身边众人道:“你们还不把道爷扶上马,快走么!”
众人立时把道人抬上马,那两个已死的同伴,也被一齐抬上了马。
上官琴在一旁见白衣少女如此厉害,自是欣慰佩服,当下忙道:“姐姐何故放他们回去,那个道人与马上这个家伙全不是好人,姐姐不如乘机除了他们才好!”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不知道,我对人一向是心存厚道,再说你们结仇经过,我并不知道,谁是谁非,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才插手管这件事!”
上官琴面色一红道:“姐姐你不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坏透了的人,没有一点人性!”
白衣少女一笑道:“算了,你不是很好么,放他们走算啦!”
屠一夫见机忙道:“女侠客千万不要听她胡说,这姑娘原是我的妻子,却勾引了这个男的私奔!”
白衣少女不由一怔,转身望着上官琴道:“是这回事么?”
上官琴不由气得面色苍白,道:“简直是一派胡说,姐姐你不要信他……我……我与你这贼子拼了!”
拔出了剑,猛然向着屠一夫扑去,白衣少女忙持剑格住道:“算了吧!”
她转过身来,望着屠一夫冷笑道:“无耻之徒,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么?快滚!”
屠一夫见计不逞,当下低头不语,遂带马过去,伸手去拉蒲天河被绑住的那匹马。
上官琴见状,忙道,“住手!”
屠一夫回头向着白衣少女苦笑道:“这人与在下有废体之仇,求姑娘把他交给我吧!”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我本可交与你的,只是我这位姐姐却好像有点舍不得!”
屠一夫恨恨地道:“姑娘何必如此与在下为难,姑娘报个万儿吧!”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字……”
她用手指了马上的蒲天河一下道:“把这人留下,快点,否则你们更别想舒服!”
屠一夫气得面色铁青,哼了一声道:“好吧,这一次一切都依你,我们总有再见之日!”
白衣少女露出两排白玉似的玉牙,笑了笑道:“很好,这还像句人话!”
屠一夫嘿嘿冷笑着,对身侧人道:“把他抬下马来,交给她。我们走路!”
他手下的人答应了一声,立时过去把蒲天河解下马来。蒲天河此刻仍然没有醒转,僵硬地躺在地上,上官琴早已扑过去,哭叫道:“恩兄,你……”
说时泪珠点点滑腮而下,白衣少女并未注意看地上的蒲天河,只向着屠一夫道:
“你们还不滚么!”
屠一夫牙齿咬得咔咔直响,连连点头道:“金砖不厚,玉瓦不薄,骑驴看唱本,我们走着瞧!再见!”
手一挥,众人一齐拨马而去。沙漠上弥漫起了大片的黄烟,这些人来得快,去得更快,转瞬之间,人马已走了一空。
白衣少女这才慢慢转过身来,望着上官琴道:“你这位朋友要紧么?”
上官琴侧过身子,道:“他因中了那妖道迷魂毒沙,此刻仍然是不省人事,这便如何是好!”
白衣少女一笑道:“这容易,你走开看我的!”
上宫琴忙闪开一旁,白衣少女由身上取出一个扁盒,由盒内取出一颗丸药,捏破了蜡衣,现出了一颗绿豆大小的药丸。
白衣少女这才抬起头来,当她目光一接触到蒲天河的脸上,由不住立时呆住了。
她脸上神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足下后退了一步,喃喃道:“哦……不!是你……”
猛然地扑过去,蹲下了身子,细细地看了看蒲天河的脸,口中徐徐地道:“蒲……
大哥……是你!”
上官琴一呆道:“咦……姐姐莫非认识他?”
白衣少女慢慢转过脸,望着上官琴,淡淡一笑,有儿分伤感地摇了摇头道:“不认识。”
上官琴呆了上呆,道:“我刚才听你好像叫他是蒲大哥,是怎么回事?”
白衣少女冷冷地道:“他不姓蒲姓什么?”
上官琴摇了摇头,笑道:“姐姐真的是认错人了,也许姐姐还不清楚,这个人乃是大漠南疆的娄大侠娄骥!”
“娄骥?”
白衣少女睁大了眸于,几乎呆住了。随后冷冷一笑道:“他是娄骥?谁说的?”
上官琴怔怔地道:“是他自己说的!”
白衣少女目光在蒲天河身上一扫,目光中含有无限凄凉,她轻轻叹了一声道:“就算他是吧!”
上官琴催促道:“姐姐快救他醒过来吧!”
白衣少女点头浅笑道:“放心,我比你更关心他。只是我还有几句话,要问问清楚。
他死不了!”
上官琴糊涂地道:“姐姐问什么呢?”
白衣少女冷冷一笑道:“这娄骥,你认识他多久了?”
上官琴呆了一下,吞吐道:“昨天才认识。”
白衣少女微微冷笑道:“昨天才认识,今天就同行共路了,真是好快!”
上官琴面上一红道:“姐姐不要这么说,我昨天如非这位娄兄救命,只怕已遭了方才那厮毒手了!”
白衣少女哼了一声,点了点头道:“你们现在又是去哪里呢?”
上官琴奇怪地看了看她,心想怪事,这人何必这么多事,问这些又干什么呀!
可是对方总是有恩于自己,她既见问,怎好不答?
想了想,上官琴就道:“告诉姐姐也无所谓,这位娄兄因要去参观赛马盛会,他初来蒙古,又不识路,小妹要返回寒碧宫,故此顺路,是以结伴而行。”
白衣少女点了点头,道:“这么说,那春如水春夫人是你师父了?”
上官琴点了点头,道:“不错,正是家师。”
“你叫什么名字?”
“上官琴。”
白衣少女点了点头,道了一声:“好!”
她把手中的那颗药丸,递给上官琴道:“这颗药丸乃是我自星星峡一位前辈处讨得的,非但有解毒去毒之效,并有培元固本之功,你与他服下之后,不消一会儿,他必定可以醒转!”
她说到这里,站起身子道:“我走了!”
上官琴忙拉住她道:“姐姐是我二人救命恩人……再说这位娄兄必定也很想拜识姐姐呢!”
白衣少女哼了一声道:“我可不想见他!”
上官琴怔了一下,道:“姐姐救人务彻,还是等他醒转再去如何?”
白衣少女眼角一瞟,已然腾身上马,冷笑道:“有你在旁,比我强多了!”
上官琴忙上前道:“姐姐……我真不知该怎么感激你!”
白衣少女冷漠地道:“不必谢,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再见!”
说罢带过了马头,上官琴忙道:“姐姐芳名可以告诉我知道么?”
白衣少女马上回身道:“娄小兰!”
上官琴蓦地一呆,道:“啊呀……你原来是沙漠虹呀……那你们岂不是兄妹么?这……”
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本来就是兄妹嘛!”
上官琴睁大了眼睛,痴痴地道:“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娄小兰在马上冷冷一笑道:“等他醒转之后,你只告诉他我来过了就是。我暂时还不想见他!”
双足一夹马腹,座下白驹一声长嘶,扬开四蹄如飞而去。上官琴忙赶上道:“娄姐姐,娄姐姐……”
可是沙漠虹座下神驹,乃是出了名的快,真可称“来去如风”,早已驰得无影无踪。
上官琴真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自言自语道:“怪事……”
她快快地转到了蒲天河身边,仔细端详了蒲天河一番,对方那冠玉的面颊,长长的剑眉,果然是生平难得一见的美男子!
上官琴看着看着,不知不觉间觉得脸上一阵阵地发热,猛然往地上啐了一口道:
“我真是……”
当时忙把娄小兰给的药丸,放在了蒲天河口中,又喂他喝了一些水,然后她退坐一边,痴痴地等了一刻,蒲天河果然长吟了一声,倏地睁开了双目。
上官琴上前笑道:“谢天谢地,你总算醒了!”
蒲天河倏地坐了起来,摇了摇头,恨声道:“屠一夫他们人呢?”
上官琴掩口一笑道:“早走了!”
蒲天河皱了一下眉,站起身来道:“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你救了我?”
上官琴笑道:“你把我也看得大高了,我哪有这么大本事!”
蒲天河望着她,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娘怎么不说?”
上官琴才笑哈哈地道:“事情可真巧!娄兄,你绝对猜不到,救你我的人会是谁?”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你不说我自然是不知道!”
上官琴望着他神秘地笑道:“告诉你吧,救你我的是令妹!”
蒲天河一呆道:“我妹妹?我哪一个妹妹?”
上官琴笑嗔道:“娄兄,你真是!救你的乃是你妹妹沙漠虹娄小兰呀!怎么,你没有这个妹妹呀?”
蒲天河顿时一惊,左右看了一眼,道:“她人呢?”
上官琴笑道:“她早走了,好像她有点生你的气。这是怎么一回事?”
蒲天河闻言,只觉得心头有说不出的苦闷,频频苦笑。心想道:天呀!这可是纠缠不清了,怎么这时候,又偏偏会遇见了她,如果她误会我和这位上官姑娘,岂不是跳到了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想到此,一时垂下了头,默默无语。
上官琴走上来道:“娄兄你还觉得难过么?”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娄……我妹妹她上哪里去了?”
上官琴用手指了一下道:“是向这个方向走的,上哪里去我也不清楚。不过她说以后还会见面,也不知怎么个见法!
蒲天河拍了拍身上的沙土,叹了一声道:“我们走吧!
说完翻身上马,上官琴这时也上了马,笑道:“你妹妹武功真好,那道人一条腿,也被她砍断了,只是她的心太好了,居然放他们逃走了!”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为人还是厚道些好!”
上官琴一笑道:“你们兄妹倒是一个论调!要知道他们要是抓住了你们,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蒲天河皱眉不语,心中却在想着娄小兰忽然出现的事情。
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自己好不容易躲开了他们兄妹,却想不到在蒙古又碰见了。在她眼中,不定我是如何无情而孟浪的一个人。
想到此,内心浮上了一阵凄凄之感!
两匹马在沙漠行着,蒲天河怀着沉重的心事,更不想与上官琴多言。
上官琴倒不以为怪,她只当他们兄妹之间,是在闹别扭,因此一路之上,尽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来谈。她向蒲天河道:“娄兄,恕我多话,你可曾娶过媳妇了?”
蒲天河不由面上一红,苦笑道摇了摇头。上官琴一双光亮含情的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下,道:“真的?”
蒲天河一笑,道:“我何必骗你?”
上官琴低头笑了笑,一双眸子微微瞟了他一下道:“你可曾知道,你是一个很讨女孩子喜欢的人……”
蒲天河怔了一下,含糊地道:“哦……是么?”
上官琴笑着点了点头,明媚的眸子,在他脸上转了一转,脸色微微发红地道:“你的眉毛长得很好,鼻子也好看,很美!”
蒲天河哈哈一笑,双腿一夹马腹,胯下坐骑猛地窜了出去,上官琴娇笑了一声,也追了上去。
一男一女,各自放马,在这大沙漠里疾驰了起来。
差不多将近日落时候,二人已来到了一处叫“克贴图码札”的地方。
这地方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由四面八方来的牧民,在这里集结成临时的住家,各色的帐篷,五光十色的布匹买卖,形成了一种边地人民独有的特色。
蒲天河与上官琴来到这里,简直就成了泥人儿一样,人马都需要进食休息。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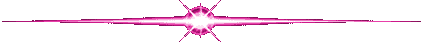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