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3)
|
|
锦衣青年手摇纨扇,扇坠儿竟是核桃大小的一颗明珠,衬以他右手无名指上的一个翠玉扳指,两相辉映,果真有几分骄人的气势,那一双灼灼神采的眸子,自一开始,即不曾把眼前这位官居四品的罗大人看在眼里。
罗老子耳目观之下,乃自断定来人绝非好相与,却是心里一口怨气难出,正不知如何自处。
当面锦衣公子却也识趣,为之一笑道:“如此花月良宵,且莫为你这个俗物坏了清兴,李长庭!”
“在!”黑瘦汉子趋前躬身听令。
“咱们手下留情,且饶过了他这一回!”锦衣青年一派轻松地说:“给我送客!”
“是。”黑瘦汉子单膝下跪,高应了一声,转身起来,直走向罗老头面前。
“姓罗的,你就请吧!”
罗老头一连哼了两声,连说了两个“好!”字,霍地站起来,招呼身边童儿道:
“我们走!”
瘦娘趋前笑道:“送罗老大人!”
老头子忽然一挥袖子说:“用不着……”转身自去。
甜甜姑娘总算找来了。
她是这里的头牌当红姑娘,设非是锦衣青年的豪阔出手,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她由别人的房里硬给招唤过来的。
黑瘦汉子李长庭与中年文士叶先生,都躲了出去,这间房子里便只剩下了锦衣青年一个人。
进门请安问好之后,甜甜姑娘才认出来这个强梁的客人,原来是他——他就是那个住在庙里的奇怪客人,一时又惊又喜,脸上充满了笑靥。
“我说是谁能有这个本事……原来是你?我的大相公你怎么来啦?”
一面说,小鸟依人样地偎了过去,却把一只粉酥酥的白嫩皓腕,轻轻攀在了对方肩上。
锦衣青年想是等久了,沉着张脸,老大的不开心样子。
“怎么……生我的气了?好啦!……人家这不是来了嘛!”一面说,玉手轻推,娇躯投怀,只是在对方身上腻着:“人家不知道是大相公你嘛,要知道是你,我飞也飞过来了……”
嘤然一笑,便自腻在他身上。
锦衣青年伸手一推道:“去!”甜甜身子一跄,差一点坐了个屁股蹲儿。
“哟……大相公,你这是怎么啦?”眼睛一红,甜甜那副样子,像是要哭了起来。
“我只问你!”锦衣青年说:“这会子你都上哪去了?让我好等!”
“我的爷!”甜甜怪委屈的样子:“还能上哪去呀?左不过是命苦哟!陪着人家有钱的大爷消遣,叫咱们往东咱们往东,叫咱们往西……”
“不要再说了!”青年手拍桌案怒声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叫你甭再接客人了,你怎么……”
甜甜呆了一呆,不免向着面前青年一再地打量不已,这件事可是透着有些稀罕……
“我的爷……你说这种话?”突然她趴在桌子上,呜呜有声地哭了起来。
“那还不是命苦……不接客怎么办?”一边哭,甜甜抬起了脸,热泪涟涟地直向锦衣青年望着:“我这个贱身子,除了爷以外,谁怜惜?谁疼?……大相公你多可怜咱们,就别再怪罪了好……”
小模样原就娇憨动人,这一伤心,宛若梨花带雨,谁还再忍心苛责?便是铁石心肠,也为之动心,更何况郎本多情?!
看看气不起来,锦衣青年这才叹息一声:“别再哭了,算我错了,好吧!”
经此一言,甜甜便为之破涕为笑,红着两只眼施施然又自偎了过来。
“相公爷,都这么晚了,不在庙里歇着,怎么会想着来了这里?……”
“你不乐意?”
“我乐意!”甜甜学乖了,嘴更甜:“我打心眼儿里就乐意!”
一只手攀在青年肩上,恁地有情样子,她说:“打前儿个和大相公分手以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颗心里头,就只有大相公你一个人的影子,成天价扑通扑通!干啥都提不起个劲儿,相公爷,你说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嗯——”
未后那一声娇哼,语音含糊,却把一半香腮,贴近到对方脖子里,樱唇半开,既麻又痒地咬着了青年的耳朵珠子……
烛影摇红,更漏已深。今宵苦短,应是安歇时候……
手挽玉人,吹气如兰。
这一霎,魂儿飘飘!锦衣青年方自欠起身来,待将吹熄了床前的灯,却是扫兴。
外面有人叩门。
“笃!笃!笃!”一连三声。
紧接着传过来那具随行黑瘦汉子的声音:“先生开门!有要事禀报!”
锦衣青年愣了一愣:“是李长庭?”
“是……”黑瘦汉子十分急促的声音道:“先生再耽搁一会,迟了来不及了!”
话已至此,青年只得下了床,所幸衣带未解,不然要大费周章。
门开了。
黑瘦汉子李长庭却不敢贸然进入,向后面退了一步。
青年不悦道:“什么事这么急,明天说不行么?”
李长庭又往后退了一步:“迟了便坏事了……先生!”
他声音放小了,就近青年身边道:“衙门里来人察客,不一会就到这里啦——”
锦衣青年陡然为之一惊。
“这……又是怎么回事?”
“准是那个姓罗的捣的鬼!”李长庭说:“这里的鸨儿正在前面应付,看看招架不住,叶先生要我赶紧护驾,通知先生,这就离开!”
锦衣青年悠悠地出了口气儿,却也无可奈何,冷笑道:“怎么走?”
“叶先生已由前面先走了,我侍候先生由高里来去!”
“好吧……”青年不悦道:“先候着!”
“遵命!”
弯身一欠,李长庭退向暗处站定。
锦衣青年怅怅关上了门,反身回来。
甜甜约摸着也猜知出了什么事情,仰着脸,迷惘的样子:“什么……爷?”
“有事,得走了!”
“走……现在就走?”
“嗯!”锦衣青年一面整理着身上衣裳,看着面前的甜甜,心里可真教舍不得。
“大相公……您别走……”
甜甜老大的不依,一扑而上,紧紧抱着了他的身子。
“我不愿您走……就是不让您走……”
“傻丫头!往后我还会常来,快起来!”
甜甜仰起脸,嘟着嘴:“真的,您可别哄我!”
锦衣青年摩娑着她雪白细嫩的肌肤:“我几曾又骗了你?甜甜,你本来叫什么名字?”
“娘家姓田,小名叫……”抬头一笑,害羞地说:“不好听,就别说了……”
说到这里,外面又在敲门,李长庭的声音道:“爷,得走了!”
“知道了!”
锦衣青年由身上摸出了个翠玉雕饰一——只玉老虎。
“这个你拿着……过两天想着来庙里……我得走了。”
甜甜接过玉老虎,瞧了一眼,笑逐颜开地握在手心里,扑上去一抱,便自腻在了对方怀里。
“干嘛老送我东西?怪不好意思的……”
“你不喜欢?”
“谁说不喜欢?您瞧……”背过身子,把贴胸的一个玉坠掏出来:“这不是大相公送的吗?人家一戴上就舍不得摘下来了
锦衣青年还要再说什么,外面已传过来嘈杂的人声,这才为之吃了一惊,叹息一声:
“我走了——”
甜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乍闻人声,吓了一跳。这当口锦衣青年,已拉门步出。
李长庭就在门口候着,一口长剑已执在手里,正自焦急,见着青年出来,才自松了口气——
“快着点,爷,背着您吧!”
锦衣青年还在迟疑,灯光闪烁,一行人已现身当前月亮洞门。
果然是衙门口的来人。
一共是六人,挂着腰刀,拿着锁链,气势汹汹,一副要拿人犯的样子,鸨儿瘦娘赔着笑脸跟在身边,老远看见,吆喝道:“相公爷,衙门口查房来啦——”
话声未了,为首的矮子捕快,已扑身而前,大声喝叱道:“站着,不许动!”
几名捕快,更是不容分说,“刷!”地扑了上来,几把腰刀,团团把二人围在了中间。
李长庭闪前一步,挡在锦衣青年身前,冷冷笑道:“你们想干什么?”
矮子捕快手上拿锁链,哗啦啦在手上甩着,打着一口广西乡音,厉声道:“我们是干什么的?问得好!”说时一双细长的三角眼,频频在二人身上转动不已。
“不错,就是你们两个!”
冷笑一声,他接着道:“老实告诉你们吧,查房是假,有人把你们给告了,没什么好说的,跟我们到衙门去一趟!”一甩脖子:“给我拿!”
其中一人抖手飞出了一道锁链,直向锦衣青年脖子上套落下来。
却是李长庭眼明手快,左手一探,哗啦一声,抓着了飞来的链子,叫了声:“撒手!”
霍地往回里一带。
来人捕快,那等蹩脚身手,如何当得他的神力一带?身子一个打跄,直向前面倒了下来。
却为李长庭飞起一脚,踢中前胸,“砰!”一声,直挺挺地仰面摔倒,登时不再动弹。
众人乍见,俱都惊叫起来。
“反了!”矮子捕快大吼道:“你们敢杀官拒捕?!”
话声未已,却为李长庭反手一掌,击中在脖颈之上,这一掌力道不轻,矮子捕快嘴里“吭!”了一声,便自倒了下来。
群声大哗里,李长庭已护侍着锦衣青年闪身长廊。
剩下的几个捕快,眼看着对方黑瘦汉子如此厉害,不过是照面的当儿,已收拾了两个同伴,哪里还再敢妄动,一时间俱都呆若木鸡,就连鸨儿瘦娘也吓傻了。
一行人只是伫立原处,呆呆向这边看着。眼看着那个黑瘦汉子护侍着锦衣青年,消失于暗夜之中,俄顷间,拔起来一个黑影子,宛若深宵巨雁,已自上了墙头,接着闪了几闪,便自消逝不见。
禅房里点着盏高脚油脂松灯——灯焰由仰头作势的仙鹤嘴里吐出来,光彩熠熠,摇动起一室的迷离,混合着淡淡的檀香味道。这味儿据说有清心爽智之效。
阿难和尚脱光了上身,骑在条凳上,少苍老方丈正在为他背上推拿按摩,力量不小,阿难和尚满头满脸都是汗珠子。
推着推着,和尚“哇!”的一声,呛出了一口瘀血。
“好了!”
老方丈后退一步,坐下来,脸有喜色地道:“这口血总算出来了,出来就好了!”
阿难和尚大声喘着气,用块布巾一面擦着,一面道:“只当是口浊血而已,谁知道这么厉害,要不是方丈师父手法高明,弟子真还浑然无知,阿弥陀佛——”
老方丈也跟着颂了一声佛号,冷冷说道:“伤你的这个人手劲儿不弱,多半练过磨磐功夫,这是属于北派少林的功夫……难道此人早年出身少林?”
阿难和尚摇摇头道:“这可不像,老师父也见过,就是那天那个姓宫的!”
少苍老和尚点头说:“我知道,见过他……”
说时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走了一趟,站住了脚说:“阿难,依你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那个姓诸葛的青年,又是什么人?”
阿难已穿上了僧衣,谛听之下,拧着眉毛,十分费解地道:“不知道,真的弄不清楚,老师父不是说,他们是安南来的珠宝客人么?”
少苍老和尚点了一下头:“实在是很难说……我原来以为那个姓诸葛的是来自京师的宦门子弟,可是看看又不像……说是贩卖珠宝的客商……味道总似不像……那青年后生好大的气派,那样子简直像是个皇帝……”
未后的这句话,倒似把他自己给提醒了,愣了愣,十分震惊地道:“难道他真是?……
阿弥陀佛——这可就难以令人置信了……”
“老师父你是说……”
“不……不……”老方丈呐呐说道:“还没有准儿……”
阿难和尚道:“这阵子安南闹事,听说杀了很多汉人,听说朝廷派了征夷将军朱能到了龙州,这几天龙州城内外,到处都是军人,说是来了好几十万,看来这地方要打仗,不得安宁了。”
*注:据明史载,永乐初年,安南(今日越南)叛臣胡一元父子,杀害了明朝册封的安南国王陈天平,自立为帝,永乐大怒,遣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统兵八十万以伐。
老方丈喟然叹道:“我知道了——”
阿难和尚道:“这么看来,这个诸葛公子,或许真的是安南的珠宝商人,因为避难而来到我们这个庙里……也说不定!”
老和尚呐呐地宣了声:“阿、弥,陀、佛……你说得不错,总之,为了庙里的宁静,诸葛施主人住我们庙里之事,千万张扬不得……你要切切告诫本寺弟子,谁要是走漏了风声,从严治罪!”
“弟子遵命!”阿难合十领命。
一霎间,传过来晚课的当当钟响声音。阿难和尚随自欠身告辞,向外步出。
禅房里便自剩下老方丈一个人。
萧萧山风,颤抖着棉纸窗棂,荒山狼号,听来倍觉凄凉。
推开窗户,向着西面偏殿瞧瞧——那里还亮着灯,显然诸葛公子一行都还没有歇着。
老方丈缓缓收回了手,一霎间心绪烦乱,再也不能安静。
他心里藏着一个极大的隐秘,这个隐秘一天不经证实,他心里一天就不能持平宁静。
虽是个跳出红尘的出家和尚,当今大事,却也不曾昧于无知,特别是四年前,本朝天子建文皇帝于燕王攻破京师,城破之一霎,深宫走失的那档子传说,江湖上早已经喧腾一时,众说纷纭,传言之一,便是建文帝来了云贵,这件事证之三年前工部尚书严震直巡视云南在泽州的忽然而死,据传便是严氏在泽州遇见了建文君,悲怆羞愧之下,吞金自尽。
老和尚不是个简单人物,风尘异人也,一身内外功夫,甚是了得,生就侠肝义胆,虽然羁身沙门,却是极有义气,眼前这人诸葛居士的种种异端,在在启人疑窦……两件事扯在一起,运思筹想,莫怪乎老和尚那一颗古井无波的心竟然为之大乱了。
脱下了身上的杏黄袈裟,把一条紫罗绸巾,紧扎腰际,虽是大袖飘飘,却也无碍行动。
老和尚决计要到偏院走走,看看那个诸葛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临行之前,他把半碗残茶泼倒地上,两只脚分别践踏,鞋底既湿,可利于高处行走,即使在滑不留脚的琉璃殿瓦上,也不虞行足滑倒。
外面星皎云净,月色如银。
轻登巧纵,倏起倏落。
不过是三五个起落,已到了西边院子。
这就是被称为诸葛居士一行人所下榻的偏殿了。
老方丈一身轻功极是了得,却也由于阿难和尚的大意负伤而心存警惕,不敢大意。
在他眼里,那个与阿难和尚对掌互伤的宫先生,也许并不是对方阵营里最厉害的人物,真正厉害的人,在他看来,应该是青年居士身边的那个高瘦汉子李长庭。
李长庭这个名字,还是他这两天才探知的。
这个人机智深沉,目光炯炯,那日一见,观诸他几个很小的动作,老和尚即已测知他的不好相与,是个相当碍事扎手的人物。
老和尚今年七十八了,自幼出家,练的是“童子功”,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几十年一天也没断过,只是佛门静寂,与人无争,武术这玩艺儿,也只是拿来强身而已。
却是,今夜似乎多少派上了一些用场。
眼看着他施展杰出轻功——“潜龙升天”,一缕轻烟般的灵巧,已拔上了殿阁。
如果他所记不差,对方那个青年居士便应是下榻在这间殿房里。
山风阵阵,引动着殿檐间落叶萧萧作响。
原来对方青年居士所住的殿堂,十分宽敞,四面轩窗衔接着环有雕栏的平台,地上铺着罗底方砖,月色里景致如画。
此时此刻,纸窗上映着灯光,更似有人在低声说话。
老方丈刚要偎身过去,耳边上响起了沙沙脚步声,一个人由侧面甬道现身而前。他便临时机警,掩藏于石栏之后。
来人手托食盘,长衣飘飘,一径来到眼前,俟到接近佛殿正门前丈许左右,足方站定,却由殿檐暗处闪出了个人。刷地掠身而前,挡住了来人去路。
“给爷送点心来了!”来人站住身子。
后者说了声:“知道!”即由来人手里,把点心盘子接了过来。
来人说:“今儿个的莲子欠火,不顶嫩,怕是不合爷的口味儿,没法子,蔡厨子这两天心里烦,闹情绪!直嚷着住不惯山里,要走!回头禀明叶先生得好好说说他。”
蔡厨子显然是一个人的外号,职掌厨房炊事,话里已有交代,想是他不习惯住在山里,已有离去之意,是以今晚这碗清蒸莲子不尽理想,有些儿欠火。
后来现身的那人“哼”了一声,冷声说道:“告诉他给我放明白一点,别以为出了宫,就没人能管得了他,没有叶先生的命令,他要是胆敢跨出这庙里一步,哼哼!小心他的脑袋!”
说了这句话,转身走向正门,在门外大声道:“爷的点心来了!”
里面有人应着,才自开门让他进去。
嘿!敢情是规矩不小。
老和尚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越加地心里激动,不能自己。
这个人到底是谁?
其实不俟再探,他心里已有数儿了。
乘着那个人送点心进去的空档,老和尚展动长躯,起落之间,已贴近佛殿。
紧跟着一长身,施展“月移星换”身法,呼地袭上了大殿一角。
这里的一切,不用说他熟极了。
身子一上去,往前面一矮,便自掩身于画檐内侧,再不愁为人所发觉。
可喜的是,就在他眼前面,嵌着一扇八角形的通气窗户,据此以视,佛堂里巨细无遗,尽收眼底。
殿房里点着五六根高盏白烛,光焰熠熠。
那个复姓诸葛的锦衣青年,盘着双膝,坐在椅子上,正自由面前人手里,接过夜点——清蒸莲子。
而那个呈送莲子的人,竟然双膝跪地,把一个黑漆盒盘高举过顶。
老和尚心里念了声“阿弥陀佛”,更加认定自己之所料非虚。
原来人前人后,这里的规矩不一,称呼亦是有别。
眼前静夜无人,不必再事伪装,自以本来面目相对应处。
青年居士拿开碗盖,用镶有象牙把柄的小小银匙勺吃着碗里的莲子,才吃了一口,便停住皱眉道:“不烂,不能吃!”
跪着的那人说:“启禀皇爷,蔡师傅这两天身子不好,闹病,换了个人,手艺差了些!”
这一声“皇爷”总算揭开了谜底,所谓的诸葛居士,什么珠宝商人……全是假的,胡诌乱盖,对方锦衣青年,诚然正是传说中流亡在外的前朝天子——建文皇帝。
他的真实姓名应该是朱允炆。
果然他还活着,而且就住在自己这个庙里,甚至于这一霎,就在自己眼前。
这个突然的证实,即使原已在老和尚算计之中,无如眼前面对的一霎,亦不禁带给他极大的震惊,心里一阵子忐忑,说不出的又惊又喜……
“阿弥陀佛,果然是他……是他……”
心里一个劲儿地颂着佛号,一双眸子眨也不眨,直盯向座上少年——少年天子。
虽说是亡命在外,居难之中,这位前朝天子、青年皇帝仍然有其架式,派头不小。
不大习惯将就。
把个青花细瓷盖碗,重重搁在几上,怒声怨道:“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要什么没什么,想吃点什么都不称心……”
跪着的那个人,前额触地说:“万岁息怒,奴才这就去瞧着,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没有……”
“算了、算了!”皇帝挥着手:“下去、下去!”
跪着的人又磕了个头,才自起身,倒退着身子走了。
皇帝忽地转过脸,瞧着一边默坐的叶先生道:“叶希贤,我叫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启禀皇爷!”叶希贤站起来拱手道:“微臣遵旨,已差人打听去了!”
“光打听有个屁用!”皇帝说:“程济呢?去了都半年了,人不回来,总该也有个讯儿吧!”
叶希贤、程济均非无名之辈,一为前朝监察御史、一为翰林院编修,听在老和尚耳里,禁不住心里又是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暗自忖道:“这两个人,竟然也还活着……”
却见那位前朝御史大夫,欠身抱拳道:“皇爷岂能不知?这阵子安南乱得很,去不得……
听说朱能带兵来了,就在龙州!”
“啊……”
“还听说……”叶先生上前一步,小声道:“朱能才一来就病倒了,六军无主,进退不能,很麻烦……”
他的消息很灵,有些连老和尚也是不知。
老和尚看着,听着,正自入神,猛可里,身后疾风飘飘,忽悠悠落下个人来。
星月皎洁,照见来人蓦落的身势,宛似深宵巨鸟,一发而止,落地无声。
好俊的轻功!
一袭月白色的肥大长衣,却把截过长的前襟塞回腰里,露出来的一双高筒白袜,月色里分外醒眼,个头儿既瘦又长,往那里一站,单腿微曲,卓然鹤立,真有几分白鹤的出尘潇洒。
头上戴着顶瓦楞帽子,却是自眼目之下扎着一方帕子,看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
双方目光交接,老和尚自觉身形败露,不由得暗吃一惊。
对方来人鼻子里轻轻一哼,二话不说,腰身轻窜,“嗖!”纵身于两丈开外,落向侧面瓦脊。
这番邂逅,却是奇怪。
一时间,倒是老和尚难以自己,放他不过了。
脚踝上着力,施展轻功中“千层浪”的绝技,老方丈身形乍起,已袭向来人身后。
对方身法饶是了得,瘦躯间弯,箭矢也似地,又自窜了出去。
老和尚自是放他不过,紧蹑着他身后,力迫不舍,星月下直似一双大鸟,一追一遁,转瞬间,已是在百丈外。
跨逾庙墙之外,眼前乱山云集。
老和尚再无所忌,嘴里喝叱一声:“你还要跑吗?”脚尖着力,呼地掠身直起。
一起即落,如风赶浪,已到了来人背后。
忖思着来人绝非易与之辈,少苍老和尚手下再不容情,身形前耸之下,用双撞掌功力,直向来人背后击去。
来人高瘦身子,“呵呵!”一笑,倏地转过身来,却把双鸟爪也似的瘦手,由两面抄起,反向对方一双手腕子上拿去。
老和尚“嘿!”了一声,撤掌旋身,“刷!”地掠身丈外,那人跨前一步拿桩站稳,便自不再移动。
“阿弥陀佛!”老和尚手打问讯:“这位施主,深夜光临敝寺山门,有什么见教?
还请当面说明,要不然可就请恕老衲多有开罪了!”
“哈哈!”来人仰天一笑:“我当是什么鸡鸣狗盗,原来是方丈大师父,这个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不知不罪,多多原谅!”
说时抱拳一揖,神色里极是自负。
打量着对方这番傲然神态,老和尚忽似有所悟及,“啊!”了一声,倏地愣住说:
“莫非是岳天锡……岳老弟台……”
来人哈哈一笑:“老和尚眼睛不花,还真行——话声出口,伸手一扯,拉下了脸上蒙帕,现出了来人轮廓分明、轩昂气势的一张长脸,老和尚认了一认,颂了一声“阿弥陀佛”便自哈哈大笑起来。
“采石一别,多年不见,岳檀越,今夜晚怎么会想到来到老和尚我这个庙里?”
老和尚脸上不失笑靥,显然是遇见了多年故旧、知己。
来人岳天锡双手抱拳,深深打了一躬:“来得鲁莽,大师海涵,老师父兴致不浅,怎么在自己庙里还用得着这般鬼鬼祟祟?”
老方丈哈哈笑了两声,不大自在地说:“此事说来话长,老弟台你初来是客,走,咱们回庙里说去?”
岳天锡哼了一声道:“正要拜访。”
老方丈说了个“好!”字,刚要转身,蓦地觉出有异,侧面前方树丛里似有人影一闪,一个人极其轻灵地拔身而起。
深夜里像是一只大鸟般的轻飘,惊鸿一现,又复隐身于沉沉黑暗之中。
老和尚“啊——”了一声,十分诧异地转向身边老友看去,便在这一霎,身侧树丛似有微风惊动,响起了轻微的一阵沙沙声。
以老和尚观察之微,自是知道有人来了。
“阿弥陀佛。”
嘴里颂着佛号,老和尚正待发言示警,身边老友岳天锡已自笑道:“是雪儿么?出来吧,人家看见你了!”
话声方顿,树丛间人影飘动,燕子也似的翩跹,面前已落下一人。
老和尚微微一惊,道了声:“阿弥陀佛!”
再看来人,竟是个长身窈窕的姑娘。
黑夜里看不清她的面貌如何,却是举动轻灵,极是利落从容,只看她来去如风,动作之敏捷,当可想知一身轻功必是不差。
乍然相见,唤了声:“爹!”便自在一边站定,只是用一双灵巧的眼睛,频频向老方丈打量不已。
“这是……”老和尚恍然记起对方似有个女儿,却是记忆模糊。
岳天锡莞尔笑道:“这是我女儿青绫,小名雪儿,和尚你大概还没有见过?”
老和尚细窥这位岳姑娘,英姿曼妙,体态婀娜,两只大眼睛,黑白分明,菁华内蕴,一望之下,即知道身负绝功,大非等闲。
“阿弥陀佛。”
老方丈单手打着问讯:“姑娘好俊的一身轻功,看来是尽得令尊传授的了!”
岳天锡嘿嘿笑道:“老和尚这一次你可看错了,我那两手如何教得了她?这丫头造化不差,自小就被南普陀的‘六如轩主’所收养,三岁离家,十六岁那年才回来,今年十八了,一身本事比起我这个老爸爸来,可强得太多了!”
老和尚一声嗟叹道:“原来是六如先生的高足,这就难怪了……阿弥陀佛——”
岳天锡这方向女儿介绍道:“这便是我常与你提起的少苍老师父,上来见过。”
岳青绫叫了声:“老师父!”深深施了一礼,便自站立一旁。
不像时下姑娘那般打扮得花枝招展,岳青绫却衣着素雅,长裙曳地,腰肢款款,衬着肩后的青霜长剑,饶是别有妙姿。
老和尚自觉这般衣着,大是失礼,仓猝会晤,却也无奈,总是素交称好,也就说不得了。
“岳檀越多年相知,深夜来访,必有要事,咱们就不拘俗礼,请随我来。”
话声一顿,双手作合十状,道了一声:“请!”
陡地拔身而起,月色里一如孤鹭白鹤,翻腾间已抄身丛岭。
岳氏父女却也不含糊,随着对方的前导,各自展现轻功,亦步亦趋,紧蹑着老和尚身影跟了下去。
眼前来到了方丈待客禅房。
为免惊俗,老方丈独自个先进去,换了袈裟,这才开门纳客。
岳氏父女坐定之后,老和尚才自唤了小沙弥倒茶。多点了一盏灯。彼此才得看了个清楚。
却见这个岳天锡,貌相清奇,论年岁当应是五十开外,却是发如黑染,一根白的都没有,眉眼间显示着一种孤高,很有些卓然不群气势。
岳青绫洁白素净,惟眉眼间秀中藏锋,颇有几分乃父的威仪,女孩儿家终是脸皮儿薄,老和尚多看了她两眼,便自脸上讪讪,随即把水汪汪的一双眼睛飘向窗外。
“阿弥陀佛!”老和尚脸现笑容道:“老朋友深夜来庙,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现在总可以明说了吧!”
“嘿嘿!”
岳天锡低笑了两声,目光炯炯看向对方道:“老和尚不要见怪,你道这庙里,我父女是第一次来么?”
老方丈愕了一愕。
岳天锡看了女儿一眼,继而笑道:“老实告诉你吧,这半个月来,我父女来了总也有七八回了,只是今夜遇着了你,才自现身罢了!”
“噢……”老方丈微似惊愕:“这又为了什么?”
“和尚你先不要问我,倒是你今夜鬼鬼祟祟,放着经不念,到人家住处偷看个什么?”
“阿弥陀佛一一”
老方丈银眉频眨,双手合十道:“这么说,你我倒像是为着同一件事了?!”
“看来是差不多!”
岳天锡喝了口茶,一面向老和尚打量着,脸上神态,含蓄着几分神秘。
“都说你这庙里风水不差,如今来了条龙,太苍得龙,地灵人杰,以后香火活该大盛特盛了!”
老方丈“啊!”了一声,轻轻颂着:“阿弥陀佛!”随即点头道:“这么说,老衲没有猜错,那位朱先生果然是落在我这庙里的了……”
岳天锡一笑道:“如今你的责任重大,老和尚你打算怎么样?”
“阿弥陀佛!”老和尚呐呐说道:“任他真龙天子,又干我庙里和尚什么事,老和尚只作不知,平日所为,吃斋念佛而已,南无阿弥陀佛——”
岳天锡会意地点头而笑。
“这就对了!”他说:“其他的事交给我们父女来做吧!”
“什么其他的事……莫非……”
“这些日子风声很紧,老和尚难道你没有听说?”
“没……有……”老和尚摇摇头,慨然道:“出家人也只是吃斋念佛而已!”
岳天锡冷冷说道:“征夷将军来了,有人说他此行奉有密旨,便是要搜查藏在你庙里的这条龙!”
老和尚微微一愣:“阿——弥——陀——佛!”
岳天锡道:“而且,我有确实的证据,京师大内也来了人,一个姓方,一个姓井,乃是当今逆皇跟前的两个败类,手底下很不含糊……”
老和尚“噢!”了一声,讶道:“你说的是方蛟、井铁昆这两个武林败类?……”
岳天锡点点头道:“原来老和尚你也认识?”
“认识倒不认识!”老和尚说:“不过他二人早年在江湖的所作所为,武林中很有传言,后来听说投归燕王发了迹,以后倒是不曾再听说了,怎么他们也来了龙州?”
岳天锡眸子里精光四射,冷冷一笑:“他们要是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老和尚不由轻轻颂了一声“阿弥陀佛”,察言观色,不言可喻,岳天锡与上谓的方,井二人,设非结有深仇大怨,亦必有瓜葛,心里明白,却不曾说破。
岳天锡凌声道:“这两个败类,如今在逆帝朱棣手下当差,据说投效了锦衣卫,如今都有了功名,他们的来意,不问可知……老和尚,你却要十分仔细小心了。”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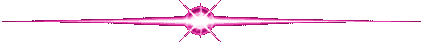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