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新记》是一部幽默作品。
“幽默”二字,是英文Humor的音译,属于喜剧的高级形式,包含着滑稽、诙谐、讽刺、机智等复杂的含意在内。之所以采用音译,恐怕是因为中文中还难以找到一个准确的对应的词汇。它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方法,通过含蓄、隐喻、引人发笑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对丑的否定和鞭挞,或对美的肯定和赞扬。懂幽默、欣赏幽默,是文化修养的表现,是对社会矛盾深刻理解的结果。正如果戈里所言:“笑这个东西要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得多,重要得多!”
中国人民,是有着幽默的传统的。早在先秦时代,哲学家们就常利用幽默小品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如《孟子·离娄章句下》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就辛辣地讽刺了那种爱慕虚荣、上谄下骄的典型。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在其中专门写了一章《滑稽列传》,记载了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秦国的优旃等人利用“滑稽”批评君王;魏国的西门豹利用“滑稽”战胜迷信,为民除害的史迹。由于其含意的隽永,言辞的智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所理解的“滑稽”的范畴,而应视为“幽默”了。魏晋以后,大量的笔记、民间故事、寓言、笑话,更是保留了不少幽默作品。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劳动人民往往通过幽默,来抒发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的希望。在处境最困难时,幽默感能成为人民乐观的精神支柱,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幽默使人发笑,但发笑并不等于幽默,真正的幽默,应包含深刻的思想和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露。在中国,幽默一开始见于历史就是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相联系的。它并不是插科打诨,粉饰太平,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是通过讽刺,谴责邪恶,宣扬正义。这乃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幽默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应当是劳动人民向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中国人常用“亦庄亦谐”来形容幽默作品,其实“谐”仅仅是形式,“庄”才是其本质。
中国人民对于幽默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很多地方戏(如川戏)中,幽默的主题是屡见不鲜的;而在表演艺术中,丑角往往具有鲜明的特征。举国上下都爱听的相声,就是以其幽默而著称。文学大师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小说,言简意赅,令人忍俊不禁而余韵深长,至今流传不衰。国外作家狄更斯、果戈里、欧·亨利等人的幽默作品,或以讽刺见长,或以结构取胜,在国内也拥有广大的读者。至于艺术大师卓别林的电影在中国所觅到的知音,恐怕是出乎卓别林本人的意料的。
幽默来自人民,人民需要幽默。然而自从十年动乱以来,幽默的内容尽管在曲艺、戏剧中有所保留,在小说中,却相对的少见了。其实在当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在举国上下改革的浪潮里,幽默比之过去更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对于一切阻碍改革的社会因素,对于一切官僚主义、因循守旧、颟顸无能、鼠目寸光、嫉贤妒能等恶习,都可以利用幽默的形式,进行揭露与批判。让人民在笑声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换句话说,在当前,幽默应该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很早就有意写一部幽默小说。1981年9月,我从美国考察回国,想为青少年写一部介绍美国实况的书。这应该是一个从东方人眼中看到的具体的美国,除了揭露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问题以外,还想包括美国人民、美国社会中很多优秀的因素,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而引起的误解和矛盾。于是很自然地,我想起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的三位主角: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如果让他们再度“西游”,必将有无穷的奇趣。把这三位习惯于小农经济社会的人送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把长期接受东方传统教育的“出家人”置于尖端科学的熏陶之下,这本身就酝酿着一种喜剧性的客观冲突。而《西游记》原著所带的浓郁的具民族特色的幽默色彩,也为改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西游新记》中,我故意尽量采用《西游记》对人物、风景、事件描写的原文,略加改动以后再赋予它新的含意,让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科学和幻想熔为一炉,达到强烈的对比,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
道理虽如此说,但是要探索民族化的幽默的特点,寻求社会主义条件下表达幽默的最佳形式;逗笑而不庸俗,谐趣而不荒唐,这种任务却不是像我这种业余作者所能做到的。所以《西游新记》只能说是引玉之砖,问路之石,希望这一尝试,能引起读者、作者的兴趣,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带来中国幽默文学新的繁荣。
从形式上看,《西游新记》实际上是一部不伦不类的作品。神话不似神活,小说不似小说。在当今世界上已有的文学分类中,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栏目去安置它,所以我就大胆地杜撰了一个“准神话”的名字。“准神话”者,似神话而非神话也。这并非我喜欢标新立异,实际上是无办法之办法。不过既然内容都是满纸奇谈,这形式也就不能考究了。姑妄名之,诸位看官不必认真也。
童恩正
1984年5月23日于成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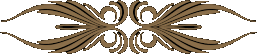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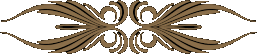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