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旌阳似已看到此点,所以启奏玉帝:“近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闲游结交,天上诸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恐后来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第五回)我们研究历史,知道革命须有组织,而要从事组织,又须联络各方人士。许旌阳以孙行者“闲游结交”,恐其“别生事端”,确是识微之见。秦末,人心思乱,而最初起义的不是豪族的项梁,也不是流氓的刘邦,而是戍卒的陈胜,盖唯戍卒才有组织。西汉末年,人心浮动,而起事者多属铁官徒阳朔三年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见《汉书》卷十《成帝纪》。。盖汉置铁官于郡县,从事采矿冶金。工人聚集一处,既有联络,而手握铁器,不难借以起事。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终而发生南北朝的对立。这个时代,政治腐化极了,然而历史上只见叛将,不见叛民,何以故呢?南北交战,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人民已经疲于奔命,而役繁税重,人民工作之后,心身极感疲惫,哪有工夫以从事革命运动。孙行者“日日无事”,而又“闲游结交”,天上诸星宿俱称朋友,若有不轨之心,多么危险。所以玉帝一听许旌阳之言,即着孙行者代管蟠桃园,“大圣欢喜谢恩”(第五回)。就此情形言之,大率是相安无事了,岂意蟠桃嘉会未被邀请,又闯了一场大祸。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历史上因饮食而引起祸患者,亦有其例。苏秦为赵相,张仪上谒求见,苏秦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张仪怒,遂入秦,用连横以破合纵之计(《史记》卷七十《张仪传》)。汉高祖用陈平计,以太牢进范增使者,既知为项王使者,改用恶食食之,项王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而卒兵败垓下,自刎而死(《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最奇怪的莫如郑灵公烹鼋之事。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弒灵公。(《左传》宣公四年)
推子公之意,固以为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而由灵公看来,饮食虽微,权力亦在君主。一位召而弗与,一位染指而尝,迹近儿戏,其实可以说是“天”与“人”的斗争,即神权与君权的斗争。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孙行者既封为齐天大圣,开府置吏(第四回),其于仙界,官不可谓不高矣。而蟠桃胜会竟然不许参加。孙行者以为“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尊席,有何不可”(第五回)。顾仙界也和人世一样,官僚办事,往往格于“旧规”。旧规请者皆请,旧规没有姓名的,虽然名注齐天,官称大圣,亦不在邀请之列(第五回)。这由孙行者看来,当然有害其自尊心,于是偷吃了仙品仙酒,又误入兜率天宫,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个葫芦金丹。孙行者知大祸已闯,所怕的乃是“惊动玉帝,性命难存”(第五回)。走,走,走,走到下界为王。即此时尚有畏敬玉帝之意,而无窥取帝位之心。
到了玉帝派兵讨伐,天将“一个个倒拖器械,败阵而走”(第五回),既为显圣真君所擒,而刀砍斧剁,雷打火烧,莫想伤及其身(第七回)。最后虽为老君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火炼,而仍不能将其化为灰烬。结果,还是跳出丹炉,“大乱天宫,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七回)。这个时候孙行者才萌轻视天宫之心,而欲夺取玉帝尊位。
政治不过“力”而已。最初还是物质上的力,积时既久,人们对“力”发生了畏敬情绪,于是物质上的力变为精神上的权威。物质上的力是有限的,精神上的权威则莫测高深。孙行者最初还惧“惊动玉帝,性命难存”,就是因为玉帝高高在上,尚有权威。但是吾人须知最能表示政治之力者莫如军事。军事失败,将令人们怀疑政府的统治力。隋炀帝时,役繁税重,“百姓思乱,从盗如市”(《隋史》卷六十四《鱼俱罗传》)。然而此辈只是饥寒交迫之徒,其势虽足以扰乱社会,而却不足以变易皇朝。到了大业八年车驾渡辽,亲征高丽,大败而归,皇室的权威便降低了。所以大业九年第二次讨伐高丽之际,世家子弟的杨玄感就乘机起事,而乱事规模亦忽然扩大。“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隋史》卷四《炀帝纪·史曰》),隋祚随之而亡。在民主国,外战可停止内讧;在专制国,外战常引起内乱。此无他,政治腐化,人心思乱,本来震慑于君主的权威,不敢反抗,军事失败,人民对于政府的力发生疑问,从而对皇室的尊严便不像从前那样的畏敬。于是过去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现在则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了。由此可知孙行者于逃出丹炉,大败天将之后,何以一反过去作风,不再畏敬玉帝,而欲窃取天位了。他要求玉帝搬出天宫,让他居住,以为“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这种革命思想与项羽所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所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同出一辙。弄到结果,玉帝只有借用外国军队,如来略施法力,孙行者便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
其实,孙行者亦有取败之道。他既已投降,籍名在箓,则与玉帝有君臣之义。臣篡君位,在吾国历史上固然不乏其例。然而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皇室式微,君主失去权威;二是臣下建立武勋,苟能树奇功于异域,则人望已归,禅让之事更易成功。司马昭平蜀之后,才敢接受九锡,传至子炎,方能称帝。晋时,桓温兵屈灞上,战败枋头,而回国之后,竟然欲移晋鼎,其不能成功,理之当然。刘裕与桓温不同,伐燕,平定齐地;伐蜀,谯纵授首;伐秦,观兵函渭。三次进兵,未曾一次失败,其武功大略不但可以震主,亦可以威民,故能坐移天历,而成移鼎之业。李延寿说:
宋武帝崛起布衣,非藉人誉,一旦驱率乌合,奄兴霸绪,功虽有余,而德犹未洽,非树奇功于难立,震大威于四海,则不能成配天之业,一异同之心,故须外积武功,以收人望。(《南史》卷十六《王镇恶传·论》)
这个见解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行。袁世凯于承认廿一条之后,竟然洪宪称帝,其不成功,理之必然。该撒树大威于西班牙,归而秉政。拿破仑立奇功于意大利,进而略取埃及,归而为独裁官。中外历史初无二致。孙行者如何呢?玉帝尚为群仙尊敬的对象,孙行者固然名注齐天,官封大圣,然而未立大威于仙界,又未树奇功于西天,只因蟠桃大会未被邀请,冲冠一怒,只为佳酿,是直子公之流,何能博得群仙同情,其觊觎帝位,终归失败,可以说是理之当然。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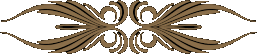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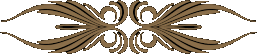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