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成书于神魔小说在中国文学苑中遍地开花的季节。作为文人有意识地整理创作的作品,它无疑是可以鉴见当时社会生活状况之一二的。它以游戏之笔大书孙悟空在三界腾挪跳跃、优游奔走的潇洒,同时又深怀对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无限忧虑:儒道释三教合一似乎是最好的出路,但均已垂垂老矣;大力张扬人的个性,又担心开了枷的人欲会膨胀至无限;在内部已趋腐朽的时候,欲向外寻求新鲜血液,可这得来也并易事。
一、三教合一—无意中的解构
《西游记》宣扬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取经故事的主角孙悟空正是这一主题的代言人,作者想要通过这一角色的塑造来展示自己的文化选择趋向。
孙悟空本是丹崖山上一块仙石孕育而成,在花果山快乐地生活。后为生存忧患困扰,不辞劳苦,远涉重洋,寻求长生不死之术,以冲破生命的极限。以求长生为诱饵的道教这时刚好迎合了他的口味。学成后不期然又与儒家的积极人世文化暗合,自封“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受儒道佛三家连手镇压,终被佛祖制于两界山下,并由此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从表面看来,学道、人儒,又历经种种磨难,修得“真心”,终竟成佛,是作者向人们提供的一个完满的文化选择趋向。作者要求人们向儒道释三家全面汲取营养,最好能自由出人,但在这里被大加宣扬的儒道释又是个怎样的面目呢?在赞语迭加的同时,那掩藏不住的暗流无法控制地从作者笔下涌出。
先看孙悟空首先遭遇到的道教。道教除了增加了法术之外,似乎只是一片乌烟瘴气:祖师太上老君只不过是个炼丹高手;五庄观的道士为一棵人参树竟要残忍地将唐僧师徒扔进油锅;宝林寺的道士是和尚的附庸;车池国的到上道士以迫害和尚为业;黄花观的道士是只与蜘蛛精交好的毒娱蚁……这一系列的道士形象莫不令人生厌。这样污浊的道教是可以向它寄什么希望的吗?作者在这里显然已失去了向人们推销道教的兴趣。
再看以国家和君主为至高无上、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牺牲自我报效国家的儒家。他们所尊崇的帝王们又是怎样的货色呢?那“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弯高上帝”,看似辉煌神圣、至尊无比,事实上却是个无能又残忍的人:他遣人骗孙悟空上了天宫,却不知怎样安排官职一;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他不得不求助于如来;卷帘大将沙僧只为“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就被他“打了八百,贬下界来”,而且“又教七日一次,将飞箭来穿’川胸胁百余下方回”(8回)。天上的玉帝尚且如此,人间的君王更是不堪:宝象国的国王因女儿失踪贬退无数官员、打死若干脾女、太监(29回);患有“双鸟失群”之症的朱紫国国王愚蠢到服了马尿、锅灰制的丸药却浑然不知(69回);比丘国的君主荒唐、残忍至极,竟然听从国丈的谗言,收集许多儿童,“要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指望长生”(78回)。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国君不是昏庸无能便是为一己私利草管人命、杀人如麻。这等“圣上”真的可以使天下人甘愿为之效犬马之劳?投身这般世界岂不是自甘与杀人魔王同流合污?这条道又显然为君子所不取。
那么只有作者花了最多笔墨渲染的佛界可做人们思想的最终归宿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佛家以“劝化众生”为己任,能以无边法力制胜一切妖魔,使其野性变成佛性,最后服膺于佛的摩下。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佛界并非什么理想胜地。就拿观世音菩萨的南海紫竹林来说,多的是被迫修道的兽类。那看门的、侍莲台的戴着禁、金箍的熊精和牛精、坐骑金毛吼与听经的莲池金鱼,伺机便跑出去为妖作怪。唐僧师徒一路上碰上的尽是佛祖有意安排的磨难,实在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的以慈悲为怀,是否真的能“普渡众生”。这里不但没有能成功地宣传佛教教义,反倒更多地向人们展示了佛界的肮脏,明示世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妙的“彼岸”,这慈航宝筏是无论如何上不得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唐僧一直向往的吗?可唐僧因为不曾备得“人事”而受了阿摊、伽叶的无字之经,及至如来授命传有字真经,阿摊还是索了唐僧的紫金钵盂,且至被羞皱了脸皮,“只是拿着钵盂不放”(98回),可见与人间是一般醒龄。
儒道释的种种丑陋在作者笔下一一暴露出自己的嘴脸,尽管作者意在宣传三教合一以给人们指定一条文化发展的道路,但他在无意中解构了这神圣的三教。自唐以来统治了中国这么多年的文化潮流已渐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二、“自明本心”—戴着镣铐的舞蹈
在《西游记》之前,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将人的主体意识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的。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热烈地追求自由,对自己的人格力量无比自信。但在个性大力张扬的同时,作者又担心主体意识的无限宏扬会引起自私欲念的膨胀,会导致与社会秩序的冲突和道德规范的违悖。更何况,儒家正统讲的是“存天理,灭人欲”,虽要“明心见性”.“自明本心”,但也不至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以吴承恩在肯定孙悟空的主体意识时,又不希望它同心猿意马一般脱离道德的轨道任意驰骋,于是又给他加了紧箍咒,好使“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栓莫外寻”,可谓是戴着镣铐在舞蹈。
紧箍咒又叫“定心真言”,无疑是象征外在束缚对人性的制约。如来就其作用对观音说,“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他若不听使唤,可将次箍儿与他戴上,自然见血生根。个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后来观音又对孙悟空说,“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逛上欺天”,“须是这个魔头,你才肯人我瑜伽之门哩”。这话里一是显露了佛家法力和强制人入门,更多的也显现了他们对孙悟空个性的拘束。事实上,这几句咒语确实是发挥了神威的,若不是这咒语,凭憨厚无能又到处滥充好人的唐僧,是断断没有什么能耐降下那三个不受管束的徒弟的。然而这期间更多的是冤枉了好人。第27回中,孙悟空打死了白骨精,唐僧却“不识贤愚”,乱念一气紧箍咒;第56回中,孙悟空为民除害,打死了一伙“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的强人,唐僧又念一气紧箍咒。诸如这样的“冤假错案”可不止一两桩。紧箍咒使“独醒”的孙悟空受尽折磨,也暴露着外来束缚的“无理取闹”。
在紧箍咒的处理上,作者是怀着既爱又恨的心情的。他既要藉此来降住不伏管的“心猿”,又怀疑它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又借孙悟空一次次地来寻求打破这枷锁的途径。虽然最终作者还是让孙悟空在成了佛的前提下,给他去了这害人的金箍儿,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意义呢?它的存在使得作者的一切努力全部化为了无。非但没有能够唤起人们对自由的强烈热爱,相反使人们更对它多添了几分恐惧。
三、外来文化—美丽的肥皂泡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必然。然而文化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它需要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输人。在封建制度走向末路的明清之际,没有外来文化的补充,儒道释的总体发展也只能是在内部的不断腐朽。《西游记》是为大力宣扬三教合一而产生的,同时也流露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困惑、焦虑和无奈。
鲁迅说,中国根抵全在道教。到了吴承恩作《西游记》的年代,道教已经只落得以粗鄙的方术巫仪见长了。当朝的嘉靖皇帝,十分钟爱道教的丹药巫术,招徕大批道士高人,每天不干正事,只是在宫中打酩设斋、炼汞化铅,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善于献媚的大臣,到处为他求访高人术士。道教徒与官僚气,升官发财,而一大批不满这一现象、欲加阻止,要么被降职流放,要么下狱掉脑袋。这种污浊的现实先就引起世人的不快,哪里还有什么兴趣去探寻道教中招人喜爱的因子呢?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也为其丹砂气所覆盖了。
儒学的发展在那时算是又进了一个高潮的,尤其以王阳明的心学为代表。它以“求放心”、“致良知”的主旨要求人们能动地以伦理自省的方式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强调主观能动性,无疑给当时思想界注人了新的活力—这也正是孙悟空强烈的主体意识的由来—而心学本身也分化出以张扬个性为特征的泰州学派这样的“异端”。但心学终归是向着“圣贤之学”的,其“存天理,灭人欲”的先决条件是不会变的,故而又有以道德完善为宗旨的另一派的存在。心学的这种分化,体现在《西游记》中,就是一面宏扬人的主体意识,一面又加以抑制了。然而即便是理论上再完善—更何况心学更符合的是统治阶级的口味呢—也挽回不了事实上的颓败局面,儒学的发展已是到了回光返照时期,吴承恩对它实是不抱多大希望了,而心学到了黄宗羲便告了段落的事实也证实了儒学的这一注定命运。
儒学的路子走不通就试试中华大地上仅剩下的佛学吧。当时以至后来,是有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佛教身上的。王阳明是信过佛的,吴承恩也作过《劝缘褐》,后来的李蛰更是索性剃了发做了佛门中人,而汤显祖六十五岁萌生阪依佛法的念头,再有公安三袁,也无不受佛学的熏陶。向佛教吸取养分,在当时是一股不可挡的潮流。这固然受统治者曾大力提倡的影响,同时也暴露了人们对儒学的怀疑失望和对文化发展的困惑和迷茫,不如入了禅去,四大皆空,方为自在。
整个取经故事,正是表达了向外寻求新鲜思想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可惜又无甚把握。《西游记》中借如来之口,说着唐时故事,影射的却是明时光景:“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生,”“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98回)国中既是如此不堪,当然要向外孜孜以求。唐僧师徒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可敬的,然而光是靠几部真经就可以救一国之民众?唐僧取经回来未及宣讲便被招去了灵山(100回),真经对东土大唐的教化作用吴承恩只字未提,这固然是因为与西游故事没什么关系,同时不也说明作者本身对外来文化也无甚信心?
综观这洋洋一百回的巨制,其间充斥的虽是神怪,但所说无一不是人间事实,体现了作者对当时文化发展的困惑和反思,而这种困惑与反思是当时的一大社会潮流。明中后叶思想启蒙的大潮原是有指望引领中国文化走向另一个高潮的,无奈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将探索新发展的进程搁浅了二百多年。
作者:李满花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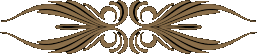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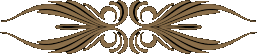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