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全书具有浓厚的男权主体意识,女性人物基本处在边缘和陪衬的地位,在众多人物形象中,女妖是极其独特的一个群体。在西行路上,对取经师徒构成威胁或与其直接发生关系和冲突的女妖精共有11人(伙),她们是:尸魔白骨妇人(二十七回);金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三十四回);灵感大王的义妹斑衣撅婆(四十八回);毒敌山琵琶洞蝎子精(五十五回);牛魔王之妻铁扇公主罗刹女、牛魔王之妾玉面公主(五十九回);荆棘岭树精杏仙(六十四回);盘丝洞七个蜘蛛精(七十二回);比丘国美后白面狐狸(七十八回);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八十回);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九十五回)等。这些精灵妖魅自有出身,法术各异,她们的存在大大丰富了《西游记》的人物画廊,也流露了作者复杂的妇女观。
一
《西游记》众多的女妖最大的共性便是行为的反常与容貌的美丽。作为取经人的对立面,妖精均非善类,但和书中面目狰狞丑陋的男性妖魔相比,女妖精几乎是清一色的美人,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笋发。团圆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这是地涌夫人金鼻白毛鼠精的俊俏模样。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被悟空称为“七个美人儿”,连唐僧也不觉“看得时辰久了”。美丽本不是过错,美丽的后面又往往与聪颖相连,然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美丽的女人无疑是祸水、是尤物。这种思维定势在《西游记》里得到有意无意的反复印证。殷小姐的美貌,使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儿出生遇难;那西梁女王,高贵富有,勇敢浪漫,却与爱情无缘,纵然愿以国王之尊求一丈夫亦不可得,堪称最失意的单身贵族;就连至善至美的观音菩萨,也是“该她一世无夫”。更有甚者,出于“不妖其身,必妖与人”侧的观念,女妖精这群外表迷人的精灵,同时被赋予了狠毒邪恶的特性。她们迷人败本,作恶害人,阻碍取经大业。她们接近唐僧,大多是为了吃其肉、采其元阳,以成太乙金仙。潜灵作怪的僵尸所化成的白骨夫人,是《西游记》中第一个想吃唐僧肉的妖怪。为此,她三次变化,几番戏弄,花言巧语,挑拨是非,虽然逃不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后命丧金箍棒下,却也使得取经人师徒反目,悟空被逐。也许是唐僧命该步步逢灾、处处有难,第五十五回,刚刚摆脱了西梁女王的柔情羁绊,又落人蝎子精的琵琶洞府。那妖怪虽然貌美如花,甚至在与悟空交战之前也不忘“烧汤洗面梳妆”,却心狠手辣。孙悟空那颗修炼过的头,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锻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可蝎子精使出倒马毒桩,只把他扎了一下,就使行者叫声“苦啊!”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抱着头,只叫“疼!疼!疼!”蝎子精的毒不仅使悟空吃了亏,八戒着了道,观音不敢近前,连如来也休其几分。
美丽女妖最反常的地方,体现在她们对传统婚恋方式的反叛与决绝的态度上。传统的妇女观主张婚姻之事要听“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女妖精却毫无此禁忌。唐僧是取经路上所有妖魔的共同目标,妖怪们都希望通过占有他这条捷径,免去修行之苦,直接成仙得道。但男怪女妖,目的相同,方式有别。在与取经人的冲突中,男妖怪大多以力相较;女妖精则常常以色迷人;男妖怪抓到唐僧,只要刷洗干净,蒸熟了便吃;女妖精得到唐僧,则多数要逼其成亲,“耍子去来”,既能采其元阳,又享天伦之乐,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女妖精总是主动追求,全无别的顾忌。玉兔精假扮天竺公主,结彩楼、抛绣球,“欲配唐僧了宿缘”,被悟空识破后,大骂弼马温“破人亲事,如杀父母之仇”。蝎子精摄得唐僧,回到洞府,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女怪拉拉扯扯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缠到有半夜时候。女子自媒自证、自主婚姻,本是明代启蒙思潮影响下通俗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话本小说,明清传奇,所涉颇多,然而《西游记》描写女妖精主动追求的行为模式,却是为了突出妖精的淫邪来衬托取经人的虔诚的,所以,女妖精往往是淫荡的代名词,其结局不是夭折于金箍棒下,便是被八戒的一顿钉耙打个稀烂。这种美丽+邪恶的女妖精模式,典型地反映了旧时代男性对女性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长期的“男尊女卑”观念下对女性的歧视;另一方面是出自本能的为女性魅力所吸引,二者的畸形统一,形成了“祸水论”。这有些类似拜伦所说的:“女人身上叫人可怕的东西,就如女人是祸水。我们既不能与她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们而生活。在《西游记》中发生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最终总是以女人的失败而告终。花妖狐魅,直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转化为“真善美”的统一。
二
共性突出,使女妖精的形象存在着某些简单化、概念化的倾向,但是,作品中的人物也并非众人一面,全无区别,罗刹女就堪称独特的“这一个”。她出身魔界,但自幼修持,已得人身,只是未成正果,住在远离凡尘的翠云山芭蕉洞。洞外风光秀丽,“烟霞含宿润,苔鲜助新青。磋峨势耸欺蓬岛,幽静花香若海浪。独特的出身、经历与环境,使罗刹女与其他女妖同中有异。作者对罗刹女独特、细腻、不乏同情心的描写,客观上冲击了女性是祸水、红颜多薄命的主观创作意图,对全书基调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反讽。
其一,她有法术,会武功。虽悟空称之为“好利害的妇人”,可她并不仗势欺人。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炎热,寸草不能生长。罗刹女有柄神奇的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四方百姓只要十年拜求一度,便可风调雨顺,布种收割。
其二,她和唐僧没有直接的冲突。她既不曾逼亲,也不打算吃其肉。只因其子红孩儿被观音收伏,母子不得常见面,为报夺子之仇,才迁怒于取经人,成了取经事业上的一大障碍。当悟空有求于她时,罗刹女不仅不肯借宝扇,反而一扇将悟空扇得无影无踪。
其三,与其她女妖相比,罗刹女更像一个符合封建家庭伦理标准的平凡女人。她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红孩儿仗着在火焰山炼就的三味真火,欺压山神、土地,还抢走唐僧欲蒸熟吃掉以延年益寿。观音菩萨为此收他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这本是他的造化,可罗刹女却不以为然:“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难以自禁的母性流露让人为之动容。她还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最后为了搭救丈夫牛魔王,她甘愿奉上宝扇。当罗刹女跪倒尘埃、流泪哀告时,分明全无了妖性,而酷似深闺大院内温柔敦厚的大奶奶了。在她的身上,似乎可看到封建伦理道德打下的深深烙印。
《西游记》塑造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运用了人、神(妖)、物相结合的特殊手法。其神魔人物形象,既有人的情感欲望等社会属性,又有神(妖)的神通广大的本领,还有物(动物、植物等)的自然属性。作者尤其善于通过动植物原型的自然属性突出各妖间的彼此差异。蝎子精长着两只钳子脚,使一柄三股叉,其哲人的本领、毒汁的利害,连观音也无奈,悟空也心惊。盘丝洞的蜘蛛精,肚脐里能放出无数软粘丝缕,把人和蜻蜓、蜜蜂粘住,想占便宜的八戒就吃足了她们的苦头。陷空山的老鼠精,居住在无底深涧,洞内周围有三百余里,一重又一重,一处又一处,巢穴甚多,其刁钻狡诈、诡计多端,堪称女妖之最。而荆棘岭的杏仙,是一棵长在悬崖边上的杏树所化。在一个月明如昼的夜晚,她手拈杏花,笑吟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姿容秀丽,举止文雅,锦心绣口,极善吟诗,在众妖中独具一格,令人几乎忘记她本是树精野怪。作者因物赋形、以形会意,使女妖形象同中有异、多彩多姿,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三
在某些古人看来,英雄与美女永远是冤家对头,儿女情长,则往往英雄气短。女人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君不见,梁山好汉大都不近女色或有手刃妇女的行为。这种对立的两性观,在宗教题材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彰显得更为突出。正因如此,各类女妖给取经事业增添了几多挫折和磨难,也令取经人的形象特征在矛盾碰撞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起到了很好的反衬、烘托的作用。
这种碰撞主要在唐僧和女妖之间进行。唐僧在《西游记》中的地位十分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水浒传》中的宋江。只是与前两个豪杰相比,唐僧显得软弱无能、昏庸偏执、人妖不分、真伪不辨。当他一味在危险面前“滚下马鞍”、“涕泪交流”之时,哪里像个得道的高僧,分明是一个百无一用的腐儒。但是唐僧的可贵与可敬之处在于一心向佛,虔诚悟道,为追求心目中的真理,心诚志坚,百折不挠。女色是修行中的巨大障碍,宋元话本中不少高僧均倒在这一戒上。在《西游记》中,女色对取经人的挑战除“四圣”变化的母女和西梁女王之外,其余全是女妖精所为。相对于现实女性“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追求,女妖精的威逼哄诱更难以抗拒。但唐僧的执著非同寻常。第五十五回,唐僧被琵琶精摄人洞府,逼进香房,女妖精毫无顾忌地主动追求,百般诱惑,唐长老却装聋作哑,全不动念。外魔的侵扰无碍禅心的坚定,神与魔在冲突中彼此相互衬托、相得益彰。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正是依靠异乎寻常的坚定和执著,才维系住他那三个莱鹜不驯的徒弟,走完了充满艰险也布满诱惑的漫漫取经之路。
这种碰撞有时也波及师徒内部。对师父的坚定禅心,沙僧深信不疑。思想灵活的悟空则是将信将疑,明察暗访的结果,总是让悟空由衷地佩服:“好和尚!好和尚!”与师兄、师弟不同,“色胆纵横”的八戒往往不相信谁能抗拒美色,师父的艳遇常常勾起他的“高老庄情结”,更让他心生羡慕,于是寻找机会,制造自己的“艳遇”。第七十二回,唐僧误人盘丝洞,蜘蛛精们捆了唐僧然后去灌垢泉洗浴。孙悟空不愿亲手“打杀几个丫头”,猪八戒却欢天喜地主动请战,其实是色心未泯。不料被女妖“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绳,动动脚,跌个龙钟;左边去,一个面磕地;右边去,一个倒栽葱;急将身,又跌了嘴啃地;忙爬起,又跌了个竖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把个呆子跌得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睡在地下呻吟”。猪八戒的乐极生悲,自讨苦吃,正有力地反衬出唐长老心诚志坚的可贵。
女妖精与取经人的碰撞和冲突不仅丰富了取经人尤其是唐僧的形象特征,还使全书诙谐幽默的一喜剧风格得到了张扬。以唐僧为例,他那一本正经的迁腐本是令人生厌的,女妖精的精灵古怪正好打破了场面的板滞,“激活”了唐僧这颗“死棋”。第八十二回,唐僧被老鼠精摄人无底洞,孙悟空定下降妖计,让唐僧哄骗妖精去游园。一心以取经为念的老和尚置身于绮罗队里已是十分无奈、十分滑稽,可为了配合徒弟,他还得强打精神,虚与周旋,竟成功地反串了一出“美男计”。角色与行为的极度不和谐,“妙人哥哥”与“御弟圣僧”的强烈反差,不仅使唐僧的性格特征—虔诚本分在欲与禁欲的矛盾对一抗得以突出,也使《西游记》浓郁的喜剧色彩在这个呆板的佛教徒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若非女妖精的多情缠绵,何来衬托唐长老的木呐忠厚?总之,西行路上的众多女妖精,不仅本身形象鲜明生动,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而且对于烘托、突出作品主要人物的个性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作者:王国伟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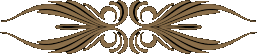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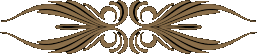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