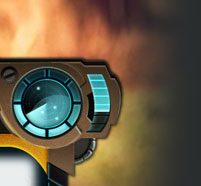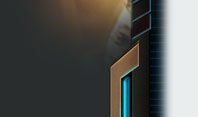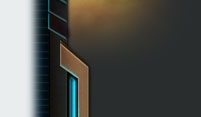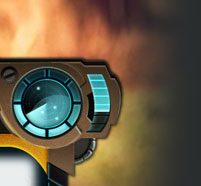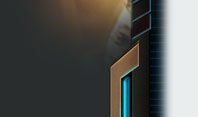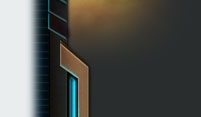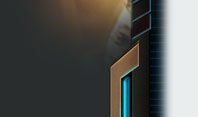 |
|
一 |
|
 |
|
每天午后,当科林和玛丽旅馆房间里暗绿色的百叶窗外面的整个城市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他们才会被铁质工具敲打铁质驳船的有规律的声响吵醒,这些驳船就系泊在旅馆的浮码头咖啡座边上。上午的时候,这些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船只因为既没有货物可装又没有动力可用,全都不见影踪;每天到了傍晚它们又不知从哪儿重新冒了出来,船上的船员也开始莫名所以地拿起
头和凿子大干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阴沉沉的向晚的暑热当中,客人们才开始聚集到浮码头上,在镀锡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吃冰淇淋,大家的声音也开始充满了正暗下来的旅馆房间,汇成一股笑语和争执的声浪,填满了尖利的
头敲打声响之间短暂的沉寂。
科林和玛丽感觉上像是同时醒来的,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都没动弹。出于他们自己也想不清楚的原因,两个人都还互不搭腔。两只苍蝇绕着天花板上的光亮懒洋洋地打转,走廊上有钥匙开锁和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最后还是科林先从床上起来,把百叶窗拉起一半,走进浴室去冲澡。玛丽还沉溺在刚才的梦境当中,他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背过身去盯着墙面。浴室中平稳的水流声听起来挺让人安心的,她不禁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每天傍晚,他们外出找个地方吃饭前,必定在阳台上消磨掉一段时间,耐心地倾听对方的梦境,以换得详细讲述自己梦境的奢侈。科林的梦境都是那种精神分析学者最喜欢的类型,他说,比如飞行,磨牙,赤身裸体出现在一个正襟危坐的陌生人面前什么的。可是铁硬的床垫、颇不习惯的暑热和这个他们还没怎么探察过的城市混杂在一起,却让玛丽一闭眼就陷入一系列吵吵嚷嚷、跟人争辩不休的梦境,她抱怨说就连醒了以后她都被搞得昏昏沉沉的;而那些优美的古旧教堂,那些祭坛的陈设和运河上架设的石桥,呆板地投射到她的视网膜上,就如同投影到一面不相干的幕布上一样。她最经常梦到的是她的孩子,梦到他们身处险境,可她却是缠杂不清、动弹不得,完全束手无策。她自己的童年跟孩子们的搅和在了一起,她的一双儿女变成了她的同代人,絮絮不休地问她个没完,吓得她够戗。你为什么抛下我们一个人跑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要来火车站接我们吗?不,不对,她竭力跟他们解释,是你们得来接我。她告诉科林她梦见她的孩子爬到床上跟她一起躺着,一边一个,整夜地隔着睡着了的她口角个没完。是的,我做过。不,你没有。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一直吵吵到她筋疲力尽地醒来,双手还紧紧地捂着耳朵。要么,她说,就是她前夫把她引到一个角落,开始耐心地解释该如何操作他那架昂贵的日本产相机,拿每个繁杂的操作步骤来考她,他倒确曾这么干过一回的。经过好多个钟头以后,她开始悲叹、呻吟,求他别再讲下去了,可无论什么都无法打断他那嗡嗡嘤嘤、坚持不懈的解释声。
浴室的窗开向一个天井,这个时候邻近几个房间和宾馆厨房的各种声音也乘隙而入。科林这边的淋浴刚刚洗完,对过住的男人接着又洗了起来,跟昨天傍晚一样,还一边唱着《魔笛》①里的二重唱。他的歌声盖过了轰鸣的淋浴水声和搓洗涂满肥皂的皮肤的嘎吱声,此人唱得是绝对地投入和忘情,只有在以为四周绝无他人听到的情况下才会这么放得开,唱高音时真声不够就换假声,唱破了音也照唱不误,碰到忘词的地方就“哒啦哒啦”地混过去,管弦乐队演奏的部分照样吼叫出来。“Mann und Weib, und Weib und Mann②,共同构成神圣的跨度。”等淋浴一关,引吭高歌也就减弱为吹吹口哨了。
科林站在镜子面前,听着,也没特别的原因又开始刮脸,这是当天的第二次了。自打他们来到这里,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秩序井然的睡觉的习惯,其重要性仅次于做爱,而现在正是他们俩在晚饭时间漫游这个城市之前用来精心梳洗打扮的一段间隙,平静安闲,沉溺于自我。在这段准备时间里,他们俩动作迟缓,极少开口。他们在身体上涂抹免税店里买的昂贵的古龙水和香粉,他们各自精心挑选自己的衣着,并不跟对方商量,仿佛他们等会儿要见的芸芸众人当中,会有那么个人对他们的衣着品貌深切地关注。玛丽在卧室的地板上做瑜伽的时候,科林会卷根大麻烟,然后他们俩一起在阳台上分享,这会使他们跨出旅馆的大堂,步入奶油般柔和的夜色的那个快乐的时刻加倍快意。
他们出去以后,也不只是上午,一个女服务员就会进来为他们清理床铺,要是她觉得应该换床单了,就把床单也给换了。他们俩都不习惯过这种旅馆生活,因为让一个面都很少见到的服务员接触到他们这么私密的生活,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女服务员把他们用过的纸巾收拾走,把他们俩的鞋子在衣橱里摆成齐整的一排,把他们的脏衣服叠成整齐的一堆,在椅子上放好,把床头桌上散乱的硬币码成几小堆。如此一来,他们更是惰性大发,很快就越来越依赖她,对自己的衣物管都不管了。两个人彼此都照顾不来了,在这种大热天里连自己的枕头都懒得拍拍松软,毛巾掉地上了都不肯弯个腰捡起来。而与此同时却又越来越不能容忍杂乱无章。有天上午,已经挺晚的了,他们回到房间,发现还跟离开时一样,根本没办法住人,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再次跑出去等服务员打扫干净了再回来。
他们下午小睡之前的那几个钟头同样也有一定之规,不过相对来说变数大些。时值仲夏,城里遍地都是游客。科林跟玛丽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后,也带上钱、太阳镜和地图,加入游客的行列,大家蜂拥穿过运河上的桥梁,足迹踏遍每一条窄街陋巷。大家仁至义尽地去完成这个古老的城市强加给他们的众多旅游任务,尽责地去参观城内大大小小的教堂、博物馆和宫殿,所有这些地方满坑满谷的全是珍宝。在几条购物街上,他们俩在橱窗前面也颇花了些时间,商量着该买些什么礼物。不过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当真跨进一家商店。尽管手里就拿着地图,他们仍不免经常迷路,会花上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来来回回绕圈子,参照着太阳的位置(科林的把戏),发现自己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接近了一个熟悉的路标,结果仍旧还是找不着北。碰上走得实在太辛苦,天气又热得比平时更加不堪忍受的时候,他们俩就相互提醒一声,自然是含讥带讽地,他们是“在度假”呢。他们俩不惜花费了很多个钟点,用来寻找“理想的”餐馆,或者是想重新找到两天前他们用餐的那个餐馆。可理想的餐馆经常是满了员,或者如果是过了晚上九点,马上就要打烊了;如果他们经过一家既没客满又不会立马打烊的,他们哪怕是还一点都不觉得饿,有几次也是先进去吃了再说。
或许,如果他们俩是孤身前来的话,早就一个人开开心心地探查过这个城市了,任由一时的心血来潮,不会计较一定要去哪里,根本不在乎是否迷了路,没准儿还乐在其中呢。这儿多的是可以信马由缰的去处,你只需警醒一点、留点心就行。可是他们彼此间的了解就像对自己一般的透彻,彼此间的亲密,好比是带了太多的旅行箱,总是持续不断的一种牵挂;两个人在一起就总不免行动迟缓,拙手笨脚,不断地导向小题大做、荒谬可笑的妥协,一心一意地关照着情绪上细小微妙的变化,不停地修补着裂痕。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那种神经兮兮动辄恼怒的主儿;可凑到一块儿,他们俩却总会出乎意料地惹恼对方;然后那位冒犯者反过来又会因为对方唧唧歪歪的神经过敏而大动肝火——自从他们来到这儿,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两回了,然后他们就会闷着头继续在那些九转回肠般的小巷里摸索,然后突然来到某个广场,随着他们迈出的每一步,他们俩都越来越深地纠缠于彼此的存在,而身边的城市也就一步步退缩为模糊的背景。
玛丽做完瑜伽站起身来,仔细考虑了一下穿什么内衣以后,开始着装。透过半开的法式落地窗她能看到阳台上的科林。他周身着白,四仰八叉地躺在塑料和铝质沙滩椅上,手腕都快耷拉到地上了。他深吸一口大麻,仰起头来屏住呼吸,然后把烟吐过阳台矮墙上一溜排开的几盆天竺葵。她爱他,即便是这个时候的他。她穿上一件丝质短上衣和一条白色棉布裙,在床沿上坐下来系凉鞋搭扣的时候从床头桌上捡起一本旅行指南。从照片上看来,这个地区的其他部分都是些牧场、山脉、荒芜的海滩,有条小径蜿蜒地穿过一片森林通向一个湖边。在她今年唯一空闲的这一个月里,她来到这里是应该把自己交托给博物馆和旅馆的。听到科林躺椅发出的吱嘎声响,她走到梳妆台前,开始以短促、有力的动作梳起了头发。
科林把大麻烟拿进来请玛丽抽,她拒绝了——飞快地喃喃说了声“不,谢谢”——头都没回。他在她背后晃荡,跟她一起盯进镜子里面,想捕捉住她的目光。可她目不斜视地看着面前的自己,继续梳着头发。他用手指沿她肩膀的曲线轻抚过去。他们迟早得打破眼前的沉默。科林转身想走,又改了主意。他清了清嗓子,把手坚定地放在了她肩膀上。窗外,大家已经开始观赏落日,而室内,他们则急需开始商量和沟通。他的犹豫不决完全是大麻烟给闹的,来回倒腾地琢磨着要是现在掉头就走,而刚才已经拿手碰过她了,她也许,很可能最后就恼了……不过,她仍然在继续梳她的头发,其实根本不需要梳这么长时间,看来她又像是在等着科林走开……可为什么呢?……是因为她感觉到他不情愿待在这儿,已经恼了?……可他不情愿了吗?他可怜兮兮地用手指沿玛丽的脊骨抚摸下去。结果她一只手拿着梳柄,把梳齿靠在另一只手的掌心上,仍继续盯着前方。科林俯下身来,吻了吻她的颈背,见她仍然不肯理他,只得大声叹了口气,穿过房间回到了阳台上。
科林又在沙滩椅上安顿下来。头顶上是清朗的天空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穹顶,他又叹了口气,这次是满足的叹息。驳船上的工人已经放下了工具,眼下正站成一簇,面朝着落日抽着烟。旅馆的浮码头咖啡座上,顾客们已经喝起了开胃酒,一桌桌客人的交谈声微弱而又稳定。玻璃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勤谨的侍应,鞋跟机械地敲打着浮码头的板条,来回奔走。科林站起身来,望着底下街上的过客。观光客们,穿着他们最好的夏季套装和裙子,有很多都上了年纪,爬行动物般缓慢地沿着人行道挪动。时不时地就会有那么一对停下脚步,赞赏地望着浮码头上那些把酒言欢的客人,他们背后衬着的是落日与染红的水面构成的巨幅背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绅士将他的老伴儿安置在前景位置,半跪下哆哆嗦嗦的两条瘦腿要给她照相。紧挨着老太太背后的一桌客人好性儿地冲着相机举起了酒杯。可拍照的老先生却一心想拍得自然些,站起身来,空着的一只手大幅度地摆了摆,意思是还是请他们回到原来不知不觉的状态才好。一直到那桌酒客,全都是年轻人,失去了兴致,那老头才又把相机举到面前,再度弯下站不稳当的双腿。可是老太太眼下已经朝一侧偏开了几步的距离,手里的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正转过身去背朝着相机,为的是借助最后的几缕太阳光察看手提包里的什么物件。老头尖声冲她叫了一声,她干净利落地回到原位。扣上手提包的咔哒一响又让那帮年轻人来了劲儿。他们在座位上坐坐好,再次举起酒杯,笑得尤其开心和无辜。老头恼怒地轻轻哀叹了一声,拉起老太太的手腕领她走开了,而那帮年轻人几乎都没注意到他们离开,开始在自家人中间祝酒,相互间开心地笑着。
玛丽出现在落地窗旁边,肩膀上披了件开襟毛衫。科林全然不顾他们之间正在玩的把戏,马上兴奋地跟她讲起下面的马路上上演的那一幕活剧。她站在阳台的矮墙边,他述说的时候她只管望着日落。他指点着那桌年轻人的时候她的视线并没有移动,不过微微点了点头。在科林看来,他是没办法重现其间那种模糊的误会了,而这正是这幕活剧主要的兴趣点之所在。可是他却听到自己将这出小悲剧夸张成了杂耍戏,或许是为了吸引玛丽的全副注意。他将那位老绅士描述为“老得难以置信而且衰弱不堪”,老太太则“疯疯癫癫到极点”,那一桌年轻人是一帮“迟钝的白痴”,在他嘴里那老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狂怒的咆哮”。事实上,“难以置信”这个词儿倒真是时时在他脑海中浮现,也许是因为他怕玛丽不相信他,或者是因为他自己就不相信。他说完之后,玛丽似笑非笑,短促地“呣”了一声。
他们俩之间隔了几步的距离,继续沉默地望着对过的水面。宽阔的运河对岸那巨大的教堂眼下成了一幅剪影,他们一直说要去参观一下的,再近一些,一条小舟上有个人把望远镜放回盒子里,跪下来重新将舷外的发动机发动起来。他们左上方的绿色霓虹灯店招突然咔嚓一声爆了一下,然后就减弱为低低的嗡嗡声。玛丽提醒科林,天已经不早了,他们马上就该动身,要不然餐馆都该打烊了。科林点头称是,可也没动窝。然后科林在一把沙滩椅上坐下来,没过多久玛丽也坐了下来。又一阵短暂的沉默,他们俩伸出手来握在了一起。相互轻轻按了按对方的手心。两人把椅子挪得更近些,相互轻声地道歉。科林抚摸着玛丽的胸,她转过头来先吻了他的唇,然后又温柔地像母亲一样吻了吻他的鼻子。他们俩低声呢喃着、吻着,站起来抱在一起,然后返回卧室,在半明半暗间把衣服脱掉。
他们已经不再有特别大的激情了。其间的乐趣在于那种不慌不忙的亲密感,在于对其规矩和程序的熟极而流,在于四肢和身体那安心而又精确的融合无间,舒适无比,就像是铸造物重新又回到了模子里。两个人既大方又从容不迫,没有太大的欲求,也没多大动静。他们的做爱没有明确的开头或是终结,结果经常是沉入睡眠或者还没结束就睡着了。他们会激愤地坚决否认他们已经进入倦怠期。他们经常说他们当真是融为一体了,都很难想起两人原来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看着对方的时候就像是看着一个模糊的镜面。有时,他们谈起性政治的时候,他们谈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恰恰正是这种共谋,弄得相互之间非常脆弱和敏感,一旦重新发现他们的需要和兴趣有所不同,情感上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可是两人之间的争执从来不会挑明,而像眼下这种争执之后的和解也就成为他们之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此两人是深怀感激的。
他们瞌睡了一会儿,然后匆忙穿上衣服。科林去浴室的时候,玛丽又回到阳台上等他。旅馆的店招关掉了。下面的街道已经渺无人迹,浮码头上有两个侍应在收拾杯盘。所剩无几的几位客人也不再喝酒了。科林和玛丽从没这么晚离开旅馆过,事后玛丽将当晚的奇遇归因于此。她不耐烦地在阳台上踱着步,呼吸着天竺葵灰扑扑的气味。这个时候饭馆都该打烊了,不过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侧有家开到深夜的酒吧,门外有时候会有个热狗摊子,问题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得到。她十三岁的时候还是个守时、尽责的中学生,脑子里有不下上百个提升自我修养的想法,她当时有个笔记本,每个周日的傍晚,她都会定下下周要实现的目标。都是些适度、可行的任务,等她一步步完成任务把它们勾掉的时候感觉很是快慰:练习大提琴,待她妈妈更好一些,步行上学,把公交车的车费省下来。如今她可真向往这一类的快慰,希望不论是在时间还是行事上至少有部分是自己掌控之下的。她就像梦游般从这一刻混到下一刻,一眨眼整整一个月就这么毫无印象地溜过去了,连一丝一毫自我意志的印记都不曾留下。
“好了吗?”科林喊道。她进屋,把法式落地窗关上。她从床头桌上把钥匙拿好,把门锁上,跟着科林走下没亮灯的楼梯。
注释
① 莫扎特所作著名歌剧。
② 德语: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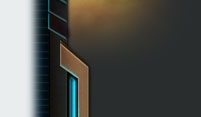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