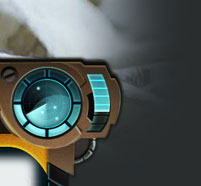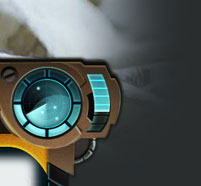|
|
一来一去 |
|
 |
|
利奇用力绷直双腿直到腿发抖。他十指相扣放于脑后,把关节弄得嘎嘎作响,还故意发出轻声的坏笑,冲着他假装在不远处看见的什么东西。他用胳膊肘轻碰我的后脑勺。好像结束了,你怎么说?
那是真的吗?我躺在黑暗中。是真的,我想那台旧“一来一去”把她摇得睡着了。古老的“一来一去”无休无止,悬停来得就像睡眠一样悄然。扬起落下,扬起落下,扬起落下,上下之间是危险的沉默的间隙,是她要继续的决定。
天空唯余一片苍黄,运河的臭气远远传来,减弱成一种甜熟的樱桃的气息,一种等待着陆时盘旋机群的忧郁。办公室里,其他人在剪今天的报纸,这是他们的工作。把专栏贴到索引卡上。
如果我躺在黑暗中,我能看见那轮廓娇脆的颊骨上的苍白皮肤,在黑暗中勾勒一条狗腿的形状。深凹的眼睛是打开的,但我看不见。牙齿上口水的一点反光透过微启的唇射出来。一圈黑发比四周的夜还要黑。有时我看着她,想着谁会先死,谁会先死,你还是我?那巨大的寂静之重,还有几多小时?
利奇。我看见利奇在这同一条走廊上不时地与经理讨论事情。我看见他们,他们一起顺着长长的无门的走廊踱步。经理挺得笔直,手深深插入口袋,弄得里面小物什丁零作响。利奇则顺从地屈身一旁,脑袋偏向他上司的脖子。他背着手,一只手的手指扣住另一只的手腕,小心地检测自己的脉搏。我看见了经理看见的,我们的形象重合了——利奇和这个男人;拧动那明亮的金属环,他们就各自弹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都在摆造型。
口水在牙齿的一点上闪光。听听她的呼吸,有节奏的起伏,熟睡的气息,不是听她。一头动物需要跟随另一头去穿越黑夜,毛茸茸黑黢黢的睡眠在一根矮枝上将快感窒息,老树吱嘎响起来,不见了,记忆,听她……屋子里气息香甜。古老的,温柔的“一来一去”摇她入眠。你记得那片小树林吗,那些虬结变形的树,无叶的枝桠交织成穹隆,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啊……清醒是一种细小而有耐性的英雄主义,那比周围的冰层还大的北极之洞在扩张,太大而难以名状,包含了视觉的无限可能。我躺在黑暗中,朝里看去。我躺在里面,朝外看去,从另外的房间传来了她孩子睡梦中的哭喊:一头熊!
先是利奇来了,其实没有先后,早晨即将过去,我倚靠着,啜吸着,独处着,利奇过来了,向我问好,亲热地在我背上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来了一记重拍。他站在茶壶旁,双腿叉开就像一个公然撒尿的人,棕色的液体流进他的杯子,他说着,你记得这次(或那次)谈话吗?不,不。他端着他的杯子走过来。不,不,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他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尽可能地靠近我,却并不能……成为我。啊,那包裹着深处排泄物的陌生人肌肤的浓烈味道。他的右腿碰着了我的左腿。
黎明前的寒冷时分,她的孩子会爬到床上,先是一个,接着又来一个,有时单只一个,他们落入成人芳香的温暖中,像海星一样附着在她身旁(记得海星如何攀附在岩石上吧),舌头搅出微弱水声。外面街道上急促的脚步声临近又顺着山坡向下渐渐远去。我躺在这一窝的边缘。鲁宾逊·克鲁索计划着用精心削尖的木棍做一道栅栏,造出感到陌生脚步的最轻微震颤就会自己开火的枪支,希望他的山羊和狗兴旺繁殖。可他也找不到另外一窝这样宽容的生灵。有时她的某个女儿会来得过早,深夜里她醒过来,把她抱走,回来接着睡。她的膝盖弯起来贴着小腹。她的房子里散发着酣睡孩子的香甜气味。
以一个感觉到需要被观望的人的缓慢动作,利奇从胸前口袋上取下一支钢笔,看了看,又放了回去,抓住我伸出去想要捡起滑到地板上去的书的胳膊,书是因为他那一拍而滑落的。门边一个关键的空间,暗示着经理,以及他到来的可能性。
巨大的重量……你记得吗?梦中人,那长着虬结奇特的树木的小树林,无叶的枝条织出一个穹隆,一个黑暗的顶,阳光从上面漏下来,射在气味刺鼻的土地上。我们踮脚走在消音的安静的植被上面,轻声耳语,脚下隐藏的根茎让我们发出咝咝声。一片非常古老而隐秘的树林。在我们的前方,是一片明亮。穹隆似乎应天上某种重压而坍塌。那明亮的半圆,那些树的枝条像灿烂的小型瀑布般垂向地面。囤在急流的中央,被阳光漂白,突兀地映着灰暗树林的是骨头,某种生灵的白骨停歇在那里。一个扁扁的,眼窝空空的头骨,一条被蚀化到濒临散架的长长的弧形脊骨,旁边是一小堆别的骨头,精密,纤细,两端呈握拳状。
利奇的手指像鸡爪般顽强。当我把它们从我胳膊上挑开时,它们机械地缩了回去。这是个孤独的男人吗?碰过他的手后,我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就像睁开眼睛仰面躺在被单下的情人开始一场谈话一样。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望着微尘在一刀阳光中飘落。
有时我看着她,想着我们谁会先死……面对面,在百衲被和乱糟糟的绒毛中度过冬天。她两手分别捏住我两个耳朵,把我的头捧在双掌之中,用迷蒙的黑色的眼睛注视着我,抿嘴而笑,笑不露齿……于是我想,是我,是我应该先死,而你会永远活下去。
利奇放下他的杯子(杯子边缘被他用成了那样的棕色!),往后一靠,用力伸直双腿直至颤抖,和我一起看着微尘在一刀阳光中飘落,阳光之外,是那个冰窟,上面,外面,我躺在睡着的情人身旁,躺着朝里凝视,回望。我辨认出了绒毛和百衲被,铸铁床的优雅细节……利奇放下他的杯子,往后一靠,双手交叠于脑后,把关节弄得嘎嘎作响。他歪了歪脑袋,示意想走动一下,醒悟到门边的空当,希望有人陪他一起出去。
一个声音挑破寂静,一朵鲜艳的红色花朵落在雪地上,她的一个女儿在睡梦中喊叫出来。一头熊!这声音与其意义混合在一起。寂静,然后又响起来,一头熊,这次声音轻了点,带着失望的降调……现在,寂静显得戏剧化,因为缺失了那简洁的话音……现在不知觉间……现在,习惯性的寂静,没有期待,寂静的重量,关于熊的视觉余影在渐渐消退的橘色中发光。我看着他们消失,躺在睡觉的朋友旁边等待,在枕上转过头来,看进她睁开的眼睛里。
我终于起了身,跟随利奇穿过空房间,沿着无门的走廊走着,在这里我见过他频繁地与人商谈,踱步,直腰或弯背。经理和他的下属,我们和我们害怕的事物不能被分开来讲述……我与利奇走到并排,他在感触他衣服的材质,手指和拇指揉搓着衣领两面,动作慢得好像没动,他在考虑他的话:你觉得怎样?我的衣服。脸上是若有似无的笑。我们在走廊上停下来,面对面,下面抛光的地面上映着我们扭曲的倒影。我们看见彼此的倒影,但没看自己的。
那圈浓密的黑发比四周的夜还黑,轮廓娇脆的颊骨上的苍白皮肤在黑暗中勾勒出一条狗腿的形状……是你吗?她喃喃道,还是孩子们?她眼睛那块地方的微弱动静表明它们合上了。她呼吸的节奏加强了,那是一个睡眠中的身体将启的自动机制。那什么都不是,是一个梦,犹如雪上红花般的黑暗中的一个声音……她向后倒去,滑进了一口深井的底部,往上看可以看到光圈在缩小,天空被我凝望的脑袋和遥远的肩膀的剪影分割。她滑了下去,她的话语却浮了上来,经过她到达我,被回音模糊。她喊,我睡着的时候进到我里面,进来……
我也伸出手指以同样的动作抚摩那衣领,然后又抚摩我自己的,每种材料的熟悉手感,以及它们传递的体温……甜熟樱桃的气息,盘旋机群的忧郁。这就是工作,我们和我们的恐惧不能被分开来讲述。利奇握住我伸出的手,晃了晃。睁开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睛。你会觉得它们好像根本不是你的。衣领更宽了,夹克后背应我的要求开有两个叉,它们是同样的蓝色,但我的上面有一点白点,整体看上去浅一些。听到身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我们继续散步。
沉睡着并如此湿润?古老的“一来一去”的联觉,咸水和香料的仓库,平滑绵延的轮廓线上一个突起,插入天际线,像倚天而立的一棵巨树,一条肉舌。我亲吻和吮吸着她女儿吮吸的地方。松开,她说,别动它。我想凑近并触碰的某种生物的白骨,那眼窝空空的头盖骨,蚀化到快脱落的弧形长脊骨……别动它。她说时我伸出胳膊。那些话里的恐惧明白无误,她说那是个噩梦,把野餐紧紧抱住——当我们拥抱时,一个瓶子当啷撞上一个罐子。我们手拉手跑着穿过树林,出来越过一个斜坡,四周是成簇的金雀花,大山谷在我们下面,大团美丽的白云,暗绿树干上一道扁平的伤痕。
是的,经理的习惯是往房间里走进几尺,停下来察看下属们的动静。但除去空气的一丝紧张(空气占据的空间被压缩了),什么变化都没发生,每个人都在看,但没有抬头看……经理的表情淹没在平滑透明的肌肤下的脂肪里,脂肪在颊骨边缘积聚,现在,像冰川一样,滑到了凹陷的眼周。深陷的权威的眼睛扫过房间,桌子,面孔,开着的窗,像一个骨碌转的瓶子一样落在了我身上……啊利奇,他说。
她房子里充满的香甜气息,熟睡的孩子们的,在暖和处晾干毛皮的猫的,还有在一台旧收音机的阀上变热的灰尘的——新闻里说,受伤的没几个,死的人更多?我怎么能肯定地球在转向早晨?到了早上,越过空杯子和斑迹,我要讲给她听,与其说是梦,还不如说是记忆,我在梦里保持着清醒状态。没有什么被夸张,除了生理厌恶的关键点,那也是适度的夸大,我会声称,这一切都是透过一个大到边上没有冰的洞看见的。
坐在窗边的三角桌边,非常宁静。这是工作,说不上快乐,也说不上不快乐,筛选返回的剪报。这是工作,寻找适合归档系统的类目。天空是一片苍黄,运河的臭气被距离减弱成甜熟樱桃的气味,盘旋机群的忧郁,办公室别处别人在剪今天的报纸,把专栏贴到索引卡上。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剪刀文雅的声音,涂胶水的声音,一只手推开了门。经理走进房间几尺,停下来查看下属的动静。
我要告诉她……她叹息着动了一下,从湿润的眼睛上推开蓬乱未梳理的头发,直起身子但仍旧坐着,双手捧住一个壶——一个来自旧货店的给自己的礼物。窗户在她眼睛里映出一个小长方形,眼睛下面的蓝色双月在她白色的面庞上勾出尖弧。她推开头发,叹息着动了一下。
他向我走来。啊利奇。他边走边说。他叫我利奇。啊利奇,我想你帮我做点事。我没听见是什么事情,我坐在那里,被变换形状吐出音节的嘴唇给迷惑住了。有件事情我想你帮我做一下。在随意而悠闲的瞬间,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利奇从一排柜子后面走出来,热烈而毫不介意,经理则兴奋而怀有歉意。利奇说,我同事会证实,人们总是搞混我们,他这么说着时手放到了我肩膀上,也原谅了我。一个很容易发生的误会,同事,允许自己和利奇被搞混。
听着她的呼吸,起伏,起伏,在起伏之间是危险的间隙,她关于继续的决定……时间的重量。我会告诉她,避免混淆。她的眼睛会从左转到右,从右到左,察看并对比我的两只眼,猜测我的诚实与否以及意图的变换,间或把视线投向我嘴里,来来回回,寻找一张脸的意义。我的眼睛也一样对着她。来来回回,我们的眼睛舞动和追逐着。
我夹坐在两个站立的男人中间,经理重复着他的指令,不耐烦地离开了我们,走到门边时又回头纵容地一笑。是的,我从没看见过他笑!我看见了他看见的——像摆好姿势要拍正式相片的双胞胎。一个站着,手放在另一个坐着的肩膀上;可能是一种混淆,镜头上的小机关,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金属环转过来,他们的形象就合二为一,只剩下一个人了。名字呢?很有希望的,理由充分的……焦虑。
“一来一去”是我的时钟,会让地球转动,黎明到来,会把她的女儿带到她床上……“一来一去”嘲笑着寂静,“一来一去”将她的孩子投入大人芬芳的温暖中,让他们像海星一样附着在她身上,你记得吗……看到你不想看见的东西时的惊心,巨大的岩石刺破潮湿的布有条纹的沙地,水线不情愿地向地平线退去,兀立的岩石中,饥饿的水塘吮吸着喷溢着吮吸着。一块胖大的黑色岩石悬在一个水塘上方,你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下方,腿臂伸展地悬挂着的是海星,如此明亮的橘色,美丽,孤单,还有那滴水的白色圆点。它紧紧扣住它掌握的岩石,水波拍打着岩石上的它,远处海水正在退去。海星并不像白骨那样因其死亡意味而慑人,它因其清醒感而慑人,如此清醒,就像沉寂夜里一声孩子的叫喊。
他们传递的身体的热量。我们是一样的吗?利奇,我们是吗?利奇伸展,回答,拍打,推开,佯装,商量,恭维,低眉折腰,检查,摆姿势,趋前,招呼,触碰,细察,暗示,握紧,低语,凝视,颤抖,摇晃,出现,微笑,弱弱地,非常弱地,说着,睁开你的……温暖?……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睛。
是真的吗?我躺在黑暗中……是真的,我想它过去了。她睡着了,没有结束,悬停来得像睡眠本身一样悄然。是的,古老的“一来一去”将她摇入梦乡。在梦中她拉近我,把一条腿搁在我的腿上。幽夜变成了蓝色和灰色,我感觉到,压在她胸下的我的太阳穴上,她的心脏那古老的“一来一去”之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