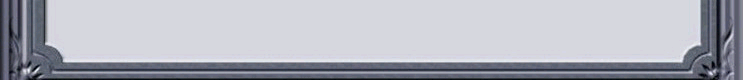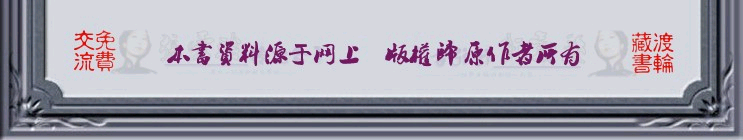第一章 水样的悲哀(音乐篇)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张爱玲《谈音乐》
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昔日的音乐家总是与贫穷联在一起的,而音乐却是贵族的玩艺儿。以张爱玲那样的出身,几乎不可能不与音乐发生关系;有那样一位受过西风熏染、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方式、笑的模样都要教给女儿,要把女儿培养成“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母亲,自然不可能不叫她学音乐。在张爱玲任编剧的影片《不了情》中,就有这么一个场景:男主人与家庭女教师为他8岁的女儿过生日,女儿吹灭了蜡烛后,正要切蛋糕,男主人阻止道:“别忙,你先弹个琴给我们听,再给你吃。”于是小女孩就坐到琴凳上去,叮叮当当地弹起来。可以设想,这完全是张爱玲少时家庭情景的再现。与那男主角一样,张爱玲的父母多半也并非是要子女成为钢琴家,只是为了让她们更具备淑女的条件,独处时可作高雅的消遣,来客人时可以助助雅兴。
※※※
张爱玲写过一篇《谈音乐》的散文,堪称张氏作品中的奇葩。在期刊上发表后,又收入随后出版的她的散文集《流言》,作了集子的大轴,也是该书中最好的篇什之一,轻灵、神气,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散文风格,一贯地使读者求浅可见其美,求深可见其识,而且隽永的思想都成了警句,比喻都成了神来之笔,爆发着思想的流星雨,令人不由得叫妙叫绝,如描绘交响乐的一段: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设若作者不是自小接触过音乐,对音乐就不会有如此深的感触;假如自小没有那么深地吃过音乐的苦头,恐怕也难以写出这样的美文来。而人往往对十分喜爱的东西不易写好,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事物刻画起来倒常常能入木,这似乎又反证了张爱玲对音乐的态度。
张爱玲自小学琴的经历对她似乎尽是痛苦的回忆,她称之为“苦难”,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她学琴是被动的,而不是出自她的意愿。就为了她看姑姑弹钢琴时发出的一句赞叹,母亲以为她有音乐天赋而把她送去学钢琴。先跟了一位俄国女琴师,虽然张爱玲的注意力在于琴师宽脸上的金汗毛、粉背上的太阳味、容易激动的性情以及极有礼貌而靠妻子养活的丈夫,唯独不在钢琴上。此后她对音乐,也总是注意到之外的方面。
后来父母离了婚,她跟了父亲生活。本来钢琴这洋玩意儿就是伴随着前妻而来的,当初学琴多半也是黄逸梵的主张,张廷重恨屋及乌,付女儿学琴费总是不情不愿,予女儿以难堪:“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这更加折损了张爱玲学琴的兴趣,后来在学校里,她常常惹琴先生生气,因而挨打,就当然是事出有因的了。
张爱玲的《谈音乐》,开头一句话便是:“我不大喜欢音乐。”随后又以她行文中很少出现的不由分说的态度补一句:“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一棍子就把音乐打死了。
但是当她话说从头,细细道来,最初的意气消散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她对音乐并非一味厌恶,其实也是有所喜爱的,表现在她对于音符极为敏感,当她“弹奏钢琴时,会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写文章,也爱用“音韵铿锵的字眼”。
还在张爱玲不怎么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与姑姑出国去了,是被父亲气走的。前清遗少的父亲虽然对女儿并非全然不关心,但由于他自己生活的荒唐以至颓废,诸如终日与一班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召妓、赌钱、吸毒、与妓女出身的姨太太大打出手等等,不可能使敏感的女儿在这个残缺的家庭里生长而不感到有所缺陷,尽管她日后不肯承认。
事实上,母亲归来后张爱玲心花怒放(有次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坐在地上看着,忽然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的表现,正是之前家庭缺少快乐的反映。而由母亲带来的快乐,是在音乐的伴奏下到来的,而那也是她第一次接触音乐。
母亲与姑姑经常邀请一些朋友到新家里来玩,节目之一便是在有着壁炉的宽敞客厅里弹琴、唱歌。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姑姑,弹钢琴是她每天必做的事情。她那双灵巧的小手在琴键上敲出另一个世界。一对细而白的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母亲经常立在姑姑的背后,轻轻地扶住她的肩,“拉拉拉拉”地吊嗓子。她穿着秋天的落叶般的淡赭色衣服,肩上垂着同色的花球,有一种飘逸的神韵。不论什么调子,经她唱出来,便有点像吟诗。但她的发音不够准,总要比钢琴低半个音阶。在抱歉地笑笑之余,她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解释,而在表情中有种异常动人的娇媚,与那琴上的花瓶里盛开的鲜花相映。
※※※
年少的张爱玲站在一边听着,看着,常常陶醉在这诗意芬芳的气氛里,禁不住说一句:“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虽然她成年后说,当时她“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其实未必,因为她在另一篇更早些的文章(《天才梦》)中说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何况音乐是与姗姗来迟的母爱、从天而降的家庭温暖、戏剧化的家庭氛围交织在一起的,对一个不乏艺术细胞的小女孩来说,几乎不可能不产生难以抵御的诱惑。
所以她对不同的音乐厚薄不一、有贬也有褒就不奇怪了。比如小提琴与胡琴,锣鼓与交响乐: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由此来看张爱玲对音乐的好恶,似乎有民族性的因素在内。胡琴与锣鼓是中国的,小提琴与交响乐是西洋的。这是一层。在外国歌曲中,则又有所区分。她拿创作歌曲与民歌作比较,显然她对前者不太喜欢:
外国的通俗音乐,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例如“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带有十九世纪会客室的气息,黯淡、温雅,透不过气来——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束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在黄昏》是一支情歌:
在黄昏,想起我的时候,不要记恨,亲爱的……
听口气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绝了男人,为了他的好,也为了她的好。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一个人住着,一个人老了。虽然到现在还是理直气壮,同时却又抱歉着。这原是温柔可爱的,只是当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烂,使我们对于她那些过了时的逻辑起了反感。
《在黄昏》又被译作《黄昏来临》,由英国奥列德作词,A.哈里松作曲。歌词内容较为抑郁,表达的情感又有怨妇的酸气,使人感到不清爽,所以张爱玲用了“惨沮”这么一个“粘湿”的词。相比之下,她对朴实率真的民歌更有好感:
苏格兰的民歌就没有那些逻辑,例如《萝门湖》,这支古老的歌前两年曾经被美国流行乐队拿去爵士化了,大红过一阵:
你走高的路吧,
我走低的路……
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
在萝门湖美丽,美丽的湖边。
可以想象多山多雾的苏格兰,遍山坡的heather,长长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空气清扬寒冷。那种干净,只有我们的《诗经》里有。
《萝门湖》(另有译作“罗梦湖”的)的曲调是F调四四拍,虽然本较舒缓,但音符的变化却颇含有起伏抑扬的节奏感,难怪被改作以切分节奏与“摇摆”的节奏感觉(会使人不禁想起“古里古怪”这个词)为特色的爵士乐。《萝门湖》共有3段歌词,第一段写“我”和恋人昔日在萝门湖畔徜徉的甜蜜时光;第二段写两人在萝门山谷黯然分手;第三段写失去恋人后心里难以磨灭的悲伤。张爱玲引的是副歌部分,她省略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想必是她一时记不清歌词了。
从张爱玲对音乐的好恶中,我们隐约可以摸到她的取舍原则。中外相比,她倾向于本民族的。因为她是中国人,喜欢本民族的东西,关键是她认为本民族的东西好;古今相比,她倾向于原生态的。因为原生态的东西自然,较少造作而多率性,往往有较多的真性情的流露,即她所说的“人的成份”浓厚,这是她最喜欢的。像她家附近军营里传出的学吹喇叭的声音,因那声音里透露出了人生的挣扎、焦愁、慌乱、冒险等等人的气息,使常人听来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张爱玲“倒不嫌它讨厌”了。
※※※
张爱玲自称不喜音乐,却使旁人产生了兴趣。胡兰成就说过:“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流行歌等,亦是张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像《谈音乐》中表述的对中国民俗艺术的指点、对中外通俗艺术的比较等等思想,都使胡兰成受到很大影响。
《谈音乐》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杂志的,后来她与他的分手,也正演绎了《萝门湖》的基调——虽然不免悲伤,态度却又清坚决绝。胡兰成虽然自诩世上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喜欢张爱玲,但他对她的了解由此看来还是不足——如果他仔细读读张爱玲的这篇文章,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对张爱玲的“缠夹不清”了。
张爱玲将“大鼓书”归入中国通俗音乐,她对它不大喜欢:“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大鼓书是过去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民国年间形成了奉天大鼓(也称奉调大鼓、东北大鼓)、吉林大鼓(也称东城调,流行于吉林市一带)、江北大鼓(流行于松花江以北地区,又称屯大鼓)、乐亭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一度相当盛行。
大鼓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演员的服装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早期演出也不用化妆,后来的女演员(俗称“女大鼓”)也不画浓妆,而只略施淡彩,外穿旗袍而已。道具有鼓,梨花板,弦。鼓不大,扁圆形,直径约25公分,是用牛皮或其他皮子蒙的;梨花板是一对半月形状的铜板(有的用竹板);弦是三弦。演出时,将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板,三弦伴奏。也有的鼓也不用,一人自弹自唱,用脚打板击节,类似“单弦”的形式。其实东北大鼓书就是由“弦子书”发展而来的。
大鼓书、评书等等可以归入说唱表演艺术一类,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开头的一段,就像极了说唱艺术的开篇: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谈到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播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说起流行歌曲中的“小妹妹”,首先使人想到电影《马路天使》中周璇唱的插曲:“小妹妹想郎,直到今……”当然“小妹妹”这股狂风,未必是自此开始刮起的。《桃花江》由黎锦晖作词作曲,于1929年创作,被称之为“新式爱情歌曲”,由王人美、黎莉莉首唱,严华、周璇也唱过,风靡一时。歌词大意为,桃花江是美人窝,胖的也美,瘦的也俏。形式是由男女两人对唱,活泼俏皮,但不免低级趣味。其中并无“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的歌词,只是由于曲调和歌者咬字的缘故才听来如此,而显然张爱玲对此不耐烦。
由中西歌唱的发音方法不同而导致欣赏习惯有异,如同中国人开始不能接受西洋唱法,看他们的歌唱家仿佛要让牙医找出龋齿似的拼命张大嘴、嘴巴张得几乎要掀到后脑勺去那样扯着脖子嘶喊觉得揪心一样,对中国的女声,外国人也一时难以接受。不只是流行歌曲,他们对京剧旦角的唱腔也觉得声音都是从肺部挣扎吐出来的,他们形容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发出的痛苦尖叫,而且那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
※※※
除了民歌发声法的缘故外,“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当然是当时听众的趣味造成的。周璇被誉为金嗓子,可见尖而扁的嗓音真的是社会的需要。大概当时大众都喜欢“小”和“嗲”,尖细的声音近于童音,也才能嗲得起来。不光是声音,《马路天使》周璇所饰一角看上去简直就是未成年少女。而过分追求嗓音的尖而扁,已经失掉了民歌唱法甜美自然的本质,难怪使张爱玲生厌。
虽然同样是尖细的嗓子唱的《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对它似乎印象并不坏,说它调子悦耳,以至于怀疑是不是抄袭西洋或东洋的。《蔷薇处处开》是1942年摄制的同名影片的主题歌,由陈歌辛作词作曲,龚秋霞演唱。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诺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这一段描写仍是《谈音乐》里的。《谈音乐》发表于1944年11月,《苦竹》的创刊号上。《苦竹》的封面是炎樱画的:满幅浓密的竹枝竹叶,一根粗壮的竹干留白,斜过画面,留白处写着一首小诗。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提到过这首诗:“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
就在《苦竹》创刊面世的同时,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里,汪伪政府破败之相凸显。而早在一年前,日本的两个欧洲盟国——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国际法西斯联盟的败局就已经定了。原作者创作这首小诗未必是为日本投降准备的,张爱玲与姑姑谈它也显然并不是先眺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此后不久写的“蔷薇处处开”这一段,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其下的作者绝望心境的写照,但张爱玲的心情又是复杂的:黑冷的深夜与到处盛开的蔷薇构成巨大的反差,使她不禁要挖苦歌者几句;同时又因为夜太黑,心太冷,更需要慰藉,哪怕它是“幼小的”、没有生命的图案。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提到弹词《描金凤》:“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描金凤》是传统经典长篇弹词作品,名字又叫《错姻缘》,不知作者是谁。书成于清朝光绪之前,共有12卷,46回。有人计算过,如果按书每天演唱两小时,得70天才能唱完。
《描金凤》写姑苏书生徐惠兰因家贫向叔父借贷,受辱自尽。江湖术士钱志节将他救起,又将女儿钱玉翠许配给他。玉翠以家传御赐描金凤相赠,作为定情之物。后惠兰被姑母接去读书,途中救了重病的书生金继春,二人义结金兰。惠兰的表兄王云卿被人害死,惠兰被冤枉为凶手而处极刑。临刑前,继春以自己的外貌与惠兰相像,设法换出惠兰而代他去死,临刑时被绿林好汉劫走。京中大旱,钱志节应诏求雨成功,得封高官,为惠兰申冤,终于抓住真凶马寿。其后,惠兰应试,连中三元,因而得以授官,并与玉翠成婚。作品情节一波三折,十分感人。
※※※
《描金凤》演唱者的“咬肉不放”,虽然给张爱玲带来不快,但“描金凤”这个名字,却使她产生了好感。抗战胜利后,她将“描金凤”作了她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但不知当时她有没有坚持把“咬肉”看完,不知她《描金凤》的灵感有无受弹词《描金凤》情节的启发?
张爱玲在她的两篇散文里,都提到了“苏三不要哭”,一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虽然考究怎样死,有些地方却又很随便,棺材头上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大出丧的音乐队吹打着‘苏三不要哭’”;二是在《私语》里写她出生的老房子:“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苏三不要哭”是首外国歌曲,名字叫Susanna,现今通译为“苏姗娜”,早年在中国被译为“苏三不要哭”,系取歌词中的一句。这首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革结束以来,一度十分流行,而显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流行过。
《苏姗娜》的曲调简短,音域很窄,节奏又较快,歌词却有3段,而又有一段副歌,这些因素导致这首歌给听者以明显的重复的印象。歌曲的本身即有许多重复,若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那重复就更以乘积的倍数折磨人的耳朵了。
《苏姗娜》歌词的内容,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来自故乡亚拉巴马的人,带着五弦琴,到路易西安那,到奥尔良,四处寻找心上的姑娘苏姗娜。他一边弹着琴,一边向路人絮絮念叨着他如何冒着夜雨上路,如何梦见含泪吃着荞麦饼的心上人,如何红日当空心却冰冷,如何为了爱情愿奉生命。歌词是伤感的,又带着为情所炙的固执。大出丧时奏它,自然是取它的伤感,布店则是取它的流行。但显然这首歌在张爱玲听来,却都是悲哀,尽管那布店的大减价也许只是促销的手段而并非生意不好。
除了散文,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也不时提到音乐。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段:
“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
《创世纪》中:“……留声机就放在桌上,非常响亮地唱起了《蓝色的多瑙河》。……华尔兹的调子,摇摆着出来了,震震的大声,惊心动魄,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尤其是现在,黄昏的房间,渐渐暗了下来,唱片的华美里有一点凄凉,像是酒阑人散了。……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有一种黑暗的热闹,简直不像人间。”
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67年的《蓝色的多瑙河》,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最初是一首声乐舞曲,后抽掉合唱,单以管弦乐器演奏获得成功。在140年的漫长岁月里,逐渐风靡全球,并且长盛不衰,成为最经典的世界名曲之一,赢得了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人民广泛的喜爱,更被本国人民引以为豪。
在维也纳,《蓝色的多瑙河》甚至被誉为“非正式的第二国歌”,显然其中不仅包含喜爱,还怀有尊敬,这与它的来历有关。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地利在7月中的萨多瓦战役中大败,敌人一度兵临首都维也纳城下。奥兵士气低落,维也纳人也几乎丧失了信心。曾任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指挥的约翰·冯·赫贝克深知音乐的力量,他希望用音乐来振奋人心,于是委托约翰·施特劳斯,一首给人以美感与力量的伟大乐曲由此诞生。
张爱玲所说“摇摆着出来”的曲调,那是黎明的脚步,可能因挟带着的能量太过巨大而显得不稳;继而那惊心动魄的“震震的大声”,那令人“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正是力量的爆发,振聋发聩、摧枯拉朽要冲破一切的力量。
在《连环套》的开头,有一段戏院音乐会的描写,与《谈音乐》里所写交响乐似而不同,对照来看颇有意思:
“……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放着汽,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叮铃当啷倾倒在巨桶里,下死劲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
音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从未占据主要地位,而永远是作为背景、引子、过场出现的,即使像上面所引的详细描述,也只出现过一次。由此来看,张爱玲说她不喜欢音乐,并非故意或姑且之言,只是在她的艺术中,音乐总是萦绕左右,无时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