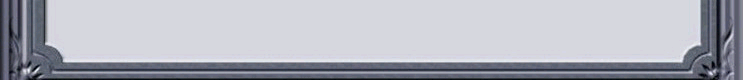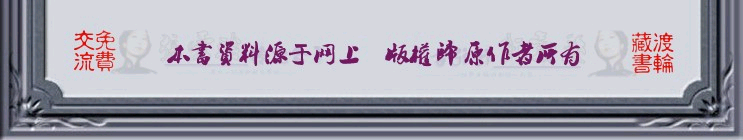第四章 感情的公式(戏剧篇)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张爱玲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归纳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俗常的生活场景:“……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
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前,鲁迅就曾批评梅兰芳被他身边一批士大夫“从俗众中提出”,变成了“紫檀架子”;说他的戏高雅得脱离了大众,“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而从张爱玲笔下看来,梅兰芳并没有被士大夫罩进了鲁迅形容的“玻璃罩”,他仍然是“俗人的宠儿”。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提到几出京剧,多是流传甚广,百姓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老戏,这些老戏自然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人性和民族心理,张爱玲所以选它们。而她又别具只眼,在观众司空见惯的事实中常常看出事物的另一面,或轻易颠覆众人对剧中人物的定评。
※※※
张爱玲写道:“……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吧。《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张爱玲对于话剧借重京剧而风靡上海感到吃惊,这可能是她对于中国话剧史的演进与京剧的发展史了解得不够造成的。话剧是舶来品,自从它被引进国内以来,与戏曲相互借用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话剧的幼稚期,对传统戏曲甚至有所依赖,比如出将入相的门帘、上场时念的“上场诗”及通报姓名等戏曲套数就常被话剧借用。由李叔同与人发起的话剧社团“春柳社”,是早期话剧的重要社团。1919年,它的一位社员吴我尊根据“霸王别姬”的历史传说创作了二幕话剧《乌江》,他在剧本之后所附的《演〈乌江〉脚本者注意》中,就建议用传统戏曲的音乐舞蹈来强化演出效果。与此同时,伴随着传统京剧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京剧界也开始从题材、服装、场景、舞美以及演员念白等方面,广泛借用话剧形式。梅兰芳就编演了许多掺杂了话剧元素的“时装新京戏”,有反映要求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玫瑰花》、歌颂革命志士的《秋瑾》、表现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愿望的《新茶花》等。所以在那时,话剧与京剧彼此关系的状况不仅不是对立的,反倒像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似的,呈现一种迫不及待地饥不择食式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局面,甚至严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
至于“五四”时期,由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批判旧戏,推崇话剧,后来所谓《新青年》派中有观点激进到主张废除京剧,引进社会广泛反响,赞成的、反对的、调和的,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有如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骂旧戏的“多人乱打”。可是这种交锋,基本还是局限在理论界,对于话剧与京剧实践虽有影响,却并没有使相对稚嫩弱小的话剧,膨胀为可以挤压京剧生存空间的巨兽,更没能打乱京剧正常发展的脚步。
《秋海棠》本是上海作家秦瘦鸥根据二十年代发生于天津的一桩社会大事件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
1927年初,直隶督办褚玉璞耳闻不久前来天津新明大戏院演出的上海新舞台京剧艺人刘汉臣、高三奎在天津期间与他的宠妾有染,恼怒异常,听说刘高二人正在北京演出,竟派兵进京,将二人抓回天津。梨园界多人为二人求情均遭拒绝,戏班方面甚至找到梅兰芳转请张学良讲情。褚玉璞原系山东土匪,后虽随张宗昌投靠奉系李景林部,组成直鲁联军,到底不是张作霖嫡系,对张学良之劝一边假意听从,一边却对刘高二人以“假演戏之名,宣传赤化”之罪,连夜(1月18日)枪杀。刑前还用刀割脸以泄愤。此事轰动津门,并迅速传遍全国,各种传媒更是争相报道事情经过,引起国人极大愤慨。
1940年秋,周瘦鹃在上海主持《申报》长篇小说连载,想起老友秦瘦鸥手头有3部小说要写,便向其约稿。不久,秦氏即将3部小说的提纲奉上,周瘦鹃看中了其中一部以刘、高被杀事件为素材的社会言情小说,这就是《秋海棠》。
十多年前,当褚玉璞草菅人命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作家秦瘦鸥做了个有心人,产生了将此事改编为一部小说的想法。为此他多方搜集有关报道,并于三十年代初,利用客居北平之便,多次到天津实地采访,甚至物色好了标致女子作模特儿。
《秋海棠》于1941年初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尚未刊完,便引起热烈反响。影剧界人士纷纷找来,欲将其搬上舞台与银幕。不久,天津、广东、山西、汉口等地话剧、沪剧、越剧、粤剧、晋剧、文明戏等形式的《秋海棠》如雨后春笋,随后又拍摄上映了同名电影(1943年出品,秦瘦鸥编剧,马徐维邦导演,李丽华、吕玉堃、仇铨主演),更增加了《秋海棠》的热度。舞台与银幕之热又带动了图书销售,一时间,《秋海棠》的各种续本也纷纷出版,甚至连周瘦鹃也不忍技痒,写了部《新秋海棠》。但其间最轰动一时的,还是秦瘦鸥亲自执笔改编的话剧《秋海棠》。张爱玲所指,应即是它。
※※※
那是1942年,秦瘦鸥应上海“苦干剧团”导演黄佐临之约,将其改为3幕话剧。由当时话剧界的重量人物费穆、顾仲彝、黄佐监各导一幕,于同年12月24日公演于上海卡尔登戏院。该剧连演5个多月,长盛不衰,破了卖座记录。张爱玲说“风魔了全上海”,并不是过誉之词。
《秋海棠》一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直隶督办虐杀艺人的巨大社会反响,《秋海棠》小说的成功,以及电影和诸多剧种的广泛影响等,另外像演员的出色表演比如曾获“话剧皇帝”称号的石挥的表演,也是原因之一。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开始由《秋海棠》的题材以为那不过是投小市民所好的鸳鸯蝴蝶派的一出庸俗的剧作,可观剧之后,看法大变,尤其由石挥的表演,他“感到这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契诃夫式的《天鹅哀歌》,带有契诃夫的哲学味道”。
只不过这些原因,多为一般人所认识,而张爱玲却洞见到另外的方面,如话剧与京剧的关系。《秋海棠》一剧的成功的确很有可能是“京戏气氛的浓”,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出“话剧里的平剧”。仅从编演人员的戏曲素养来看,《秋海棠》剧的京剧气氛浓也并不奇怪。编剧秦瘦鸥受祖父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曲艺术,及年稍长,又与故乡草台班戏曲艺人多有往来,深谙个中三昧;主演石挥练过身段,学过武打,平常喜操胡琴,生、旦、净、丑都能来两下,为饰演唱花旦的秋海棠,他还向梅兰芳求教,“偷学”程砚秋的小动作。由此看来,《秋海棠》剧京戏气氛的浓厚部分是由演员对京剧的痴迷带来的。
张爱玲对京剧的见识是作家的见识,不仅为普通观众所无,也为京剧行当中人所无。张爱玲对京剧独特的见解,似乎证实了“见多识广”那句话,她张口“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仿佛表明她看过不少京戏剧目。她写道:“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出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那句话。”
《得意缘》又名《雌雄镖》、《星沙驿》、《风火岩》等。故事说的是山东人卢昆杰奉母命到四川投奔母舅督抚徐世忠不遇,因盘缠用尽,难以返家,遂靠卖艺糊口。风火岩山大王狄龙康见卢相貌堂堂,有意招为女婿,于是将他带上山来。卢婚后思念母亲,欲与妻子狄云鸾同返,但山规只许入不许出,夫妻于是硬闯寨口,最终被祖母挡住去路。云鸾掩护丈夫逃跑,而独自向祖母苦苦哀求,祖母终于心软,放二人下山。
《龙凤呈祥》系《美人计》与《甘露寺》连演,故事取材于传奇《锦囊记》及《三国演义》:刘备丧妻,诸葛亮用锦囊妙计,使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段。
《四郎探母》的故事与《杨家将演义》第41回类同,说的是杨四郎被辽邦擒获后,与辽邦铁镜公主成婚。当辽宋战事又起,佘太君亲征。四郎思念母亲,在公主的帮助下私自出关,来到宋营,与母亲兄弟相会,随后返回辽邦,事被萧后得知,几乎被斩,被公主求情救下。(图67、图68)
这3部戏都写了夫妻之爱亦即张爱玲所说的“性爱”与别的爱的冲突,《得意缘》、《四郎探母》的确是夫妻之爱与母子之爱亦即张爱玲所谓“家族之爱”的冲突,但《龙凤呈祥》却似乎不是这二者的冲突——刘备之所以要在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下逃回荆州,似乎并不是为了天伦之情与乐吧。
《红鬃烈马》是京剧传统剧目,剧名后又称《王宝钏》。说的是大唐丞相的女儿王宝钏爱上有志有才有貌却无钱的薛平贵,遭到父亲的反对,离家与薛共同生活。适逢西凉来犯,唐王在全国招募人才组建讨伐大军,薛平贵应招被唐王封为将军,王丞相想叫薛平贵死于战场,使他充任“马前先锋”。薛平贵到寒窑与王宝钏告别后赴军。在军中,薛平贵被王丞相的亲信、副统帅魏虎用酒灌醉,绑在马上送交西凉大营,想叫他落个投敌叛国的罪名。之前薛平贵与西凉公主代战曾有一战,代战对薛心生恻隐,西凉王因而不仅未杀薛平贵,反招为驸马。18年后,已经继位做了凉王的薛平贵忽然想起王宝钏,于是在一天夜里与代战不告而别,骑着红鬃烈马独自来到武家坡,假扮成一个军人,百般挑逗王宝钏,试其贞节,后才以夫妻相见,并以西凉王的名义封王宝钏为正宫娘娘。夫妻来到丞相府,要揪魏虎去见唐王,王丞相眼见阴谋要败露,于是造反,废唐王而篡位。在代战率领的西凉人马增援下,薛平贵主持平息了叛乱,坐上王位。王宝钏与代战相见,彼此情同姐妹,都不肯做正宫娘娘。薛平贵赐给二人各一对龙凤宝剑,允诺三人共同掌管天下。(图69)
※※※
张爱玲却觉得:“《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张爱玲在此批评的只是自私的男性,而不是批评这出戏。因为这出戏“浑朴含蓄”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并没有“赞美”男性的这种行为。因此她认为这是“京戏的可爱”的地方。(图66)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乌盆计》是谭派名剧,又名《奇冤报》、《定远县》,故事见于元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明传奇《断乌盆》、《三侠五义》第五回《包公奇案——乌盆子》等。除了京剧外,还有七八个剧种都有此剧目。京剧《乌盆计》说的是南阳绸缎商人刘世昌在外结完帐后偕仆人回家,路经定远县时遇雨,于是借宿窑户赵大家。赵夫妇见财起意,用毒酒害死了刘世昌主仆二人,碎尸后与陶土拌和,烧制成乌盆。世昌的鬼魂向赵大供奉家中的判官钟馗诉冤,钟馗表示愿做他的证人。鞋工张别古向赵大要债,赵大以乌盆相抵。别古将乌盆带回家中,听了世昌冤魂的诉说,于是携乌盆到定远县衙门,向知县包拯告状。包拯听了世昌的诉说,即刻提审赵大夫妇,并将赵大杖毙。
张爱玲提到京剧《乌龙院》。《乌龙院》的本事略见于《水浒传》及《水浒记》传奇中宋江与阎惜姣一节。《乌龙院》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全本的《宋江杀惜》,包括《乌龙院》、《刘唐下书》、《坐楼杀惜》3个折子戏,这3个折子戏也时常单演;二即指单演的《乌龙院》,又名《宋江闹院》。显然张爱玲所指的不是全本,而是单演的《乌龙院》。其剧情为:
逃难来郓城的阎某去世,宋江慷慨解囊,为其安葬。阎某的妻子将女儿阎惜姣许给宋江为妾,宋江兴建乌龙院给阎氏母女居住,后隐约听说惜姣与他同衙门的文书张文远私通。有天到乌龙院来,惜姣故意怠慢他,两人发生口角,宋江愤而离去。
在一般观众眼里,《乌龙院》不过是一出女人恩将仇报的戏。张爱玲却看出盖世英雄的宋江偏偏被女人鄙夷着的痛苦,她认为其原因是女人除了要钱以外,更要爱,而宋江只会给钱。张爱玲举出剧中人物的几句对话:
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嗳,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
旦:“知道你还问!”
观众对此一般只会当做寻常的妻子抢白丈夫,或者戏中的插科打诨,张爱玲却认为它包含了“最可悲”的他爱她而她不爱他的成份,其打量人性的眼光的确较之常人更“入骨”一些。
但仔细想来,张爱玲的理解似乎也并非毫无破绽。宋江与惜姣,未必存在前者对后者的“单恋”,也就是说,宋江到底爱不爱惜姣,其实也是个问题。惜姣嫁宋江,本是阎妻对宋江感恩及图养老而“执意”的结果;惜姣红杏出墙,至少部分原因是宋江冷落了她的结果;宋江微闻妻子不贞的传言而至乌龙院,只有为夫的正常反应,并无更多“爱付流水”的伤心。所以这一对夫妻自始至终对彼此都没有多少爱心,曾经有的只是好意,而这好意也很快因外来的爱而被削灭了。
※※※
由此看来,张爱玲对男性心理的把握也有失准的时候。所以她的两次婚姻均告不幸,而她都是“吃亏”的一方。
张爱玲文中提到《纺棉花》及《新纺棉花》两出戏。前者剧情为,银匠张三娶妻3天便外出做生意,一走3年,音信皆无。妻子王氏去年生了一个儿子,平常以纺棉花度日。这天天气晴和,她又纺起棉花来,一时高兴,便唱小曲以自遣。恰好张三结清账回家,在门外聆听妻子小唱,又扔银子过墙,冒充别人,以此试探妻子。王氏接到银子,心有所动,开门来见扔银子的人,没想到就是张三,夫妻俩于是半真半假,欢喜团圆。原戏还有奸杀、王氏出斩等情节,但在张爱玲所看到的《纺棉花》中已经截掉了。
《纺棉花》只有旦丑两个主要角色,原为清末民初以戏中串戏、插科打诨取胜的时装小戏。有意思的是40年代搬演时又火了一把,演《纺棉花》的旦角很多,梅兰芳的学生言慧珠和童芷苓都饰演过,虽然据40年代后期主编上海《艺文画报》、与梅兰芳有很多交往的刘龙光说梅兰芳曾不准言慧珠上演《纺棉花》。
在40年代的京剧舞台上大受观众欢迎的《纺棉花》,可以说是京剧不景气的时代里的一个亮点,也可以说是京剧艺术的悲哀。思想开放的人看见《纺棉花》敢于出新、善于借用时尚元素、强调艺术的娱乐性以增强舞台吸引力的勇气;艺术态度严肃的人则视《纺棉花》为歪门邪道,道德感强的人更斥《纺棉花》为低级趣味,骂得狠的也有直称其为“下流淫荡戏”的。而这几种人在戏中都不难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佐证。
比如,《纺棉花》角色身着时髦旗袍,或演唱《四季相思》、《九连环》、《十八摸》、《大沽调》等小调,或学唱四大名旦唱段,或兼唱《二进宫》诸角色,甚至将议论社会新闻编进唱词,总之随心所欲,花样百出。
《纺棉花》戏开始,王氏这样介绍未归的丈夫:“是个小买卖人,也不是铜匠,也不是铁匠。是他妈个银匠。”王氏纺棉花,幼儿啼哭,王氏哄不住,心中烦躁而骂:“你哭你哭,滚你妈的蛋!”这种粗俗的语言,在戏中不时出现。整部戏除了一首接一首的唱曲,就是夫妻俩隔墙调情,说一些暧味挑逗甚至粗鄙的话。戏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张三(白)我问你,我去了三年,家里头谁照应的?
王氏(白)照应我的人多得很,上上下下都是的。
张三(白)有这么些人来,这屋里头挤不下,你到底有个准的?
王氏(白)准的有一个。
张三(白)在哪里?
王氏(白)你顺着我手看,就是那个戴金丝眼镜的!
张三(白)对不住,对不住!我的家主婆承你照应,明朝请你“一枝香”吃大菜!得罪,得罪!
京剧中这类远归丈夫试妻的戏不少,像《武家坡》、《汾河湾》、《桑园会》都是,但情节较为“正经”,角色以老生与正旦应工,不像《纺棉花》是小丑与花旦。且旦角均为贞妇烈女,守身如玉,固然符合主流社会道德规范,较之王氏,却也少了人性,只不过《纺棉花》中的人性,被它的格调稀释了。与《纺棉花》相近的戏,有一出《小上坟》,也被视为“淫戏”,也如同张爱玲给《纺棉花》下的评语,被说为“近于杂耍”,出演的也同样是小丑与花旦。戏的末尾一段与《纺棉花》更是如出一辄:妻子被问及多年来被谁照应时,回答是:“正厅上洋装打扮,戴金丝眼镜的,小白脸儿。”丈夫则冲着台下说:“承蒙照应。明天请你坐汽车,吃大餐。”
《新纺棉花》是《纺棉花》中一幕的铺陈,形式上虽非完全迥异,毕竟内容上有所不同。可能是这个原因,它未遭受像《纺棉花》那样不堪的批评,反说它“内容接近民众生活,而且在表演上吸收了许多农家妇女劳动时的身段,唱腔中又吸收了一些民歌的唱法,使平剧别开生面”。
通常情况下,低级趣味是包含色情成份的,张爱玲却将后者从前者中离析出去。对于她所“提纯”后的文艺作品中的低级趣味,显然她并不是一味排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本不是道德感十分强烈的人;二是她认识到低级趣味的群众性——“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她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只限于小圈子里传观——“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而想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并且主张读者“要什么”,作者“就给他们什么”。而张爱玲给读者的,是软性刺激。其巧妙在于,既刺激了读者,又不会像苏青那样动辄被骂作“黄色女作家”。比如《倾城之恋》所给读者的刺激即是:“书中人还是先奸后娶呢?还是始乱终弃?”她深知“普通的读者最感到兴趣的恐怕是这一点”。
※※※
有着这样的写作观,所以张爱玲没有简单地给两出戏作是非评价,尤其没有给《纺棉花》下道德判词,只是平心地指出它艺术上的跑偏——“逸出平剧范围之外”,又注重从国民性上寻找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她总结出3条,一是幽默的无情,二是喜欢越轨,三是喜欢占他人小便宜。
其一是指《纺棉花》的题材本是奸杀罪案,派生出的《新纺棉花》却变成了喜剧,张爱玲由此认为“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意思无外乎有二,一是说国人幽默的彻底和单纯;二是说国人在笑声中丧失了恻隐和悲悯。
张爱玲虽然自称对京剧是外行,但实际并非一无所知,实际上她看过一些京剧,对京剧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思想。比如她深知京剧的“规矩重”,“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所以一旦有机会稍稍坏一下规矩,国人精神上便得大愉悦,因而皆大欢喜了。
国人的爱占人小便宜,与喜欢越轨有相似的一面,都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往往物质上并没有得到实惠。张爱玲借用市井语言“吃豆腐”来形容,颇为恰当:“《纺棉花》成功了,因为它是迎合这种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戏。张三盘问他的妻,谁是她的恋人。她向观众指了一指,他便向台下作揖谢道:‘我出门的时候,内人多蒙照顾。’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观众被感动的原因除了演员的奉承话中听以外,还有就是可以参与到戏剧中来,台上与台下的严格界线被打破。这一点张爱玲也已经提到了。
“空城计”有时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3个折子戏的统称,有时单指其中的一出折子戏,又名《抚琴退兵》。故事见于《三国演义》。诸葛亮驻守空虚的西城,司马懿率大军来犯,诸葛亮见势不能敌,于是下令大开城门,自己在城上饮酒抚琴。司马懿生性多疑,又知诸葛亮素来谨慎,料必有诈,于是不战而退,轻易丧失了活捉诸葛亮的佳机。
“空城计”这著名故事给人的最深印象,通常是诸葛亮的大智大勇,张爱玲却又另有视角:“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冈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恩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
张爱玲的注意力放在了对诸葛亮内心世界的探究上,为报先帝知遇之恩,忙白了胡子又历此大险,空城一计,事后固为笑谈,当时却有可能搭上老命,怕是诸葛亮想想也自后怕吧?这样为扶不起的阿斗去“舍命忘身”,究竟值得不值得呢?反正张爱玲是觉得不值的,否则她不会感到他心里“略有点凄寂的况味”;虽然他若不如此,张爱玲也可能不会说他是个完人。“完人”本是神性化的,在百姓的心目中,诸葛亮已然是神,至少如神——料事如神。而“凄寂”是人性化的,张爱玲在消解诸葛亮的神性。她是不喜欢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的,即便是神,也要是带有人性的神才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