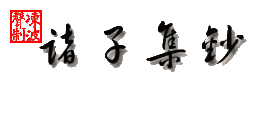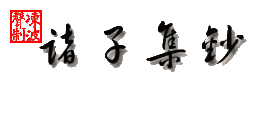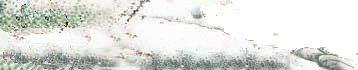| |
自從隋文帝楊堅統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裡,顏氏家訓是一部影響比較普遍而深遠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寫道:“古今家訓,以此為祖。”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這一則由於儒家的大肆宣傳,再則由於佛教徒的廣為徵引,三則由於顏氏後裔的多次翻刻;於是泛濫書林,充斥人寰,“由近及遠,爭相矜式”,豈僅如王鉞所說的“北齊黃門顏之推家訓二十篇,篇篇藥石,言言龜鑑,凡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不獨顏氏”而已!
唯是此書,以其題署為“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於是前人於其成書年代,頗有疑義。尋顏氏於序致篇云:“聖賢之書,教人誠孝。”勉學篇云:“不忘誠諫。”省事篇云:“賈誠以求位。”養生篇云:“行誠孝而見賊。”歸心篇云:“誠孝在心。”又云:“誠臣殉主而棄親。”這些“誠”字,都應當作“忠”,是顏氏為避隋諱,而改;風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終制篇云:“今雖混一,家道罄窮。”明指隋家統一中國而言;書證篇“臝股肱”條引國子博士蕭該說,國子博士是該入隋後官稱;又書證篇記“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這些,都是入隋以後事。而勉學篇言:“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書證篇引廣雅云:“馬薤,荔也。”又引廣雅云:“晷柱挂景。”其稱廣雅,不像曹憲音釋一樣,為避隋煬帝楊廣諱而改名博雅。然則此書蓋成於隋文帝平陳以後,隋煬帝即位之前,其當六世紀之末期乎。
此書既成於入隋以後,為何又題署其官職為“北齊黃門侍郎”呢?尋顏之推歷官南北朝,宦海浮沉,當以黃門侍郎最為清顯。陳書蔡凝傳寫道:“高祖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這可見當時對於黃散之職的重視。之推在梁為散騎侍郎,入齊為黃門侍郎,故之推於其作品中,一則曰“忝黃散於官謗”,再則曰:“吾近為黃門郎”,其所以如此津津樂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門兼美”吧。然則此蓋其自署如此,可無疑義。不特此也,隋書音樂志中記載:“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云云。”而直齋書錄解題十六又著錄:“稽聖賦三卷,北齊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撰。”則史學家、目錄學家也都追認其自署,而沒有像陸法言切韻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稱其入隋以後之官稱為“顏內史”了。
在這南北朝分裂割據的年代呢?王儉褚淵碑文寫道:“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樂,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鑑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這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寫照。當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朝秦暮楚,“自取身榮,不存國計”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於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揚名”,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從憂患中著一條安身立命的經驗:“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他一方面頌揚“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面又強調“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舌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方面宣稱“生不可”,“見危授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難得”,“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因之,他雖“播越他鄉”,還是“靦冒人間,不敢墜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終於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三為亡國之人”。然而,他還在向他的子弟強聒: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甚至還大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死,北齊宦者田敬宣之“學以成忠”,而痛心“侯景之難,……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大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當其興酣落筆之時,面對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往來賓主如郵傳”者,吾不知其將自居何等?如此訓家,難道像他那樣,擺出一副問心無愧的樣子,說兩句“未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就可以“為汝曹後車”嗎?然而,後來的士子大夫們卻有像陸奎勳之流,硬是胡說什麼“家訓流傳者,莫善於北齊之顏氏,……是皆修德於己,居家則為孝子,許國則為忠臣”。這難道不是和顏之推一樣,無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語嗎?
顏之推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唐人崔塗曾有一首讀庾信集詩寫道:“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游;唯有一篇楊柳曲,江南江北為君愁。”我們讀了這首詩,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顏之推;因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倫,他們對於“朝市遷革”所持的態度,本來就是伯仲之間的。他們一個寫了一篇哀江南賦,一個寫了一篇觀我生賦,對於身經亡國喪家的變故,痛哭流涕,慷慨陳辭,實則都是為他們之“競己棲而擇木”作辯護,這正是這種悲劇的具體反映。姚範跋顏氏家訓寫道:“昔顏介生遭衰叔,身狎流離,宛轉狄俘,阽危鬼錄,三代之悲,劇於荼蓼,晚著觀我生賦云:‘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為畎畝之民,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辭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玩其辭意,亦可悲矣。”他“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於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處世祕訣,說起來好像頭頭是道,面面俱圓,而內心實則無比空虛,極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寫道:“每常心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這是他由衷的自白。紀昀在他手批的黃叔琳節鈔本一再指出:“此自聖賢道理。然出自黃門口,則另有別腸——除卻利害二字,更無家訓矣。此所謂貌似而神離。”“極好家訓,只末句一個費字,便差了路頭。楊子曰:‘言,心聲也。’蓋此公見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老世故語,隔紙捫之,亦知為顏黃門語。”紀氏這些假道學的庸言,卻深深擊中了這位真雜學的要害。當日者,顏氏飄泊西南,間關陝、洛,可謂“仕宦不止車生耳”了。他為時勢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說那樣,“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梁武帝蕭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練,後又捨身同泰;顏氏亦嚮風慕義,直至歸心。梁元帝蕭繹崇玄,“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顏氏雖自稱“亦所不好”,然亦“頗預末筵,親承音旨”。當日者,梁武之餓死臺城,梁元之身為俘虜,玄、釋二教作為致敗之一端,都為顏氏所聞所見,他卻無動於中,執迷不悟,這難道不是像他所諷刺的“眼不能見其睫”嗎?他徘徊於玄、釋之間,出入於“內外兩教”之際,又想成為“專儒”,又要“求諸內典”。當日者,梁武帝手敕江革寫道:“世間果報,不可不信。”王褒著幼訓寫道:“釋氏之義,見苦斷身,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數等差,而義歸汲引。”因果報應之說,風靡一時,於是顏之推也推波助瀾地倡言:“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又勸誘他的子弟:“汝曹若顧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他這一席話,難道僅僅是在向他的子弟“勸誘歸心”而已嗎?不是的,他的最終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場”。何孟春就曾經指出:“是雖一家之云,而豈姁姁私焉為其子孫計哉?”
顏氏此書,雖然乍玄乍釋,時而說“神仙之事,未可全誣”,時而說“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而其“留此二十篇”之目的,還是在於“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這是古代時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訓家的唯一主題。
此書涉及範圍,比較廣泛。那時,河北、江南,風俗各別,豪門庶族,好尚不同。顏氏對於佛教之流行,玄風之復扇,鮮卑語之傳播,俗文字之盛興,都作了較為翔實的紀錄。至如梁元帝之“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使寶貴的文化遺產,蒙受歷史上最大的一厄;以及“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以及當時的“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以及俗儒之迂腐,至於“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這些,都是很好的歷史文獻,提供我們知人論世的可靠依據,外此其餘,顏氏對於研討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亦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此書對於研究南北諸史,可供參攷。顏氏作品,除觀我生賦自注外,像風操篇所言“梁武帝問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這個人就是夏侯亶;勉學篇所言“江南有一權貴”,以羊肉為蹲鴟,這個人就是王翼;文學篇言“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這個人就是姜質;省事篇所言“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這兩個人就是祖珽、徐之才。這些,都可以補證南北諸史。教子篇所說的高儼,兄弟篇所說的劉瓛,治家篇所說的房文烈和江祿,風操篇所說的裴之禮,勉學篇所說的田鵬鸞和李庶,文章篇所說的劉逖,名實篇所說的韓晉明,歸心篇所說的王克,雜藝篇所說的武烈太子蕭方等:這些,都可與南北諸史參證。而風操篇所說的臧逢世,慕賢篇所說的丁覘,涉務篇所說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馬云云”:這些,更足補梁書之闕如。慕賢篇所說的張延雋,勉學篇所說的姜仲岳:這些,更足補北齊書之俄空。又如雜藝篇所說常射與博射之分,則提供我們弄通南史柳惲傳所言博射之事。
第二,此書對於研究漢書,可供參攷。舊唐書顏師古傳寫道:“父思魯,以學藝稱。……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大顏、小顏之精通漢書,或多或少地都受了家訓的影響。如書證篇言“猶豫”之“猶”為獸名,漢書高后紀師古注即以猶為獸名;同篇引太公六韜以說賈誼傳之“日中必(上彗下火)”,師古注亦引六韜為說;同篇又引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而訓導為擇,師古注亦從鄭氏說,訓導為擇。這些地方,師古都暗用之推之說,尤足攷見其遵循祖訓,墨守家法,趨惟謹,淵源有自也。
第三,此書對於研究經典釋文,可供參攷。經典釋文是研究儒、道兩家代表作品的重要參攷書。纂寫經典釋文的陸德明,是顏之推商量舊學的老朋友,他們的意見,往往在二書中可攷見其異同。如書證篇言“杕杜,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此大誤也”;詩唐風杕杜釋文則云:“本或作夷狄之狄,非也。”書證篇言“左傳‘齊侯痎,遂痁’……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此臆說也”;釋文則引梁元帝之改疥為痎,此尤足攷見他們君臣間治學的相互影響之處。書證篇引王制“臝股肱”鄭注之“□衣”,謂:“蕭該音宣是,徐爰音患非。”釋文則云:“擐舊音患,今宜讀宣,依字作□,字林云:‘□臂也,先全反。’是。”音辭篇言:“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釋文敘錄條例則云:“質有精麤,謂之好惡;心有愛憎,謂之好惡。”至如書證篇言: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灌木,叢木也。”“近世儒生,改菆為□”,而有徂會、祖會之音之失,更可訂正釋文所下徂會、祖會、亦外等反的錯誤。
第四,此書對於研究文心雕龍,可供參攷。如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六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文心雕龍宗經篇則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統其端;記傳盟檄(從唐寫本),則春秋為根。”與顏氏說可互參,這是古代主張文章原本五經的代表作。同篇又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鬥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記,大較如此。”文心雕龍程器篇則云:“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譸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顏氏論證,與之大同。同篇又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文心雕龍附會篇則云:“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色;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他們所持的文學理論,都以思想性為第一,藝術性為第二。不過,之推所謂事義偏重在事,彥和所謂事義偏重在義,故一為皮膚,一為骨髓,非有所抵牾也。蕭統文選序寫道:“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很好地說明了二者的具體內容及其相互關係。
第五,音辭一篇,尤為治音韻學者所當措意。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序寫道:“黃門此製,專為辨析聲韻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義,實為研求古音者所當深究。”
外此其餘,在一向重道輕器的歷史時期,他對於祖晅之的算術,陶弘景、皇甫謐、殷仲堪的醫學,都給予應有的重視,也是難能而可貴的。
這部集解,是以盧文弨抱經堂校定本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續家訓、羅春本、傅太平本、顏嗣慎本、程榮漢魏叢書本、胡文煥格致叢書本、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朱軾朱文端公藏書十三種本、黃叔琳顏氏家訓節鈔本、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屏山聶氏汗青簃刊本。我所見到的還有嘉慶丁丑廿二年南省顏氏通譜本,以其所據為顏本,無所異同,且間有新出訛謬之處,故未取以讎校。其它援引各書,亦頗夥頤,不復一一(爾見)縷了。
此書在唐代,即有別本流傳,如歸心篇“儒家君子”條以下,廣弘明集卷二十八引作“誡殺、家訓”,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且著錄之推誡殺一卷;則唐代且以此單行了。同篇之“高柴、折像”,廣弘明集“折像”作“曾皙”,原注云:“一作‘折像’。”凡此都是唐代有別本之證。而廣弘明集卷三引歸心篇“欲頓棄之乎(今本‘乎’作‘哉’)”句下,尚有“故兩疏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兩句,則
本書尚有佚文;這當是顏書之舊,固非郭為崍所引風操篇“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之下,尚有“戴逐稱安道則家弟”一句之比——此乃郭氏妄為竄入,因為乾隆時人所見家訓,不會多於今本。宋淳熙台州公庫本,今所見者,係元廉台山氏補修重印本,故間有不避宋諱之處。此本頗有影鈔傳世者,知不足齋叢書即據述古堂鈔本重刻(無校刊名銜),光緒間,汗青簃又據以重刻。盧文弨校定本所據宋本,蓋亦鈔本,故與宋本時有出入,翁方綱譏其未見宋本,是也。我所據的,尚有海昌沈氏靜石樓藏影宋鈔本及秦曼君校宋本。此外,又得見董正功續家訓宋刻殘本卷六至卷八共三卷,此書除全引顏氏原文可供校勘外,頗時有疏證顏書之處,今亦加以甄錄。惜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之七卷本半宋刻半影鈔者,今亦不可得而見矣。外此其餘,如敦煌卷子本勤讀書鈔(伯、二六0七)、劉清之戒子通錄、胡寅崇正辨、呂祖謙少儀外傳、曾慥類說等,亦頗引顏書,多為前人所未見或未及徵引,今皆得而讎校之,於以是正文字,實已不無小補,不知能免於顏氏所譏之“妄下雌黃”否也?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顏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這部著作從事集解之外,我還把顏之推傳和他流傳下來的作品,統統收輯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參攷。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