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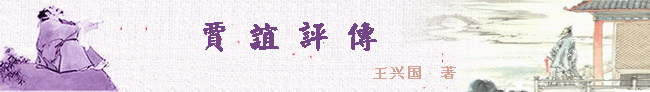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二 礼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贾谊礼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礼治重要性的思想,以等级制为核心的法律不平等论,以及某些关于礼治的具体制度的思想。以下我们分别对这些思想进行一些分析。
(一)关于礼治的重要性
礼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一种产物。《礼记·曲礼上第一》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对于"定亲疏"一词,《十三经注疏》的解释是:"五服之内,大功已上,服粗者为亲;小功已下,"服精者为疏。"这就说明,礼本来是对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她)的亲属和亲戚应根据与死者的不同关系而穿着不同的丧服的规定。人们在一个人死后穿不穿丧服,穿什么样的丧服,不仅标志着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且反映出一定的伦理准则。能不能按礼的规定行事,便反映出人们是否具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既然对一个人死了之后还必须如此严格地按照礼的规范行事,那么处理活着的人际关系,其中不仅包括宗族之内,而且推而至于宗族之外乃至整个社会,就必须更加注意严格遵守礼的规范。后来懦家提出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便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礼制规范。如果说,在礼范畴发展的早期,其主要内容是处理亲疏关系的话,那么到了这时,便加进了贵贱。等级关系。礼也就逐渐由一个伦理范畴而演变为一个既有伦理意义又有政治意义的范畴。随着儒家和法家的对立,礼治与法治斗争的深化,礼作为一个政治范畴也就越来越具有独立的意义了。贾谊论礼,其出发点和着眼点,首先也在于其政治意义。在《礼》一文中,贾谊指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将贾谊的这段话与前面我们引用过的《礼记·曲礼上第一》那段关于礼的说法相对照,便可以发现,《曲礼》中那段话,是从"定亲疏"出发,达到"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目的,其伦理色彩是十分鲜明的;而贾谊的这段话,强调的是明等级,使"尊卑大小,强弱有位",以达到"固国家,定社稷"的目的。其分析是完全从政治上立论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所以贾谊特别强调礼的"明等级"。别上下贵贱的作用。他说:"明等级以道之礼","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傅职》);"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俗激》);"寻常之室无奥之位,则父子不别;六尺之舆无左右之义,则君臣不明。寻常之室。六尺之舆处无礼,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乱,而况其大者乎!"(《礼》)这些话清楚地表明,贾谊认为,礼的作用就是要使上下、尊卑等级分明,不同等级的人们都要按照礼对不同等级所作出的行为规范行事,如果违反了这些行为规范,那就会出现"上下踳逆,父于悖乱"的局面。
贾谊虽然突出地强调礼的政治作用,但这种强调不仅不否认礼的伦理作用,相反,而是以其伦理作用为基础的。这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作为政治意义的礼本来是从作为伦理意义的礼演化而来的;而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来看,作为整个政治国家结构的基层组织的,仍然是以"亲亲"为支配原则的家族制。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不仅要求人们在处理亲子关系时,做到"孝";而且要"移孝作忠",即象对待父母一样来对待君王,从而做到"忠孝双全"。《论语·为政》篇有这样一段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段话虽然是讲孔子对于参政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对孝与忠,即伦理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其中已包含了"移孝作忠"的思想萌芽。这些情况表明,儒家是把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统一起来的,其伦理是为政治服务的,其政治原则也是以伦理原则为基础的。贾谊继承了儒家的这一传统,所以他的"明等级"是以"定亲疏"为基础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礼治才能真正实现。他说: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礼》)
这里讲的"札之至"中的"至",是"极致"的意思。贾谊认为。不同等级的人,只有谨守上下尊卑的区别,认真实行礼对自己行为的规范,即所谓仁、忠、慈、孝、爱、敬、和、柔、慈、听,等等,才能达到礼的极致,即一种既等级分明又互敬互爱的普遍和谐状态。所谓"礼之质"的"质",具有"本体"、"本质"之意。《礼记·曲礼上第一》:"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十三经注疏)解释说:"言道,言合于道。质,犹本也,礼为之文饰耳。"《曲礼》中的这段话与贾谊关于"礼之质"的那段话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说,人们的言行只有符合于"道",即仁、忠、慈、孝、爱、敬、和、柔等等,那才是抓住了礼的本质。反过来说,人们只要抓住了礼的本质,按"道"的要求行事,那么就可以做到"行修言道"。贾谊对"礼之至"和"礼之质"的强调,说明他的礼治思想的政治目的,是希望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否真正建立了起来,则要看人们是否抓住了礼的本质,并按照礼的本质要求("道")来行事。
贾谊有一段话,对礼的作用和重要性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笑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于恭敬、搏节、退让以明礼。(《礼》)这段话,被《礼记·曲礼》全部收入,作为阐明礼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基本论点。据《十三经注疏)的解释:"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这就是说,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是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礼来规范,才能成功。这表明礼首先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行为规范。至于"教训正俗",是说通过说服教育改良人心风俗,这大体上也是属于伦理的范畴。往下提到的"分争辨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宦学事师"、"班朝治军,莅官行法"等,虽然也包括某些伦理及民事纠纷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属于政治的范畴。至于最后提到的"祷祠祭祀,供给鬼神",则是属于宗教迷信的范畴。由此可见,在贾谊看来,礼的实用范围包括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事人事鬼,事君事亲均离不开礼的规范。象贾谊这样对礼的作用作出如此全面的的论述,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以前,虽然有荀子的《礼论》,并且荀子还说到:"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荀子的这段话,虽然为贾谊对礼的作用的论述规定了一个基本方向,但显然还只是一个纲,而贾谊则根据这个纲进一步理出了若干条目,从而使人们对礼的作用的认识更加具体和全面。所以,后人在编辑《礼记》时,将贾谊这段话收入该书第一篇文章《曲礼》,作为对礼的作用的经典性论述,便决不是偶然的了。
(二)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
贾谊不仅对礼的作用有全面的论述,而且对礼的实质,或者说阶级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这就是他关于礼的阶级不平等思想。本来,儒家以亲亲为内容的礼治思想是以明确区分等级差别为前提的。墨子之所以提出"兼以易别"的主张,就是针对懦家这种阶级不平等论的。所以盂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 子·膝文公下》)荀子继承了孟子这一思想,特别强调礼的别贵贱的作用。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指礼义、情性--引者)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荀子·礼论》)贾谊的礼的阶级不平等论正是对荀子这种"别"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孟子和荀子的"别贵贱"的主张是与墨子的"兼爱"思想相对立的话,那么贾谊的礼的阶级不平等论则是与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相对立的。在战国时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逐步壮大,他们在政治上必然要求争得自己的地位。而传统的重亲亲和别贵贱的礼,却限制和排斥着这些人。所以,他们必然要起来批判它。韩非子说的"爱多者,则法不立"(《韩非子·内储说上》);"不避权贵,法行所爱''(同上书《外储说右上》),就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是,人们阶级地位的改变,其某些政治主张也会随之而改变的。同样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贾谊,之所以一反先秦法家"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的主张,而重新强调儒家的礼的阶级不平等论(实际上也就是法律的阶级不平等论),这正好说明自秦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汉初,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夺取政权到巩固已得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既然已经取得了自己的政权,就不存在向其他人夺权的问题了、相反,倒是害怕别人夺他的权。既然他们自己已经成了"贵"者,那么法家的"法不阿贵"这个向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便过时了,如果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那就等于把法律这把刀子对准了自己。所以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新兴地主阶级在汉初重新抬起儒家的法律不平等论,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尽管贾谊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提出阶级论的主张这个事实本身却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性。
据历史记载,贾谊提出礼治的阶级论,其动因是周勃下狱这件事。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汉初政治虽然标榜黄老的清静无为,但其刑罚还是相当苛繁的,还保留有某种程度上的法家的"法不阿贵"的遗风。而这种作法已经威胁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安定与团结,所以贾谊以"投鼠忌器"来比喻它: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罪;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舆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此则所以为主上预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阶级》)
所谓"欲投鼠而忌器",也就是俗话说的"打狗欺主"。人们之所以忌讳打狗,是怕侵犯主人的权威。贾谊所以宣传投鼠忌器,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主的权威,即所谓"尊君之势"。文中讲的"望夷之事",仍是以秦王朝失败的教训来证实这一论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胡亥用阴谋继承皇位之后,听任赵高专权,诛杀宗室,下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狱,使他们或自杀或车裂而死。当秦末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向武关进入之际,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谎报军情,于是将二世杀害于望夷宫。贾谊认为,二世之所以有"望夷之事",即被赵高杀害,是与他严刑峻法,随意杀害大臣分不开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君主自身孤立无辅,失去应有的威势,另一方面则必然助长权臣的淫威,使赵高可以指鹿为马,直至弑杀君王。贾谊所谓"投鼠而不忌器之习",是说二世被赵高杀害,乃是他自己随意戮辱大臣的必然结果。这个故事是能够打动汉朝统治者的心的。所以《汉书·贾谊传》说,汉文帝接受了贾谊关于礼貌大臣的建议,"养臣下有节"。
贾谊认为,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要养臣下有节,那就必须严格地区分等级,使不同等级的人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享受不同的"礼"。他以建筑物的"阶级"形象他说明了这种等级制的重要性: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阶级》)
这段话表明,贾谊的等级论(或阶级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人为地造成一种"势",使天子"其尊不可及"。按照这种等级论,就是要将社会的行政官员以及贵族划分成不同等级,前者即所谓公、卿、大夫、士,后者即所谓公、侯、伯、子、男,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天子"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各级官吏和贵族则是这个塔不同层次的结构,至于广大老百姓,只不过是这个金字塔的地基,而不是塔本身(即所谓"众庶如地")。显然,在贾谊看来,尽管进入这个金字塔内部结构的这些人,虽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天子服务的,但这些人与作为这个塔的基础的广大庶人相比,其身分要高贵得多。因此,如何对待这些有等级身分的"贵"者,就既有一个"欲投鼠而忌器"的问题,也有一个是否尊重其贵者身分的问题。这样,便引出了贾谊的履冠不可颠倒论: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今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地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阶级》)
贾谊这种"尊尊贵贵之化"的理论,其封建主义色彩之浓厚自不待说,因此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对它进行批判,也不算过份。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种维护等级特权利益的阶级自觉。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就可以发现,贾谊礼貌大臣的思想,也还包含有某种积极的合理的因素:这就是强调要尊重大臣的人格。我们知道,封建帝王往往把臣下当作自己的奴才,以狗马视之。臣下的生杀予夺一概操之于帝王,所谓"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就是这种绝对君权论的反映。面对君主的这种绝对权威,一些正直敢谏的大臣,往往不得善终;相反,一些逢迎拍马之辈倒可以沐猴而冠。这样就容易助长官吏的趋炎附势之风,不顾廉耻,不重气节。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贾谊提出等级论,要求帝王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一种比较宽容的礼让政策,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培养大臣为帝王效忠的自觉性。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其眼光显然也比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看得更长远一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贾谊多次提到的豫让事中行之君的故事看到。春秋战国之间的晋国有个豫让,他开始替中行氏当家臣,后来智瑶消灭了中行氏,豫让便替智瑶当家臣。当赵襄子消灭智瑶之后,豫让改变姓名,用漆涂身,吞炭使哑,一定要报襄子灭智瑶之仇,"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有人问豫让,为什么中行氏灭亡了,你不报仇,而智瑶灭亡了,你却这么坚定地报仇?豫让回答说:"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故为之国士用。"从这个故事出发,贾谊发挥了如下一段议论: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折节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大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无耻,謑苟(《汉书·贾谊传》作"謑诟",謑音谐--引者)无节,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俱无耻,俱苟安,则主上最病。(《阶级》)贾谊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人主善待臣下,要以"国土"之礼去养成臣下的"廉耻"之心,使之做到避利而趋义,而不要"见利则趋,见便则夺"。
贾谊有一句名言:"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汉书·贾谊传》;《贾谊新书·阶级》作"札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这句话被视为贾谊主张法律不平等论的典型言论。杨鹤皋在《贾谊的法律思想》一书中指出,贾谊继承了儒家的"法律不应平等的思想,明确提出了'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的主张。"于传波说:"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非同小可,因为大臣享有刑事豁免权,罪大也不过是自杀,这就等于公然宣布,法律主要是用来镇压下层人民的工具。"(《试论贾谊的思想体系》,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 年第3 期)我觉得这些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思想发展史来看,正如于传波的文章所说,贾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理论上的创始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出自《礼记·曲礼》。于文指出:"《礼记·曲礼》中的这句话可以断定是从贾谊那里抄来的。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了'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在这之前,《荀子·富国》有"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的话,而《曲礼》和贾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样。在贾谊之前,只有高堂生的《士礼十七篇》,即今天的《仪礼》,其中没有这一类的话。《曲礼》是汉朝人的作品,这是明显易辨的。《曲礼》中有85 个字的一大段和贾谊《新书·礼》中的文字一样,这只能表明是《曲礼》抄了贾谊。贾谊曾为大臣周勃被囚事件给汉文帝写了一篇上书,详细地阐明了大臣不受刑的理由。所以,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系统地作为理论提出来的是贾谊,而不是荀子,更不是苟子以前的什么人。"我觉得于传波的这段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把应该列举的一些主要论据都说出来了。这里,我还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补充两点说明。其一,贾谊虽然是"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这一法律不平等论的经典表述的发明者,但却不是法律不平等论思想的发明者。正如杨鹤皋在《贾谊的法律思想》中所指出,它是贾谊对儒家思想的继承。荀子虽然提出了"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刑不上大夫"的命题;而在《周礼·秋官司寇》中,则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的说法,这里实际上包含有"刑不上大夫"的思想萌芽。其二,如果说荀子的"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是儒家对法律不平等论的肯定命题的话;那么荀子的学生李斯提出的"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则是从法家立场出发,对荀子这一肯定命题的否定。贾谊作为荀子的再传弟子,他总结了韩非、李斯等片面强调法制的经验教训,提出"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是对韩非命题的否定,对荀子命题则是否定之否定;但是其对儒家法律不平等论的概括和表述却更加准确和鲜明了。贾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显然是和他把"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作为韩非子"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反命题这一点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证明贾谊的确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理论的创始人。他将儒家的法律不应平等的思想(实际上也就是礼不应平等)用"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于"作了经典的表述,从而使之流传久远,影响深刻,因而其消极作用的确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消极作用,即使在二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来。但是,我认为这种消极作用更多地是从这句话的客观效果而言的。至于贾谊的主观意图,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他是希望通过礼貌大臣使之养成一种讲气节的自觉的人格。
(三)关于礼的具体制度
贾谊在论述礼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同时,还根据汉初社会的客观情况,对某些具体的礼制也作了论述。总的来说,贾谊认为各种具体礼制的实施,要达到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别贵贱"。所以他说:"人之情不异,面目。
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等齐》)这一段话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的贵贱差别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而后天又是靠各种具体制度来维系的。这里讲的等级和势力是带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等级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势力,同样既有经济的势力又有政治势力。而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掌握了经济权和政治权,贵也就是必然的了。但是贾谊认为,光有这些实权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各种具体礼仪,使这种权贵者从外在形式上表现出来,才能做到等级分明。贾谊说:"等级分明,则下不得疑;权力绝尤,则臣无冀志。"(《服疑》)那么,用一些什么具体礼制来标示人们等级身分的区别呢?贾谊认为包括很多方面,诸如名号、旗章、礼仪、秩禄、冠履、衣带、环佩、车马、宫室、器皿等等。总之,一切均必须以人们的等级地位的高下来决定相应的标准。所以他说: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端异,则札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官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饮食异,则祭把异,则死丧异。(《服疑》)这里,贾谊把名号、权力、事势摆在最前面,说明他认为这些方面的"异",即等级区别是最关键的、带实质性的区别。但同时,他认为其他方面的区别,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才如此不厌其烦地加以列举。在这些具体的区别中,贾谊针对汉初情况,又特别强调两种区别:其一,是服饰的区别。贾谊认为:"衣服疑者,是谓争先(光)。"(《服疑》)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权力、名号之类是看不见的;宫室、器皿之类也是不能跟着主人跑的,车马虽然可以跟人跑,但人总有下车马活动的时候,但是只要人公开:进行活动,衣服,冠履总是二刻不能离开的。所以,要识别一个人的身分,最经常、最直接的标志就是衣服、冠履、汉高帝之所以禁止商人乘车、衣丝,其道理也就含有明等级之意。可是随着汉初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其生活水平必然相应提高。这样便出现了生活方式上的僭越。这就是贾谊说的:"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大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瑰玮》)据贾谊说,汉文帝当时还"衣皂绨",可是"靡贾侈贵,墙得被绣"(《孽产子》),就是说"富人大贾"在服饰方面的悟越不只是"拟天子",而是超过了天子。这显然是贾谊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当时要建立礼制首先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于是贾谊提出了"制服之道",他说: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服疑》)这段话反映了贾谊对服饰在礼制中的特殊重要性的认识。
其二,是制度和名号方面的区别。如果说贾谊强调服饰方面应该不平等,主要是针对"富人大贾"的话,那么他强调制度。法令、名号等方面的区别则主要是针对同姓诸侯王。他指出同姓诸侯王打着"一用汉法"的旗号,表面上似乎很尊重中央政府,其实是想与皇帝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由于诸侯王在宫法上"一用汉法",因此在官制、秩禄、名号等方面也必然出现僭越的现象,因而使贾谊深感叹息,觉得"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等齐》)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那么"所谓臣主者非有相临之具、尊卑之经也。特面形而异之耳。近习乎形貌,然后能识,则疏远无所放,众庶无以期,则下恶能不疑其上?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同上)为了纠正这种悟乱状态,贾谊便重申"周礼",他说"古者周礼,天子葬用隧,诸侯县下";"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审微》)贾谊的这些主张,明显地具有复古主义的倾向,但这种复古主义又是积极地为现实的政治、即巩固中央集权制服务的。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