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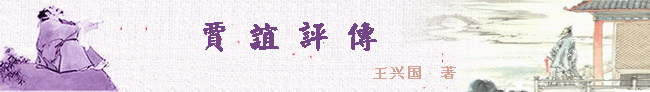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三 不废法治
(一)论法的必要性
贾谊虽然十分重视礼治,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礼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法治。他反对的只是象秦统治者那样,只知道实行严刑峻法,而并不一般地否认法的作用和重要性。他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干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吵,使民日迂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汉书·贾谊传》)
在贾谊看来,礼和法各有不同的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是说礼的作用偏重于教化,在人们的过失。罪恶未产生以前,通过"劝善",即说服教育,从而防患于未然。"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说当罪恶已经发生之后,那就必须毫不姑息地施以刑罚。正是由于礼和法二者的作用不同,所以它们之间不能互相替代。关于这一点,贾谊曾以"芒刃"和"斤斧"的关系予以生动的说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众理解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制不定》)这段话表明,在贾谊看来,不论是礼还是法,它们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芒刃"之于"斤斧"而已,各有各的用场。譬如解牛,锋利的刀于只能用于枝节之处,至于遇到了髀骨和股骨之类的大骨头,那就非斧头莫属了。
(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
贾谊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是综合儒法、继承儒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知道,早期儒家是重视礼治而反对法治的。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后来,随着先秦法家的兴起,作为集儒家思想大成的荀子便在继续强调礼治思想的问时,也部份地吸收了法家关于法治的思想。荀子认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这表明荀子虽然重法,但由于他把君子视之为"法之原".这样又势必把人治放在第一位,把法治置于第二位,所谓"故法不能独立,类(指律例--引者)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同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生李斯和韩非继承了荀子的重法思想,否定了他的礼治思想,但由于一味强调严刑峻法,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失败。贾谊总结了这个教训,所以又重新回到了荀子礼法结合论之上。但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所发展。我认为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贾谊追随荀子的足迹,进一步扩大了法的范围。在荀子以前,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对"法"的理解,往往都是与"刑"联系在一起的,即把法仅仅理解为一个治罪的惩罚条例。例如,前面所引孔于讲的"齐之以刑",还有商鞅说的"重刑而建其罪","重罚轻赏"等等,都是把法与刑、罚连系在一起的。显然,这是对法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荀子的贡献就在于,他扩大了人们对法的范围的理解。例如,他在《荣辱篇》中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这里所说的"法则、度量、刑辟、图籍"显然都是属于法制一类的东西。杨柳桥在《荀子诂译》中引杨惊解:"度,尺寸;量,斗斜。刑辟,刑法之书。图,模写土地之形;籍,谓书其户口之数也。"荀子是把这些都当作三代的"治法"的,这就使法的范围不只是限于"刑辟",而且包括了各种政治、经济的法则和制度。这样一来,荀子实际上就把礼和法在一定范围内沟通起来了。因为所谓礼,固然有注重恭敬、谦让及思想教育的一方面,即属于态度和方法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如何实施礼的许多具体制度和法则。这些制度和法则在封建社会同样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对此,荀子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按梁启雄的《荀子简注》,所谓"大分"指"总纲";所谓"类"指"礼法条文以外比附类推的律例"。这就是说,在荀子看来,礼是法的总纲,也是各种律例赖以推衍的基本根据。这样,荀子便把礼和法沟通了起来,从而扩大了法的范围。贾谊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表现在,他明确地把制度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内容。他说: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瑰玮》)贾谊对"制度"的这种强调,固然是为了实行其"别贵贱"的礼治的需要,但是从制度所具有的强制作用来看,岂不又是一种法治吗?所以贾谊接着说:"擅退则让,上悟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好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同上)按制度办事就是守礼,破坏了制度就是违法。贾谊通过制度这个环节,使礼治与法治二者沟通了起来。因此,我们既可以说他发展了礼治思想,使之蕴含了法制的内容,也可以说他扩大了法的范围,使之兼容了礼的制度节文,并使之法律化。
必须指出,荀子虽然扩大了法的范围,但由于他强调"君子者,法之原也",因而主张"有治人无治法",这样实际上就贬低了法的重要性,并且这一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十分长远。贾谊与荀子不同,他十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贾谊虽然没有明确地论述过法的产生根源,但他关于"治法"高于"治人"的思想却是十分明确的。在《制不定》中,他曾以黄帝为例,说明如果缺乏制度,将会带来什么后果:黄帝与炎帝是亲兄弟,各人占有天下之一半。黄帝要实行其号令,炎帝就是不听,结果双方"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贾谊认为,这件事说明"大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就是说,如果缺乏明确有效的制度,就是象黄帝这样的圣君,他也是无法对付叛乱的。相反,"地制一定,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五美》)这表明,贾谊认为制度建设对政权的巩固和安定具有决定意义。贾谊重视制度的作用,并不否认人的作用。但他在重人的作用时,并不是象荀子那样把人说成是法制的源泉,而是强调人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去积极地创设各种制度。这一点,他在上汉文帝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中说得十分明白: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汉书·贾谊传》)
显然,贾谊对制度与人,即法与人的关系的看法比荀子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可是贾谊关于制度重要性的思想却长期被淹没了,今天我们重温这些思想,仍然深感有现实意义。
其二,是将法家的"势"论引人礼之中,从而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
关于这一点,于传波在《试论贾谊的思想体系》一文中已经谈到。他说:"贾谊对礼的最大创造是他提出了一个置'势'人礼的'礼之数'。对于君臣之间的礼,他是这样讲的:'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新书·礼》)这个'礼之数'是他首创的,传统的礼中没有大小、强弱。强弱是势,大小是数;而数只是势的度量。大小、强弱都是势的内容,这就是置'势'人礼。是为了和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相应而提出的理论概念。目的是强调天子国大势强,诸侯国小势弱,这样才能防止诸侯造反。"(《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 年第3 期)我觉得于文的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对于文的观点,我认为需要补充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一、于文指出:"本来在传统的礼中是没有势的地位的。恰恰相反,是以贬势去衬托德和仁的。"并且举出孟子讲的"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孟子·尽心上》)加以证明。我觉得不仅孔孟是贬势的,即使是主张礼法结合的荀子也是不重视势的。关于这一点,侯外庐同志早已指出:"荀子也常言木,但不很重'势'。故他批判'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却忽略了他的论'势'。"(《中国思想通史》第1 卷第580 页)荀子曾经说过:"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 子·君道》)荀子的这种重人轻势的观点,是从其"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直接引伸出来的。贾谊继承了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思想,但摒弃了他的"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他的重势的思想与他重制度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于文援引林甘泉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3 期《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文中的一个论点,即认为贾谊的"强干弱枝"的势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吕氏春秋·慎势》。我觉得如果仅就"强干弱枝"这个方面来说,《吕氏春秋·慎势》的观点对贾谊确有直接影响。但我认为,贾谊关于势的内容包括的面很广(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贾谊的哲学思想时还要详述),既讲"人为之势",也讲"自然之势"。从这方面看。他可能是更多地批判继承了先秦法家的势论。我们知道,在早期法家中,慎子是以重势而著称的。他说:"毛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则见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元緆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走背跋踚穷谷野走十里,药也。走背辞药则足废。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由此可见,慎子所讲之"势",乃是欲达到主观愿望所要惜助的客观条件及其规律。韩非认为,慎子讲的这种客观条件乃"自然之势":"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韩非子·难势》)在韩非看来,"自然之势"过于强调了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具有机械决定论的意味,所以他主张人所设之势。那么他所说的"人之所设"的势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没有明确的界说,但从他说的"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来看,他是将法与势联系起来,以为只要通过人主设"法"来加强自己的"权势",就是"人之所设"之势。所以他说:"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同上《心度》)这说明,只要通过法这个"本"使其权重,就是加强"势";韩非对这种"人之所设"之势的重视,反映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但这种片面地强调"人之所设",也容易造成一种流弊,就是不顾客观条件和形势,一味地强调严刑峻法,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例如秦二世时,赵高就是利用二世希望具有"振威天下"之势的心理,怂恿他戮同室,诛大臣,造成"宗室振恐"、"黔首振恐"(《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局面,结果众叛亲离,身首异处。贾谊正是总结了这些教训,所以他在谈势时,既讲人为之势,又讲自然之势,就是在强调人为之势时。他认为也必须按客观规律(理)办事。所以他谈势时,往往是和理字相连。如说"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阶级》)因此,他认为"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礼》),才既合"理",也才能形成一定的"势"。尊卑、大小、强弱各有恰当的地位,又各各遵守自己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之数",也就是说,才符合理势统一的要求。反之,如果颠倒了这种关系,那就是"失理",失理必然造成混乱。所以他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谄而相饬,设輹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时变》)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