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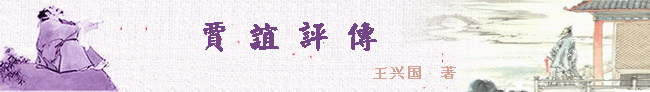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二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一)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制
面对同姓诸侯王的骄恣和叛乱,贾谊十分忧虑,认为是值得"痛哭"的一个危险事态。他把中央政权比作"本",把诸侯王比作"末",认为让诸侯王的权势任意扩大,是一种"轻本而重未"的作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尾大不掉,未大必折"的局面。贾谊在当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分封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秦王朝的批评中看出。他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属远》)在《过秦中》一文中,贾谊又把秦二世不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这种分析,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来看,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却有其认识上的原因,这就是如王夫之所说:"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读通鉴论》卷二)贾谊虽然不反对分封制,但他却从汉初几十年分封制的实践中看出,如果不从制度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诸侯王加以限制;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更加膨胀,"本细末大"的状况也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他沉痛地向文帝进谏:天下之势方病大痉。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搞,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铜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治安策》)
当然,也许贾谊把当时的形势说得过于严重了一点,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袄,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此时而乃欲为治安,虽尧、舜不能。臣故曰,时且过矣,上弗早图,疑且岁间(俞樾《诸子平议》谓"间"当"闻")所不欲焉。"(《宗首》)也就是说,贾谊之所以反复强调本细末大的危险性,是希望能够引起最高统治者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的重视,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呢?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所谓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已作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然而礼制是属于外在的。表面的东西,它们虽然可以从形式上对诸侯王予以限制,但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制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侯王在礼制上的潜越,正好反映了他们经济实力的强大。而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在封建社会又是与诸侯王国土面积的辽阔分不开的。对此,贾谊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所以,他除了强调定礼制之外,更突出地强调"定地制"。贾谊从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覆灭,得出一条经验教训:"大抵强者先反。"他说:"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囊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欲诸侯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葅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强》)贾谊这里讲的"强"固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但土地和人口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战功又不如韩信、彭越、黥布等人显赫,所以不敢怀异心。当然,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谋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诸侯王本人的野心,也有中央政府出于加强集权的原因,而采取的某些阴谋手段。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一些诸侯王国的强大,导致本细末粗,尾大不掉的局面,的确对中央政府形成一种巨大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以说是抓住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一个关键。
(二)定地制的思想实质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实施方案,就是"定地制"。他说: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五美》)对于贾谊这种"割地定制"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它贯穿着贾谊一贯主张的仁政思想。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打的是"仁"、"义"的旗号: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土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启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地制一定,卧赤子在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五美》)
可是,贾谊的这些仁、义说教,一时还难以改变汉文帝的主意。因为当时文帝正信奉黄老之学,崇尚无为,加之人承帝统不久,基础不固,不敢过多地去触犯那些诸侯王。对此,贾谊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在《藩伤》一文中,贾谊批评这种"无为"实际上是"善低莫邪而予邪子"的自杀政策,"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他说: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莫邪而予邪子?自祸必矣。爱之故使饱梁肉之味,玩金石之声,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活大臣,全爱子,孰精于此。(《藩伤》)
这里,贾谊批评的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贾谊不仅主张"有为",即坚定不移地进行"众建",而且建议文帝抓紧时机,及早进行"众建"。
他甚至批评文帝优柔寡断是"不仁":诸侯势足以专制,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专制,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微之怨,犹之无伤也。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偕冠,陛下且见之矣。岂不苦哉!力当能为而不为,畜乱宿祸,高拱而不忧,其纷也宜也,甚可谓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苟身常无意,但为祸未在所形也。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可谓仁乎!(《权重》)
贾谊的批评,都落脚到一个"仁"字之上。因为所谓"力当能为而不为",就是说主观上既有能力、客观上也有必要去干的事,却偏偏不去做,那岂不是"畜乱宿祸"、"故成六国之祸"吗?这种作法当然也是"不仁"的一种表现。
还必须指出,贾谊之所以把"割地定制"作为施"仁政"的一种方式,是与他继承了孟子"正经界"的思想分不开的。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盂子·滕文公上》)本来,孟子讲的"正经界"是指土地制度,即认为只有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才能制止暴君污吏在经济上的侵夺和扩张。可是贾谊却将孟子的思想推而广之,把"割地定制"也称为"正经界"。他说:"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至无状也。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一通》)孟子之所以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是因为他看到了物质利益上的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孟子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主张用"井田制"的措施来达到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社会理想,却是违背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贾谊将孟子的这一思想用之于阻止汉代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一方面既具有儒家"仁政"的美名,另一方面又达到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实际目的。由于他的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尽管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某些曲折,但最后还是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必须指出,贾谊"割地定制"的主张外表虽然打的是儒家"仁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实行的却包含着不少法家的思想。关于这一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早已指出。他说:谊之言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字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逾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侯王之地而众建之,富贵骄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此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李斯?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惨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灯余一焰,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言何容易哉!(《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在批评贾谊时的儒家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他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全盘加以否定,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王夫之指出,贾谊这一主张是"阳予阴夺之术",因而他和法家一样是主张"相縻以术"的,这一点却是道出了实情。因为尽管贾谊在《五美》一文中说,割地定制之后,"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但是这种"割地"的结果,必然是使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而中央政府的力量不断壮大。谓之"阳予阴夺",不亦宜乎!然而,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种"阳予阴夺"并不坏,它的确起到了巩固中央政权的作用。王夫之对贾谊的批评,更多地是一种道德评价。如果从当时现实情况的需要出发,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贾谊的这种"术"的。
贾谊"割地定制"主张中包含的法家思想,除了王夫之所指出的"阳予阴夺之术"以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法"。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中的"制"实际上是一种法制。就是说,要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法制上加以明确。在《制不定》一文中,贾谊把诸侯王比作"髋髀之所",把法制比作"斤斧",说:"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众理解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己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这里,贾谊把仁义与法制都看作人主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既反映了他的礼法结合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为了对付那些为非作歹的诸侯王,更着重地是要实施法制。
其二,是"势"。法、术、势相结合,这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特点。贾谊也吸收了这一思想特点。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割地定制",就是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势。贾谊说:"树国必审相疑之势"(《藩伤》)。就是说,天子封国建藩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让诸侯国的势力无限膨胀,以至达到"上下相疑"(同上)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葅醢耳,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天下无可以侥幸之权,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且知其安。"(《五美》)可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本细末大",即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而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因而造成一种"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的本末倒置的状况。对此,贾谊十分忧虑。所以他用楚灵王的教训警告汉文帝:"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日:'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于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尹申亥之井。为计若此,岂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细末大,弛必至心。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大都》)这个故事说明,楚灵王只顾眼前利益却不顾长远的危害,结果导致"尾大不掉",臣主之间形成一种相疑之势,最后使自己遭至灭身之祸。正是鉴于这种教训,贾谊强调要审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做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起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日: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干里也。(《审微》)
所谓"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这句话具有唯物辩证的因素,因为它肯定了人性是可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如此,人们便可以经过人为的努力,制止那种不利于自己的客观趋势的发展。这样做既可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势),又削弱了对手的地位;同时还可以使最高统治者获得"仁"的美名:由于他削弱了诸侯王们的势,制止了他们的人性向"窥且望"的方向发展,因而能"活大臣,全爱子"。这就是贾谊"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论基础。
(三)定地制主张的自相矛盾处
最后,必须指出,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并不彻底,也就是说,其主张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这种矛盾就表现在:一方面他认为"疏必危,亲必乱"(《亲疏危乱》),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依靠亲者;一方面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另一方面又主张给亲子"益壤"。
在《亲疏危乱》一文中,贾谊对汉文帝说,汉初刘邦封异姓诸侯王,"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这种"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的局面,如果换成汉文帝,"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当然,文帝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异姓诸侯王与他的关系疏远,自然难以控制。对此,贾谊进一步指出,那么"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各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能为治乎?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贾谊这里举的一些同姓王均是汉文帝刘恒的亲属。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的长子,文帝的异母兄,卒于文帝元年(前179)。楚元王刘交,高帝弟,文帝的叔父,卒于文帝元年。赵王刘如意,高帝中子,文帝异母兄,惠帝元年(前194)被吕后酖死。幽王刘友原王淮阳,赵王如意死后徙赵,高帝子,文帝弟。吕后七年(前181)被幽死。共王刘灰,高帝子,文帝弟,原王梁,吕后七年赵王刘友死后,徙赵,同年自杀。燕灵王刘建,高帝子,文帝弟,卒于吕后七年。淮南厉王刘长,高帝子,文帝弟。以上七王,在文帝即位前死了四人,文帝即位当年又死了两人,文帝初年健在者只剩下一个淮南王刘长。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亲弟弟,居然在文帝六年(前174)谋反,废王之后,在谪蜀道中绝食而死。所以贾谊有理由说: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虽离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听!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乃启其口,匕首已陷于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诸侯,此所谓亲也者。(《亲疏危乱》)
贾谊所揭露的诸侯王的这些罪状,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当淮南王叛乱被召至长安之后,丞相张苍,典客冯敬等就曾上书文帝,历数淮南王的罪状,其中有"淮南王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等等。可见,贾谊说那些同姓诸侯王"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大子自为者",的确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然而,贾谊的这个认识并没有贯彻始终。这就表现在他一方面说"疏必危,亲必乱",可是另一方面又建议文帝依靠自己的儿子,扩大其封地。文帝有四个儿子,文帝二年,立刘启为太子,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刘武为代王。文帝四年更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这三个诸侯王国,紧挨着中央政府所直辖的郡,将它们与其他较疏远的同姓诸侯王国隔离开来,所以贾谊说:"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以代、淮阳耳。"(《益壤》)但是,"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禁御哉?"而"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国耳。今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国命子,适足以饵大国,岂可谓工哉?"(同上)贾谊讲的这些情况与当时这些诸侯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因为淮阳的确比吴、楚、齐、燕这些王国的面积为小,而代位于最北边,与匈奴接壤,自顾不暇。当时,困淮南王刘长谋反,其国正空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但其间隔着淮阳和长沙两王国。所以贾谊主张文帝将淮南之地分给几个亲子诸侯王,然后将他们的领地适当加以调整。他说: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苦之甚矣,??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陛下岂如早便其势,且令他人守郡,岂如今子。臣之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梁即有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无后患;代可徙而都睢阳,梁起新郑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今所恃者,代、淮阳二国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计,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则陛下高枕而卧,终无山东之忧矣。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益壤》)贾谊这种扩大文帝亲子诸侯国地盘的作法,对巩固文帝的政治地位肯定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但与他的"疏必危,亲必乱"、"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一贯主张却是明显相背驰的。对此,贾谊自己可能也有所意识,所以他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为不可,剽去不义诸侯,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同上)显然,贾谊这种思想是对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观点的发挥。所谓"义"者,宜也。
在盂子和贾谊看来,只要符合形势的需要,观点自相矛盾也是可以的,仍不妨其为"大人"。可是,对贾谊的这种自相矛盾之说,王夫之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贾谊畏诸侯之祸,议益粱与淮阳二国之封,亘江、河之界,以制东方,何其言之自相背戾也!谊曰:"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今高拱以成六国之势。"则其师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掩矣。乃欲增益梁、淮阳而使横亘于江、河之间。今日之梁、淮阳,即他日之吴、楚也。吴、楚制而梁、淮阳益骄,而使横亘于江、河之间以塞汉东乡之户,孰能御之哉?己之昆弟,则亲之、信之;父之昆弟,则疑之、制之;逆于天理者,其报必速。吾之子孙,能弗以梁、淮阳为蜂虿而雠之乎???封建之在汉初,灯炬之光欲灭,而姑一耀其焰。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谊操之已蹙,而所为谋者,抑不出封建之残局,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由此言之,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忧贻子孙也。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而谊何为焉!(《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说,贾谊的主张"不出封建之残局",是符合事实的。如同我们前面所说,贾谊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分封制。王夫之指出贾谊之说"自相背戾",也是有道理的,这种扩大亲子封地的做法,只不过是"以缓目前",而"以忧贻子孙"。由此可见,贾谊"益壤"的主张,尽管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毕竟是一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主张。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