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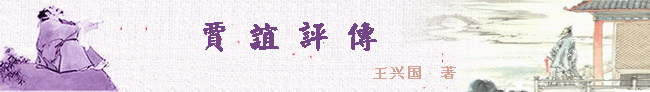
|
三、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
(一)传统的夷夏之辨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的儒家的华夷之辨。这种观点认为,中原民族(古代称为"诸夏"或"华夏")在文化上比四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古代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有时混称"夷狄"或"戎狄")要先进。这种先进,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原民族尊重传统的礼制,而少数民族则往往没有这些礼制。所以孔子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说,当时的"夷狄"虽然有君主之设,但却不遵守礼法,所以君臣上下的名分有也等于无;而"诸夏"则不然,由于它注重礼制,所以即使无君,等级秩序也照样存在。这种以是否有礼制来区分华、夷的做法。在汉代依然存在。我们且看当时汉使与中行说辩论的问题。如"匈奴俗贱老","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网庭之礼"(《史记·匈奴列传》)等,便都是属于礼的范畴。
既然中原民族的文化水准高于四境的少数民族,那么从逻辑上讲就应该是先进领导落后,而不是相反。因此,当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四境的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的情况时。那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贾谊认为,这时天子就要挺身而出,采取怀柔措施去争回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他针对"天子下临,人民悹之"的说法,反驳道:"苟或非天子民,尚岂天子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慉渠颇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则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也,岂下临人之民哉?"(《匈奴》)显然,贾谊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点,又反映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因此贾谊对西汉前期强大的匈奴屡侵边境,迫使堂堂的汉朝皇帝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史记·匈奴列传》)的状况十分不满。所以他在给文帝上书时,激愤地说:天下之势方倒县,窃愿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蛮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县之势也。天下倒县,莫之能解,扰为国有人乎?非特倒县而已也,又类,且病痒。夫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数千里,粮食馈饷至难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于焉,望信威广德难。臣故曰"一方病矣"(《解县》)
这里,贾谊的首足、上下之分,显然和儒家传统的礼制观点分不开。但是,他所说的"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已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介胄而睡",却是对当时官民、将士为抵抗匈奴入侵而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体现了贾谊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
所以,贾谊对汉文帝对匈奴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十分不满。他说: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增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戒人诸侯也,势既卑辱,而祸且不息,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势卑》)
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车舟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今称号甚美,而实不出长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边长不宁,中长而静,譬如伏虎,见便必动,将何时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窃为陛下不足。(《威不信》)贾谊批评文帝的这些话不可谓不尖刻,然而文帝却为什么不为所动呢?这里,内部诸侯王强大,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前往代地,准备抗击匈奴,便趁机谋反,发兵欲袭荥阳。这时,文帝只好"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史记·孝文本纪》)。除了诸侯牵制之外,汉初社会国力不够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汉高帝平城之困,给汉初几个皇帝留下了比较深的心理压力,因此一谈匈奴,往往为之变色。所以自高帝使刘(娄)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始,中经惠帝、吕后,至文帝,均只好按高帝对匈奴的这一既定方针办。当然,文帝一朝也并不是没有以武力抗击过匈奴。例如,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入侵北地,居河南为寇。文帝就曾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颖阴侯灌婴击匈奴。贾谊逝世之后,文帝也曾数次发兵击退入侵边境的匈奴。但是这些武力行动都是属于防御性质的战争,基于国力所限,当时只是将匈奴驱出约定的界限之外,而无力长驱直入,致使匈奴远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贾谊在上文帝书中所建对匈奴之策,也绝无用武力驱除匈奴之语。相反,而是强调"王者战义,帝者战德"(《匈奴》)。这一点,固然反映了贾谊重礼治的一贯思想,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岂不是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国力还不足以用武力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吗?贾谊说过:"匈奴不敬,辞言不顺,负其众庶,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匈奴》),这里所谓"负其众庶",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匈奴的实力比较强大。
(二)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
既然武力驱逐没有力量,和亲又过于屈辱,那么就只有用儒家的方法,即"战德"了。所以贾谊说: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于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然不承帝意?(《匈奴》)
所谓"以厚德怀服四夷",当然是儒家的传统主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就是说,只要实施德治,那么老百姓和诸侯、属国就会象众星拱北斗一样,团结在你的周围。《礼记·中庸》把"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称为"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治理国家的九种方法之一。贾谊的"战德",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然而贾谊对付匈奴的方法,也不纯粹是儒家的,其中也包括某些法家的"术"。例如他说:陛下肯幸听臣之计,请陛下举中国之祸而从之匈奴,中国乘其岁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残亡,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答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杀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成惮大信,德义广远,据天下而必固,称高号诚所宜,俯视中国,远望四夷,莫不如志矣,(《解县》)
所谓"举中国之祸而从之匈奴",就有悖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条。这样做,也许还是为了实现贾谊自己所说的"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益壤》)的一贯主张吧。不过,这样就必然会要使用法家的种种权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更加清楚地看出。"饵"者,钓饵也。放长线,钓大鱼,就是一种权木。朱熹的弟子昌父就曾看出这一实质,他说:"'五饵'之说,恐非仁人之用心。"对此,朱熹回答:"固是。"(《朱子语类》卷一三五)
所谓"三表",即"以事势谕天子"之信、爱、好。贾谊说: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己诺,若日出之的灼。故间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图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枝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刚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匈奴》)
贾谊讲的"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所谓"爱",是爱"胡人"的面目外貌;而"好",则是喜欢其技艺。他说:"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也",也就是"仁"的表现。而在信、爱、好三者之中,"信为大操",是帝者守信义的一种表现。可见,贯穿"三表"的基本思想是儒家的"战德"。不过,贾谊既然把匈奴比作"猛兽",他对汉文帝说:"今不獦猛兽而獦田彘,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所獦得毋小,所博得毋不急乎?"(《势卑》)加之儒家历来又视戎狄为缺少礼义的民族,因此他所说的"爱"和"好"是否为真心,就很值得怀疑了。既然不能做到真心,其"信"也就难免不使人怀疑其真诚。因此,贾谊的谕爱、谕好、谕信的本身,就使人感到带有权术性质。
贾谊所说的"五饵"为:其一是以锦绣华饰坏其目,这就是所谓"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骖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其二是以美胾炙坏其口,即所谓"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胾炙肉,具醯醢。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令来者时时得4此而飨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悇憛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其三是以音乐舞蹈坏其目,即所谓"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俱)乐,吹萧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待),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惟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其四是以财富厚赏坏其腹,即所谓"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囷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囷京之畜,皆过其故王,虑出其单于或(域),时时赐此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腹。"其五是厚待胡人贵族及其子弟,以坏其心,即所谓"于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后得入官。夫胡大人难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上即飨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婴儿得近侍侧,胡贵人更进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钱(醆),时人偶之。为间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拊胡婴儿,捣遒之,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闲且自为赣之。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缓,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韩非子认为"术"有七种,其二就是"信赏尽能"。他说:"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又说:"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年储说上》)这就是说,人臣象兽鹿吃荐草一样,喜欢厚赏。贾谊的"五饵"都是属于厚赏的内容,他希望通过对匈奴民众和权贵的厚赏,达到"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又引其心、安得不来"的目的。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他说:故三表已谕,五饵既明,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彼其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摲)之。此谓势然。其贵人之见单于,犹迕虎狼也;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其众之见将吏,犹噩迕仇雠也;南乡而欲走汉,犹水流下也。将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此谓战德。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贾谊讲的"战德"虽为儒家的词句,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乃是法家的实质。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他说:"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千石大县,以天下之大而困于一县之小,甚窃为执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试理此?夫胡人于古小诸侯之所铚权(获)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计,半岁之内,休屠饭失其口矣;少假之间,休屠系颈以草,膝行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唯上财幸。而后复罢属国之官,臣赐归伏田庐,不复垮末廷,则忠臣之志快矣。"(《势卑》)透过贾谊的这些言论,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灼然可见。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