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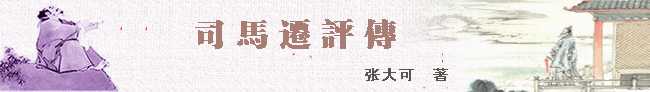
|
四、答壶遂问述作史义例
史学是什么?在司马迁时代,整个思想界还是一片朦胧的认识,司马迁本人也没有直接提出"史学"的概念。但是,在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头脑中,早已孕育成熟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且父子两代早已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司马谈已经为此耗尽了一生。当大初历颁布之时,汉兴已历百年,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封禅改历,举国欢庆。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在激动之中深感修史责任的重大,岁月磋跎,一种紧迫感也在催促自己要奋力写作。这时他想到了父亲的遗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
先人,即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宣扬清明盛世的教化,验证、核实《易经》所阐述的幽明变化之理,效法《春秋》述史,依据《诗》《书》《礼》《乐》来衡量一切。司马谈发凡起例,功业未就而与世长辞。如今这副担子落在自己的肩上,一定要实现父亲的遗愿而不敢推辞。司马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同制历的好友壶遂。于是壶遂向司马迁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①壶遂之间实质是委惋地问司马迁为何要作史,也可以说是把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
司马迁答壶遂问,展开了长篇的大论。他认为史学应具有"刺讥"与"颂扬"两个方面的作用。"刺讥"的作用是为后人立法,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干预。"颂扬"的作用是描绘理想,展示对开明政治的向往。从司马迁回答的内容来看,着重引董仲舒之言,说明青年时期的司马迁是深受公羊学的影响。壶遂两次提问,司马迁两次回答,都作了恢宏议论,详载于《太史公自序》中。两次问对,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均是围绕史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下面分层论述。
1、《史记》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壶遂问,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作了三个层次的回答。首先,他认为《春秋》明世教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迁借董仲舒之言立论,以"余闻之董生曰"起论,既表现了自己的谦逊,更表明自己所发的议论是言之有据。董仲舒认为,孔子之时,周道衰微,天下混乱,而孔子四处碰壁,他知道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于是退而著述《春秋》,通过对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时事的褒贬来表明看法,作为天下后世的是非标准。司马迁在转述董仲舒的话中又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孔子自己说过,与其空言论道,还不如因事见义更为显明,所以孔子借史事以论治国之道,通达周王之事。接着,司马迁直抒己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这段话中,"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两句是关节。上,指国家① 顾颉刚云:"获麟,《春秋》之所终也,帝尧,《尚书》之所始也。谈既欲继孔子而述作,故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见《司马谈作史》,收入《史林杂识初编》。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执政者,《春秋》阐明夏、商、周三王之道以作借鉴;下,指广大臣民,《春秋》分辨人们行事的伦理纲纪以供遵循。说得直率些,这两句话就是说《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②。具体内容,司马迁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就是要求史学提供历史的范例,判别嫌疑,辨明是非,决断疑惑,用以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明确前进的方向。第二,"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要求史学鲜明地赞美善良,贬抑丑恶,颂扬贤人,谴责坏人,用以教育人们扬善抑恶,敢于与黑暗抗争,争取光明。第三,"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就是要求史学保存历史文化传统,载述已灭之国、已绝世系的史实,从中总结兴亡之理。以上一切,司马迁认为都是治国的大道理。这是第一层。
其次,司马迁认为《六经》皆为治国之书。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这段话不用解说,转述成今语,意义十分显明。司马迁说,《易》这部书,是专门讲说天地四时与阴阳五行的,其作用是阐明自然物理的变化;《礼》这部书,是治理人们的纲常,其作用是节制人欲,指导人们的行动;《书》这部书,是记载先王的事业,其作用是指导政事;《诗》这部书,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其作用是表现风俗人情;《乐》这部书,是研究声音协调,快乐怎样兴起,其作用是发扬和气。《春秋》这部书,辨别是非,其作用是引导人们遵守道义。《六经》从不同的角度教化人民,陶冶性情,达到治国的目的。于是司马迁作了如下的结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义。
这段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中借孔子之口更鲜明地表达出来。其言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即《六经》。凡《六经》之学都是教化人们,都是为治国治世服务的。司马迁言此,表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史记》,即《太史公书》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它是比肩《六经》的思想著作,是统括天人关系的文化总和,尤其是效《春秋》宣扬道义,使人明辨是非。这是第二层。
再次,《春秋》拨乱反正,是礼义之大宗。这一层是司马迁答壶遂问的重点,高度评价《春秋》的治政作用,文长不具引,撮述大旨于后。
司马迁说,治理乱世,使社会走上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他认为《春秋》这部书,虽然只有几万字,事例却有好几千,万事万物的分散或聚合的道理,都包括在《春秋》里面了。《春秋》书里记载着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例,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有他的国家,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它的原因,都是由于失掉了礼义这个根本,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认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的人,只要熟读《春秋》,懂得了君、臣、父、子这四行的道德,就可防患于未然,使社会一切和谐;否则就要遭到各种不同的祸害。于是,司马迁得出结论:② 司马迁与壶遂的问答载于《史记》卷一百二十《太史公自序》,以下不再注。"《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很明显,司马迁把史学的教育宣传和改造人的作用,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春秋》不是一部简单记载历史事件的流水帐,而是一部对全社会各色人都离不开的政治道德教科书,是纲纪人伦的哲学书。每一个人都需要它,就如同需要布帛五谷一样,简直不可须臾离开了。这是第三层。
以上三层,层层递进,充分说明了《春秋》是孔子修成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寄托,是治世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些看法来自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①。在西汉,"春秋公羊学"成为官方的最高哲学著作,指导统治的理论基础,自然引起司马迁极大的重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评价孔子修《春秋》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一生功罪系于《春秋》,这也是公羊家的观点,司马迁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过是借孔子修《春秋》以明自己的述史之志,也就是司马迁一生功罪也系于此了。很明显,司马迁是借题发挥以阐述《史记》的大旨。《春秋》被宋人讥为"断烂朝报",价值没有这么高,而《史记》通过对古今人物史事的全面褒贬,惩恶劝善,恰然是这样。
2.《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述史,颂扬大汉威德。
壶遂,西汉著名的天文学家,官至詹事,职掌宫内皇后、太子事务,秩二千石。汉武帝打算用壶遂为丞相,会病卒,司马迁深深惋惜,称他是"深中隐厚""内廉行修"的君子。太初元年时,壶遂尚为中大夫,为待从皇帝左右的谏官,秩千石,相当于古制上大夫,所以司马迁在记述中尊称为上大夫。壶遂听了司马迁关于史学"刺讥"的作用后,表示了至交长者的关切,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提问。壶遂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的意思是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孔子才作《春秋》拨乱反正,留下议论来裁断礼义,当作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得以尽职,万事俱备,都各得其所,先生要论著的,想要阐明些什么呢?实际上壶遂是委婉地提出警告,效法《春秋》著书,岂不是把今天的太平盛世当作乱世了吗?说明白点,述史刺讥,不能不触犯时忌。司马迁觉得壶遂的警告很有道理,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临终遗言关于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内容,认识到史学不只是"刺讥",起礼义的法制作用;而且史学还有"颂扬"的意义,宣扬某种理想境界,净化人们的思想。《春秋》采善贬恶,推尊三代,以周室为榜样,不就是要树立一种理想的境界么!于是司马迁回答说: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里"唯唯,否否,不然"的应对,是司马迁对当时激荡情怀的描写和①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修《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又在《儒林列传》中说,孔子追修经术,"为天下制义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又说"故因吏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这些话头,明确指出孔子在道义上、纲常伦理上,为后王、后世立礼义之大法,供人遵循。回味。直译语意为,"是是,不不,不是这样的",表达的意思是:"啊啊,你的话很对,史学并不完全是刺讥。"司马迁语噎而口吃的神态跃然纸上,这种激动情怀表示了对壶遂关切、警告的感谢,说明这场讨论很有意义,司马迁深化了对史学"颂扬"意义的认识,他在转述了父亲的话之后,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司马迁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译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在这段话里,把颂扬汉家威德的主题说得至为明白而中肯。客观上,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内政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观上,肩负先人遗言的重托,且又身为史官,不能不载述当朝的圣明之德。"余尝掌其官",尝,通常,为现任,或任职已久之意。"余所谓述故事"云云,司马迁表示了谨慎和谦虚,说明自己的写作只是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不敢比攀《春秋》创作,以当一王之法。实际是语意双关,表明自己效法孔子"述而不作",一丝不苟实录史事。字面意义,"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而内里追步孔子,效法《春秋》的感情,更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综上所述,司马迁答壶遂问,是他在太初元年确定新的《史记》断限之际进行的一次理论探讨。实质是具体地阐明了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本始主题,即效《春秋》述史,采善贬恶,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的原则,并以人物为中心来表现,同时颂扬大汉威德。这里,司马迁还没有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因为,司马迁的异端思想那是受祸以后的事。也就是说,司马迁答壶遂问,阐述的是以《春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思想,凝练成一句话就是"惩恶劝善"。惩恶即是刺讥,劝善即是颂扬。史学的这两个功能以后者为主,所以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主要内容。它的进步性在什么地方呢?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有过如下评论: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于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①。刘知几肯定了"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一个优秀传统。司马迁推崇《春秋》,也是肯定这一个传统。所谓《春秋》的褒贬笔法,就是为了突现惩恶劝善。所谓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亦是为了惩恶劝善。固然这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秩序,但贬斥乱臣贼子,褒奖圣君贤相,也是古代人民的愿望。一个正直的史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录,爱憎分明,也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献出生命。
① 参见本书前第三章第二节《受学于董仲舒》有关内容。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