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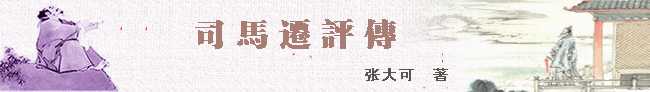
|
五、受李陵之祸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四十八岁。这是《太初历》颁布后的第七年,他埋头撰述《史记》的工作进入了高潮,正当"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了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这场灾祸使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了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因此,对李陵之祸的前因后果,以及司马迁受祸后的心态,都需要作全面深入的探讨,才能说明司马迁立场、思想的转变,以及怎样发愤著书。
1.受祸始末。
司马迁受祸始末,在《汉书·李陵传》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①,都有着详细的载述。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建章监,骑射技术有乃祖李广之风,谦虚下士,甚得战士心。天汉二年五月汉武帝下达了出击匈奴的动员令。秋九月,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为策应偏师,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约在今蒙古高原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吸引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李陵的担子很重,汉武帝派老将路博德率领骑兵一万为他的后援。李陵长驱直入,到达目的地后派陈步乐回朝廷报告。汉武帝十分高兴,朝中请大臣无不举杯祝贺。正在这时,孤军深入的李陵却遭到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重兵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集倾国之力穷追李陵不舍。李陵且战且退,经过了十几天的激战,汉兵歼敌一万多,但终因寡不敌众,粮尽矢绝,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全军覆没,投降了匈奴。老将路博德耻力李陵后援,汉武帝让他别出西河,使得李陵孤军奋战而无救,这是汉武帝调度失计演出的悲剧。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一个庸才,因为他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所以汉武帝把重兵交给他。贰师本是大宛的都城。太初年间,李广利兵征大宛,拜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李广利凭恃皇亲国戚专宠,纯粹是一个庸将。天汉二年出征匈奴,汉武帝想让他立功增封,但这个庸将率领的三万骑兵未遇匈奴主力,却打得大败亏输,损兵折将而返。汉武帝刚喝了群臣的庆功酒,突闻两路兵败,大大扫了帝王之尊的颜面,因此食不甘味,听朝不怡。阿议逢迎之徒,猜中了汉武帝的心事,讳言贰师之败,全委过于李陵。同是一个李陵,打了胜仗,朝臣们"奉觞上寿";李陵败降,朝臣们落井下石而"媒蘖其短"。更有甚者,同是败军之将,李陵十恶不赦,贰师却若无其事。司马迁认为,这是不正常的风气,公道、良心、正义到哪里去了?他对李陵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对阿谀逢迎的朝臣们充满了愤慨。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说了他的看法。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国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①。
起初,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意见,他久久地沉思,领悟到上了老将路博德的当,没有派兵救援李陵,于是"遣使劳陵余军得脱者",还派因杆将① 《史通》卷八《人物》。
① 李陵事附《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中。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李陵。公孙敖在边境候望李陵一年多,没有建功,借捕获的俘虏之口谎报"李陵教单于兵以备汉",武帝大怒,族灭了李陵一家。实际教练匈奴兵的是另一个降将李绪,而不是李陵。李陵家被族,李陵成了可耻的叛徒,李氏一门蒙受恶名,司马迁受株连被判"诬罔"罪而蒙受腐刑。按汉律,"诬罔"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量刑是大辟死罪。《汉书·武帝纪》载,"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栾大是方士,他的神仙骗术被揭穿,以"诬罔"罪被杀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有两种办法免死。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汉书·武帝纪》载,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将军李广、张骞、公孙敖等人,都曾因种种原因触犯军法论死,赎为庶人。二是景帝时所颁法令:"死罪欲腐者许之。"①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有在死与腐刑二者之间作选择。不过以腐刑代死罪,并不由犯死刑者单方面的"欲"来决定,它还要执法者"许之"。《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兄张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食"。征和二年巫蛊案,犯死者成千上万,只有张贺一人幸免,以腐刑代死,因有张安世为言。张贺与司马迁是同时代人,受刑时间也相隔不久。西汉自景帝颁布以腐刑代死的律令以来,终汉武帝之世,士大夫犯死罪而改宫刑的记载,也只有司马迁与张贺两例。汉武帝欲置人于死地,既不可赎,也不可腐。如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汉军伏击匈奴。由于单于警觉,没有中伏。大行王恢奉命深入敌后拦击匈奴辎重,他见匈奴主力退回,自己所部三万人寡不敌众,当机立断撤退了汉兵。汉武帝认为王恢本为首谋,而不能主动出击,于是论罪下狱。尽管丞相田颛和王太后出面营救,汉武帝仍不赦免,王恢自杀狱中。由此看来,汉武帝尚没有置司马迁于死地的意思,所以才听其以腐刑代死。可是汉武帝却不彻底赦免司马迁,听其以腐刑代死,必欲折其心气而后快,显示绝对君权的威严,难怪司马迁要发出"明主不深晓"的怨言了。
腐刑,即宫刑,起源很早,传说夏商时代就有了。《汉书·刑法志》载,西周有"宫罪五百",说明宫刑律令已十分严密。颜师古注:"宫,淫刑也,男子割腐,妇人幽闭。"这说明宫刑原本是用来惩治淫刑的。犯淫行罪,卑鄙下流而为人所不齿。虽然成千上万的宫廷宦官,以及士大夫受宫刑并非淫行,但他们最羞辱而神秘的一体被割除,在形式上与犯淫行受宫刑是一样的。《报任安书》列举历代宦官,尽管为人主所亲近,但"刑余之人"却为士大夫所不齿,这就不难理解了。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为了保持名节,不要说受腐刑,公堂对簿都受不了,如李广、萧望之等人的自杀就是例证。司马迁断言,尽管人情都有"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的习性,但"激于义理者不然",即便是"臧获婢妾犹能引决",何况立言著述的堂堂太史令呢!司马迁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抉择之中,所受痛苦的熬煎,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沉痛思考和严酷抉择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提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如果人的一生,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圣人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① 这里是串述,原文见《报任安书》。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为孝道的最高准则,这是司马迁借父亲之口提出的新颖见解。这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立名为核心的荣辱观。《史记》未完成,名还未立,因此他的身躯和生命是属于《史记》的,也是属于父亲和自己的理想的,他不能去死而要坚强地活下来,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就这样,司马迁选取了以腐刑代死的抉择。
2.司马迁受祸合于法而不合于情,是一场冤案。
如何看待司马迁受刑,我们必须尊重事实立论,他的《报任安书》是最权威的事实依据,还有《汉书·李陵传》作佐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此时距司马迁受刑的天汉三年已六年,可以说是司马迁痛定思痛的回顾,完全是真实可信的。李陵降敌是出人意料的,司马迁和汉武帝都没有估计到。在李陵案前,司马迁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常从巡武帝,君臣之间,鱼水相得。尽管在政治上,司马迁的认识与汉武帝的行事有分歧,他作为一个实录史事的历史家,批评了汉武帝的"多欲"和"无限度"的外征内作,但本意是出于忠心,目的在于敲警钟,他又没有上陈政见来反对汉武帝,所以两人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再说汉武帝,他是一个刚毅志骄的雄主,哪能容得下阻他"鸿图"的人!汉武帝诛杀大臣如同草芥,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岂能挡他的"鸿图"?司马迁自己并没有认为汉武帝要借机惩治他,因此那种"长期政治分歧、矛盾积累的总爆发"的看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司马迁是否"坐举李陵",并犯有"诬罔罪"呢?《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但这只是卫宏的推论,因为《报任安书》和《汉书·李陵传》都无司马迁举李陵事。《报任安书》特别慎重交代了司马迁与李陵"趣舍异路",并无特殊关系,所以司马迁觉得冤枉。司马迁是怎样被定罪的呢?《报任安书》说: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汉书·李陵传》作了更为明晰的记载: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今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两书记载十分明确,司马迁之被定罪,不是"坐举李陵",而是"沮贰师","为陵游说",最后被阿顺上意、深文周纳的酷吏们定为"诬罔"罪的。司马迁只是"推言陵功",在言词上没有触及贰师,因此说他"沮贰师"法律上不成立,它只能是阿顺上意的朝臣们的叽叽喳喳。"气为陵游说",顺理成章,但在汉武帝未族灭李陵之时,亦不便给司马迁加罪。因此司马迁受祸是受族灭李陵家的株连,此时定为"诬罔"罪,可以说是"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了。荀悦《汉纪》正是这样记载的。荀悦说,司马迁上言陵功,"上以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如何评价司马迁受刑,弄清他的受刑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荀悦的说法是否有根据,尚需作一番考证。
李陵败降匈奴在天汉二年十月。司马迁受祸在天汉三年,《太史公自序》言之确凿:"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所谓七年,是指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因这几句话是上承太初元年"论次其文"而说的。汉武帝族灭李陵家,《资治通鉴》编年系于天汉四年正月汉兵大出击匈奴之后。其依据是《汉书·李陵传》,"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这是司马光推断失误。天汉二年十月到天汉四年正月,恰好一岁有余。其实天汉二年十月到天汉三年十二月已是一岁有余。再看,天汉四年正月大出征,兵分四路,计步骑二十一万。四路将领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因■将军公孙敖、游击将军韩说、强弩将军路博德。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步骑十二万为主力。如果这次出征是为迎接李陵而战,因主力是李广利,应当说是"上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深入匈奴迎陵",而不应记载为公孙敖。汉军在天汉四年一月天寒地冻之时大规模出征,合理的逻辑只能是汉武帝族灭李陵家这一政治事件的必然发展。按汉武帝的心理,应当是迎接李陵不成,怒而族其家,并大发兵击匈奴,必欲战败匈奴雪天汉二年之耻,并捉拿叛徒归案而后快,所以才给李广利以如此重兵。此役在天汉四年正月,正可反证族灭李陵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岁末决狱大辟亦是常法。很自然,司马迁被株连受腐刑亦当在天汉三年十二月。
司马迁同情李陵,鄙视李广利,他为了"塞睚眦之辞"而怒而愤而敢言,表现了一个正直史家的高尚情操,千古而后犹正气凛然。可以想见,司马迁推言陵功,语言必激切,语气带夸张,如"仰亿万之师"、"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举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等等,写《报任安书》时犹运于笔端。司马迁欲尽"拳拳之忠","以广主上之意",未免过于天真直率,带着浓厚的书呆子气。满朝文武委过李陵,是为贰师解脱,而司马迁偏偏渲染李陵苦战之功,既不顺从汉武帝之意,便是不从流俗,违拂众怒,所以论罪"诬上",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了。尤具讽刺意味的是,汉军迎陵不得,匈奴单于"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其家被族,司马迁的"诬罔"罪就足以成立了。
这一点,司马迁本人亦未作辩护。《报任安书》说:"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又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把李陵降敌"聩其家声"与自己受腐刑"重为乡党戮笑",相提并论,既是纪实,也是无以辞其责的苦闷写照。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陵的降敌作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说:"单于既得陵,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司马迁既明且哲,熟读《春秋》,而身不免于刑戮,从礼义上说,他亦未能尽守《春秋》之义,忠于主上而未能顺从主意。也就是说,按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义理,司马迁蒙受"诬罔"罪是"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司马迁推言陵功,说他杀敌过当,其功可以抵过,还是中肯的,汉武帝族灭其家更是残酷无情的。言事者说陵母妻子"无死丧色",更是莫须有的胡说八道。专制者欲加臣民以罪,何患无辞!但李陵兵败降敌,成了叛徒,这个案是不能翻的。司马迁为李陵辩降,这个短我们也不必讳言而曲为之开脱。
依上所述,司马迁受祸合于当时的法理,但不合人情,仍然是一场冤案。因为"诬罔"罪是以言论定罪,并无客观标准,有罪无罪完全在人主的喜怒之间。汉武帝时代有腹诽之法,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但在绝对君权时代却又是天经地义的。以言论定罪是专制主义的特征。按理,以言论定罪应以主观动机为准绳。而司马迁的劝谏,主要用意并不在替李陵辩降,而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讲了事实真象,希望汉武帝应公正地对待将士的成败;主观动机,则是宽武帝之心,尽"拳拳之忠"。可是事情却走到了善良用心的反面,司马迁的言词刺痛了汉武帝的心病,这位"圣明之君"一下翻过脸来,全不看他多年侍从尽职的分上,"卒从吏议",使司马迁遭受腐刑的奇耻大辱。所以,从情理上说,这又是一场冤案。尤其是面对李陵降敌这个事实,司马迁有口难辩,所以他极其沉痛地说:"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又说:"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司马迁身受刑辱,心蒙冤抑,而口却不能道,世人不理解,他那正直而纯结的心灵陷入了绝境的痛苦之中,那该是多么的屈辱啊!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