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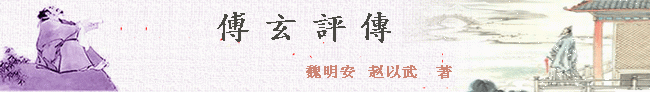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三、关于圣人无情有情的讨论
玄学家认为,圣人比之凡人,才性是统一的;才为"兼材",能"统领众材",性为"中庸",是"兼德而至"的。如果说"才"是外现可见的话,那么"性"又如何把握呢?"性"的外现只能通过"情"去观察。接下来的问题是:圣人"中庸"之性表现出的情是怎样的呢?正始中,玄学领袖何晏宣扬"圣人无情"。《三国志·钟会传》裴注曰:"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在《论语集解》里,何晏又补充道:"凡人任情,喜怒违理。"可见,圣人无情,凡人任情,是有区别的。
何晏的"圣人无情"说,详细内容没有进一步披露,直接的线索不可寻,"其论甚精"只能令人猜测:或曰是名士崇尚自然,标榜清高,成为钟情风流的借口;或曰是圣人以礼节情非无情,凡人任情应有情。这些猜测一般是从《论语集解》里找根据,或者从后来玄学家的言论里去推论其本意。但是,何晏"甚精"之论为什么风靡一阵后,就被王弼的"圣人有情"说取代了?
而且王弼批评"圣人无情"说"失之多矣",显然不单是理论本身不完善的问题,恐怕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遇到实践中难以解释的困惑,因而需要加以修正。对此,何晏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叹服不迭:"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钟会传》裴注)这里肯定有名堂。现在,我们看看傅玄是怎么说的:王黎为黄门郎,轩轩然乃得志,煦煦然乃自乐。
傅子难之曰:"子以圣人无乐,子何乐之甚?"曰:"非我乃圣人也。"(《北堂书钞》卷五八)
(刘)陶字季冶,善名称,有大辩。曹爽时为选部郎,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当此之时,其人意陵青云,谓(傅)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
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爽之败,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三国志·刘晔传》裴注)
王黎为黄门侍郎后得意忘形,已在正始九年(248 年)。《三国志·钟会传》裴注曰:"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王)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裴秀为黄门侍郎是在25 岁时,《三国志·裴潜传》注引《文章叙录》有记载,即在正始九年(248 年)。裴秀被用为黄门侍郎后,何晏想再增加王弼,丁谧却推荐了王黎。王弼与王黎本来关系很好,"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三国志·钟会传》裴注)。而"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三国志·钟会传》裴注)。至于王弼,他的圣人有情说也已出笼,认为圣人"同于人者五情也","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三国志·钟会传》裴注),何晏主无情,却对主有情的王弼格外器重,说明王弼之说中"应物"的新义,正是何晏最感兴趣的东西,也就是说,圣人无情有情的相同点是"应物"。玄学家们都是不能忘情世事,急于功名利禄之徒,即便在他们内部,争夺计较也很激烈。"三狗"中的丁谧与何晏争衡,新人王黎与王弼相夺,可见"应物"用世已经"累于物"了,所谓"无累于物",显然说到做不到。
玄学家们不但在无情有情上作文章,而且在圣人凡人上打主意。傅玄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玄学家们是以"圣人"自居的。王黎得官而乐,支吾自己不是圣人;刘陶以"得天下"的"智者"立论,宣称"仲尼不圣"。他们得意时顾不得无情有情,"图国"时忘乎所以,失败后"谢其言之过"。这一切证明玄学理论的用意所在,绝不是抽象空洞的有无、本末之辨,而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极为密切。《颜氏家训·勉学》曰: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也。??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
??有情而"在乎己身","无累"而"弃之度外"。玄学家在正始年间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拔擢同党"有旧者",排斥异已不从者,正始年间形成了以曹爽为核心的阴谋集团。曹爽专擅朝政,已有"无君之心",他依靠的就是一批玄学家。王肃将何晏之辈比作如弘恭、石显等"前世恶人",时人谤书谓何晏、邓飏、丁谧为啮人之"三狗",谣谚称这伙人是"乱京城"的祸首。正始名士被一网打尽后,"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三国志·王凌传》裴注),这是与司马氏不一条心的王广评断的,更可见他们很不得人心。
所谓圣人无情有情,可以在理论上沟通,实践中不发生矛盾;所谓圣人"图国",又能在孔子与玄学家之间推出新意,呼出主题。"圣人"有现实形象,"无情"可有可无。傅玄没有把"圣人无情"这个玄学命题当作高深的理论看待,而是从现实政治出发,揭露它的虚伪性和真实用意。这给我们提供了把握这场论辩的可靠依据。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