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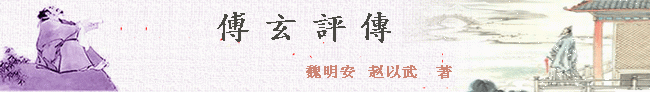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四、关于名教与自然的矛盾
《晋书·王衍传》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以"无"为本,"无"就是"道",这个"道"无物不在,"无往不存",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又自然生成万物。
按照玄学家的这个理论,什么难题都不在话下,都能解释得通。因为"无"为本,"有"为末,"无"在"有"中,"有"归于"无"。不但无情有情能沟通,而且名教与自然也能沟通。这就是:儒家名教是"有",道家自然是"无";以无为本,所以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可以引向自然。这个理论的现实意义在此。它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现实政治中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的。
正始以后,玄学以无为本的理论成为士人立身存命的指导思想。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竹林名士"的生活方式。嵇康、阮籍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任情放纵,不顾礼教的束缚。他们中有的人是不满司马氏残酷屠杀异己的行径,自然放诞。作为内心苦闷的象征(如阮籍),或者是有意反抗的表示(如嵇康);但是也有效仿而并不十分认真的人在,例如刘伶、阮咸诸人并不是存心要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只是想求得自适。然而,有意也好,无心也好,总之士人中普遍出现了一种与名教隔膜的情绪,这对现实政治显然是有害的。
司马氏掌握曹魏政权后,主张以名教治国。傅玄是站在司马氏一边的。
他在《傅子·礼乐》篇里讲道: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旨,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日君臣,以立邦国;二日父子,以定家室;三日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废矣。礼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谓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谓之远乎?由近以知远,推己以况人,此礼之情也。
可见,礼教是治国"大本",这个"大本"建立在三纲基础上,是"立人之道","正天下"的法宝。封建伦理秩序的"大本",当然不能以老、庄的道家学说去解说,不允许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必须强调并维护名教的尊严。所以,傅玄在多处申述道: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丽乎天。(《文选》卷五九,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注)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卷五)经之以道德,纬之以仁义,织之以礼法。既成,而后用之。(《意林》卷五)《论语》,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意林》卷五)
这种明"大教"、隆"道化"的思想,是《傅子》里很突出的主题,也是傅玄入晋后向晋武帝上疏中陈述的"王政之急"。"退虚鄙"以"敦风节",摄"纲维"以斥"虚无放诞之论",恢复名教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玄学思潮影响下的社会风气,这正是魏晋之际现实政治斗争中最迫切的任务。傅玄所谓"大本"所在,立言著论,上疏陈事,亦有鉴于此。
综上所述,傅玄从现实政治角度抨击魏晋玄学,是作为当时人的认识来立论的,这就显得十分重要。他的意见,至少在下述三个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内容。
第一,玄学是在魏明帝统治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远因是汉末以来政治思想变化的结果,近因是曹操、曹丕父子的政治路线影响的产物,现实基础是"旧学"复兴、名教治国引发刺激的作用。如果将玄学出现解释成曹魏政权与后来司马氏斗争的需要,那么,不仅时间有置后之嫌,而且因果有颠倒之误。
第二,玄学是从如何品评人物中脱胎而出的一门古为今用的学问。它搬来道家之说,力图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焦点是在选举用人问题上,这在魏明帝时期尤其突出。即便是在正始中及其后的论辩中,玄学主题演化为有无、本末等形而上学的命题,哲学思辨的特点十分鲜明的情况下,那些命题的背后仍掩藏着士人得势失势的真实用意。泰始二年(266 年),傅玄上疏抨击"虚无放诞之论",所以归结在"举清远有礼之臣"上,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嘉平元年(249 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牢牢地握有政权,何晏一伙被杀了,王弼也死了,到泰始二年,其间相隔17 年,玄学家不再得势,不少人改弦易辙,依附了司马氏,个别人(如夏侯玄)也不能成大气候。现在有晋已经立国,新朝伊始,傅玄却危言耸听:"亡秦之病复发于今!"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如果玄学仅仅是一种哲学探讨,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这就说明,即便玄学家于正始以后不再掌管选举,可是这17 年中,玄学仍在选举用人的问题上起着不利于"敦风节"的坏作用。而且,事实证明,傅玄上疏后,直到西晋灭亡,玄学仍在深入,影响现实政治是多方面的,豪门世族掌权,名教自然统一了,士人的心态、行为也变了。后来傅玄也心安理得,不再抨击玄学,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傅玄是批评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玄学是经学的反动,它出现以后,就应该受到传统儒学的抵制和反对,以维护名教之治的尊严。这也就是说,所谓两晋之际才有玄学阵营中的裴批评玄学唯心论、外儒术的葛洪指斥"风颓教沮"的玄学思潮,恐怕就显得迟了点。因为在他们之前,玄学出现至少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又是人们常讲的"天下多故"的时期,名教与自然之间激烈斗争,如果名教一方没有代言人,那是解释不通的。尽管玄学家讨论的是哲学问题,从理论上辨名析理,重在名理;政论家讨论的是现实问题,从政治角度强调循名责实,重在事实,但是,玄学并未脱离现实,玄学家与政论家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孤立存在。名教自然之争,不仅表现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而且也反映在水火不容的思想交锋中。傅玄抨击玄学的言论,主要是在曹魏时期写成的,这就很可贵;批评玄学的人物,当然不只是傅玄一人,但他是其中持论激烈的代表。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