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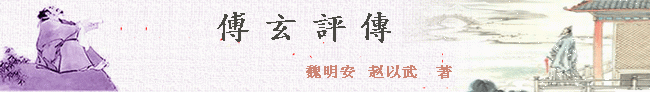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二、贵儒学之业,因善教人
傅玄提出"尊儒尚学"、"贵其业"的建议,入晋前、入晋后的出发点是不尽相同的。入晋前,他在《傅子》里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教化的角度立论的;入晋初,他向晋武帝上疏,是着眼于人才的培养。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他在《傅子》中的观点。
(一)人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
儒家先师孔子未论人性善恶之分。在他以后,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不赞成笼统的性善性恶之论,主张有善有恶。在曹魏正始前后,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性恶论。比如杜恕讲:"议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当待以善意。"(《三国志》本传注引《杜氏新书》)前面我们已指出,博玄是主"水性说"的,即认为人性是随环境变化的,善恶是因时因势而异的。在防恶重教的意义上,具有法家倾向,与荀子的重教思想是一致的。傅玄主张"立善防恶"(《法刑》),以礼教为"大本",推行教化。他说:"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丽乎天。"(《文选》卷五九沈约文注引)即认为道德教化(即"道教")的作用是客观存在,如日月中天。
更重要的是,在傅玄看来,民是"可教"的,人性是可以教化的。《贵教》篇曰: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者乎!
又曰: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则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
除了善恶转化、利害选择而外,人还有好学的一面:人之学如渴而饮河海,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意林》卷五)所以傅玄强调"宣德教者,莫明乎学"(《意林》)。学是基础,要"尚学"。根据傅玄入晋后所言,"汉魏之失"是士族子弟"徒系名于太学",因而儒学是不被重视的。这个批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需要稍加解释。
汉代儒学的衰落,严格地讲是从确定它的"独尊"地位以后开始的。谶纬化、繁琐化、教条化,窒息了儒学的生命力。汉未工符《潜夫论》提出兼容百家的主张,其实就是想挽救不景气的儒学,他虽然倡导崇儒贵学,但儒学的权威地位己遭到世人的普遍怀疑,不加以改造是不行了。曹操执政以后,贵的是刑名法术,不讲儒学的那一套;入魏后,曹丕倡黄老之学,虽然表面上也有尊孔立庙、恢复太学、撰集经传的举措,但黄初仅六七年,儒学也不可能一下子复兴起来,倒是老子学说更受人欢迎。接着,明帝继位,他一开始就宣布"以经学为先"。太和二年(228 年)、四年(230 年)连下二诏,既明确指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又痛斥"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六年(232 年)还进一步严办浮华案。魏明帝在位十几年里,始终深疾浮华之士,力求罗致"经明行修"的人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加强对太学的管理,实行过考试、推荐制度,讨论过考课法,可以说是以一种积极姿态谋求振兴儒学的,既下诏明令,又有实际行动。再从明帝周围辅政大臣来考察,他们绝大多数也是赞同尊儒贵学的,陈群、董昭、高堂隆、王昶、卢毓、崔林、钟繇、杨阜、辛毗??一大批受过传统儒学熏陶的有识之士也在努力贯彻明帝的路线,态度明朗,出谋划策,显得很有气势。按理说,明帝时期儒学应该复兴,可其实不然。我们读《三国志》,从《王肃传》注引《魏略》序文和《刘馥传》所出刘靖疏文可知,从魏初至高平陵之变这30 年,也包括明帝在位的十几年在内,儒学始终复兴不起来,京城太学办得"学业沈陨",弟子避役入学,博士粗疏不堪,学成者寥寥无几,浮华交游成风难禁。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傅玄的解释,这是曹操、曹丕父子不重视儒学,而玄学却得到广泛的传播造成的后果。其实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儒学自身的不景气造成的。刘大杰先生在《魏晋思想论》一书中曾指出,经学玄学化是魏晋思想界的新倾向之一;玄学给衰微的儒学添入了新鲜的东西,言辨义理比枯燥乏味的教条更对士人有吸引力。这是很有道理的。玄学作为一种思潮,是儒学不振之果,而非不振之因。明帝死后,正始年间玄学很有市场,老子上升到与孔子并为圣人的地位,以道家学说注释儒学经典《周易》、《论语》也成为玄学家(如何晏、王弼)感兴趣的尝试。倡无为、体自然,不仅是士人生活中处世的准则,也渗透到国家政治领域的各个环节。这种变化也不能仅从齐王芳懦弱和曹爽集团的专权来解释。正始以后,司马氏专权,号称以名教治国。嘉平初,王昶向司马懿献策,就重提魏明帝时期的方针:"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三国志》本传)司马懿也很重视。那么,儒学的境况是否从此好转起来了呢?没有。魏末高贵乡公在位时,太学博士庾峻感到"时风重庄老而轻经史"(《晋书》本传)。晋初傅玄大声疾呼"汉魏之失未改",这说明儒学在正始以后乃至入晋以后仍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人们的重视,不景气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变。由此可见,儒学不振不能归咎于提倡不力,也不能怪罪于玄学思潮.关键是它自身的衰微,还没有力量走出困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复兴就能复兴起来的。世风的形成,不能用强行手段去改变,提倡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傅玄将儒学一直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于统治者的政策,意在提醒司马氏以尊儒贵学为当务之急,用心是良苦的,但实际上收效不大,道理就在于此。不过,他从人性的角度立论,提出可教、好学的问题,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比正始中王基、蒋济,桓范、杜恕等政论家的议论,要更切时事,更有价值。
(二)贵教在于"因善教义"、"国义立礼"
由人性认识出发,傅玄提出"因善教义"、"因义立礼"的贵教主张。
《贵教》篇曰: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士有仗节成义、死而不顾者矣。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立礼者也。因善教义,敌义成而教行;因义立礼,故礼设而义通。若夫商、韩、孙、吴,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争,唯争是务。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没矣。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夫其所以同,则同乎禽兽矣。不唯同乎禽兽,将乱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以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乱,几希耳!
这段文字通过对儒、法、兵三家学说的比较,得出了贵教的结论。儒家重礼治,修礼让;法家(商秧、韩非)"束之以法",兵家(孙武、吴起)"要之以功",重力治,任力争。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修礼让,兼济其善,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好利之心独用",则"将乱甚焉"。我们指出过,傅玄是主张援法入儒,儒法兼济的。但是,他首先强调的是礼治,认为礼教是立政使民的"大本",是"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破礼教,废礼义,等于是自去"藩卫","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礼乐》),这是亡秦的教训,应该引为鉴戒。人性善恶要"兼济",达道既"通儒"又不"释怯",也要"兼济"。善可因,恶可改,立礼贵教,以尊儒为"大本",这是《傅子》里多处申述的道理。《傅子》里还特别引用亡秦之例,说明"专任"、"独用"法刑暴政之失。
人晋以后,他仍然讲到"以法术相御"(《晋书》本传)是不明"大教"、不存"义心"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上述一段话里批评的是法、兵二家之说,却未提道家。老庄思想在士人中一直很有影响,正始以后,"法自然而为化"(阮籍《通易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是对司马氏虚伪礼教采取不合作立场的宣言,这影响到士人的生活方式、政治态度,却不能左右政局。与政局直接有关的,是司马氏的政策。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是标榜以名教治天下的。但是,司马氏父子却实行残酷的镇压屠戮政策,名教的虚伪引起了士人的反感。鲁迅说过,嵇康、阮籍其实是"太相信礼教",他们言行似乎有"毁坏礼教"的倾向,其本心只是对司马氏篡政表示不满。①嵇、阮是相信礼教的一种类型,傅玄是另一种类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司马氏的态度。傅玄提出行"礼义之教"以争取人心的对策,显然有针砭时弊的动机,有"匡正"司马氏的动机。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