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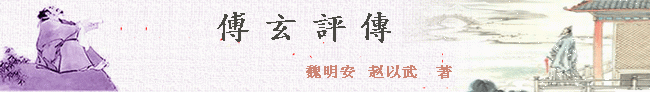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四、后论
以上三章,我们从谋"君人南面之术"的角度,主要对《傅子·内篇》的思想意义及其价值,作了一些探索和解释。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中第一 章第二节,特别引用了傅玄上疏"五事"之一、四两段文字,认为其中"功力" 就是"劳役的代名词",而劳役地租的形态又反映的是"屯田制下的剥削率"。这 两点判断,我们以为似乎与傅玄疏文之意不很切合。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虫》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七章, 有一节为《傅玄的经济思想》。其中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分民定业论;二, 财政观点;三,农业问题;四,货币概念。胡著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的, 这与我们本章所论的角度不同,某些看法也不尽一致。可参见。第一,《内篇》的理论意义,在于提倡"有为"而治、"无为而化"的一套南面术。
在傅玄看来,"有为无不成",不能用"无为而治"的方法理世治乱,统御天下;但是又要"恭己慎有为",不能是"无不为",为所欲为;所谓"无为而化"是"慎有为"的结果,而不是去"有为"的产物。《内篇》所论,当时人王沈评价是"经纶政体,存重儒教";清人纪购的评语是"关切治道,阐启儒风"。二者共同指出《内篇》的主题跟政教有关,不谋而合。傅玄要论证的是:"政体"的主体是君、臣、民,关键在君;"治道"的要领是"通儒达道",首先要"尊儒尚学"。对于君主而言,"恭己"而"慎",止欲宽下,以著恩信,这是明君"有为"的前提;御臣要有术,治民要兴利,统政要儒法兼济,这是明君"有为"的内容,也是手段;"上下相奉","无为而化",这是明君"有为"的目标。
傅玄主张"无为而化",却不赞同"无为"而治;主张"通儒达道",即援法入儒,儒法兼济,却特别低斥"以法术相御"的暴政。前者是针对道家思想影响时代思潮的现象而言的,后者是有鉴于魏末政治的现状而言的。傅玄入晋后的名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就有批评这两种倾向的用心。这两句话也可谓《傅子·内篇》理论意义的佐证。
第二,《内篇》的政治意义,是为司马氏政权谋求篡政而立服务的。
从《晋书》本传的记载可知,《内篇》的完成时间在入晋之前,不可能在入晋之后;写作时间主要在司马昭执政时期,其中有的内容也有可能写于此前,甚至有明帝末年、齐王正始年间写成的可能性,但修订成篇的时间仍应以司马昭执政、傅玄出任地方官这一期间为依据。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本传载录傅玄入晋之初向晋武帝先后所上三疏,其指导思想、主要观点仍与《内篇》所论相近,尽管《内篇》详论"为治"之道,上疏直谏"为政"之失,建言当务之急,出发点不尽一致,但彼此颇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前面几章虽以《内篇》为主,又多处援引傅玄入晋后的上疏,相互参照,就是有鉴于此的。
傅玄政治上倾向司马氏,拥护司马氏,态度是明朗的。但是,入晋前后司马氏的统治政策与所作所为,又是让傅玄感到十分担忧的,弊端不少,为政多失,所以他要"匡正"、直谏,用心亦在于维护司马氏政权。
第三,《内篇》所论,上疏所言,其现实意义是很突出的。
关于这一点,上述两点里已有涉及。我们要强调的是,傅玄立论的基础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不是纯粹从理论上构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所要阐述的道理,提出的主张、建议,以儒为主,兼取法、道,明显地具有荀子思想的特点,也吸收了汉魏以来主张儒法兼综的政论家的思想成分。我们在前几章的论述中,充分注意到这一倾向,说明傅玄作为一名政论家,其立论的渊源所自。但是,我们更注重联系现实政治来证明其中蕴含的意向。王沈引述汉文帝评论贾谊政见的话有"今不及"之论,这也正是傅玄政论的显著特点之一。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内篇》是《傅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傅玄作为一名思想家的主要依据。今所见《傅子》存文,《内篇》并不完整,有的内容散失不见了,现存成篇较充实者与零散段落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很难完全沟通。这当然很可惜。但是,他主要的思想观点可见,他的真实用心可知,这又使我们有可能对他的现有政论文字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与评论。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采用孤立切割的传统方法,将傅玄思想分成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民本思想等等单独的结构去剖析,而更着眼于他所论内容与司马氏政权之间息息相关的特征,从"南面术"的层面上分析其中的意蕴。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古代思想家、政论家共同的意愿。他们立论倡言,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探索上,都有当时的考虑,不过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已;有的能看出来,有的不甚明显,不够清楚罢了。傅玄的《内篇》属于前一种情形,这是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当然不能忽略。
接下来,我们想就傅玄所论"南面术"的时代意义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作些补充说明。
傅玄的政论、上疏所及,换个角度讲,又是最早批评司马氏政权的文字资料。虽然作为政论文的《傅子·内篇》成于禅魏之前,是讨论新政权如何谋求禅代而立的"南面术"的,正面立论的色彩浓重,策略性很强,但是问题的提出却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晋书》本传言及的"多所匡正"的意思。换句话说,凡是《内篇》着意强调的内容,都是司马氏所作所为不大经意甚至倒行逆施的地方。入晋之初,傅玄又利用谏官身份,直言进谏,批评时弊。这前后的用心是一致的,立论也好,陈事也好,都是从治国安民的意义上探索如何拨乱反正的有效途径的。然而,鉴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限制,有晋禅魏前后,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拨乱反正的根本转变。别的不说,就君王而言,傅玄热切拥护的司马昭,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傅玄希冀的方式行事,更不可能更弦改辙,弃旧图新。司马昭热衷暴虐,用人不当,已经为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不良的基础。司马昭死于禅代前夕,他的儿子司马炎更不是有为之君,有晋伊始,政权建设以及当务之急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晋武帝司马炎无力克服,而且他本人贪欲不正,又优假士族,在晋初表面升平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危机。"刚劲""峻急"的傅玄,虽然有"匡正"之意,却无回天之力。我们发现,泰始五年(269 年)以后,傅玄对政局的批评趋于缓和,甚或不再坚持原先的立场,恐怕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
其实,"南面术"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的政治理论的规范。它对汉代以后有为之君特别是建基开国的明君,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君明必须臣贤,臣贤又要求明君要敢于识佞。孔子虽然很早就注意到"恭己正南面"需要"远佞人"(《论语·卫灵公》)的问题,但是"远"之首先得"识"之。从"识佞"的意义上加以强调,这是傅玄政论中很独特的内容。傅玄力图援引秦亡的教训和"汉魏之失"的实例,以引起司马氏的警惕,呼吁"用直臣",以开创一种"有道"的政治局面,可惜没有实现。真正认识到这一卓越见解的理论意义,并付诸实践的,是唐初唐太宗与魏徵形成共识。运用于"贞观之治"中,才得以实现它的价值。
西晋王朝在傅玄死后,很快实现了灭吴而统一全国的鼎盛局面。但是好景不长。武帝一死,昏庸的惠帝即位,西晋王朝的下坡路就急转直下,内乱外祸导致了它的灭亡。傅玄之后,批评西晋积弊的净臣有刘毅、傅咸、鲁褒、裴等人。他们的言论很激烈,批评很直接。西晋灭亡以后,从总结西晋亡国的教训方面切中肯綮的史论家有葛洪、干宝、范宁等人。他们认为,玄学误国,惠帝不才,导致了西晋的速亡。当然,批评时弊、总结亡国教训,西晋后期的诤臣和东晋时的学者确实有相当精当的言论,后世史学家对此一致首肯,一再引述,说明其认识价值和理论意义具有昭示性质。但是,我们将傅玄早期言论与上述诸家于西晋后期乃至隔朝之议取来对比,会很惊奇地发现:后者议论所及的实质性问题,正是傅玄早年急切指陈的老问题。虽然这些议论指事更直接具体,陈情更具锋芒,论理更不容动摇,确有更可观照的参考价值,但要害并不出傅玄当初所议及的范畴。因此,从超前性上讲,傅玄的政论、上疏是认识西晋衰亡的可贵文献,至少可以证明:西晋政权的腐败在立国之初就己显示,它的病入膏盲是必然的,其衰亡只是迟早的事。惠帝不惠,外戚干政,八王之乱,外族介入,以及玄风大畅、士族清谈等等,都是一连串的偶然拍合,其实只是腐败的链条上的环节,要说其中某一端是腐败的原因或征兆,固然不错,似乎也讲得通,但要从根本上认识,都不够深刻。如果我们从傅玄入晋前讨论"南面术"的时代意义上去认识西晋的衰亡史,似乎更能追溯到大厦必倾的深刻原因。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或政权的衰变,其原因都隐藏在它貌似强盛的背后,发轫于它的上升时期.绝不能仅仅着眼于后期明显的一蹶不振的诸多现象之中。《傅子·内篇》讨论的"南面术",并没有为司马氏建基立业所采纳;入晋初,傅玄直谏的"王政之急",也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和严格贯彻。"亡秦之病复发","汉魏之失未改",蒸蒸日上和欣欣向荣的时刻,傅玄如此唱反调,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使然。他的理论纲领未被采纳,他的预见性的直言未受重视,不等于没有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像傅玄这样,于王朝政权未立将立、始兴而盛的时期,孜孜于内在的弊端,清醒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并建言上疏的思想家,认真推究起来,不是很多;特别是他指出的危机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得到应验,这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傅玄的"南面术"没有应用于西晋,却受到唐代君臣的高度重视,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很熟悉唐初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励精图治,魏徵犯颜直谏,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前代佳话之一。"贞观之治"确可谓拨乱反正的历史范例,也可谓"南面术"自觉成功应用的少见的样板。唐太宗命魏徵编纂《群书治要》,首先取决于唐太宗真心重视学习借鉴历代封建政治学说的迫切愿望;魏徵摘要汇集前代典籍中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内容,也首先出于他完全为着唐王朝的根本利益。中国古语讲"君明臣贤",但真正造就这种君臣关系的历史时期,为数很少,"贞观之治"可谓难得的一次结合。《群书治要》里大量摘引《傅子》文,说明魏徵极为重视傅玄的意见,唐太宗也从中学到了为君治国的有益东西。因为唐太宗懂得,天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通鉴》卷一九二),他很重视秦朝特别是隋朝速亡的教训,深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因而清醒地决定采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方针,并把"任贤能,受谏诤"作为两条根本的措施。这些正是他作为"明君"的难能可贵之处。同时,唐太宗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选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这又是像魏徵这样的直臣能够被选中并始终得以直言无隐、犯颜切谏的背景与条件。所以,"君明臣贤"中,关键在于"君明"。只要"君明",正如《傅子》中所说的那样,贤臣"求无不得"。傅玄虽是刚直之臣,可惜他没有遇到真正的"明君"。魏徵既是直臣,又恰逢像唐太宗这样一位英明之主,这是他比傅玄幸运的地方。"贞观之治"中"君臣论治"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持续维持,是中国历史上"南面术"真正贯彻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书生议论的少见的例子。傅玄于魏晋之际向司马氏勾画的"南面"蓝图,时隔近400 年后,才在唐初切实引入政治生活中来,为魏徵奉为至宝,为唐太宗观若鉴戒经典,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幸还是不幸?其实是既幸又不幸,二者兼而有之。历朝历代的君主,包括被后世公论是"昏君"者,在位时无不以"明君"自视自处,臣僚们或阿谀,或希求,或规谏,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当朝君王当作"明君"看待,因而奸佞当道而忠直被黜的悲剧一演再演。"南面术"在理论上再完善,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难以有效实施。被罢官被杀头的直臣何其多!傅玄被罢官而未遭杀头之祸是其幸,他的一套"南面术"在唐初总算受到唐太宗、魏徵的赏识,也是身后之幸。初唐君臣从傅玄政论里获得有益的启示,这也是有道理的。《傅子·内篇》是从总结前代之夫,为新王朝的建立,贡献大计方略的。这与初唐的开国新政面临的选择,是很近似的。当后来盛唐时纵横家赵蕤在《长短经》中再一次大量引录《傅子》文时,赵蕤没有得势,《傅子》也未再次引起盛唐君主的重视,其中多少还是有点必然性的。皇权巩固了,盛世出现了,歌舞升平中继续老调重弹,说什么励精图治一类的惩戒话,顶多是点缀,还需要认真当回事吗?赵蕤想"救弊",他的学生、大诗人李白想匡世,可以说都不识时务。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