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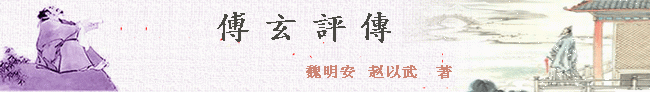
|
三、"评断得失"的史学见解
傅玄曾为史官,编撰过《魏书》,评论过"三史故事",现存《傅子》里保留了大量有关内容,《三国志》裴松之注文引用较多,且较为完整;其他典籍里零星散见,多是摘引片断,缺少上下文的照应。联系起来看,从中可见傅玄对历史人物、典籍方面的不少独到见解,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一)
关于历史人物、事件方面傅玄在自己的政论文里,经常举引历史故事,作为论证问题的重要论据,涉及到的人物多达30 余人。这种引史为证的说理方法,亦为前世当时的思想家、政论家以及文人政客普遍使用,傅玄沿用此法而已,无需特别在意。当然,他有时能根据论题角度,对同一人物作出相应的评价。例如,对辅佐秦国的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傅玄就既议其非又论其是,显示出一种通达的特点。再比如,傅玄对曹操这位乱世枭雄,肯定的地方较多,《傅子》里赞扬的文字不少,但也批评他疑诈任法的另一面。类似的例子还有。这说明傅玄的历史观中辩证的思想是较为明显的。《傅子》里这方面有价值的内容,略可见数端。
首先是对古史记载的一些新颖见解。比如他说:若谓黄帝后乃有舟揖,庖牺之时长江大河何所用之?(《意林》)
这是对《世本》记载的质疑。《世本》曰:"共鼓、货狄作舟。"(《艺① 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讨论《傅子》时引用。这段文字为《纯 常子枝语》卷三六所出。"纪文达"指《四库总目提要》的总撰者纪昀。
② 叁见《傅子·叙》。文中提到的《中论》,为汉末徐斡所撰;《中说》为 隋代王通所撰。《隋书》或《唐书》将这两种著述置于儒家类,与《傅子》不在 一类。
文类聚》卷七一引录)《说文解字》曰:"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济不通。"据传说,共鼓、货狄是黄帝二臣,活到尧、舜时代。所以一般认为,舟楫的发明应用是在"黄帝后"。傅玄不相信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认为在黄帝之前的远古时代,例如人类传说中的"庖牺之时",就应该有舟楫的利用。古史邈远,文献不足,考古难证。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傅玄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但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却是新颖的,值得考虑。类似的例子,又如:虢是晋献所灭。先此百二十余年,此时焉得有"虢"?则此云"虢太子",非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虢太子死"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
又,同篇裴骃《集解》亦引,文字与此稍异。)
是时,齐无桓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句下,《索隐》引)这两条文字是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的。神医扁鹊在世,当在赵简子专国时期,即春秋时晋昭公、顷公、定公在位期间(前531 年后)。而貌的灭亡是在晋献公在位时(前676-651 年)的事。所以傅玄说,扁鹊当时不可能与已灭120 年的虢之太子及不存在的齐桓侯发生任何瓜葛。
以上这些片断评论,对我们认识古代史不无参考价值。
其次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议论,别具只眼。比如他说:孟轲、荀卿若在孔门,非唯(子)游、(子)夏而已,乃冉(伯牛)、闵(子骞)之徒也。(《意林》)
这是将孔门后学孟子、荀卿与孔子弟子进行比较的。《论语·先进篇》记录孔子学生各有所长的情况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闵子骞、冉伯牛是孔子早期学生,孔子称赞过闵子骞的孝(《先进篇》),探望过冉伯牛并对他病重不愈深深叹惜(《雍也篇》)。子游、子夏是孔子后期学生,专心教学,有学问而不做官。傅玄这里是对孟子、荀子表示敬意的,认为二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德行。孟子重义,荀子重礼,都对孔子重仁的学说有继承有发展;孟、荀生前游说诸侯,不合当世,愤疾异说坏政,退隐著书,都显示出一种"不相与谋"的君子本色。所以傅玄以为"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的这种德行表现,其实是盂子、荀子身上更可贵的一面。又如他说: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太平御览》卷五九九)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好《谷梁春秋》,著成《洪范五行传论》,重灾异变化,以此解释人事政治,迷信思想十分浓厚;但是此公在元帝、成帝之世,却上疏直言,敢于同外戚许嘉、史高以及王凤等人的放纵行径作斗争,痛斥宦者弘恭、石显的弄权作乱,虽迭遭下狱免职的打击,但其志不移,于社稷"言多痛切,发于至诚"(《汉书》本传语)的初衷不变。刘向之子刘歆既通《谷梁春秋》,又好《左氏春秋》,在学问上主张"兼包大小之义",不可"偏绝""守残"(《汉书》本传语),显得不同异常,因而"诸儒皆怨恨"(《汉书》本传语);但是他不肖其父,缺乏斗争精神,害怕人生风浪,当王莽篡政以后,他竟屈事奸佞,成为"国师"。傅玄对刘氏父子二人的评价,兼顾德行与学识两个方面,认为各有优长之处,很难一概而论。
傅玄对前代拨乱反正的帝王为政特点,也有言简意赅的评价。比如:三皇贵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后义,三王先义而后辞。(《意林》)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傅子》里多处用到"势"与"机"这两个字眼,所谓"势使然也"、"应机而变"云云,就是强调要顺应时势,成无定法的意思。三皇五帝也好,汉魏开国之君也好,他们成就王治霸政的功绩虽然近似,但手段策略各异。从这个意上来讲,傅玄的概括也比其他史家之论有独到之处。《韩非子·功名》篇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傅玄所谓"势"、"机"之义,似乎有综合韩非四方面内容的意味,区别只在于:"势"侧重于外部客观的因素,"机"侧重于内在主观的因素,所以"势"可"使然","机"要谋运。试看: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也。(《意林》)二 汉之臣焕烂如三辰之附长天,长平之卒拓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势使然也。(《意林》)??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口与心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随焉。(《意林》)"势"要借,"机"要发,审势而运机,这是胜败安危的关键。《傅子》里记载郭嘉为曹操分析打败袁绍的十条有利条件,正是这一原则成功应用的典范。傅玄为司马氏谋"南面术"时,也有借鉴历史的成分在其中。
傅玄对帝王用人的得失,也有所评议。比如,《举贤》篇就提到刘邦创业,困于巴汉,萧何荐了韩信这位"饿夫""怯子",使刘邦的事业如虎添翼。又如,《傅子》记三国事,主要突出曹操周围聚集的人才,不单有豫州故旧,还"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征用荆、扬、雍诸州名士,确实有"不间远近"、"至心待人"(郭嘉语)
的气量。在这一点上,刘邦、刘秀都远不及曹操。傅玄对刘秀用人是这么说的:光武凤翔于南阳,燕雀化为鹓雏。(《意林》)
东汉开国,刘秀对南阳乡里感情太深,功臣外戚几乎是青一色的义军故旧网络。这种模式在东汉前期凝固不变,大大地限制了这个政权的生机。"燕雀"得志而尊,实际上是新王朝的劫数。
最后,《傅子》所记,有不少内容可补正吏之缺,它的吏料价值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蒯躬,字叔孝,性方严,有容仪。人望而畏之,有过其门者,皆整衣改容。(《太平御览》卷三八○)
蒯躬其人,史书无传无名。从《傅子》的这段记载里,虽仍不得其详,但反映出傅玄选材记事时自有体例的特点。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大量注引《傅子》文,正是注意到它在当时超越他处所见的优长,引用50 余处,七八千字。后来,选材谨严的《资治通鉴》在反映三国政治、军事的历史时,不少材料直接取自《傅子》,而且大段移用,几乎一字不动。比如:郭嘉陈述袁、曹十败十胜之言,傅斡说马腾、谏曹操南征,刘晔巧诈言伐蜀,马钧发明指南车等,这些极重要的资料都是《傅子》中独有而他处不见的。除正史资料外,《通鉴》记叙建安至正始一段史事,取材裴注《傅子》的文字,在数量上是最多的。
此外,我们还能注意到《傅子》中关于风俗、交往方面的逸事记录。例如:汉宣帝时范延寿奏处三男娶一女之讼事,汉末西域火烷布、苏合香相继传入中原事,曹操倡节俭表现在王公服色简易,嫁女不奢等细微之处,魏明帝时竟有已死去30 年的妇人复生的可疑事在京城传扬,等等。这些内容引起了傅玄的注意,大概在《傅子》中原有大量采撷,略可见记录怪异的另一特点。①以上我们只能从《傅子》现存文大体推测判断其史料性质。大量的文字不存,使我们无法深究。我们可以确信,傅玄的《魏书》是独立完成了的,它在《傅子》中或为中篇里的主体部分,其篇幅肯定远远超过今可见到的零星记载。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唐刘知几《史通·序传》所议,傅玄曾写下过一篇"自伐","夸尚"的"自序"。刘知几看到过这篇序文,今存《傅子》文中有述及傅玄自身家世的文字,按照严可均的意见是《魏书》的组成部分。按照惯例,自序是《魏书》的压篇之作,说明《魏书》已成,出于博玄一人之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二)关于历史典籍方面
傅玄对前代典籍的异同、优劣的辨证意见,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下面分项介绍。
1.《国语》的作者傅玄曰:"《国语》非邱明所作。凡有共统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
这是现在可知的最先否定左丘明作《国语》的文字资料。司马迁《报任安书》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代以来,相传《国语》和《左传》都是左丘明所作。其实根据后人研究的结果,这两部史书都不是左氏之作。傅玄当时是通过对比二史所记同事不同文、一虚一实的相异特征,发现了其中破绽的,认为二者"不可强合",如果《左传》是左氏之作,则"《国语》非邱明所作"。
2.《论语》、《孟子》的成书傅玄曰:"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然子舆,孟子之字也。"(《文选》卷五四,刘孝标《辨命论》注引)
关于《论语》的成书情形,《史记》记载没有具体反映。《汉书·艺文志》讲,这部书是孔子与弟子间"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就是说,《论语》一书成于孔子死后。傅玄的意见基本上沿袭班固之论,不过他突出了仲弓的作用。仲弓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出冉雍的字,他比孔子小29 岁,在《论语·先进篇》列入"德行"名单里,《雍也篇》多涉有关他的言行。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里,引用了傅玄的话,认为《论语》出自孔子不同学生及再传弟子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德行"的四位弟子中,颜渊、冉伯牛死于孔子之前,而有关闵子骞的言论,又是他的学生追记而成(据杨伯峻《导言》),他比孔子小15 岁,似乎没有着手记载他与孔子间的交往言谈。因此傅玄以为应从仲弓算起,虽不详依据何在,但确有合理的成分。
关于《孟子》的成书情形,《史记》说是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合作而成的。傅玄认为:第一,孟子本人亲自著成七篇;第二,其书受《论语》影响,是"拟其体"的产物。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的结论是,《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孟子》仿《论语》而作,取题、成章的格式完全相同,汉代将二书同视作"传记"并立博士,可见后人也认为是同类之作。①这实际上跟傅玄的意见出入不大。只是傅玄提到孟子有字子舆一事,不知何所出。因为《史记》未出孟子有字,东汉赵歧、徐斡也不知其字,曹魏时王肃、傅玄却凿凿而言,说孟子有字"子舆"。这或有所本,但后世学者大多持怀疑态度。
3.《管子》的作者问题傅玄曰:"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困学纪闻》卷一○引)
关于《管子》一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傅玄的怀疑意见,可以说是相当有眼光的。在《四库全书》编纂以前,学界普遍认为《管子》是管仲所撰,②很少有人怀疑。《总目提要》引述了傅玄的文字,也引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文字,结论是折中含混的,认为管仲手撰与他人记述笺疏,并"由后人混而一之"。真正使问题深入明朗的研究工作,是当代前辈学者罗根泽、郭沫若等人进行的。罗根泽考出战国以前没有私家著作的结论,③可以当作定论。管仲生活的时代尚属春秋前期,诸家看法虽有前后差异之别,却都赞同《管子》书的全部或一部分,均不可能有管仲自著的文字。至于《管子·轻重》篇,郭沫若认为"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据"(《<管子集校>校毕书后》);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王莽时所成。④因为《轻重》篇是讲理财问题的,涉及到货币的流通管理,因此它不可能成于汉代以前,也是有根据的。
傅玄于1700 多年前发表的关于《管子》一书的总体意见,为当代学者所证实,这反过来可以证明傅玄在当时学术上的独具慧识。傅玄之后,他的这一真知的见少有人注意,长期被埋没。南宋学者朱嘉、叶适虽持论与傅玄相近,①但是否受傅玄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4.《世本》的成书时间傅玄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②(《意林》卷五)
《世本》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作《史记》,从《世本》中借鉴其体例,利用其史料,这是《隋书·经籍志》等多处记载① 参见《经书浅谈·<孟子>》,载《文史知识》1982 年第2 期。
② 《汉书·艺文志》:"《筦子》八十六篇。"("筦"与"管"同)属于道 家类。《隋书·经籍志》:"《管子》十九卷。"属于法家类。二志均题为管仲所撰。
③ 参见《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载《诸子考索》。
④ 叁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版。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五
七、叶适《水心集》都以为《管子》非管仲所著,既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
② 严可均《全晋文》卷五○,于此段文字下加按语:"'汉末,字当有误。或兼《续世本》言之。"但是,据唐刘知几《史通·占今正史》所载,《世本》"终乎秦末"。刘氏很可能是引述傅玄这段话的大意,则"汉末"应为"秦末"之误。
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世本》15 篇,这是西汉未刘向校定而成的。这部书的作者,刘向说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③,不免笼统,而与傅玄同时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说是"左邱明所作"④,则反映出刘向以后附会的流行看法。
令人佩服的是,傅玄又是独发高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所谓"楚汉之际好事者所作",不仅为唐代刘知几认同,而且时至今日似乎仍不失为的论。5.《桓子新论》的内容评议傅玄曰:"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其博也。"(《北堂书钞》卷一○○)
桓谭于《后汉书》有传。他是西汉未、东汉初一位知名学者,曾受业于刘歆、扬雄,晚年仿刘向《新序》、陆贾《新语》,著成《新论》29 篇,呈送给光武帝刘秀,"光武读之,敕言卷大"(《后汉书》本传引《东观记》)。《隋书·经籍志三》"儒家类"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录而成三卷。
《新论》一书问世后,不仅光武帝"善焉"称道"卷大",而且同时代的学者,例如刘歆、扬雄、班固都各在自己著作里征引其中不少内容;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是多处推崇,认为当代著作里"君山(桓谭字)为甲"。总之,桓谭《新论》在东汉初年赢得盛誉,号称博学多通。
傅玄对《新论》评价不高,第一说它烦杂,第二称它"旨诡"。从现存《新论》遗文来看,其中有论政事的,有述见闻的,有读书笔记,也有随笔杂感,还有不少自矜的文字,确实涉及面广泛。桓谭在政治上主张尊王贱霸,个人经历上有过屈事王莽担任掌乐大夫的一段发迹史,并在自己的著作里津津乐道。这可能是让傅玄反感的原因所在。漫无边际的烦杂内容,在《新论》一书里是存在的;言行相诡的内在缺陷,质诸桓谭,也是不可否认的。①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傅玄对前代典籍的评议,大大超出了当时人的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的见,这对后人仍具有不能低估的参考价值。
(三)"三史"得失
傅玄在世时,"三史"指《史记》、《汉书》与《东观汉记》。他对这三部史书特别是后二史发表了相当出色的见解,从中可见他的史学观。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说的: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卷五)③ 见《史记集解·序》中《索隐》所引。
④ 见《颜氏家训·书证篇》所引。
① 另外,清人秦嘉谟在《世本辑补·诸书论述》里按语曰:"《世本》为 周初至战国时史官相承而作。"此说亦有一定影响。相比较而言,傅玄之说显得 稳妥一点,因为他当时见到的资料比后人要多。"相承说"从时间跨度上讲有数 百年之久,可能性较小。
① 关于傅玄评论《新论》的意见,钱钟书认为尚难令人信服。《管锥编》第 三册第976、977 页指出:"通观《新论》,桓氏识超行辈者有二:一、不信谶纬,二、不信神仙";"窃意《新论》苟全,当与《论衡》伯仲";"傅玄??自应持之 有故;然据残存章节,吾尚未甘傭耳赁目,遽信斯评"。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守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意林》卷五。又《史通·书事篇》所引,去首尾二语)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未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史通·核才篇》引)
以上这三段话联系起来看,傅玄的看法是:《汉书》既是一部有成就的"命代奇作",又有严重的缺陷,与《史记》相比,"非良史";《东观汉记》历次修撰,每况愈下。这些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就傅玄所言,逐项考察一番。
第一,班固《汉书》讳言其父修撰之功,盗名作弊。《史记》与《汉书》修撰过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父子二人相续而成的。但是,司马迁《自序》里明确交代,他完成《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而班固《叙传》不仅只字未提其父班彪修史之功,而且在《汉书》中多处作手脚,冒为己功。史家于此多有揭露。《后汉书·班固传》讲,班固是在其父死后,"以彪所续前史未详","欲就其业"的,后来他因事下狱,其弟班超向明帝"具言固所著述意",又得以继续完成《汉书》。刘知在《史通·古今正史》里指出,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续修当中入狱,"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因此,后人统计《汉书》中有90 余人篇是因袭《史记》之文的,加上班彪所撰65 篇,合计150 余篇,占了纪、传人数的一半。现可知出于班彪之手者,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明标其名,而《元帝纪·赞》、《成帝纪·赞》所称"外祖"、"姑"显然是班彪口吻。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指出:"观固叙传中于彪续《史记》六十五篇,绝不叙及,而记己撰《汉书》事,亦绝不言秉承先志,与太史公《自序》迥乎不同,则固之攘善盗名,殆无可追。"此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第二,从三个方面力贬《汉书》非"良史"。傅玄虽然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汉书》的成就为"命代奇作",至于"奇"在哪里,他并没有具体言及,我们不好细论;但是从内容上贬低它的价值,却是明确有所指的,认为"论国体"、"叙世教"、"述时务",都是有意用曲笔,掩盖事实真相的。
班固著述《汉书》的宗旨是"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传》语)。
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唯心史观去评论、总结西汉一代历史的得失,因而只能写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评语)的王朝正史。这与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一家之言"是正相反的。因此在体例上,《汉书》以帝王为中心,一帝一纪,删掉《史记》中有的《项羽本纪》,增入了《惠帝本纪》以代《吕后本纪》,将汉未徒有其名的成、哀、平三帝也分别立纪"以显国统"(《史通·本纪》语)。在纪传里,掩盖各种社会矛盾,美化统治者,这是处处体现出来的。博玄说《汉书》"饰主阙",那是班固修史中有意使官方色彩变浓的倾向决定了的。至于"抑忠臣",班固在《匡张孔马传》里猛烈抨击的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等儒相,正是傅玄赞许的人物,例如匡衡、张禹,《傅子》里讲:"匡衡以善《诗》至宰相,张禹以善《论语》作帝师,岂非儒学之荣乎!"(《意林》卷五)还有,班固在《晁错传》里攻击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张辅就极为不满,说班固"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晋书》本传)。
傅玄批评《汉书》"贵取容"、"贱守节"。这与后来刘宋时范晔的意见一致。《后汉书·班固传论》指出,班固"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下,唐李贤注引了《游侠传》里班固对剧盂、郭解的一番议论以为证,其中竟有"其罪不容于诛也"之语。相反,班固却将残害人民、作恶多端的张汤和杜周,从《史记·酷吏传》的体例里抽出,为之另立专传,表明了回护的倾向。类似的例子,又如《王莽传》,实际上是以传代纪,编年记事,俨然是帝纪的变通,洋洋洒洒,长达4 万余字,反映出东汉初年班固、桓谭等一帮人对工莽新朝眷恋难舍之情。另外,班固将陈涉不入《世家》而入《列传》,他在诸《列传》的题目上或称名,或称字,或书官爵,在正文里有意剪裁,都是费心良苦的。这些都说明,班固修史出于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目的,不但体例变了,而且行文措词中褒贬取舍间的感情也变了,正史的面目再清晰不过了。
傅玄还批评《汉书》统御文字"谨词章而略事实"的弊端。《汉书》后来赢得了"详赡"的盛誉,原因就在于其中大量引用奏疏、赋文等文字,占的篇幅不小。当然这在保留史料方面是有价值的,应该肯定。但是作为史书,资料引述过多,而记事部分却很薄弱,又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陷。我们读《汉书》,不难发现一些传记除了引用文字外,正文少得可怜,几乎可视作串词看待。还有一种情形,傅玄没有明确讲到,晋代张辅说到了,即"中流小事,亦无足取焉,而班皆书之"(《晋书》本传),这也同样是"略事实"的表现。
由上可知,傅玄指出《汉书》的三不足,并非罗致不实之词,而是它在指导思想、体例以及书法上客观存在的问题。傅玄说得并不过分。
第三,《东观汉记》写得很拙劣。关于《东观汉记》的详细修撰情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东观汉记》有极为详尽的考证说明。这部史书在东汉一朝前后断断续续修撰过四次。第一次是在明帝永平年间(58-75 年),由班固等人(傅玄提到的陈宗、尹敏、杜抚、马严均在其中)在兰台或仁寿阈修成《世祖本纪》及列传、载记28 篇,称为《汉史》或《建武注记》,亦即傅玄所谓的"中兴纪传"。第二次是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至元初之末(120 年),由刘珍领衔续修,修史地点移至东观,任务是在班固等人第一次修出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增加有关内容,国史的面目己具,称为《汉记》。《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东观汉记》,出以刘珍之名,由此而来。第三次是在桓帝元嘉、永寿年间(约151-155 年),由伏无忌、边韶等人修撰(傅玄提到的未穆就在其中),他们新成114 篇,加上班固等第一次所成28 篇,加目录1 篇,合143 篇,《隋书》所谓143 卷之数已具备。第四次是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7 年)直到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修撰人有马日、蔡邕,还有傅玄道及的卢植、杨彪,任务主要是修订已成部分,增入的内容主要是《灵帝纪》。所以《隋·忐》讲"起光武记注至灵帝"。
刘勰指出,"傅玄讥后汉之尤烦"(《文心雕龙·史传》)。所谓"后汉",即指《东观汉记》。①傅玄发现,《东观汉记》从一开始就问题不少,① 刘勰在同篇里,还写道:"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傅玄现存文字, 只是批评《东观汉记》的体例与《汉书》相比,"尤烦""不足观",越到后来越不像样子,继成之文"盖陋"。因此,傅玄认为这跟班固始修形态的关系很直接。如果说《汉书》可称力"奇作"的话,《东观汉记》只能说它是庸作。这是什么意思呢?傅玄没有深入说明,只怀疑"拘于时"是使其然的一个因素,言外之意,这不是主要因素。联系他批评《汉书》的意见,恐怕所指应在修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因为《东观汉记》不存,我们已无法加以证实。
另外,据史书记载,董卓作乱时,献帝东迁途中,史书典籍"略无所遗","湮没不存"(《后汉书》的《蔡邕传》、《献帝纪》),因此有人认为《东观汉记》在这场浩劫中遭厄全亡。我们从傅玄的言论中可知,或许蔡邕撰集部分多失,而《东观汉记》总体上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傅玄于曹魏正始年问得以阅览全稿,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后来《隋书·经籍志》载录143 卷之数,也是真实情形。
(四)傅玄的史学观
傅玄不仅有关于对历史人物、前代典籍以及"三史"得夫成败方面的言论,而且他有撰写《魏书》的实践,从中可见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他认为,"良史"应该具有直笔的特点。他不满《汉书》、《东观汉记》的书法,就是因为其中曲笔大重,"拘时"陋习太浓,以致歪曲了历史真相,颠倒了忠好是非。他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首发之论。晋代张辅、刘宋时范晔、唐代刘知几等批评班固及其《汉书》之失的意见,实际上都没有超出傅玄议论的思想高度。而且他们并没有像傅玄那样,兼及《东观汉记》。如果说《汉书》还多少受到《史记》的影响,只是"续前史"而作出增删调整的话,那么《东观汉记》就是另起炉灶,从中更能反映班固史学思想的偏失。因此,观察《汉书》应该而且必须联系《东观汉记》编修的指导思想。傅玄这样做了,而上述其他几位史学家却缺少这一环节,尽管他们当时都有条件看到《东观汉记》。
傅玄撰成的《魏书》,今可见存文不多。刘知几大概看到过这个完本。
他在赞同傅玄批评《汉书》意见的同时,讥讽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史通·书事》)这话既针对班固,又有挖苦傅玄的意味。刘知几总的倾向是崇扬《汉书》的,他捎带着批评了傅玄,是说傅玄所成《魏书》也并不见得高明。这里应该先说明白,评论与写作是两码事,相提并论不合逻辑。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就《傅子》中所记三国事,作点粗略考察。傅玄记叙三国人物,内容较完整的,今存《刘晔传》和《马钧传》。刘晔在曹操时作为谋士,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帝时作为辅臣,心计太盛,自我暴露。傅玄记这个人物,既显示其机智的一面,又揭示其巧诈的一面,赞其美而叹其伪,写得很有特色。至于马钧其人,巧于工艺,拙于言辞,功不可没,用不可妄,立传书其事,就很不寻常。通过这两人的传记,我们能够发现傅玄传人重事实的特点。刘晔也好,马钩也好,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既不应以长护短,又不能以长攻短。
再看其他零星记载。如记曹操,写他南征孙权失利之误,记他北代袁绍不好,似乎不及文字"尤烦"的问题。刘勰当时或 另有所见,可惜傅玄关于"尤烦"的具体内容,文字已不存了。
前"欲讨之,力不敌"的犹豫,表现他广延有识之士又事事咨询的虚心态度,反映他在"天下凶荒"之时裁帛为蛤的简易处境,点出他受人(丁仪)离间诛杀名士的草率行径,等等,这些内容是《三国志》未载入的,从中可见曹操其人既力统帅又为凡人,既是英雄又是枭雄的双重性格特征。又如记魏明帝,写他防范大臣,下令改变舆服之制;傅玄攻击何晏好着妇人之服力"服妖",其实也是言及魏明帝的,因为这是明帝僻好,此风是他刮起来的。再如记吴、蜀之事,写东吴孙策、孙权治下人才济济,境内安宁;叙蜀汉刘备手下有"三杰佐之",而诸葛亮又是。"一时之异人",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出天下三分的历史实际,并不因曹魏挟天子之重而轻贬其他割据政权。傅玄还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论,如管宁之"醇德"、胡昭之好学、荀彧荀攸之贤、袁涣华歆之清、郭嘉之谋、傅嘏之识、曹仁之勇,以及何晏,邓飏一伙的朋党无行,等等,有的材料充实,有的仅留只言片语,但不管怎样,这些点滴所见仍是我们了解把握这些风云人物的少见线索,也是理解曹魏史实的重要依据。
因此,仅从《傅子》今存有关曹魏史有的记载来看,傅玄秉笔直书的这一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跟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是很有关系的。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