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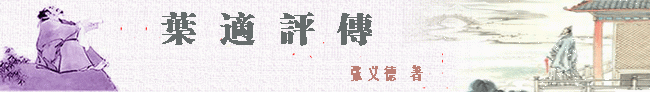
|
一 叶适对《易》的批判
历史上所传下来的《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说明卦、爻的卦辞、爻辞。相传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又称《十翼》,自两汉以来都说是孔丘所作。有宋以来,欧阳修就开始在《易童子问》中怀疑"十翼"为孔丘所作的说法。但道学家们却不予理会,仍守旧说,并据此大做文章,以宣扬他们的"义理"。《易》学在道学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叶适对《周易》的批判性研究,就是针对道学家的《易》学而发的。他说:自有《易》以来,说者不胜其多,而淫诬怪幻亦不胜其众。孔子之学,无所作也,而于《易》独有成书,盖其忧患之者至矣。不幸而与《大传》以下并行,学者于孔氏无所得,惟《大传》以下之为信。虽非昔之所谓淫诬怪幻者,然而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之道犹日出入焉而已。余既条其大指,稍厘析之,诚涣然如此,则孔氏之成书翳而复明,《易》之道其庶几乎!(《习学记言序目》卷四,本章中以下引此书只注卷数)叶适这里所说"虽非昔之所谓淫诬怪幻者",显然是指"今世"之学者,而他对《易》"条其大指,稍厘析之",就是为了批驳那种"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的浮文虚论。具体来说,有如下一些:
(一)否定"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说
叶适认为,所谓"伏羲文王作卦重爻"的说法,"与《周官》不合,盖出于相传浮说,不可信"(卷三)。可见他怀疑"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的传统说法的根据是《周礼》(即《周官》)所记载的材料。
他说:大卜(即太卜,周代的一种官名)"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详此,则《周易》之为二易,别卦之为六十四,自舜禹以来用之矣。而后世有伏羲始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又谓纣囚文王于羑里,始演《周易》,??学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后天之论,不知何所本始。(卷七)
这就是说,"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他又分别批驳说:后世之言易者,乃日"伏羲始画八卦",又日"以代结绳之政",神于野而诞于朴,非学者所宜述也。(卷四)学者所述,应该有根有据;而"伏羲始画八卦"之说,是"神于野而诞于朴"的相传浮说,无根无据,不可信。
他又进一步批驳"文王演《周易》"之说:然则《周易》果文王所改作,而后世臣子不以严宗庙,参《典》《谟》,顾乃藏之于太祝,等之于卜筮,何媟嫚其先君若是哉?(卷七)
这是说《周易》不过是藏于太祝的占缸之书,把这说成是周文王所改作,是不合王朝的体统的。因此,叶适认为:"《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周有司所用也。"其作者不可考,"《易》不知何人所作"(卷四十九)。
叶适以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八卦:日与人接,最著而察者八物,因八物之交错而象之者,卦也。此君子之所用,非个人之所知也。(卷三)
他又以变化观点来说明"易":以其义推之,非变则无以为易,非经非别则无以尽变,古人之所同者,不知其安所从始也。(卷四)
从以上两方面说,易卦都是"不知其安所从始",很难归于某具体人的;"君子之所用"的"君子",也并非哪一两个人,而是指"周有司",即周代的史祝之官,"所用"就是占筮之用。正因如此,所以《周易》中,凡卦之辞,爻之繇,筮史所测,推数极象,比物连类,不差毫发。(卷七)
由此可见,把八卦附会到伏羲身上,把六十四卦说成是文王所演,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破了这个陈说,叶适从根本上破除两宋道学家把《易》附会《河图》、《洛书》,编造所谓"伏羲先天、文王后天之论",认为此说"不知何所本始",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对《易传》为孔丘所作提出怀疑
叶适说"《易》不知何人所作",不但指《易经》,也包括《易传》,也就是《十翼》。他在怀疑"伏羲文工作卦重交"的同时,对《十翼》为孔丘所作也提出了怀疑: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亦无明据。《论语》但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其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
(卷三)在这里,叶适对"十翼"为孔丘所作在全体上是怀疑的,认为此说"无明据","未敢从";但是他又肯定《彖》、《象》二辞为孔丘所作:《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卷三)孔子独为之著《象》、《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卷四十九)
这样一来,就与前面在全体上怀疑《十翼》为孔丘所作自相矛盾了。这是叶适论学的一个小小的不严密处。在肯定《彖》、《象》为孔丘所作之后,对"十翼"的其他诸篇,叶适都否定其为孔丘所作:至于所谓《上下系(辞)》、《文言》、《序卦》,文义重复,浅深失中,与《彖》、《象》导,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卷三)
其余《文言》、《上下系(辞)》、《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会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也。(卷四十九)当然,叶适肯定《彖》、《象》为孔丘所作,其余不是,有以《彖》、《象》为《易》之正,而其他篇非正的意思在里面。
如他在论《乾》卦时说:乾《文言》详矣,学者玩《文言》而忘《彖》、《象》。且《文言》与《上下系(辞)》、《说卦》、《序卦》之说,嘐嘐焉皆非《易》之正也。(卷一)
按《上下系(辞)》、《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有害。(卷四)
尖锐地批评了《文言》、《上下系(辞)》、《说卦》、《序卦》等《十翼》中的大多数篇章为"浮称泛指","去道甚远",非《易》之正。叶适肯定录辞、象辞为孔丘所作,但是,恰恰是象辞和象辞,为历代习《易》者(包括宋代的道学家)所不重视,他们总是利用《十翼》(除《彖》、《象》外)大做文章。"故《彖》、《象》掩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卷四十九)叶适对此深为不满。而叶适否定《十翼》(即《易传》)为孔丘所作,也就抽掉了道学家立论的根据。
在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化典籍中,"经"具有特殊的地位。"传"作为"经"的解释,地位低于"经"。如《春秋》的《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只是《春秋》经的附属品。但《易传》由于被附会为孔丘所作,却取得了与《易经》同等的"经"的地位。叶适敢于否定《易传》为孔丘所作,也就否定了它的"经"的地位,这同他认为《周易》"不知何人所作",只不过是"周有司所用"的卜筮之书一样,都是很大胆的举动,是当时的"疑经"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是值得称道的。
(三)对"易有太极"等说的批判
前面所述叶适对《易》的作者提出的怀疑,其中已涉及到《易传》某些内容。下面我们再看叶适对《易传》内容所作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首先是对道学家奉为"宗旨秘义"的"易有太极"的批判。他说:"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微兆往往卦义所未及。故谓《乾》各正性命,谓《复》见天地之心,言神于《观》,言情于《大壮》,言感于《咸》,言久于《恒》,言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矣。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始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
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卷四)
这里所着重批判的,是《易传》中《系辞上》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段话,认为其"文浅而义陋"。分别来说,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叶适否定了《易传》中包括《系辞》在内的大部分篇章为孔丘所作(如前所述),在这里又指出孔丘述《易》涉及到一些内容,但是,"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孔丘根本就没有说到"太极"的问题,因此,这个作为道学家"宗旨秘义"的"易有太极"归于孔丘名下,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叶适认为,"太极"这个概念来自道家。但作为"虚无之祖"的老聃还没有提出,到《庄子》、《列子》才开始有"太始"、"太素"等"茫昧广远之说"。而"传《易》者"把这些概念挂到圣人(指孔丘)名下,"为'太极'以骇异后学"。第三,后学(指道学家)对这个并非出自孔丘的"易有太极"之说,"鼓而从之,失其归会",从而离开儒家的"道"越来越远了。第四,叶适既揭示了《易传》(这里主要是指《系辞》)、道家、后学(指宋代道学家)之间的联系,就以自己的观点来反对以上三者的神秘主义观点。道学家的"无极"--"太极"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脱胎于《易传·系辞上》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说虽少有差异,但基本一致,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生成论。叶适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八卦"是由"八物"而来的:"物"是根本的,"卦"只是"物"的"象","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八卦')"。
这个说法,朴素切实,清楚明白,毫无神秘色彩。叶适就以自己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来反对《易传》中"易有太极??"的神秘主义的宇宙生成论,同时也否定了道家和宋代道学家的类似观点。
对叶适的这个批评,后世有的学者持有异议。如清人黄体芳认为,叶适说"太极生两仪等文浅义陋",是"一时愤激之言而不可转相师述"(《习学记言序目》附录一黄序),意思是说叶适感情用事,立论偏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叶适这个批评"语皆未当,诚不免于骇俗"(卷一百十七)。其实,这是叶适晚年的作品,是作了认真研究的结果,"骇俗"则有之,"语皆未当"乃纪晓岚的苛责;也不存在感情用事的问题,因此不能说是"一时愤激之言"。在此之前,朱陆争论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无极而太极"(按:据考原文本为"自无极而为太极")时,陆九渊认为"太极"之前再加"无极"是多余的;朱熹认为"太极"为"理"之总汇,"无名可名",以"无形而有理"来解释"无极而太极"。叶适则另辟踢径,考定"太极"为孔丘所不道,根本就不是儒学的概念,而是从道家那里来的,因此与儒家的"道"相去甚远。这就把朱陆都反对了,是叶适与朱陆鼎足而三的表现之一。而他还以其朴素唯物论观点来解释"八卦"源于"八物",反对了道学家奉为"宗旨秘义"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就是哲学上两条根本路线的对立,为黄体芳等人所无法理解了。
叶适还从二程的"天理"论同《易传》的联系上,批判了二者。《易传·系辞上》有如下一段话:《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二程对此极为重视,利用它来论证他们的"天理"。如说:圣人作《易》,未尝言无为,惟日"无思也,无为也",此戒夫作为也;然下即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动静之理,未尝为一偏之说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动",小则事物之至,大则无时而不感。(同上,卷三)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尝动来?因不动,故言寂,然虽不动,感便通,感非自外也。(同上,卷二上)二程利用《易传》中的话,是要论证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易》本身的"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来论证其"天理"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即"天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元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就是"天理"的永恒性;"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同上),主宰一切,"小则事物之至,大则无时而不感",就是"天理"的普遍性。总之,是以《易》的"寂然不动"来论证"常理不易","理"是超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本体。其二,是企图以此来解决"天理"论中的一个困难问题。原来二程的"天理"是来自佛教的真如佛性,其意为永恒不变的"永恒真理"或本体。在佛教中已有某些宗派提出:人人皆有佛性,何以有人成佛,有人不能成佛?其说纷纭。
二程感到他们的"天理"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天理"是绝对的善,普遍存在,人人心中皆有的,那么何以有人为善,又有人为恶?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二程从《易传》中找到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篇话,加以发挥。其意为:《易》本身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但人用《易》以占事,诚心诚意,感而通之,遂能明白天下之至理,"天理"就具备了。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感"字,"感便通";但这个"感"又不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感性认识,因为"感非自外也",还是被封闭在自己所设置的超感觉的圈子里的。那么,这个"非自外"的"感",何以能"通天下之故"呢?这就只能求助于"神"。《易传》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二程则借用了一个"诚"的范畴,加以改造,用以说明"天理"与人的关系。他们说,天理即"诚",又说只要人们心存诚敬就能感知天理。而"至诚如神","诚"也被解释成人的神秘主义精神状态。二程企图借助《易传》上述神秘之论来解决"天理"论的难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越说越糊涂,陷入神秘主义泥坑而不能自拔。
叶适批评了《易传》中的上述言论,同时也批评了二程。他尖锐地指出:按《易》以《彖》释卦,皆即因其画之刚柔逆顺往来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无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
余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也。今《传》之言《易》如此,则何以责夫异端者乎?
(卷四)叶适明确指出《易传·系辞》中的上述说法都合于道家而不合孔丘的思想,而道学家据此立论,以迎合佛教思想,从而是"中国之人实自乱之";道学家指责佛老为异端,而正是他们自己与佛老思想相通,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其为异端呢!叶适进一步批评说:按程氏(指程颖)答张载论定性①??皆老佛庄列常语也。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以《易·大传》误之,而又自于《易》误解也。??嗟夫!未有自坐佛老病处,而揭其号曰"我固辨佛老以明圣人之道者"也。(卷五十)叶适认为,在远古时代,"经籍乖异,无所统壹,怪妄之所由起,转相诞惑而不能正",是可以谅解的。而宋代的道学家思想的混乱,是由于轻信了《易传》的缘故。他说:后世学者,幸《六经》之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无所变流,可以日用而无疑矣,奈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悲夫!盖孔子已尽究古人之异学,发于《彖》、《象》,其述天地精微,皆卦义所未言。不幸《大传》、《文言》诸杂说附益混乱,是以令学者纷纷至此。
夫悬日月以示人,惟无目故不能见,若有目而昧之,可谓智乎!(卷十六)对于《易传》中"易有太极"等说,后人有不同解释。宋代道学家利用它们来构筑其唯心主义的"理"("太极")本论,叶适对其批判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叶适在批判中,主要根据古老的"五行"、"八卦"的朴素唯物论,而对理与气的关系未作论证,尤其是对张载的气本论未予注意,这是一个缺点。第二,对于《易传》本身所包含的辩证法的内容,叶适也在否定《易传》的同时,未作充分的注意,不能在批判中吸取其合理的思想,这是叶适这个批判中的又一缺点。
① 程颢答张载论定性:"所谓定者,静亦定,动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性为有内外也。性为随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音在内也?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下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本,则又乌可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苦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其害在于是内而自私也,用智也。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何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圣人未尝绝物而不应也。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能以方怒之时.遽忘怒心,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叶适批评此论时,曾摘引其中言语,与原文稍有出入。观此论,其要为"内(心)外(物)两忘","无事则定",与老氏之"以无为本",慧能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异曲而同工。叶适从此为"老佛之常语",是为确论。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