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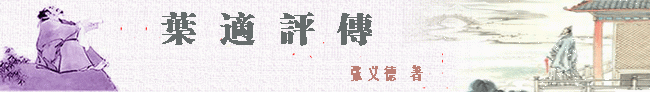
|
二对其他古代著作的考订
儒家之"经",除了《易》以外,还有《诗》、《书》、《春秋》等。
叶适对孔丘删《诗》、定《书》、作《春秋》都有怀疑。他说:旧传(孔丘)删《诗》,定《书》,作《春秋》,余以诸书考详,始明其不然。
(卷四十九)下面分别说明。
(一)"《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叶适对"《书》为孔氏之书,《序》亦孔子作"之说,提出了异议。这个说法出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而班固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则根据孔安国。但"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前后浮称"(卷五)。班固引"洛出《书》"是"字文为书",叶适认为此说"已甚陋";孔安国则说孔丘"讨论《坟》、《典》","芟夷烦乱,翦截浮辞",按照这个说法,"则是孔子并大训亦去取也,岂有是哉!"(同上)叶适认为:文字章,义理著,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以为法言,??孔氏得之,知其为统纪之宗,致道成德之要者也,何所不足而加损于其间,以为孔氏之书欤?(同上)因此,《尚书》百篇,并非出于孔丘之手,说经他删剪取舍,是不实之词。叶适还认为,《书序》也是"由旧史所述","非孔子作也"。其根据是《序》中"明记当时之事",如"升自"、"放太甲"、"杀受"等,"皆其《书》所无有",孔子怎么会"断然录之"呢?叶适认为,春秋以后,许多文化典籍都收集在孔丘手中,"不因孔氏而获见《书》之全者寡矣",何况后世古文《尚书》是从孔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因此,"其尽归之孔氏,不足怪也"。但是,这终究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训,推孔氏有述无作之心,则盖有不然者。后有君子,当更考详。(卷五)
孔丘删《诗》之说,《史记》说得很具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也说孔子"删《诗》为三百篇"。叶适对此十分怀疑,他说:"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卷六)。他怀疑此说的根据有三:第一,以《春秋左氏传》为证。"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同上)。既然是十取其一,那么十分之九的大量逸诗在哪里呢?第二,以《论语》为证:"《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同上)第三,以周代"以诗为教"为证。
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以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同上)
这就是说,周代以《诗》为教,即便对《诗》有所取舍,也是朝廷的事,不会由几百年后又在周王朝不任任何职务的孔丘来把作为"一代之教"的《诗》删得十不存一。那么,孔丘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又作何理解呢?叶适解释说,当时距周王朝东迁已二百余年,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日益强横,战乱频繁,鲁、卫诸国往往变坏,文物残缺,管理文化典籍的史祝之官沦溃散亡。在这种情况下,《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同上)这就是说,孔丘只是整理而不是删《诗》、《书》。整理当然有利于后世,其功不可磨灭,但是不应对这个"失于考订"的删《诗》《书》说,盲目相信,"随声承误"。
(二)"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
"孔子作《春秋》"说,始于孟轲。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膝文公下》)
至汉司马迁作《史记》沿袭此说,有"因史记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世家》)之说。宋代道学家亦深信不疑。胡安国说:"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朱熹说:"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六)叶适认为,"孟子去孔子才百余岁,见闻未远,固学者所取信而不疑也。"(卷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他说:孟子言《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所作以代天子诛赏,??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考详,乃有不然者。(同上)
叶适从两个方面批评了盂轲"孔子作《春秋》"说:第一,否定"《春秋》鲁史记之名"。叶适指出,《春秋》与《诗》、《书》不同,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从其实,不可乱也"。周王朝东迁以后,王室不能自振,而诸侯并起。"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续《诗》、《书》之统绪,使东周有所系而未失。"(同上)但旧的载事之史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然则《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同上)这就是说,孔丘对原有的史书只是加以修正,而不是"作《春秋》"。
第二,否定了"代天子诛赏"之说。叶适说,以功罪为赏罚是"人主"的事情,以善恶为是非是"史官"的职责。孟轲说孔丘作《春秋》是"天子之事",代天子行诛赏,是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叶适认为,孔丘对《春秋》修而不作,其中明辨是非,类似于史官的职责,并非代天子行诛赏。他说:且善恶所在,无问尊卑,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则《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同上)
叶适从这两方面批评了孟轲以后,又进一步指出孟轲此说对后世的不良影响:后世之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其底丽者,小则以《公》(《公羊传》)、《谷》(《谷梁传》)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同上)
(三)叶适的孔子观
叶适对那种把《春秋》中的一切褒贬予夺都归于孔丘的看法深为不满。
他说:盖二百四十二年所关诸国,好恶不一,是非不同,彼皆自欲表章劝惩于一时,而必日待孔子而后定;且孔子举以前代之劝惩为非是,而必日由我而后可:此后人之臆说,相承之议论,非圣人经世之学本然也。(卷十一)
这种"臆说"是后人强加给孔丘的,并不是孔丘"经世之学本然",这个评论是很正确也是很重要的。在考订《诗》、《书》与孔丘的关系时,叶适也有类似的说法: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亦次第之义当然尔。(卷六)
以上两段论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叶适无疑是十分尊崇孔子的。但是,他认为对待孔丘也应该实事求是,对孔丘功绩的评定要恰如其分,不能无限夸大,把并非其功绩的内容强加到他的头上;同时,要把孔丘放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看待其学说,不能割断历史,把一切都归功于孔丘,而抹煞在他之前的"古圣贤者"的贡献,制造一切都开始于孔丘的偶像。对此,叶适还有更为系统而明确的论述: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掩前闻,一归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同上)
叶适对孔丘和儒家《六经》的这种态度,显然与把孔丘和《六经》神化,"托孔孟以驾浮说,倚圣经以售私义,穷思极虑而无当于道,使孔氏之所以教者犹郁而未伸"(卷十一)的俗儒,有着根本的区别,充分体现了永嘉学派的务实精神。
(四)对《周礼》的考订
此外,叶适对《周礼》为周公所为也有怀疑。永嘉学派是很重视《周礼》(即《周官》)的。如陈傅良就认为"《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几于理矣。"(《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
并指出因为王安石变法以《周礼》为据而废《周礼》是"因噎废食"(同上)。
叶适也很重视《周礼》,在《进卷》(见《水心别集》)和《习学记言序目》中都有专门论述。但是,对《周礼》成于周公有怀疑:《周官》独藏于成周,孔子未之言,晚始出秦汉之际,故学者疑信不一。好之甚者以为周公所自为,此固妄耳。(卷七)
叶适以此为妄的根据是:"余所疑者,周都丰镐,而其书专治洛邑"(同上)。都丰镐者为西周,洛邑是周室东迁后的都城。《周礼》一书既"专治洛邑",都是东周之事,"书之所不言,不可得考,而周之所以致盛治(按指西周成康盛世),则犹有不尽具者,此其为深可惜也。"(同上)周公执政于西周之初,说《周礼》为周公所自为,难以成立。但是,叶适认为,《周礼》"虽不必周公所自为,而非如周公者亦不能为也"(同上)。
(五)对儒家经典以外著作的考订
如《老子》一书的作者,司马迁曾记叙孔丘问礼于老聃,叹其为"龙";老聃原为周室守藏史,去职至关,关令尹喜强之著书,乃著言道德书上下篇;这是将孔丘问礼的老聃与《老子》书的作者合而为一人。叶适以庄周言论考之,庄称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也说孔丘赞其为"龙"。叶适认为,这是道家"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不可轻信。他说: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
(卷十五)老聃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余尝疑其非聃所著,或隐者之词也。(卷七)这就是说,孔丘问礼之老聃同《老子》一书的作者决不是一个人;《老子》的作者是"隐者",而不是周室守藏史老聃。这是很有见地的。
又如《国语》的作者,历来都认为与《左传》的作者同为一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之说。叶适"以《国语》、《左氏》二书参较,《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然所采次仅十一而已。"(卷十二)《左传》记事,往往与《国语》有所不同。"《左氏》之取义广,叙事实,兼新旧,通简策,虽名曰《传》,其实史也。"(卷十一)
"《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烦简自应若此"(卷十二);而《国语》记事。往往有"谬妄不足信"之处。因此,《国语》的作者与《左传》的作者,决非一人,"盖《国语》出于辨士浮夸之词"(同上)。这个看法也很有参考价值。
再如《管子》一书,叶适认为"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否定了"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卷四十五)
的说法,甚合该书之原貌,常为后来学者所称引。对该书的内容,叶适认为是"申(不害)、韩(非)之先驱,(商)鞍、(李)斯之初觉"(同上),也是准确的,与当代学者认为是"齐法家"之书相一致。
叶适对古代著述的考订,看去似乎琐碎,其实有其深意。第一,从考订中我们可以看到叶适是把古代的典籍(包括儒家的经书)当作历史文献来对待的,与儒家的传统把它们当作神圣的东西有根本区别。由此可见永嘉学派的求实精神。第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叶适是把古时的圣人当历史人物来看待的。特别是对孔丘,叶适把他看作是圣人,但不认为他是"神人",对于他的功绩主张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把并非他的功绩强加给他,而应放到一定历史联系中来考察。这些,都是很可贵的。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