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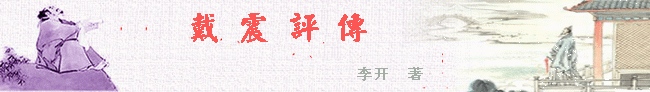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二是治经时要考证
治经时要考证经典名物,弄懂文献中的天文、历法、史地、音韵、律吕等,为通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当然是个书本求知的方法,今天看来,光有这些并不能真正弄懂,还需要科学的分析方法,辩证的综合思考,和当时的时代条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等等,都是通经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没有那些基本知识,那就连门限也没有蹩进,根本谈不上弄懂。仅就通经中的考证名物而言,戴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反映了一代宗师治学的广袤视角和谨严求实精神。他有感于自己的治学过程,深有体会地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诂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未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①,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②。这里戴震已经提到研究文献、通经中的中法和西法的比较及其应用问题。如天算中的勾股,西人用三角,但“三角”之法穷而必以“勾股”御之。在戴震看来,只有懂得中国传统的“勾股”,方能“法之尽备”,无往而不能释疑解难。无疑,戴震的考证名物的方法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研究古典文献,乃至一切历史科学的基本功。考据,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考据,本质上是个知识论方法,是个以书本知识为主要领域而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应该说,考据学是包含着这一“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的特质的。问题是,求实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书本,而应该是实践性的研究。戴震的时代,自然科学已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系统。戴震以当时尚属先进的我国自然科学成就诠释群经,在古代学术史上再辟一治学门经,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从此,经典名物的考证在有清一代蔚成风气,以自然科学诠释若干疑难成为不可缺少的治经内容,大大拓展了治经和治学的新路,也为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找到了国家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① 戴震误,应为九寸,见本书24 页注③。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至184 页。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18 页。
学术:经学的发展框架,从而为乾嘉学人在自然科学方面大显身手打下了基础,这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又是极有利的。当然,这一自然科学为阐释群经服务的指导思想也有其明显的不足,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使自然科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但前期戴震的主张还多半停留在古代文献范围内的“格物致知”,尚缺乏实际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精神(在实际进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因而又不利于把自然科学大踏步推向前进。但和儒家传统中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做法相比,戴震的这一治学主张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加之他本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成就,无疑对清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其三,戴震批判
戴震批判陆九渊、王阳明的“尊德性”,为朱熹的“道问学”张本,除了表明他前期不反程朱的立场外,事实上也是从学术渊源上阐明“以词通道”,力戒空疏,考证名物,博物求知等一整套方法的正确性。考证离不开淹博,淹博是“道问学”的必然,章学诚曾就宋儒朱陆分疆,不可调停,承朱熹之学者必为博学多闻等阐述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垢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伯厚(王应麟)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①章学诚还历数朱熹一传至五传,实际上以和他同时代的戴震为殿后。他说:“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②章学诚所说的“生于今世”者,就是指乾嘉学人,尤指戴震。章学诚是明确地视戴震为朱熹宗传的第六代的。章氏的论述,无疑是戴震早年学宗朱熹的一个有力旁证。同时,章氏还指出这一派的特点是多学而识,寓约于博。至于这一派发展到乾嘉,尤重名物考证和自然科学知识对治经的作用,章学诚也是深有所知的。他说:“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①十分清楚,章学诚把考证名物,解其天象历法,看作“实学求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章氏的这一段话,简直就是针对戴震所说的“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不能卒业”一语而发的。如果象“乃命羲和”这一类问题不能索解,不了解“前人遗蕴”,那只能因① 《文史通义校注·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2 页。② 同上,264 页。
① 见《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三·朱陆》,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64 至265 页。不淹博而造成“识不足”,故戴震曾谓治经“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里,章学诚的看法与戴震早期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四。戴震提出 “十分之见
1755 年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质就是强调“识断”,即治学的“见识”。前面提到的“以词通道”,考证名物,寓约于博,都不过是求得“十分之见”的方法和手段,如不循此途径,“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戴震认为,非“十分之见”的种种议论,只能“徒增一惑”,成为“识者之辩之”的对象。经有识之士数辨,而后乃达“十分之见”,“十分”为“极致”之意。见解可以臻于极致,但朴学的求真认识并不封闭。实际上,戴震求“十分之见”的极致是一个认识过程。梁启超曾把“十分之见”与“非十分之见”当作科学的定理与假说之分①。钱大听曾谓戴震之学的根本之点是“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②,而对于他人的真知灼见,没有不加以虚心吸收的,钱大听曾说戴震“亦不过(按:过分)骋其辩以排击前贤”③。余廷灿论戴学一段,也是对戴震“十分之见”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有一字不准六经,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不为歧旁骄枝所惑,而壹禀古经,以求归至是,符契真源,使见者闻者,洒然回视易听。”④这里说的“至是”亦即戴震的“十分之见”的“极致”。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是他个人早年治学的甘苦阅历的结晶。就在给姚鼐的信中,他表达了个人的治学体会:“昔以为直者,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者,今见其坳”。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完全道出了笔耕不止的一代学人反复实践,殚思竭虑,一步步向真理逼近的过程。
为求学问的“十分之见”,戴震主张以高尚的学德保证之。他说:“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兔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①为学需解蔽,这就是戴震的结论。这蒙蔽来自两处,一是受别人的蒙蔽,一是自我的盲目性,受自己的蒙蔽。种种蒙蔽中,名利可能成为最大的蒙蔽,受名利的蛊惑,或者攻击他人抬高自己,或附骥他人煊赫一时。有了此类“蔽”,决不能闻道。为学受人受己蒙蔽,还是个识力不足的认识能力问题;追逐名利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个品质问题。大凡治学之初,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难成定见,一旦初见成效,又极易产生自我盲目性,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从而“以己自蔽”。认识此“两蔽”不易,认识后在行动中去此“两蔽”更为不易,这无疑需要反复的治学实践和长期的学德修养。戴震前期论学强调“闻道”中去其“两蔽”,可谓一代学入兼哲人的自我反思而得出的至理名言。在认识并实行去人蔽的基础上,前期戴震得出了汉儒、宋儒“得失中判”的结论,告诫人们不要让汉儒、宋儒蒙蔽自己,这一观点到了可能是戴震后期著作的《与某书》中进一步发展。在认识去己蔽的基础上,就在这一封给姚鼐的信中,明确表白了自己不愿好为人师的态度,拒绝了姚鼐的从师要求,把师生关系的含意置于严格意义上的古师友同道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震传》。
③ 同上。
④ 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
① 《答郑丈用牧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6 页。
其五,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
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这是对一代学术畛域的新的建构。《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未,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①戴震这段话,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文章为其中之一,而对文章,不排斥其有道,文章同样是可以载道的。特别象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学问为三,义理居其首,义理之学,研核天下之大道。有了前面所列戴震早期论学的几个要点:以词通道,考证博洽,问学重知和极致之学识、学德,就不难懂得到达“义理”之路。后来,戴的学生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补充说道:“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还说:“后之儒者,划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段玉裁的理解不完全符合戴震的原意,段氏主张义理来自考据,文章也由考据而得。这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而段玉裁又不完全能理解、欣赏戴震哲学思想的情形下所作的一种略有扭曲的看法。如前所述,将戴震关于义理、考据、文章的划分放在他早期论学的系统中考察,方能看出其“闻道”统贯于三者的学理逻辑。关于古今学问三分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如此明确、完整的表达尚属首次,在古代史传中早有所谓儒林、文苑之分,宋代以后更增设了所谓“道学传”。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所云“今人之学者有四”,即分为“儒”、“文”、“学”、“笔”。《程氏遗书》卷十八载程颐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颐完全将学问的三分对立起来,当然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正如戴震所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①相较之下,段玉裁可说是“得其制数”的人,程颐是“失其制数”的人,而戴震则是强调“闻道”。“义理”、“考据”、“文章”的三分及其关联,也是戴震本人强调的“十分之见”的一个样板,这是一个古今学问畛域的宏观范畴,在彼时彼地的时代学术条件下,戴震的三分说较少片面性。
① 《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戴震早期对学问三分及其术语的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义理、考据、词章的说法至今仍在使用。在当时,戴震的提法问世后,简直成了学界的口头语言,影响所及,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与戴震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7)从文章之学本身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理学、考据学、经世济民致用之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学,作为文章的内容。此后,姚鼐继方苞(1668—1749)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和刘大櫆义理、考据(又称“书卷”)、经济为文章之实等说之后,受戴震、段玉裁的影响,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统一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此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②姚鼐还表彰了王昶丰富的阅历见闻对其义理、考证、文章的帮助,表彰他善于运用独得天厚的条件,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而获得的极大成功。王昶恰恰是戴震的知交,他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说:“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姚鼐说:“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①与此同时,姚鼐还批评乾嘉年间的考据是“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批评言义理者是“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他们的共同毛病是:“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之所以如此,是“其故由于自喜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②。这里,姚鼐批评程朱理学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也批评乾嘉的汉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针对戴震的。姚鼐对专宗汉学,崇汉抑宋之风是不满的,认为“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③,已不满到将考据学和时文作者同等视之了。这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姚鼐在学问“三分”问题上与戴震是有共识的。在“三分”的术语提法上完全一致,却不取方苞、刘大櫆的提法。对此,曾国藩曾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④除此而外,姚鼐还承认汉学“非无有善”,其“博闻强识”也是有助于学问的,因而主张吸收,以为文章增色。《与陈硕士》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并且还得出了与戴震庶几一致的结论。他说:“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①也就是说,文以载道,方有可能成为“十分之见”的极致之文。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戴震首创的“义理、考据、文章”之分在文章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反响及其新发展。戴震的学问“三分”说影响是极深远的。② 《(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① 姚鼐《<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② 同上。
③ 姚鼐《复蒋松如书》。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杂著》,载《曾文正公全集》。① 姚鼐《敦拙堂诗集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