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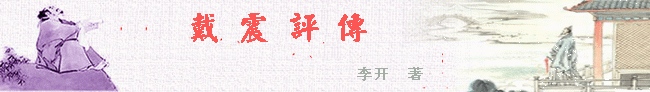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二、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著成的三部书。
清康熙三年(1663 年),戴震的乡先辈方以智刊印了洋洋巨著《通雅》五十二卷。该书体例略仿《尔雅》。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继《考工记图注》(1746 年)之后,大约在1748 至1750 年间,有《尔雅文字考》十卷。今本《戴震集》中有自序一篇。书成后一直未能刻印,今恐已亡扶。据自序云,本书原是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对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昺疏的缺失。至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於《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雅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可见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划的,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是一部奠基之作,对戴震本人来说则为“小学始基之矣”②。于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也同样如此。此后,有清一代有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钱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此外,还有专释《尔雅》名物的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关于“释宫”、“释草”、“释虫”的诸小记,任大椿《释绘》,洪亮吉《释舟》,钱大昕《释人》,阮元《释门》,刘宝楠《释谷、钱》等,还有专释《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尔雅汉注》、黄爽《尔雅古义》等,乃至晚近王国维《尔雅草木乌鲁虫鱼释例》,竟把传为周公之作的《尔雅》发挥得淋漓尽致①。有清一代的《尔雅》学群书,是以戴震开其端的。
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有《诗补传》和《屈原赋注》。《诗补传》一书,约乾隆十五年(1750 年)是仲明游徽州时曾索要此书,因“尚俟改正”而未进。而《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言及该书著作和经学讲习之难时说:“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情、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并说待《诗补传》“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段玉裁编集的《戴震文集》经韵楼本中有《毛诗补传序》一文,落款有“时乾隆癸酉(1753年)仲夏戴震撰”字样。然《戴震集》中又有《诗比义述序》一文,说:“昔王申(1752 年)、癸酉(1753 年)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按:当指《辨郑卫之音》等)成一帙。”可见癸酉《诗补传》尚未成书。段氏《年谱》中说:“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也是据戴序推定的。鉴于此种矛盾情形,钱穆曾说:“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②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戴震又改注《周南》、《召南》,名曰《果溪诗经补注》①。是仲明与戴相晤时索观的那个本子,戴因“戒其颓情”、“特惧忘失,笔之于书”云云,与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 年)至十五年(1750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8 页。
①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何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7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中华书局影印本312 页。
① 共二卷,见载《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年)著成的《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象,序云:“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且可推知其写作过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成书的。
关于以《诗补传》命名的书,今不见于《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本),仅有据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收录的《毛郑诗考证》五卷。段玉裁在《年谱》中曾说:“《文集》中《诗生民解》本出《毛郑诗考证》,先生曾为余言,可取出修改,入于《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时,因入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诗摽有梅解》,亦取诸《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初名《诗补传》。”今安徽丛书本《全集》中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收有《召南·摽有梅》的《诗摽有梅解》全文,足见《年谱》中说的《诗经补注》即指《杲溪诗经补注》,而《全集》中的《毛郑诗考证》即通常称说的《诗补传》。或以为最早是仲明索要的那个《诗补传》未刊待考。
戴震在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始作《诗补传》,应该说是很早的事。在戴震之前,有康熙丁卯年间(1687 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有康熙年间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乾隆年间经学全盛,除戴震外却没有人专治《诗经》,一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胡承拱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矣的《诗毛氏传疏》。戴震的《诗经》研究,可谓开乾嘉学派研究《诗经》之首。梁启超曾评戴撰《诗补传》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询治《诗》良法也。”戴震《毛郑诗考证》五卷贯彻了他早期论学的大旨,以词通道,博洽综贯,在训诂名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试以人们很熟悉的《诗·邶风,静女》中的诗句为例:卷一《静女》首章“俟我于城隅”。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震按:传,笺就城隅取义,非《诗》意也。“城隅”之制,见《考工记》、许叔重《五经异义》、古《周礼》说,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候伯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据记考之公侯伯之城皆当高五雉,城隅与天子宫隅等,门台谓之宫隅,城台谓之城隅,天子诸候台门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称。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入门之所也。“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此膳俟迎之礼。诸侯娶一国,二国往腰之,以姪、娣从,冕而亲迎,惟嫡夫人耳②。媵则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后入。“爱而不见”,迎之未至也。“爱而”犹隐然。《说文》引此作“ ”,郭注《方言》引此作“ ”。“彤管”之法,女史书,宫中之法度。故《春秋传》日,《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归荑”,言乎说舍近郊也。《尔雅》于郊外谓之“牧荑”。亦以为洁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见其人;继思得见其物;始言至城下,终乃言至于郊,非实有是事,可知《静女》之刺,思贤媵,怀女史之法者也。盖卫夫人拟其君之宫中无是女,以备嫔媵。及女史之法废也,学者罕闻“城隅”,而《诗》遂失其传矣。①由以上可见戴震补传的条例是:补正传笺之缺失;考释《诗》及传笺中①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见《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十二册本)。② 春秋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也以侄娣随嫁,随嫁和陪嫁者统称为媵(yìng)。① 见《安徽丛书》六期,《毛郑诗考证》卷一《静女》章。的一些关键词语或名物,考释时一般先引古代文献依据,后判其义(词语、名物义、句意);归纳诗意。这一条例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为后来治《诗经》的学者所遵循。
《静女》这首诗,本来是首爱情诗,清儒的普遍毛病是以儒家功利主义解释诗旨,戴震诠释《静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功利意义外还讲了“比喻”意义,如“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想其人,继思得见其物”,这都表明作者对《诗》旨的一些开明的认识。关于如何研究诗旨,戴震还说了这样的话:“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②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同义名物训释去自由开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也就是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事实上,戴震著《毛郑诗考证》,于诗旨不是不说,而是努力从其实情体会之,时常越出儒家功利说解的藩篱。这不仅在《静女》中能见到诗旨的比喻说法(其实正是其本旨),而且戴震在作一般理论概括时已讲到说诗旨时当参照的文化史情形,从而试求谋图《诗经》中爱情诗的应有的地位。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子之言《诗》也。而《风》有贞淫,说者因以‘无邪’为读《诗》之事,谓《诗》不皆无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诗》也。”①到了后期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更重视以实情解释诗意。从表面上看,好象戴震的解释与旧注洛守儒家封建功利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解释《诗》意时,总是在儒教礼义规范的前提下几乎干篇一律地指出与统治者的联系,把本来很有人民性的诗篇说成了某国君、某侯妃,某卿大夫的自我写状或教谕,戴震解释《诗》意时,经常注意到在儒家礼义规范的前提下指出诗篇中的男女悦慕、民生心声的本旨,和毛郑解《诗》旨、朱熹集传解《诗》旨已有很大区别。本来,先秦产生的儒家礼义规范内容极为丰富,区间极广阔,可容纳性很大,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制的烙印,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特别是到了宋代,才日益禁锢划一,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先秦儒家伦理指导下解释《诗》旨,戴震注重指明其民生民情,与旧注专以儒家功利释之已判若二途,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传日,采采,事采之也(疏云,言勤事采菜)。卷耳,芬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韩诗》云,顷筐,欹筐也。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集传》日,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多貌。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怀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怀之之事也。周犹偏(按:通‘遍’)也,通也。行,路也。行,为行列字之音,训旁及。而《春秋传》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断章见意,如邵至之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为一②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3 页。①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美一刺,于《诗》之本指,不然也。荀卿书日,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不贰。其得诗之意者欤!《补注》列述了毛传、朱熹《诗集传》、《春秋传》等的解释,但只是立此存照,并不同意,唯荀卿之言《诗》旨,言情致忠贞不贰,“其得之欤”。又如戴震对情诗《野有死麇》的概括:《野有死麇》(三章)言礼教之兴,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诗》辞所涉,曰林野,曰麇鹿,曰龙吠,亦以见乡曲之远于都邑也。或日,《诗》言女之不可诱,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何也?女之待嫁,所愿者,吉士也;士之归妻,所愿者,有女如玉也。“诱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动于爱悦(《祭义》曰,如欲色然,张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而卒能无失乎礼义,则风化之所被可知矣。此《诗》教之善行,以情见礼义与?上文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戴震是重视《诗》中的礼仪教化作用的,但他重礼教的同时也重视男女爱情生活,或者说,他在具体诠释《诗》旨时,往往先发现其中的爱情生活,进而指出,这应当是合乎礼仪的爱情。作者的深层思想,难道不是在追求道德规范和情感欲望的一致吗?
《杲溪诗经补注》中有一篇很长的《摽有梅解》,是一篇专门的诗论。
该文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确定了爱情诗在《诗经》乃至在古代文献中存在的地位、必然性及其价值。在戴震看来,爱情、婚姻、夫妇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就不能不涉及这些正常的生活,而人伦规范、札教等不是禁锢民生、民俗、民风,而是导引归正,不致人欲横流,毁坏人性。他说:“古者嫁娶之期,说歧而未定。其以少长论者,或主于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为期尽之法。据《诗》、《礼》证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弃而字??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恐至于废伦也。亦所以顺民之心,而民自远于犯礼之行也。”②又说:“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首章言十犹余七,次章言十而余三,卒章言皆在顷筐,喻待嫁者之先后毕嫁也。《周礼》所言者,实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诗所言,即其见之民事者也。”①戴震对《诗经》的解释,也不乏儒家功利,如前所说,当他试图以儒家道德规范诠释诗意时,他总是注意到道德规范和民生、民情、男女悦慕的一致②。除此以外,戴震还从《诗经》中努力发现另一种功利:劳动者从事农桑之事的艰难、欢乐和从中悟得的道理。例如对《葛覃》的概括:葛覃(三章):不忘女功也。《礼》,后夫人亲蚕不亲葛。盖当时服葛之时,犹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赋之,因以感而思归宁也。《周书·无逸》之训,以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诵以为戒,然则《葛覃》之义,其以视忘女工之勤劳而骄侈是从者,孰宜法,孰直戒,可知也。讲到《诗》旨即作诗时的本意,那就涉及到《毛诗大序》问题。陈启源,朱鹤龄以及戴震之后的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载《杲溪诗经补注》卷一。①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 页。
①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5 页。
② 后来汪中《述学·释媒氏文》、俞正燮《癸巳类稿·媒氏民判解》都曾进一步发挥戴震关于古代制度中婚姻自由的见解。
③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胡承珙、马瑞辰、陈矣等,部因“尊汉”、“好古”而群守大序。但也有举叛旗的,戴震的同乡姚际恒(1647 一约1715)就是一例,他著《诗经通论》,坚决主张废除《毛诗大序》,另著《古今伪书考》(见《知不足斋丛书》),依据古书流传有绪的一般规律,认为有名著作各史经籍志上都有著录,或在别的书上记载它的渊源,如突然发现一书,向来无人提及,其中必有蹊跷,《毛诗大序》就是这样的书。他指出,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未提及,可证为西汉前所无,是为伪作。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以儒家礼教功利说诗的传统,使人为之耳目一新。除姚际恒以外,崔述、方玉润皆持这样的观点,崔著《读风偶识》,方著《诗经原始》,连同姚著三部书历来不为清代正统派所重。戴震对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持何态度呢?只能说,聪明的戴震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只是以自己的较为通达的开明之见诠释诗意。在《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中,以及经韵楼本《戴震文集》收录的论《诗》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毛诗大序》。人云:不表明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推揣其本意,戴震的态度是想避开那圈定的儒家传统的诗旨说教,寻求《诗》的本意,以得“十分之见”。联系他在《毛诗补传序》中所说及的于诗旨可存而不论,让读者据训诂名物的诠释,依原诗而推证之,他对《毛诗大序》的态度,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诗经·魏风》的《伐檀》和《硕鼠》是人民性很强的两首诗,它凝聚着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下的早期民主的精华。前者对不劳而获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阶级,给以严厉的质问与尖锐的讽刺,后者写农奴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两首诗,戴震当年作何理解呢?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岸)兮”震按:檀者??伐檀乃宣之河之干,盖诗人因所闻所见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支之不用也。因叹河水之清,而讥在位者无功俸禄,居于污浊,盈凛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及于民,是谓素餐也。①《硕鼠》二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传:直,得其直道。笺云,直,犹正也。震按:笺与传相足,其说是也。《论语》曰,人之生(性)也直。得我直,谓得遂其性。不违生人之正道。后来,王引之曾将诗中的“直”解释为“所”。“爱得我直”,等于上文的“爱得我所”③。戴震把“直”字解释为人性之“直”。去“乐国”的目的是能顺遂其人性,得到自由。戴震的诠释是颇为别致的,言下之意是说,硕鼠不劳而获,“莫我肯德”,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而“逝将去汝”,前往那“乐国”,也是为了寻找和恢复那失去的人的本性。戴震是在近乎以早期启蒙思想诠释《诗》旨。至于剥削者毁灭人的正直的本性,见解尤为深刻。
① 见《毛郑诗考证》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同上。
③ 见《经义述闻》卷五。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