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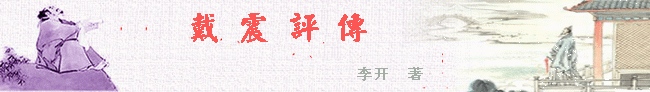
|
三、生计维艰注屈赋
如果说戴震早年著《诗补传》时还为经书所限,著《屈原赋注》时就更大胆地阐发了一些自由思想。据《年谱》载:乾隆十七年(1752 年)“注《屈原赋》成”,是年三十岁。《年谱》还说:“歙汪君梧凤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1752 年)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可证也。”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有《屈原赋注》十二卷,注明“歙县汪氏原刻”,那是因为有“汪氏原刻”本九卷另加《音义》三卷。安徽丛书本还收入了《屈原赋注初稿》三卷,为歙县许承荛氏藏稿本。关于《屈赋音义》,《年谱》说:“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所自为,假名汪君。”今考署名汪梧凤的《屈原赋注》题跋云:右据戴君注本为《音义》三卷,自乾隆王申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常置案头,少有所疑,检古文旧籍,详加研核,兼考各本异同,其有阙然不注者,大致文辞旁涉,无关考证。然幼学之士,期在成诵,未喻理要,虽鄙浅肤末,无妨俾按文通晓,乃后语以阙疑之指,用是稍为埤益。又昔人叶音之谬,陈季立作《屈宋古音义》为之是正,惜陈氏于《切韵》之学殊疏,未可承用,兹一一考订,积时录之,记在上端,越九载矣,爱就上端钞出,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体例略拟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庚辰(1760 年)仲春歙汪梧凤。这段文字,从叙述《音义》的写作过程“兹一一考订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云云,似乎出自戴震本人之手。《年谱》讲《音义》“假名汪君”,莫非这段题跋文字也是戴震代作的嘛?但不管是戴震手笔还是汪梧凤亲笔,其中叙述的情况该是真实的。其要点有:《音义》诠释的一些词语是经“详加研核”的,有考证价值,不注释者则“无关考证”;《音义》的著述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注音力求舍弃朱熹等人的不科学的叶音说①,取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并正其舛疏;写作的过程及体例。所叙述的写作过程,与《尔雅文字考》“偶有所记”、“录之成帐”,与《诗补传》“特惧忘之,笔之于书”的写作过程极其相似。在写作时间上,因《音义》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故可能《屈原赋注》九卷在前,《音义》在后。
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家境非常贫困,“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飨,闭户成《屈原赋注》。”“饔飧”原义为早晚两餐,此处或泛指食物。因乏食只得进以乞讨而来的面屑,竟然还在发愤著书。其时戴震己成家,可以想见戴震妻朱氏是怎样茹苦含辛地为成全丈夫的事业而苦挣扎,苦张罗。段玉裁曾评述此时的戴震云:“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一个“亨”字,昂扬挺拔,贫贱不移,活现出戴震早年之志,这正是一种“中华民族脊梁”的硬骨头精神。
和《诗补传》相比,《屈原赋注》更注意概括原文本旨,戴震将《离骚》分成十段,对各段大意都作了明确概括。例:① 南北朝人读上古韵文感到不押韵,临时改读以求押韵,叫叶(xié)韵,也叫叶音,叶句。这是不明古音之理造成的。宋代吴棫、朱熹也主张叶音说,但已有所不同,立足于改今音叶占韵。清儒以钱大听为代表,力反叶音说(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跋韵补》),但未区分吴棫、朱熹叶音说与南北朝叶音说的不同。其时戴震对叶音说的看法也是笼统的。不过,吴棫、朱熹的叶音说与陈第的科学的古音学说仍是很不相同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反信谗而府怒”:第一段自叙生平大略,而终于君之信谗。“余因知謇謇之为患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第二段申言被谗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和调度以自娱兮”至“蜷局顾而不行”:第十段托言远逝,所至忧思不解,志在眷顾楚国。终焉。
戴震不仅概括大段的意义,而且对大段中的小段意义也作出概括,这等于是在层层揭示《离骚》的丰富内涵。例如第二段中的一小段:“予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承上见怒于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独惜其变操不常,无任贤图治之略“戴震如此苦心孤诣地寻找《楚辞》中的义理精核,完全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考证的同时必须力求“闻道”的“十分之见”。从经书到《楚辞》,反映了作者这一早期学术思想的应用进一步普遍化了。戴震曾说:“余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③戴震早期就已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于考据中䌷绎理性认识,这是他的特色,“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云云,已隐含着对朱熹《楚辞集注》的若干责难。至于对书中训诂名物、事典的注释,目的仍是使读者循此而稽核要旨,防范学界的赝品,他说:“今取屈子书注之,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然后赡涉之士,讽诵乎章句,可明其学,睹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①至于书名,亦从《汉书·艺文志》。戴震说:“书既稿就,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由此也可知戴震早年伏处山野时,从汉之志早定,这无疑是晚明以来知识论传统的继续,亦知戴震前后期虽有不同,但尊崇汉儒,折向往古,却是前后一贯的。从《屈原赋注初稿》三卷看,戴震著述此书时是很有批判锋芒的。试看他的一些批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戴震批住:“君之疏己,皆由党人,故光入党人,逐篇反复言此,不敢慈君也。”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戴震批注:“说到君便住,若因党人带出,又祗云信谗,立言婉曲之至。”③“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戴震批注:“君之所以信谗。”“君之所以信谗之故。浩荡,广博不专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怨言不察,《惜诵》所谓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逸)注谓不察万民善恶,《文选》注谓不察众人悲苦,皆非是。”旧注未敢言怨恨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屈原赋目录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2 页。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国君的,由戴震言之,引《惜诵》说“国君不可依靠”,这里显然继承晚明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黄宗羲《原君》曾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强烈谴责“君”,与黄宗羲痛斥“君”何等相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直是禁书,戴震写国君“不可恃”这类话,在雍乾年间是多么危险。注释《楚辞》在雍乾年间是件凶多吉少的事,一是屈原亡国破家的哀痛,二是楚怀王、顷襄王的昏庸,都极易惹出是非来。戴震早年著《屈原赋注》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是否有深沉的民族感情在内,现在已无法知道,不可妄断。顾炎武曾以为读屈赋有确立人格的作用,人格不立,一切学问皆成废话,并认为忌圆滑;行方严是最要紧的。他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②戴震在三十岁而立之年著《屈原赋注》,对确立他的心系百姓的独立人格是有重要作用的。此外,著《屈原赋注》既要贯彻他早年治学寻求“十分之见”的主张,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君之类的禁区。当时,文人士子一般言及《楚辞》都很危险,更不必说专书著述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写了一首《赠芹圃》的诗,末句本为“一醉读楚些”,因为怕人穿凿为借《楚辞》怨伤时君,附会成“不满当今圣上”,而改成了“一醉白眼斜”,这样诗味全无。
戴震早年之作《屈原赋注》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姜亮夫曾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①关于《九歌》就是突出的一例。有关《九歌》的性质,王逸和朱熹都曾认为是楚地的祭歌。②而关于《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神,则从未有过深究。戴震《九歌补注》则云:“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为神名,殆起于周末,汉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唐宋祀之尤重。盖自战国时奉为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祀神所歌也。《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吕向曰,祠在楚东,故云东皇,未闻其审。”③这就告诉我们:太一神是后起的;因汉帝之故进入了长安;太一神是全国性的神,非楚神;《九歌》为屈原所作;《九歌》为屈原就当时祀典(当然就不限于楚了)赋之,非祀神所歌;“东皇”之“东”亦非指楚之东;“太一”本为天上一恒星(极星)最明者。其中“非祀神所歌”,尤非楚地“祀神所歌”,正可看作纠正王逸、朱熹之说。其余见解,亦殊可贵。周勋初先生曾说:“东皇太一一神,是燕齐方士利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他起先产生于齐国,战国中后期,大约只是流传在民间。汉武帝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始由谬忌(按:方士名)传入长安,并成为君临全国的至上神。”“《九歌》中的许多神抵,有非楚人能把者,因此,《九歌》不是楚国的民间祭歌,不是楚国的郊祀歌,也不可能是汉人的作品,不论从它的形式来看,从它的内容来看,或是从古代有关的记载来看,均应断为屈原的作品。”①周先生是从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入手研究《九② 《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① 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 年版247 页。
② 参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朱熹《楚辞集注》卷二。
③ 戴震《九歌补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
① 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156 页至157 页。
歌》得出上述结论的,可视为有关《九歌》性质及作者问题的定论。以戴震十八世纪中叶的论述与现代科学研究的结论相比较,庶几可近,我们不能不叹服戴震的识力。后来,卢文明为《屈原赋注》作序时,对戴震此说曾表而出之:“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②此外,《屈原赋注》对若干词句的解释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例如对《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中的“三后”一词,王逸注释为禹、汤、文王,朱熹释为“疑为三皇,或少吴、颛顼、高辛”。戴震注则更近情理,他说:三后为楚之先君而贤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又如《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中“败绩”一语,王逸注:“绩,功也”,“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戴震注云:车覆日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传》“败绩厌覆是惧”,是其证。④又如《离骚》“启《九辩》与 《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历来都把“夏康”连读,解释成夏启之子太康。戴震发掘其内证所云,其说可信。言启作《九辩》、《九歌》,示法后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娱自纵,以致丧乱。“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又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诸家之说甚详,戴震注云:战国时言神仙者,托之昆仑,故多不经之说,篇内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又如《九歌·湘君》“薛荔柏兮蕙绸”,此“柏”字王逸注和朱熹集注都释为“搏壁”,此为何物,后人难明,戴震引汉刘熙《释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针对后世对屈原赋的一些误解,诸如认为其辞“放恣怪谲”、“炫文辞而昧其旨、“未尽善”等,戴震说:“屈子辞无有不醇者。”为此,卢文绍曾认为戴震关于屈原赋的识力可与班固、颜之推、刘彦和相媲美,甚至超过了他们③。
在《天问注》中,戴震既贯彻他早年论学以自然科学诠释群经的主张,又充分考虑到《天问》中引用神话传说故事的特点,反对字字穿凿,句句求证。他说:“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骛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诸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序愤懑是也。篇内解其近正,阙其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①戴震说:“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②在注释《天问》中,有的注释使人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写“天对”。例如《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戴震注云:夜光,月也。德(按:性质),常德也。如刚德不变其刚,柔德不变其柔之谓。疑月何德,而死乃复育,如是终古乎?死,即所谓死霸(按:魄,月魄)也。育,生也,所谓生霸也。月之行,下于日,其浑圆之体,常以半圆向日而有光。人自地视之,惟于望(按:夏历月十五日)得见其向日之半,故光盛满。晦朔则光全在上而下暗,余皆侧见而阙。谓之死,谓之生者,据人目所见云然。戴震的这一注释简明易懂。关于生魄、死魄问题,直到晚近王国维著《生霸死霸考》才更为详密④,在王国维之前,戴震这一以黄道视运动为基点的解释,是最通达和准确的,也是最切合《天问》原意的。今人游国恩称赞说:“详其文义,‘死’、‘育’俱当指月魄言,戴说是也??今者天文历算之学既明,而月之无光,及其盈亏之故,尤无疑义。”①又如《天问》:“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屈原的这一问是问地球的形状,戴震注则兴致勃勃地作起“天对”来,在天体视运动中考察起地球上的昼夜、节气等变化大势,注云:《太傅礼》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步算家测北极高下,及月食之暗虚,得地体周九万里。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高一度。南至赤道下,南北极与地适平,昼夜漏齐,无永短。北至极下,赤道与地适平,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凡气朔之时刻,渐东则气朔早,渐西则气朔迟。月遇暗,虚而亏食,东见食早,西见食迟。此地与天相应之大较也。地之广轮,随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测之矣。圆长日椭。衍犹延也,羡也。最后三句,是正面回答屈原提问中的大地测量问题的。由于地球是个椭圆,南北直径“随其方所”而“假天度以测之”。戴震的回答完全正确。
又如《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对地球上寒暑变化的原因问题,旧注几乎没有能正确回答的。戴震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来注释《天问》,可谓答问相契,天衣无缝。戴震回答说: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闸,《虞夏书》以璇玑玉衡写天,遗制犹见于《周髀》(非汉之浑天仪)。赤道者,中衡也。日自北发南,冬至当外衡;自南敛北,夏至当内衡;春秋分当中衡。中土在内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与中土互异。中衡之下,两暑而无寒;暑渐退如春秋分,乃复。南北极下,凝阴常寒矣。《周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举其概云尔。地为大气所举,日之正照,气直下行,故暑。非正照之方,气不易到,则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所说的“赤道”是指天球赤道。因地球公转而形成的天体视运动中,太阳在天球赤道两侧作视角投影为40 余度的余弦曲线运动,是为黄道视路径,在太阳的视运动过程中,即在黄道上的移动形成节气变化,可用来描述寒暑变化。由于地球上各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④ 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中华书书1959 年版第1 册19 页。
① 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 年版59 页。
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地所处位置的不同,相对于天球位置的投影也不同,故同是某一节气,南北气温各不相同。所谓“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引用《周髀》来注释《天问》,说明地球上寒暑的不同,已将《天问》中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化作天体运动问题来阐释其根源,是极有创造性的做法。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成书的《屈原赋注》中引用的古代天文知识看,这时戴震对古代天文的研究已趋成就了。后来著《七经小记》中的《原象》篇提到:“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间。赤道者,中衡也”,“自南敛北,入次四衡为春,入次二衡为夏,当其衡启也。自北发南,出次二衡为秋,出次四衡为冬,当其衡闭也”,“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阳下行,故暑;日远侧照则气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等等,与《屈原赋注》对照,两者的提法完全一致,可见戴震对古天文历算的钻研和运用,早在伏处山野著《天问注》时就已成熟了。
就在著《屈原赋注》的前一年(1751 年),戴震曾手抄浙江鄞(Yín)县(今宁波市)鄮(mào)山周容著《春酒堂诗集》。鄮山商业很发达。《方舆胜览》引《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这与屯溪、休宁有某种相似之处。周容其人呢?是清代的名士,字茂三,明代诸生,明亡后曾出家为僧,后以母亲在堂而返俗,曾纵游天下,结交皆明代遗民,绘松林枯石以鸣志,萧然远俗,有人以博学鸿儒荐之,竟以死拒之。著有《春酒堂文存》四卷,《春酒堂诗存》六卷、《春酒堂外纪》一卷。就是这样一位入清不仕,超轶不群,铁骨铮铮,以诗文自娱的明末诸生和清初名士,引起了青年戴震(戴震也就在乾隆十六年即1751 年这一年补休宁县学生的)的倾心仰慕,戴震手抄《春酒堂诗集》卷首至卷终(可能就是今存的《诗存》六卷本)共两大册,更从其字字工整,笔笔稳落的工楷字书看,手抄全诗只能看作心心相印之举。手抄的第一首七言律诗《虎过》云:鹊噪鸟啼干叶鸣,隔溪斜映竹篱横,雨过沙路踪应阔,日坠松冈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独居名,山翁笑说相逢惯,不惯输租到市城。
“虎过”疑地名。诗中一派山村野景,诗主人淡泊致远,乐天知命。倘移花接木,说全诗写休宁的山野村民,亦无不可。似乎可以这样说,直至戴震四十四岁(1766 年)著《果溪诗经补注》时,心灵深入仍萦怀此“春酒堂”首诗的意境而不能挥去,“杲(gǎo 明亮)溪”二字,就字面义为“明澈见底之山溪,”用作补注《诗经》之名,段玉裁释为“盖以自别于诸言诗者”①,今谓“明澈之溪”的意境乃至用字,正可见于《虎过》诗的首联和颔联。段玉裁说:“先生不随俗为别号,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②魏建功则认为“杲溪”为戴震注《诗》时的自称③,青年手抄,中年自号,戴震心迹灵痕,竟以周容这样的遗民和名士为知已。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变的,岂可以逸情直逐视之?戴震与“春酒堂”之神交,可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内心世界的认识。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7 页。
② 同上。
③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见《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3O 页。
|
|
|
|
|
|
|